
张光直从小就是学霸。在北京,不管小学还是中学,他从来都是第一。在台湾大学,著名考古学家李济曾对人说,数年间最高兴的事,就是张光直成了他的学生。在哈佛,著名的莫维斯教授一开始并不看好张光直,这个亚洲学生一言不发,也不记半字笔记,但到了考试的时候,这位毫不起眼的学生,却交了一份理论丰富、论证详实的答卷。教授这才知道,自己遇到了一个天才青年。
张光直就是传说中“不仅比你聪明,还比你努力”的人。李济、余英时等人的回忆,都说到他的勤奋和用功,哈佛还曾流传着一个传说:度完为期一周的新婚蜜月,回到哈佛时,他的手里拿着刚写完的长篇论文。
聪明,用功,学问了不起,对于张光直来说,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他能成为世界顶尖学者,更因为他不是把研究中国考古当成饭碗,而是作为一项事业,一项值得投入思想、灵魂直至整个身心的事业。
张光直最大的学术愿望,是使中国考古学的区域性知识,具有全球性的意义,置身于世界文化舞台当中。他坚信任何解释模式和理论框架,如果经不住中国的感性材料的检验,都不可能具有真正的普遍意义。同时他也认为,中国考古学家只有具有全球视野,才能从比较文明的角度理解中国的特殊性。
1996年,亚洲研究会授予他杰出成就奖,颁奖词说:“张光直不知疲倦地致力于促进和发展中国和东南亚考古学。在这一过程中,他所表现出的超群的领导力和献身精神,是少有学者能匹敌的。”

年年考第一的学霸
一口标准的京腔,词汇和语音里纯正的北京味道,让所有与张光直接触的大陆学者、学子感到亲切。
张光直1931年出生在北京。在质朴感人的自传《番薯人的故事》里,张光直回忆他在老北京度过的童年,每天上下学走上高高的城墙,古都的景色一览无余;烧饼、麻花、炸油饼,酸酸的豆汁,蒜香钻鼻的煎灌肠,满满都是怀念。
在家里,张光直还能说一口地道的台湾话,他的父亲叫张我军,是台湾台北县人。张光直先后就读于北平师范大学附小、附中,他上初中、高中都是免试的,因为他从来没有得过第二名,都是考第一。
抗战胜利后,张光直追随父亲回到故乡。但作为一个成长于北京的台湾人,这个特殊的身世对张光直影响很大,他对海峡两岸的关系特别关注,努力“架设桥梁”,使两岸学者间的交流得以顺利进行,并取得了一系列显著的成就。
受教殷墟考古学家
回台湾两年多后,张光直曾遭受牢狱之灾:由于受中学老师影响,他写了一些左翼观点的文学作品,1949年4月,他遭到秘密逮捕,经家人多方营救,一年后才得以出狱。
一年的牢狱之灾使他变得成熟起来,他不再热衷浪漫的文学,却对“人之所以为人”产生了浓郁的兴趣,决定报考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
在家复习几个月,张光直轻松考取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这个系的老师十分牛,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李济,以及他在安阳殷墟发掘的同事董作宾、石璋如、高去寻云集于此,此外还有历史民族学家凌纯声、民族学家芮逸夫等,他们分别给予了张光直不同的影响。
台大毕业后,因李济的推荐,张光直得到哈佛奖学金,前往哈佛读研。这个中国学霸在美国继续开挂,十多年时间,成长为世界顶尖的考古学者。
中国学霸美国开挂
初到哈佛,张光直对旧石器考古非常感兴趣,曾想专攻这个技术复杂的领域,但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定放弃,认为自己最大的优势和首要的职责,都在于中国考古学研究。
这位来自中国的学生以令人吃惊的速度进步。在台大上本科期间,他就发表了十来篇论文,在哈佛就读期间又发表了20多篇。人们很难想象,在课业繁忙的情况下,他究竟如何能发表这么多的作品?!
博士毕业时,张光直已经是非常成熟的学者了。他进入耶鲁大学任教,惜时如金,刻苦工作,十年大约发表60余篇学术作品,从助理教授做起,差不多三年一个台阶,到1969年升为正教授,然后成为人类学系主任。这样的成长速度,在美国大学非常罕见。
张光直博士毕业那年,应邀参加世界最高水准的考古学会议,那年他才29岁,是与会考古学家中最年轻的。此后二三十年里,能够在世界最高水准的学术平台上谈论中国考古的学者,只有张光直一人。

培养后学不遗余力
看到慕容捷这个名字,以为一定是中国人,见到人,才发现是位金发老外。正发愁英语不行没法采访,他开口说话,一口纯正的京腔。
慕容捷是张光直的学生。1975年,他在耶鲁大学选修张光直的《古代中国考古学》,被张光直的热情感染,也被广袤无边的中国古代所吸引,从此追随左右,数十年以研究中国考古学为业。
慕容捷说,张光直在哈佛开始了一系列的课程,但他特别喜欢给大一新生上课,因为这些学生不仅刚接触考古,更是初次面对亚洲,他陶醉于把考古学的醉人之处传授给学生们。
张光直对研究生要求十分严格,但对大一新生们却过于宽容,为了鼓励学生选修,他不惜给较高的分数。
不仅对自己的学生,对所有喜欢中国考古学、前来求教的人,张光直都不惜时间和精力,给予真诚的支持。
亚利桑那大学约翰·奥尔森教授到哈佛大学东亚考古论坛演讲,演讲结束后到张光直办公室拜访。奥尔森谈起当年学习中国考古学时遇到很多困难,给张先生写了很多信,张先生是有信必回。张光直听到这里,起身从文件柜中抽出一沓厚达三寸的信札,对奥尔森说:“我们的通信都在这里。”可见,张光直一辈子在扶持后学方面花了多少心血。
张光直在台湾演讲时,曾有听众问道:“您最感遗憾的事情是什么?”张说:“像考古人类学这么重要,这么引人入胜的学科,为什么青年学生报考的人数如此少呢?这是我最感遗憾的。”

数十年教师生涯中,张光直以这样积极的姿态吸引学生,他最终真的桃李满天下。在美国、中国台湾搞中国考古研究的,一半以上是他的学生,而中国大陆、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等国,都有他的学生,有的已是著名的考古学家。
寻商探宋
2017年9月24日11时许,商丘睢阳区郑庄村外,秋日的阳光明亮而温暖,几位中国考古学家与美国考古学家握手言欢,快乐而亲密。
他们是久别重逢的老友。20多年前,他们曾并肩在此发掘数年之久。时光匆匆,老友重聚,前来故地参加“豫东考古与夏商考古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学术探讨之余,别有一种暖暖的怀旧氛围。
郑庄一带是宋国故城遗址,从西周到东周,七八百年时光里,这里都是中原大地上的重要城池。但由于黄河长期泛滥淤积,这座大城被深埋于地下,渐渐销声匿迹,不为人知。
20多年前,这些中美考古学家发现了沉睡千年的宋国故城,他们原本在商丘大地追寻“大邑商”——早期商文明的踪迹。因黄河淤积,豫东考古困难重重,他们没能发现预期目标,却发现了商人后裔宋国人建造的这座大城。
20多年前,他们在商丘的发掘曾令全国考古界瞩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中外合作考古项目,采用的多学科联合考古,给国内考古界带来新思维新路径。
这次联合考古是张光直全力推动的。在中国大陆做考古发掘,尤其是在商丘发掘,解决商人起源问题,是他平生梦想,他为此努力了很多年。

1 何处寻觅“大邑商”?
张光直与考古学家邹衡是极好的朋友。
邹衡在纪念文章中说,他是郭宝钧的门生,张光直是李济的关门弟子,而郭、李二位是安阳殷墟发掘的老同事,因此他和张光直“自然感情亲密”。
两人相识,是张光直给邹衡发邀请,欢迎他去哈佛。邹衡去美国时,张光直亲自飞到纽约机场接他,帮他扛行李,大概扛得又累又渴,半路打开自来水喝了几口凉水。
到达哈佛后,张光直安排研究生每天帮他买菜,隔段时间请他外出撮一顿,过年更是陪他去唐人街游玩。每当邹衡离开波士顿去外地讲学,张光直都是自己开车接送。这样一来,怎么可能不成为好朋友?
张光直来中国,也每每拜访邹衡,有次在邹家逗留了一整天,两人讨论了很多学术问题,也有一些分歧,张光直相信商汤的亳都在商丘,邹衡则认为在今郑州。争执起来,张光直要打赌,邹衡开玩笑:“我没有美元。如果我有,恐怕你有多少输多少。”
上世纪70年代后,中美关系逐渐正常化,热心推动中西方考古学界交流的张光直,与许多国内考古学家成了朋友。他尝试提出合作考古的建议,起初连连碰壁,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事情渐渐有了可能,但关于发掘地域的选择,却与几位好友发生了争论,事情因此被耽搁。
当时反对意见主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是商丘长期被认为“无古可考”,或者说“有古难觅”,黄河长期泛滥淤积,古代遗址多被深埋于十几米以下,发掘十分困难;二是前些年考古发掘表明,在商人建国前后,商丘一带分布的文化遗存主要是岳石文化,考古界一般认为岳石文化是古代东夷的遗存,因而难以解决商人起源问题。

但张光直也有他的道理。他设想的早商都城应该有城墙,城内应有夯土高台建筑,以及统治阶级使用的青铜器、玉器。他认为邹衡的商文化起源于豫北说,是基于陶器的研究,它们可能是商文化的部分源头,甚至只代表平民阶层,而贵族统治阶层是不一定会在陶器上反映出来。所以他觉得必须去别的地方找。商丘是商人发祥地的说法,在古代文献中向来有记载,李济当年在安阳殷墟发掘时,曾在山东城子崖发掘,认为殷商一部分来源于山东,相当一部分从东方来。
时至今日,这个问题仍难成定论。在此次“豫东考古”会议上,刘绪、袁广阔、张立东等教授从不同角度进行探讨,认为商人发祥于商丘说,仍有证据支撑,历史真相到底如何,只能期待考古发掘的新发现。
2 豫东考古有成果有遗憾
1990年,张光直代表哈佛大学皮博迪博物馆与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签订原则协议,随后他就前往豫东,在商丘、柘城、永城、夏邑等地考察。
1994年1月,双方正式签订合作协议。张光直对豫东考古倾注了巨大的热情,人员组织、计划实施、经费筹措等方面都花费了很大精力。美方先后参加考古地工作的地质勘探、磁力测试、雷达探测等方面的有拉普、荆志淳、墨菲、慕容捷、瑞地、席思,田野发掘有冷健、高德、李永迪、曹音、史密斯等。
1994年,中美考古队发掘了商丘潘庙遗址、虞城马庄遗址,1995年发掘柘城山台寺遗址,1996年地质勘查发现宋城遗址。宋城的发现是一大成果,仅此一项,此次合作考古即可说获得了成功。
可惜的是,这时候张光直已经重病缠身。他牵挂着商丘,却来一趟都难,曾经飞到北京,却还是难以到商丘发掘现场。即便如此,张光直还是两次来到发掘现场。第一次是1994年秋,这次他健康状况比较好,虽然步履缓慢,但精神甚佳,兴致也高。

第二次是1997年10月14日,这次身体状况已大不如前,完全要由轮椅代步,但他仍执意前往工地,执意下了轮椅,手执小铲,神情专注地在探沟内掘土。那情景,使所有在场的人眼睛湿润……
豫东考古,有人说是张光直晚年的遗憾,有人说发现宋城已是成功,但他的博士后冷健告诉记者,来自商丘的发掘报告,是最能让张光直温暖和喜悦的信息。“先生只要处于清醒的状态下,他想到的永远都是工作,念叨的总是商丘的考古发掘。”
3 适当时机再寻“大邑商”
豫东古遗址多被深埋在十多米以下,发掘十分艰难。“地下水哗哗地冒,只能边抽水边发掘。”冷健说,“在宋城之下,还有两层夯土,但太深没法发掘,只能用探铲打下去,发现很小的陶片,但不足以辨认。”
说起当年,慕容捷也是心有不甘。这位波士顿大学教授说,由于资金和技术条件的限制,当年没有能够继续发掘,“现在如果能够找到合适地点,并发掘至10米至12米深,我认为有可能找到早商文化的直接线索。现在资金和技术已不再是问题,缺的只是合适的时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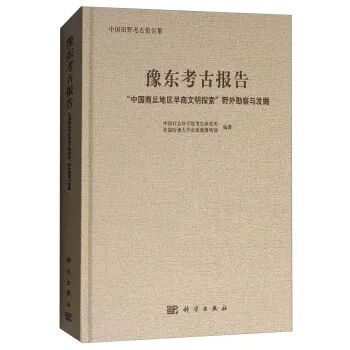

文章来源:商丘地方文献馆
总策划:刘少杰
统筹:江涛
原标题:《张光直:一位让商丘永远怀念的考古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