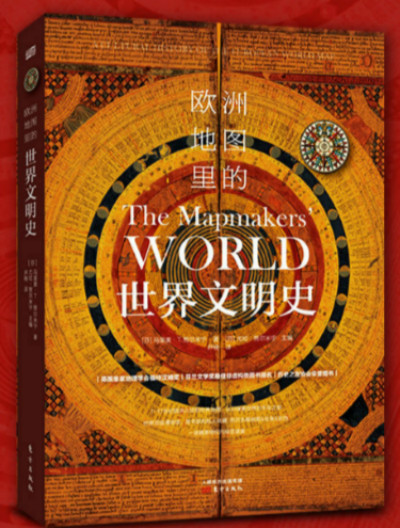一
18世纪的法国,尤其是首都巴黎,成为了当时地图制作、销售和收藏方面最重要的中心之一。一些德高望重的制图师都在巴黎工作,包括尼古拉斯·桑松、阿莱克西斯—胡伯特·亚伊洛特、让—巴普蒂斯特·诺林与儿子让—巴普蒂斯特·诺林二世、尼古拉斯·巴约勒、纪尧姆·德利勒及其继承人菲利普·布歇,还有卡西尼一家四代人。
乔凡尼·多美尼科·卡西尼(即卡西尼一世,1625-1712)在17世纪70年代长居法国,并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法国风格的让—多米尼克·卡西尼。他曾受聘负责管理巴黎天文台,该天文台由法国皇家科学院赞助。在卡西尼一世之后,卡西尼家族的后三代人都在这所天文台服务,他们作为18世纪制图与宇宙学领域的重要角色,对法国的崛起起到了重要作用。

对于18世纪的天文学家、制图师和水手而言,学习如何在地图上及海上确定经线,是一件颇具挑战的事。直到16世纪,针对解决此问题的提议通常都集中在发展月距测量技术方面。然而,这一方法在数学上非常复杂,所需的测量不切实际。17世纪早期,望远镜的发明开启了测量世界时间并以此确定经度的新方法。这一新方法不用测量我们的月球,而是需要测量木星的卫星的运动。
1668年,卡西尼发表了木星卫星月食的精确时间表,该表可作为天文学者与制图师的“通用时钟”。世界各地的观察者可以同时用他们自己的望远镜观察木星卫星的运动,他也就可以用卡西尼的表来计算他们所在地相对于本初子午线的经度。
1670年,卡西尼开始为新成立的法国皇家科学院绘制一幅世界地图,他也将自己的天文表用在制图上。首先,卡西尼的地图并未采用先做木雕或铜雕然后再印刷的方法,而是在天文台西侧塔楼的圆形地板上绘制。这个圆形极地投影直径约7.3米,由于其尺寸巨大,在上面标注精确的位置坐标就要比在小地图上容易得多。
卡西尼为其地板地图收集坐标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为准确定位这些地点,卡西尼对全世界四十个地点利用了天文测量法,其中包括魁北克、圣地亚哥、非洲最南端、果阿和北京。这项任务由法国皇家科学院组织完成,法国国王提供了资金支持。
1696年,在巴黎印刷出版了一份卡西尼地板地图的副本,这幅地图大小为对开尺寸。这幅在科学史上非常重要的地图的作者是卡西尼的儿子、年轻的天文学家雅克·卡西尼(即卡西尼二世,1677-1756)。这幅极地投影地图以其极简主义风格著称,缺少所有巴洛克风格地图的标准装饰元素,它是第一幅试图精准呈现经线的世界地图。换句话说,地点的经度位置不再是通过估算,而是基于准确的天文测量得出。
法国皇家科学院成立于1666年,由太阳王路易十四与其首席大臣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1619-1683)创建,后者主要负责17世纪与18世纪多个最重要的欧洲制图项目的设计与生产。这些项目就包括对法国国土进行精确测量,通过使用三角测量法和实地考察来确定陆地的准确大小与形状。
使用三角测量法对整个法国帝国进行测量是一项庞大的事业,持续了数十年之久,同时要求众多来自全国的测量员参与。1733年,塞萨尔·弗朗索瓦·卡西尼·德·杜里(即卡西尼三世,1714-1784)开始组织编辑一幅地图,该图以测量员收集的信息为基础。1744年,他出版了自己制作的地图《新法国地图》(原名为法文Nouvelle carte ...de la France),图中不仅包含整个帝国边界的细节,还有法国所有重要城市与村庄的位置,这幅著名并且相当巨大的地图现在被简单地称为《卡西尼地图》(法文原文Carte de Cassini)。
让—多米尼克·卡西尼(即卡西尼四世,1748-1845)继承了其父的工作,1793年,他完成了一部巨幅法国详细地形图集,各种场景的形状——谷地、山丘、高山——都有描绘。作为18世纪制图领域最伟大的成就,该图集多达182页,若将其连接成一整幅地图,可达12米高,11米宽。之后三角测量法也用于测量其他国家甚至整个大洲的疆域。
根据艾萨克·牛顿(1642-1727)所提出的万有引力理论的推测,地球的两极地区呈扁平状,法国皇家科学院第二个大任务的目的就是要确定这一推论。在18世纪初,法国科学界普遍支持勒内·笛卡尔(1596-1650)自相矛盾的观点。虽然地球形状的问题纯粹是科学方面的,只能通过在极点附近测量来解决,但这里也涉及更大的问题。在许多法国学者的思想中,法国整个的科学遗产都岌岌可危,因为它太依赖于笛卡尔的思想及其自然哲学。
在法国皇家科学院,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被认为是来自英国的威胁,没有无懈可击的证据,很少有人会接受。于是远征北极圈和赤道搜集证据的探险队出发了。一位天才的年轻数学家皮埃尔·路易·莫佩尔蒂(1698-1759)负责这次探险,他们最北到达芬兰拉普兰的托尔讷河谷,在那里他对经线弧度进行了测量,终于证实了牛顿理论的正确。地球确实在两极地区稍微扁平化,而法国科学家们不得不逐渐转为支持牛顿的自然哲学。

二
纪尧姆·德利勒(1675-1726)与卡西尼家族成员一起成为18世纪初法国科学制图领域的重要人物之一。德利勒在让—多米尼克·卡西尼那里受到了当时作为天文学者能获得的最好教育,之后,他被选为法国皇家科学院成员,并在那里工作多年,同时也为法国宫廷服务。1718年,德利勒获得了国王和皇家学院授予的“首席皇家地理学家”头衔,这保证了他可以光荣退休,并且相对于其他商业制图师的地图,德利勒制作的地图的价值得到了提升。德利勒对制图的改进包括修正地中海的宽度,并将下加利福尼亚重新连接到北美。
路易十四在统治法国期间,有效地利用科学、艺术和制图为君主政体服务。法国制图师、“皇家雕刻师”和地图商人让—巴普蒂斯特·诺林(1657-1708)就创作了几幅赞美太阳王卓越功勋的地图。1700年,诺林出版了一幅著名的已知世界壁挂地图,无论是在地理还是雕刻技术方面,这幅图都代表了法国当时制图的最高水平。诺林的世界地图的使用与流传时间之久可谓异乎寻常:在数年里发布了很多修订版本,最后一版于1767年出版,距离第一版已过去近七十年。尽管在当时此图地理上的某些知识几乎就要过时,但它仍然在法国学校里发挥了重要的教育作用。

随着巴黎成为欧洲地图制作中心,英国的制图业也在向前发展。推动力来自于英国作为海洋力量迅速增长的影响力,以及他们与西班牙人、荷兰人还有后来的法国人纠缠不清的争夺主导地位的斗争。商船和海军都需要更详细的地图和更好地确定船只位置的技术。
自16世纪以来,通过使用倾斜仪测量纬度,精度偏差已经达到可以小于1°,但是直到18世纪早期,测量经度时仍然可能出现几度的误差。由于无法确定一艘船在海上的确切经度位置,从而导致世界各地发生许多致命的沉船事故。卡西尼的新方法基于对木星卫星的观测,而不是更费劲的月球距离测量法,但这仍然不切实际,因为在摇晃船只的甲板上进行天文观测十分困难。由于在实践中“天上的钟”无法在海上工作,所以要寻求新的解决方案。
1707年,英国议会宣布发起公开竞标,以找到解决这一重大海上安全问题的办法。奖赏非常丰厚。欧洲许多卓著的科学家都努力寻找答案,有些人采取的方案极为复杂且不可行。要找到真正实际的解决之道还得等几十年。海难仍在继续发生,地图上东西方向经度不够精确已无法让人接受,但情况依旧。船的位置距离欧洲本初子午线越远,错误就越严重。
长久以来,大家明白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必须在遥远位置的船上获得准确时间。船只需要已知经度的某个位置的确切时间进行比较。只要知道这个时间,计算经度就会非常简单。因为地球每小时向东自转15°,那么通过计算当前位置和比较位置之间的时差,人们就可以知道船只相对于比较位置的经度。如果一艘船的本地时间相对于比较时间(格林尼治时间)晚了五个小时,那它一定位于西经75°(在加勒比海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明白,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案是要有足够准确而持久的时钟。
在18世纪早期,测量时间仍然主要使用摆钟,但在长达数月的海上航行中,想让摆钟保证计时准确是行不通的。因此就需要有一个在船只运动和温度变化的情况下仍然能保证比较时间准确的钟表。
约翰·哈里森(1693-1776)是一位来自英国的木匠兼钟表匠,他致力于开发运行精确的钟表。在这项工作中,他与当局及科学界一样遇到了很多挫折和困难。然而,哈里森也获得了鼓励和经济支持,这使得他能够开发出第一个准确而持久的航海计时钟。经过多次海上试验与数次修正后,终于在1762年,哈里森的H4型“航海表”的精确度超过了所需精度。哈里森的儿子威廉参加了航海表在牙买加航行中最后五个月的测试。返回英国后,他们发现手表在整个航程中只慢了不到两分钟。詹姆斯·库克在1772-1775年的首次环球航行中,随身携带着这一计时器的K1版复制品。钟表对经度计算的准确度超出库克预期,他也开始默默地信任了这款表。

哈里森的工作成果还包括许多机械发明,其中一些为后来所有高精度计时工具的制作奠定了基础。他持久而顽强的工作对海上安全、海上经度测量和地图绘制有着深远影响。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精准计时器在航海与测量领域得到广泛使用,因为它在东西方时间测量方面精度的显著提升,影响了许多地图的制作。许多海岸线被重新绘制,岛屿也被重新定位。
三
启蒙时代的科学活动以多种方式在当时的世界地图上留下印记。测量仪器得到改进,科学考察在世界各大海洋上展开。这其中必须提到两位水手——他们甚至在詹姆斯·库克展开其高精度考察之旅前就极具影响力:这就是威廉·丹皮尔和埃德蒙·哈雷。两人都对世界地图中的科学内容产生了重大影响。
威廉·丹皮尔(1651-1715)的事业始于做海盗,以及劫持了他的第一艘考察船。丹皮尔总共环球航行三次,并帮助完善了澳大利亚北半部的地图。他还成为了一名狂热的自然观察者。丹皮尔在他的作品《新荷兰航行》(1703)中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这部作品在对自然描述以及制图方面都具有开创性。书中包含两幅由荷兰制图师赫尔曼·莫尔绘制雕刻的世界地图。其中一幅地图十分吸引人,因为它是根据丹皮尔所进行的科学观察绘制的。该地图使用线条和箭头描绘了主要的海洋风系:印度洋的大信风与季风。丹皮尔还在一篇题为《论风》(1699)的文章中单独出版了这幅科学世界地图。
另一位航海科学家、天文学家埃德蒙·哈雷(1656-1742)丰富的科学工作涉及天文学、光学、地球物理学、气象学、磁学和制图学。世人对他的工作十分尊重,英国皇室更是在1720年任命其为皇家天文学家。他是国际公认的名人,还曾与让—多米尼克·卡西尼合作研究彗星。如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彗星也是最著名的一颗彗星,哈雷计算并准确地预测这颗彗星将在1758年回到我们的太阳系。哈雷也对牛顿的理论非常精通,并且向国王詹姆斯二世(1633-1701)解释了这些理论对研究潮汐与洋流的意义。哈雷还在牛顿的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编辑工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哈雷曾对大西洋进行考察,并亲自担任了“帕拉莫尔”号的船长。这些航程最远一直向南延伸至南极,其主要目标是确定地球磁性的性质和在各个地区的偏差变化。地磁偏角作为一种现象——北方和北方的指南针磁针之间的偏差——自哥伦布时代以来就被海员们所熟悉。很多人试图测量各个地区的偏差,希望这有助于确定经度。但是,由于地磁偏角每年都有所不同,哈雷明白它针对这方面毫无可用之处。
像丹皮尔一样,哈雷也对地球的风力系统感兴趣。1686年,一幅描绘地球风系的创新地图与哈雷的一篇文章一起出现在皇家学会的一份科学出版物《哲学会刊》中。该地图展现的区域大小仅限于大约非洲南北端的范围,包括西边的加勒比海与南美洲以及东边的香料群岛。因此,地图重点描绘了大西洋和印度洋。细虚线用来描绘盛行信风的流动方向,当时已知的风系便以此方式得到展现。哈雷对于大西洋信风非常熟悉。

哈雷的航行也催生了其他重要的科学世界地图。这些都基于哈雷在大西洋进行的考察和他做的磁测量。他的一幅仅限于大西洋范围的地图于1701年出版。这是第一次在地图中对地球物理现象进行形象描述。基于他对变化差异的测量,这幅地图包含一种曲线——等偏线,这些线跨越海洋,用来描绘等磁差位置。
哈雷将其对地磁与制图的众多研究成果融合到1702年在伦敦出版的世界地图中。该图包括北部和南部的海洋以及所有的大洋,地图的一周似乎超过了360°。我们在这幅有趣的世界地图中可以看到,图的两侧都绘有澳大利亚,体现了当时人们对这块大陆的了解程度。
在这幅地图上,哈雷的变化等偏线已经从大西洋延伸到印度洋。哈雷将这幅地图编入其1705年出版的《奇象杂记》(原书名为拉丁文Miscellanea curiosa)中。哈雷与丹皮尔均对风系理论进行了发展,而这幅反映磁性变化的地图,随后也得到补充,增加了描绘风系的图形。这幅改进后的世界地图在18世纪的一百年中几乎一直在出版。许多著名的制图专家和普通制图师都出版过这幅地图,包括伦敦的约翰·塞勒,巴黎的路易斯·雷纳德,阿姆斯特丹的赖尼尔与乔舒亚·奥滕斯。

哈雷的科学世界地图是18世纪在科学、实验测量与制图领域发展和创新的绝佳范例。哈雷的地磁等偏线把常量描绘为地图上的曲线,无疑创建了一个范式。我们已经习惯于在地形图(高度)、航海图(深度)和天气图(等压线)上看到这些曲线。
四
两大因素对18世纪欧洲制作的世界地图的改进产生了特别影响。第一个是之前提到过的经度测量的进步,第二个是法国和英国皇家学会组织的大规模研究考察带来的影响。通过更准确的测量,大陆及其海岸的位置也更为准确。在库克(1728-1779)与法国人路易斯·安托万·德·布干维尔(1729-1811)和让—弗朗索瓦·拉彼鲁兹(1741-1788)的探险过程中,以前未勘察过的一些地区,尤其是太平洋中的一些区域出现在了地图上。
在18世纪世界地图中能够看到更为准确的新地理信息,加利福尼亚重新连接到北美,再加上澳大利亚南部与东部海岸,以及对阿拉斯加的勘察,这块最后一个未知大区域也出现在了地图上。在19世纪,南极洲与加拿大的北极群岛也在地图上最终定形。
白令海峡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未被探索过,人们因此对其并不了解。虽然在俄罗斯海军服役的丹麦人维他斯·白令(1681-1741)在自己早期航行中到过该地区,但从未真正探索过阿拉斯加海岸。但他确实发现了阿留申群岛。人们有时猜想亚洲和北美之间有一个大陆桥。也有人认为在日本北部有一群大岛屿。当时的地图提出了许多关于西北航道存在的假设。由于尚未发现通过北冰洋到达太平洋的海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许多人甚至相信有一条水路可以一路贯穿北美。这一想法的根源可以在探险家塞缪尔·德·尚普兰(1574-1635)对北美的考察中找到。法国人纪尧姆·德利勒制作了一幅地图,包括这些想象中的五大湖区、白令海峡和北美的内陆水道,该图流传广泛,在许多世界地图中都能看到它的影响。德利勒的法国同胞菲利普·布歇(1700-1773)在自己的地图中介绍了北方地区的地理和地形。他还出版了一幅极地投影世界地图,并提出了自己关于世界山系位置的理论。他将这些山系描绘延伸至海洋水面之下,并连接着各个岛屿。
五
1794年,由亚伦·阿罗史密斯(1750—1823)绘制的一幅地图在伦敦出版,此图中所有已知的大洲都被放在了正确位置——除了尚未探索的极地地区。这幅大型壁挂地图用两个半球描绘世界,旧大陆(欧洲、亚洲和非洲)与澳大利亚位于左半球,右边是新大陆(北美和南美),这种地图布局与18世纪的通行做法相反。这种表现方式是在向詹姆斯·库克船长致敬,是为了提醒人们注意到他在1769—1779年三次著名的探险活动。阿罗史密斯地图的地理精确度很高,这幅地图表明当时的测量技术已经高度发达。白令海峡的正确位置与海岸线的正确形式均基于库克最后一次航行的测量。库克第三次航行的目的之一是试图找到从太平洋到大西洋的北海航线。
詹姆斯·库克在英国皇家学会和英国海军部的主持下完成了所有的探险活动。因为1769年会有金星凌日,航行的目的首先是进行天文测量,同时收集关于“可能存在的南方大洲”的准确地理信息。阿罗史密斯的地图用不同颜色的线记录了库克的航程。第一次航行(1768-1771)的路线用绿色表示,第二次(1772-1775)为红色,第三次(1776-1779)为蓝色,直至夏威夷群岛附近用黑色表示,因为库克1779年在此遇害。
库克在天文学、航海与带队探险方面的技能都很强大,在科学探险史上无人能出其右。他绘制了澳大利亚东海岸数千公里的地图,并证实了新西兰由两个岛屿组成,没有与任何神秘的南方大陆相连。在第二次航行中,库克在约南纬60°的南太平洋海域来回航行了数万海里。1744年2月,他的船进入了距离南极1100海里以内的范围,即南纬71°10',他在这里并没有发现“可能存在的南方大陆”。库克还绘制了北太平洋地图,发现了汤加、斐济、新赫布里底群岛、复活节岛和夏威夷,后者被他称为三明治群岛。在第三次航行中,他从今天的俄勒冈州北部沿着北美洲西海岸航行,并绕行阿拉斯加到达了北纬71°44'的地区,但海冰阻止了他继续前进的步伐。
在第一次航行中,库克采用月距测量来确定他所处的纬度和经度,但在第二次航行中,他就能够用我们之前提到过的约翰·哈里森开发的著名的袖珍精密计时表K1来检查他的计算结果。库克第二次航行持续了三年,共航行了7万海里,这表明哈里森的袖珍精密计时表确实能够承受海上旅行的苛刻条件。在库克航行之后,精密计时表在远洋航行中日渐普及,显著提高了导航和位置查找的准确度。因为与夏威夷当地居民发生纠纷,1779年2月14日,詹姆斯·库克船长在他的第三次航行中遇害。有一句悼词这样评论道:“可能海洋是他的坟墓。但整个地球是他的纪念碑。”
六
18、19世纪,世界地图的地理信息越来越准确,开始为科学与政治目的服务。有了准确的地理信息的帮助,各帝国的边界与殖民地能够展现得更为精准。随着19世纪的到来,制图学被用于支持有着明确地理边界的单一民族独立国家以及这些国家的帝国主义殖民政策——这些政策的起源可追溯到地理大发现时期。
除服务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之外,世界地图也被用作展现许多其他类型信息的基础。使用多种绘图工具及颜色,世界地图可以描绘那些在自然与地理环境中观察到的现象。人们开始制作描绘洋流、山脉、植物带的世界地图。地图通过颜色来表现地表形貌,这种方法我们如今依然能在学校的地图中见到。
19世纪,越来越多的探险活动深入到非洲、亚洲与美洲的内部,欧洲人此前难以到达的或未知的地区开始成为焦点。尼罗河这样巨大的水路资源也陆续被发现,人们发现这条河的上游源头不再是古人认为的“月亮山”,而是一个大湖,本着殖民主义精神,它被冠以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名字,称为维多利亚湖。各国派遣了许多重要的探险队,跨过每个海洋,到达世界的各个角落。许多重要的科学、地理与海洋研究大大增进了我们对世界的了解。人类在大洋上展开数万海里的航程,其中包括法国的儒勒·迪蒙·迪维尔(1790-1842),为俄罗斯海军远征波罗的海地区的德国人亚当·约翰·里特尔·冯·克鲁森斯滕(1770-1846),还有英国的乔治·纳尔斯爵士(1831-1915),他们针对海底地形、洋流等展开了研究。从制图角度而言,他们对塔斯曼、布甘维尔、库克与拉·佩鲁斯等前辈的工作进行了补充。
西北航道与东北航道是否适合航行的问题在19世纪仍然是海员们关注的主题,许多探险队被派往这些北方水域。经过英国海军部的一系列大规模探险,终于将最晚发现的北美洲部分海岸与格陵兰岛绘制在了地图上。英国海军多次冒险进入了北美洲北部,让我们逐渐对北冰洋地区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在19世纪末对失踪的约翰·富兰克林爵士探险队的大规模搜寻过程中,这一地区最后的未知海岸也得以进入地图。不过,直到20世纪初罗尔德·阿蒙森(1872-1928)才成功驶进西北航道。在19、20世纪之交的时候,探险家已经证明,在北极地区没有开放海域,也没有任何大的岛屿,更没有墨卡托曾相信存在的磁山。北极仅是被漂浮着的冰块的北冰洋所覆盖。挪威探险家弗里乔夫·南森(1861-1930)驾驶着他的船“弗雷姆”号,从西伯利亚的北边到格陵兰东岸随极地冰川漂流,最终证明了这一理论。
生于芬兰的诺登斯科德(1832-1901)代表瑞典驾驶“维加”号成为了开辟东北航道的第一人。诺登斯科德在探险中绕行了整个欧亚大陆,经由新开凿的苏伊士运河从里海回到地中海。在此过程中,诺登斯科德解决了一个古老问题——大陆是否被海洋所包围。正如约翰·曼德维尔爵士早在14世纪预言的那样,只要有“一条状况良好的船和出色的团队”,人们确实能够环球航行游遍所有大洲,或从一个大洲航行到另一个。19世纪90年代,在完成了最为艰巨的一次探险后,诺登斯科德专心投入到地图收集与制图历史研究当中。他在这一时期出版的《摹本—地图集》(1889)和《水域图》(1895-1897)仍被看作地图史上的经典之作。
(本文摘自尤哈·努尔米宁著《欧洲地图里的世界文明史》,尹楠译,东方出版社,2019年11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