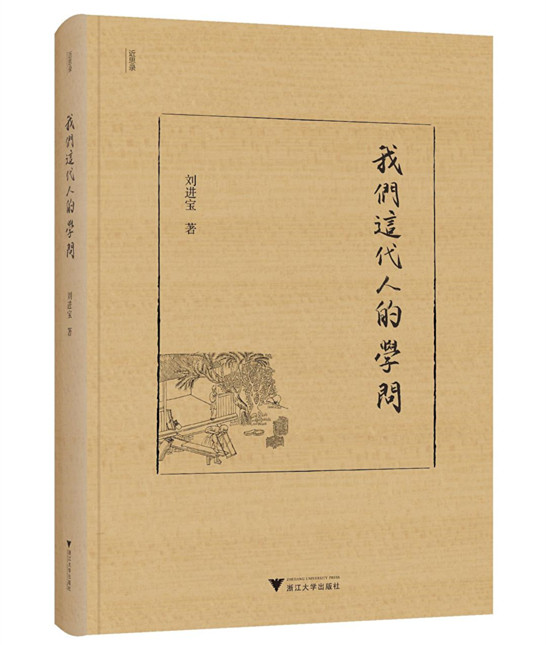《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所载荣新江先生的《中国敦煌学研究与国际视野》(以下简称《视野》)一文,从“可恨可喜”与“以德报怨”、《劫余录》与“伤心史”、伦敦留难与巴黎协作、“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四个方面,就贯穿中国敦煌学学术史的“国际视野”和“爱国主义”问题做了高屋建瓴的阐述。
正如荣新江先生在《视野》一文中所说:“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拥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敦煌学史,没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敦煌学史,更没有‘评判高下,辨别优劣’的敦煌学学术史。”笔者非常赞同荣新江教授的论述,同时作为对荣教授大作的响应,也为了能对编写敦煌学学术史贡献一点绵薄之力,现对所谓藤枝晃“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之说提供一点补充。
关于“敦煌在中国,教煌学在日本”之说,荣先生在《视野》中说:“正好就在大陆敦煌学刚刚重新起步的1981年,日本京都大学的藤枝晃教授应天津南开大学之邀,来南开举办敦煌学讲习班,并油印发行了《敦煌学导论》……然而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的敦煌学界流传着一种说法,说藤枝晃在南开讲演时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一说在京都)。’这话一经传开,就使得许多充满爱国主义热情的中国学者十分不满。笔者曾经向几位当时听课的中国学者询问这话的来历,他们都说这话其实是请藤枝晃来讲演的南开某位先生说的,意在请大家重视这位一般学子还比较陌生的敦煌学家。在今天看来,这话无疑是个误传。”

藤枝晃教授于1981年初能来南开讲演,除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一大的形势外,与当时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历史教学》总编辑、著名日本史专家吴廷璆教授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1932—1936年吴廷璆教授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现京都大学)留学时,藤枝晃也恰好是京都大学史学科的学生,他们两人是同学。
正如荣新江先生所说,据几位当时听课的中国学者说,“这话其实是请藤枝晃来讲演的南开某位先生说的,意在请大家重视这位一般学子还比较陌生的敦煌学家”。这里的“南开某位先生”实际就是指吴廷璆教授。当时的敦煌学研究,虽然在国内已经起步,但对一般学人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正是为了让大家重视这门还比较陌生的学问、重视国内一般学人还比较陌生的藤枝晃教授,吴廷璆教授在藤枝晃刚来南开或来到南开前夕,就呼吁学界重视敦煌学和藤枝晃。在《外国史知识》1981年第4期上,有一篇“本刊专访”,题目就是“诲人不倦的吴廷璆教授”。在这篇专访的后面有一段话,很值得引起注意:
吴先生还讲了日本史学界近来发生的一件事情:日本有一部很有名的《三经义疏》,历来公认为是公元六、七世纪间日本圣徳太子所写。有一位名叫藤枝晃的京都大学老教授在研究我国敦煌写经钞本中发现这三部佛经中的《胜鬘经》义疏原来是魏晋时代中国人所写,因此证明《三经义疏》根本不是圣德太子的著作。藤枝晃教授这种实事求是的学风引起了日本学术界的震动。说到这里,吴先生深有感触地说,我们的年轻人一定要有志气参与改变“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不正常状态,要有志气改变史学研究的落后状况。
《外国史知识》当时是月刊,1981年第4期出版于4月14日,而藤枝晃教授是4月8日开始在南开演讲的,前后只有一周时间,中间只隔5天。在当时的排版、印刷条件下,如果吴廷璆教授是4月8日所讲,要在4月14日出版的杂志上刊载,中间还有记者的采访、杂志社要预留版面等,应该是比较困难的。更可能的应该是在藤枝晃教授来南开前夕吴廷璆教授讲了此话,讲的是“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而不是“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
由于吴廷璆教授已有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之说、之想,因此,当4月8日藤枝晃在南开演讲,吴廷璆教授主持并介绍藤枝晃教授时讲了此话。为了突出日本和藤枝晃,就改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了。
由于藤枝晃1981年来中国时,他还没有去过敦煌,因此这次的中国之行,还有去敦煌参观的愿望。当时,不论是天津,还是北京、上海,都没有直达敦煌的航班。去敦煌必须要在兰州中转。这就有了藤枝晃在兰州的演讲。
藤枝晃路过兰州时,在西北师范学院(现西北师范大学)进行了学术演讲。这次演讲的主持人是著名隋唐史研究专家、时任甘肃省历史学会会长、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的金宝祥教授,其介绍者就是吴廷璆教授。因为吴廷璆教授和金宝祥教授在20世纪40年代前期曾是四川大学的同事,两人有着密切的交往,1986年秋,当两位老人都70多岁时,吴廷璆教授还专程到了兰州,住在金宝祥先生家中共叙友情。正因为有此友情与联系,当藤枝晃在南开讲演结束去敦煌时,吴廷璆教授就写信希望金宝祥教授给予接待。
当时的兰州还比较封闭,外国学者很少能来兰州,再加上藤枝晃是国际著名的敦煌学专家,甘肃又是敦煌学的故乡,金宝祥教授也是当时甘肃少有的几位敦煌学研究者之一。(1982年4月15日,教育部高教司在给教育部党组的报告《关于发展敦煌学的建议》中说:估计国内现在对敦煌学有研究的学者,老中青合计100多人,其中副教授、副研究员以上约四五十人。文中举例说到“厦门大学的韩国磐教授,山东大学的王仲荦教授,西北师院的金宝祥教授,北京师院的宁可教授,天水师专的张鸿勋副教授等,都对敦煌学有所研究”。见《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一九八三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会刊》,第186页。)这种种因素的组合,就有了藤枝晃在西北师范学院的演讲并引起的轰动。

当时敦煌学已经开始复苏,兰州大学于1979年建立了敦煌学研究小组,同时邀请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段文杰先生和甘肃省图书馆的周丕显先生为历史系进修班开设了“敦煌学”课程,并于1989年2月出版了《兰州大学学报》的“敦煌学”专刊(即《敦煌学辑刊》的第一期)。另外,敦煌文物研究所正在编辑《敦煌研究文集》,筹办《敦煌研究》;西北师范学院、西北民族学院、甘肃社会科学院等单位,也有学者关注敦煌学。
正是1981年5月26日在西北师范学院的演讲中,藤枝晃说到:“有学者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同时还讲到“高昌的文化有独特的特色”等。
在1981年那个极具爱国主义的时代,藤枝晃的演讲,尤其是“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和“高昌文化的独特性”之说,立即引起了大家的争论,许多听讲者还纷纷向中央有关部门和新闻媒体写信反映。当晚我们宿舍中的同学也曾激烈争论,有的同学甚至说:“藤枝晃是帝国主义者,怎能说高昌文化具有独特性?这不是想将高昌从中国割裂出去吗?”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这样一句学术评判为何会引起巨大的反响呢?这既与当时极具爱国主义的时代因素,即“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女排的“五连冠”引起国人的振奋等有关,也是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尽管“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但从国人的心态来说:此话我们可以说,但外人不能说。我们自己说,是我们的谦虚,我们有自知之明;外人说了就是对我们的小瞧,乃至对我们的污蔑。就像谁的小孩有了错误,家长批评、责备,甚至打骂,都是天经地义的,但别人稍稍说一下,家长也是不乐意,甚至反感、气愤的。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敦煌研究组组长宋家钰研究员说:“日本一位学者的‘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之说一出,国内一些学者深感有伤我们的自尊。”(宋家钰《“敦煌学中心说”引起的反思》,载《光明日报》2000年9月21日)可以说就是这一国民心态的写照。
“教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之说在中国引起较大的反响后,听说藤枝晃曾有过辩解:原话不是他说的,他只是说有学者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而翻译没有将此话完全翻译说明,因此造成了误会。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之说的误会,在整个八九十年代影响到了中日两国的学术交流。据有的学者说,日本有些学者也指责藤枝晃,说他此说搞坏了中日学术关系,影响了中日两国敦煌学的交流与合作。1987年9月,敦煌研究院主办的“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在敦煌召开时,藤枝晃应邀参会,再次来到了敦煌。在来中国参会前,他还从日本专门给金宝祥先生写信,希望去敦煌前,在兰州西北师范学院见面座谈。藤枝晃到兰州后,在西北师范学院专家楼小会议室与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系、敦煌学研究所的老师如金宝祥教授、陈守忠教授和笔者等七八人座谈约两小时。从会议室出来后,我与藤枝晃先生走在一起,他对我说:“上次在你们这里搞得很不愉快。”藤枝晃先生此话,显然是指1981年5月在西北师范学院的演讲,因为此前他只来过西北师范学院一次。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之说一经流传,在当时那个极具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时代,从上到下,从官方到民间,从政界到学者,都感到的是气愤、震惊,而没有人去探究它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但不可否认,它“在客观上无疑对中国敦煌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视野》,第174页)。因为在爱国主义的感召下,加强敦煌学研究,就成了爱国主义的象征,也是弘扬我民族精神的动力。此后,从官方到学界,都更加重视敦煌学的研究及有关研究组织的建设。1983年8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成立,虽然是国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但确实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之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此说促使了我们更快地加强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
(本文原载《历史研究》2007年第3期,收入《我们这代人的学问》,刘进宝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