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冠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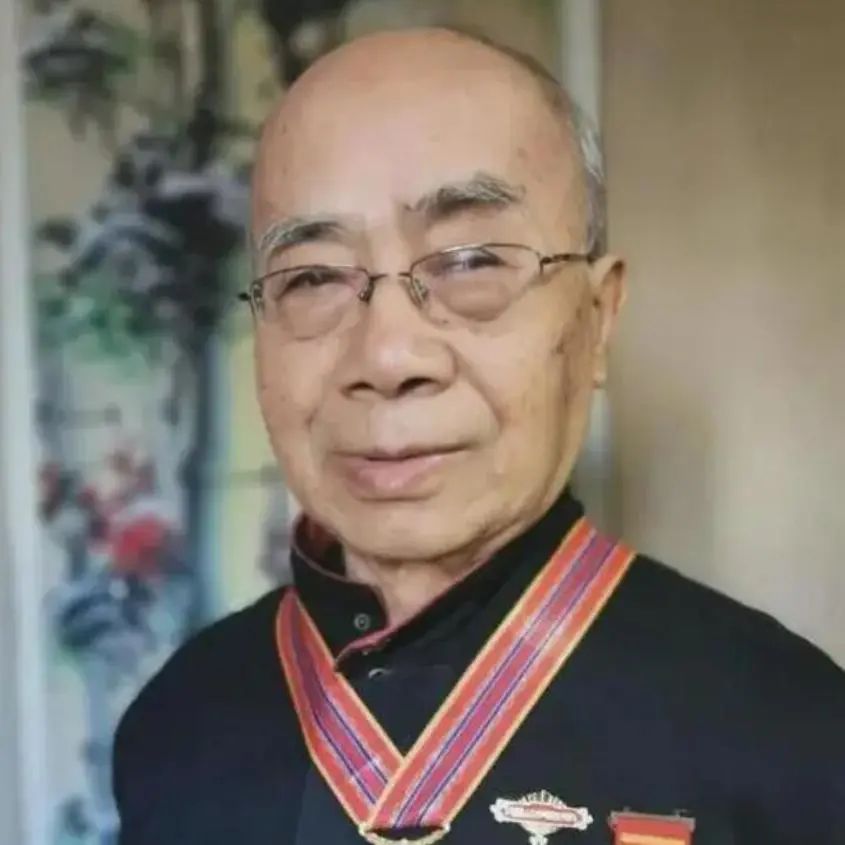
(向上滑动查看更多)
新中国资深外交官;1950年调入外交部,1951-1954年派往朝鲜,在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工作;历任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随员、国际关系学院和外交学院讲师、外交部美大司副处长、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领事、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一秘、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参赞、常驻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常务副代表等职。
音频
前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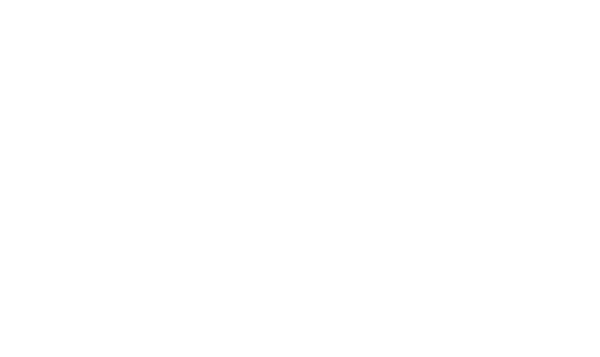
1954年日内瓦会议杂忆(上)
正文

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与中国代表团人员在一起合影。图源:《建国初期的外交部》
日内瓦是个国际会议十分频繁的地方,也是国际旅游胜地,是个高消费的大城市。对大部分中国团员来说,就是在日内瓦,他们开始了同西方生活方式的直接接触。
我和几名青年人住在旅馆的最高一层。不像现在的旅馆,最高一层往往是“总统套间”的所在地。我们的顶层却是一层阁楼,窗子窄小,打开窗户,不见“花园城市”的美丽景色,而是后院里破旧的屋顶。它们无疑是旅馆中房价最低的房间。然而,各人住的却是单间,面积约有30平米,地毯、沙发、席梦思一应具备,跟国内简陋的集体宿舍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简易房间,不带浴室,但房内有一洗脸盆,盆架两侧各有一条两头相接,可以循环使用的布巾。这分置左右两旁、长长的布巾作何使用,引起了争论:有的同志认为右边的是擦手用的,左边是擦脚用的;有的不以为然,认为没有区别。研究了半天,没有达成共识。
为何一条小小的布巾竟引起争论?事出有因。为了增强抵御“资产阶级歪风”的能力,出发前我们几个青年人还专程到北京饭店去体验一下生活。虽然那时的饭店还未扩建,孤零零的一座老楼陈旧不堪,但它的“豪华”已令我们瞠目。进了一间套房,浴室里见到一个矮矮的、长圆形的、脸面朝天的白瓷设施,有的同志不知它是何物,便乱拧开关,被喷了一脸的水。事后得知,那是冲下身用的卫生洁具,后悔不已。从中,我们得到一个教训:新鲜玩意儿,不知是何物,切勿乱动,以免洋相。
洗澡间是公用的,使用时找旅馆服务员要钥匙。第一次试用时,我朝浴缸放了大半缸的水,不仅水清见底,而且水质很好,呈自然的浅绿色。日内瓦的用水,源自阿尔卑斯山的融雪,故而如此透明清澈。我跃身盆中,半浮半沉地浸泡在这圣水中,实感劳累之余泡个热水澡乃人生一大享受。泡着,泡着,记忆把我带回到两年前的一次经历:
春节前,按照中国人的习惯,要沐浴更衣,以象征除旧布新。可是在战争的环境下,条件十分艰苦。夏天好办,溪流中、瀑布下都是洁身理想的去处。大冬天,如没有火,没有设备,便浴不成。设法吧!听说没有遭受很大破坏的中立区——开城有开澡堂的,我们几个人便相约同去一试。
到了城里,找到地方,付了费,我们便脱衣入浴。没有想到浴室甚小,大概是我的阁楼房间那么大,但池子里早已泡满了人,说朝鲜话的、说中国话的兼而有之。站在池旁,只见暗黑水面上的一个个人头,像铁锅煮饺。
室内蒸汽腾腾,室温尚可,那气味却令人窒息。怎么办?既来之,则安之。我不敢入池,只好从池里舀水冲身。那池水的颜色,如说像浑汤酱油,也不夸大。最后,想找点清水冲洗也无处可觅,只好就此结束了辞岁之浴,带着别人身上的垢泥返回驻地。
我们是幸运儿,此时此刻正在日内瓦享受着一池清水,但遥想国内,还不知有多少同胞和同事继续战斗于污泥浊水之中!
在大饭店里生活的难处之一是吃饭。我们这些人都随意惯了,在食堂用膳,去了就吃,吃了就走,顶多20分钟。在“玻璃袜子”吃饭,从点菜到喝完咖啡,至少一个小时。尤其“受罪”的是,还得遵守一大套规矩:西服领带、正襟危坐、喝汤不得出声、盘碟刀叉不得碰撞、说话要轻声细语……也难怪,周围都是衣饰华丽、举止斯文的西洋女士先生,旁边还站着穿着燕尾服、戴着白手套、替你撤盘端菜的侍者。更不说中西餐的区别,再名贵的法国大菜,多吃几天,黄油味就把你熏倒,你就想起面条、酱菜来了。
我尤其不能适应那“大陆早餐”,虽它有鸡蛋、牛奶、火腿,营养丰富,但中国人的早餐以米面为主,没有一定的量,肚子会觉得空空如也。可惜那“大陆早餐”的面包,虽烤得焦脆,还包了一层纸保温,但薄如纸张,实在不足以充饥。吃正餐时,如你仔细观察,也会发现:中国人吃饭的餐桌上,面包的消费特别旺盛。
大约10天之后,总领馆替代表团在市内找了一栋小楼,我们便乔迁出“玻璃袜子”,开始了在日内瓦的一段新生活。
小楼位于一个住宅区内,环境幽静。楼后还有个小花园,大树的枝叶蔽天。每天清晨,你还在梦中,枝头上的小鸟已开始鸣叫,组成一曲美妙的交响乐。这时你拉开窗帘,准可发现天已蒙亮。
我们二三人一间,分居全楼。室内,除床位和放衣箱的地方外,就没有什么立锥之地了。床单和枕套定期换洗,有专人负责,不需个人操心。卫生间当然公用。比起旅馆来,“生活空间”小了点,但费用大量节约,也没有感到不便。许多人住在一起,互相照应,其乐融融。
最令人满意的当推吃饭了。代表团工作繁忙,成员的工种很多,工作时间也不一致,早出晚归者有,日中出门者有,夜间伏案者更是不计其数。三餐的制度显然不能满足多种需要。为此,代表团采用了“快餐”制。冰箱里储存着大量的成品和半成品,外加饮料和水果。团员们可以随时取用、各择所好、不受数量限制,众人称便。但没有人替你服务,一切“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当然,食物都是就地取材,中式食品凤毛麟角。但心灵手巧者也可西材中用,自己动手做个中式的汤、菜,作为调剂。困难之处是:炊具全是西式的平底锅和平铲,炒、煎起来很不顺手,而且往往热油四溅。难怪代表团撤离时房东要求赔偿厨房、地板,因为食油把它浸透了一层。
安全保卫也是我们重点关注的问题。日内瓦是个相对安全的地方,但它也是国际谍报中心。那么多“共产党分子”集中居住于一处,很可能成为敌对势力活动的目标。代表团采取的保卫措施之一就是加强巡逻。白天有专人负责,夜间则是组织全体人员轮流看守。值班分上下夜,每组两人,前后4个小时,主要任务是看管门窗,发现险情,包括水、火、气的安全。
我也轮值过几次。每次我们都是带着对全体同志安全负责的高度责任心,在夜深人静、睡意正浓的时刻,克服疲劳,提高警觉,手持电筒,从顶楼到地下室往返巡视。值得一提的是,全体女同志也参加了这一光荣的任务,有时女同志值的是后半夜的班,换班时还需去女宿舍唤醒。
白天,门前有瑞士警察站岗。这完全是为了应付当地的好奇者和上门拜访者。有他们挡驾,我们就方便多了。他们也是采取轮值制,一天数人。我多次观察了他们换岗的情况,交接前都要互相敬礼并简单交代,这没有什么新鲜之处。引起我兴趣者是他们使用的交通工具都是私人的摩托车。上岗时骑来,置放身边,下岗时扬长而去。见了几回,我感慨万分:什么时候中国警察也能骑着摩托车上班?
发达和富裕令人羡慕,但它们不是一切。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和道路、自己的价值和追求。
原标题:《1954年日内瓦会议杂忆(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