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钮笙佳 上海市法学会 东方法学 收录于合集 #法学前沿 12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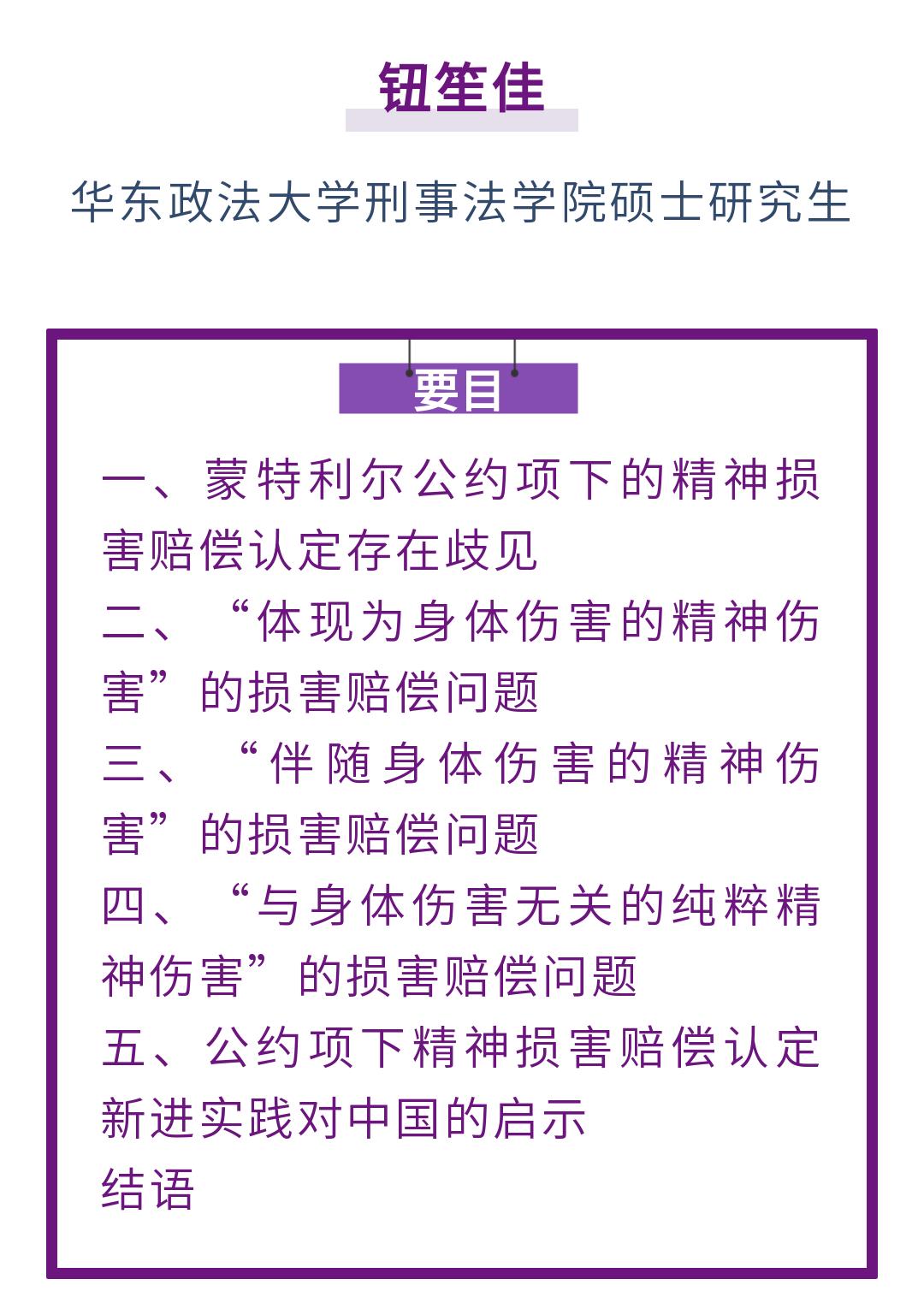
蒙特利尔公约对是否允许精神损害赔偿规定不明,导致公约适用实践中存在诸多认定分歧。剖析主要缔约国司法实践与新近实践动向,结合公约的议定过程与其目的与宗旨的实现路径,指出针对“体现为身体伤害的精神伤害”,因其属于公约项下的“身体伤害”而应当准予赔偿;针对“伴随身体伤害的精神伤害”的损害赔偿,不苛求身体伤害与精神伤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仅要求事故同时造成身体伤害与精神伤害即可准予对该精神伤害进行损害赔偿;针对“纯粹的精神伤害”的损害赔偿,建议将其纳入公约准予赔偿的范畴,各国法院在实践中应尽快建立起规范精神伤害认定的初步标准,助推蒙特利尔公约目的与宗旨的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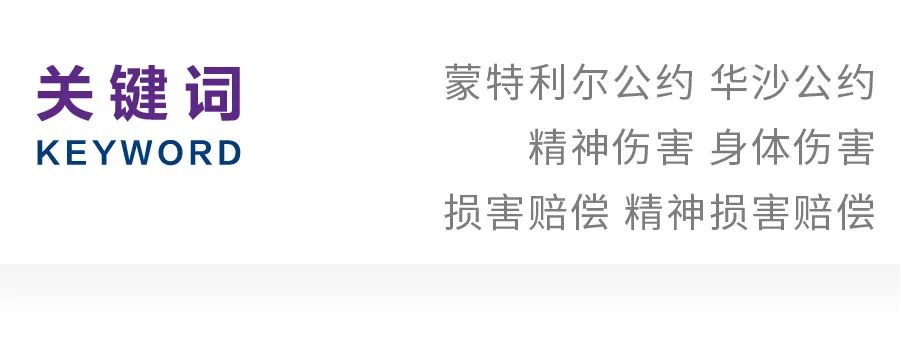
一、蒙特利尔公约项下的精神损害赔偿认定存在歧见
1999年于加拿大蒙特利尔通过的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以下简称蒙特利尔公约或“公约”)是1929年关于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简称华沙公约)体系下国际航空私法一体化和现代化的改革成果,也是目前认定国际航空运输承运人损害赔偿责任的重要法律渊源。如何解释蒙特利尔公约对旅客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直接影响各缔约国承运人和旅客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但自1999年以来,各国司法实践对公约的解释实践仍未明晰精神损害赔与不赔的界限,并随实践发展引发了诸多歧见,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公约作为统一实体规则的效用。本文通过分析蒙特利尔公约及其前身华沙公约中关于承运人对旅客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结合实践澄清争议原因,主张对纯粹精神伤害的损害赔偿纳入现有的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框架中。同时联系我国民法典和民用航空法中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为建立旅客精神损害赔偿的成熟体系提供一些建议。
(一)
专涉及精神损害赔偿认定的公约规则
针对国际航空运输中的旅客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法院通常会援引蒙特利尔公约第17条进行认定,即只要造成死亡或者伤害(injury)的事故是在航空器上或者在上、下航空器的任何操作过程中发生的,承运人就应当对因旅客死亡或身体伤害而产生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换言之,提出精神损害赔偿必须满足如下三个条件:(1)存在造成死亡或者身体伤害的事故;(2)该事故发生在航空器上或者在上、下航空器的任何操作过程中;(3)旅客蒙受的损害与死亡或者身体伤害“存在关联性”。
(二)
公约约文中精神损害赔偿认定标准付之阙如
之所以使用“存在关联性”这种模糊表述,是因为公约关于“精神伤害”(mental injury)的赔偿认定未作明确规定。这导致各缔约国法院在适用与解释公约的过程中,即使支持精神损害赔偿,亦容易引发分歧。具体原因在于,公约表述在以下两方面均不够清楚,从而引发了解释疑难。
其一是“在死亡与身体伤害的情况下”(in case of death or bodily injury)中的措辞“在……情况下”(in case of)。一种理解与作为作准文本之一的中文本一致,认为“在……情况下”表明承运人仅对死亡或者身体伤害“造成的”精神伤害进行赔偿,即采用“因果关系论”;而另一种理解则认为“在……情况下”表明精神损害赔偿只要求存在旅客死亡或身体伤害的情形,即便其遭受的精神伤害并非是由死亡或身体伤害“造成的”,承运人也应当对旅客的该种“伴随身体伤害的”精神伤害给予赔偿,即采用“伴随关系论”。
其二是术语“身体伤害”(bodily injury)。身体伤害一词到底能否包含精神伤害,尤其是与身体伤害无关的“纯粹精神伤害”(pure mental injury),一直存在争议。在当代国际航空旅客运输中,基本认可“身体伤害”一词能够包含精神伤害。在此范围内,一种观点仅支持包含由身体伤害引发的精神伤害,另一种则持即使是纯粹精神伤害也应当包含在内的态度。对于仅“伴随身体伤害”而非“由身体伤害造成的”精神伤害,以及纯粹精神伤害是否包含在身体伤害之中的讨论,其实面对的共同难题依然是如何界定精神伤害与身体伤害之间的关系。
此外,除了语言固有的模糊性导致精神伤害与身体伤害之间的关系难以界定以外,认为纯粹精神伤害不在赔偿责任范围内的观点大多受到华沙公约的影响。以法语为唯一作准文本的华沙公约使用的“lésion corporelle”(身体伤害)一词的前缀带有物理性的、身体性的倾向,似乎将纯粹的精神伤害排除在身体伤害之外。但实际上,在法国国内法语境中,“lésion corporelle”一词是能够囊括精神伤害的。对此,航空法学者René H. Mankiewicz指出,在1929年起草华沙公约时,法国国内法专家使用的“lésion corporelle”一词恰恰是带有精神性含义的。如果该词仅仅是指物理上的身体伤害,起草者们既没必要在此术语之前单独列举其他形式的物理伤害写入约文,也完全可以使用特指身体创伤(blessure)的其他术语。另外,法文本是华沙公约唯一的作准文本,对“身体伤害”的解释理应遵从法文原意。但蒙特利尔公约的英文本和法文本具有同等作准效力,因此在解释时,法文本的影响力并不具有排他性。
其实,在蒙特利尔公约议定时,各国就试图将旅客的精神伤害纳入承运人赔偿责任范围内,“精神伤害”这一术语也通过了国际民航组织法律委员会的审议,但递交至1999年5月外交会议的最终公约草案中仍然只保留了“身体伤害”一词。对此,部分缔约国达成了一项解释性声明:各国法院可以根据国内法的发展状况自行决定是否给予旅客精神损害赔偿。埃及代表特别指出,既然“身体伤害”的含义仍然在发展中,应当由实践揭示其内涵并赋予其统一的含义。也就是说,各国法院的实践在认定精神损害赔偿标准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三)
司法实践中精神损害赔偿认定解释未尽一致
在美国1991年“Floyd v. Eastern Airlines案”(以下简称“Floyd案”)之前,各法院对“身体伤害”一词的理解存在明显分歧。司法实践中对旅客精神损害赔偿的态度也是泾渭分明。一些法院认为旅客的情感痛苦也可以获得赔偿。如在1972年“Hussel v. Swiss Air Transport Co案”中,法院认为公约意图保护旅客在国际航空运输中的权益,因此对其遭受的“身体伤害”应作扩张解释,即将精神伤害、心理伤害“尽收囊中”。另一些法院则认为,非系身体创伤引发的精神痛苦不得赔偿。如在1974年“Bumett v. Trans World Airlines案”和1975年“Romans v. Swiss Air Transport Co案”中,法院认为无论“身体伤害”一词的语义认定是否受到华沙公约法文本的约束,精神伤害均不属于“身体伤害”,纯粹的精神伤害亦不能获得赔偿。
美国实践中的这一分歧在“Floyd案”一审判决被推翻后得到了解决。当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审查华沙公约的立法背景和议定过程后明确指出:在事故没有造成旅客死亡、身体伤害或者其他身体肢体上的损伤的情况下,承运人无需承担华沙公约第17条下的损害赔偿责任。换言之,1991年后,大部分美国地方法院都遵循“没有身体伤害或物理性(physical)伤害的情况下,精神损害赔偿不属于华沙公约第17条调整范围”的审判逻辑。
在英国,2002年“King v. Bristow Helicopters Ltd案”(以下简称“King案”)和“Morris v. K.L.M. Royal Dutch Airlines案”(以下简称“Morris案”)中,原告皆对自己所遭受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以下简称“PTSD”)、噩梦、焦虑等精神痛苦提出损害赔偿请求。在“King案”中,法院认为原告忍受的精神伤害与其患上消化性溃疡的身体伤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从而支持了原告的主张;而在“Morris案”中,则因伤害缺少身体性、物理性的症状,法院驳回了其提出的对纯粹精神痛苦的损害赔偿请求。
在法国,法国国内法允许精神损害赔偿,且规定了工作事故中的精神损害赔偿方案。尽管法国国内法早在1857年就有关于精神伤害的法律规定,但针对航空事故,法国法院并未就“身体伤害”一词是否包含精神伤害或者公约第17条是否包含精神损害赔偿发表明确的观点。
在中国,2005年“某女士诉美国西北航空案”中,法院认为承运人应当关注旅客蒙受的伤害,这其中既包括物质伤害也包括精神伤害。由于某女士并非针对在飞行途中所受的烫伤提起诉讼,而是对后续航空公司的处理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和公开道歉,本着“不告不理”的原则,法院未对身体伤害问题这一实体问题展开审理,最后支持了原告某女士提出的“1美元精神抚慰金”的赔偿请求。这或许意味着对精神伤害的损害赔偿请求并非必须依附于身体性、物理性伤害才能成立,而是囊括在第17条项下的独立的诉请理由。
(四)
当前精神损害赔偿认定争议的具体表现
综上所述,典型国家适用公约的实践表明,无论是法文本还是英文本,对“身体伤害”一词的认定均存在程度不一的分歧。即使是在一国内部,得出类似结论的不同判决,其分析说理也可能大相径庭。虽然公约的适用实践至今未能形成统一的认定标准,但至少为我们提供了将精神伤害纳入蒙特利尔公约中可予赔偿的损害的两种不同路径:其一是通过建立精神伤害和身体伤害之间的联系,将满足特定联系的精神伤害纳入赔偿范围;其二是扩大术语“身体伤害”的范畴,使其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身体伤害,又囊括精神伤害。
尽管两种路径各自又衍生出不同的研判方式,但主流观点依旧沿袭着美国“Floyd案”中的判理:由事故造成的物理性身体伤害直接或间接引起的精神伤害才属于公约项下“身体伤害”的范围,准予对此进行损害赔偿。但此种情况下的损害赔偿并不是单独针对“纯粹的”精神伤害的损害赔偿,而是法院认可将某些精神伤害视为身体伤害的一种,从而可以在第17条的赔偿规则下获赔。这是因为随着医学科技的发展,身体伤害会直接造成精神痛苦的结论得到了证实。换言之,法院支持的仍然是基于身体伤害的损害赔偿,并非纯粹基于精神伤害的损害赔偿。当前,仅以“精神伤害是否与身体伤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或“精神伤害是否是由身体伤害造成的”作为精神损害赔偿的认定标准,可能遇到的疑难问题主要体现为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体现为身体伤害的精神伤害可否认定为身体伤害?即当事故虽未直接造成传统认知中的身体伤害,但引发的精神伤害根源于旅客身体内在变化时的损害赔偿问题。由于该种内在变化的“身体性”和“物理性”往往易于被忽略,法官在认定时大多将其排除在身体伤害之外。
第二,伴随身体伤害的精神伤害可否单独获得赔偿?即当事故造成身体伤害的同时也造成精神伤害,但两者之间没有显著的因果关系时,此精神伤害是否可以获得赔偿的问题。受华沙公约影响,法院在认定精神伤害时长期要求其由身体伤害引起;但事实上,公约语义本身并未设此限制,近年来实践中也逐渐出现仅伴随身体伤害的精神损害赔偿取得成功的案例。
第三,与身体伤害无关的纯粹精神伤害可否获得赔偿?即事故没有造成旅客的身体伤害,且造成的精神伤害也不伴有任何身体伤害时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随着消费者保护水平的逐渐提升,旅客在航空事故中遭受的精神性痛苦、情绪性伤害等纯粹精神伤害能否被公约涵盖的争议又重新被提起。
二、“体现为身体伤害的精神伤害”的损害赔偿问题
(一)
可医学手段识别的精神伤害属于身体伤害
法院借助现代医学手段将某些精神伤害视为身体伤害的论调虽然没有从正面回应两者之间的法律问题,但为公约下旅客请求纯粹精神损害赔偿提供了新的道路。在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诞生前夕的“Weaver v. Delta Airlines,Inc案”的判决中,原告提出的“PTSD是一种身体伤害”的主张得到了蒙特纳州地方法院的支持。由于像PTSD这类身体伤害,不仅仅只有恐惧和惊吓等情绪上、心理上的表现,而且还会对人的大脑与神经元产生身体性的影响。法院将该案的核心问题界定为,在医院出具确实诊断的基础上,特殊类型的身体伤害能否获赔,并认为即使恐惧本身不属于华沙公约第17条下的身体伤害,大脑作为承载恐惧的客观载体,其受到的伤害也应属身体伤害。尽管该判决在2002年被宣告无效,但其肯定的身体伤害与精神伤害之间存在联系的观点,值得在21世纪的司法实践中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在消费者保护理念日渐提升的今天。
2015年5月澳大利亚南威尔士州最高法院对“Casey v. Pel-Avation Pty,Ltd案”(以下简称“Casey案”)作出的判决再次认可:PTSD作为一类特殊的精神伤害,与身体伤害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联系。该案中,专家说明PTSD间歇性或者长期性导致的功能性伤害反映出的大脑功能的改变,在Casey女士身上体现为神经递质活动模式的改变和大脑中的化学变化。法院认为,虽然大量的案例都将PTSD排除在身体伤害之外,但PTSD之间亦有差别。Casey女士遭受的记忆与专注力退化,以及大脑的其他功能性伤害应当属于身体伤害的范围。随后被告航空公司Pel-Aviation提起上诉。上诉法院虽然推翻了一审判决,但同样表示“‘身体伤害’意味着对一个人的身体造成的伤害,没有理由认为这其中排除了对人类大脑的伤害”。
(二)
精神伤害可通过评估认定为身体伤害
与事故造成身体伤害引起精神伤害的情况不同,体现为身体伤害的精神伤害在事故发生时并没有造成传统医学意义上的身体伤害,因而将其认定为身体伤害需要突破对“身体”一词的固有认知。这无疑给法院提出了极大的挑战。澳大利亚“Casey案”中上诉法院给出的判决理由是,大脑化学性或者是生理性的变化不足以证明脑部伤害的存在,必须要有证据表明大脑的某个部分或者某些部分遭到物理性的破坏才能认为存在实际的身体伤害。该判决实际上从侧面认可了脑部伤害可以是身体伤害的一种,因而只要证明精神伤害能够通过某种方式评估为脑部伤害,就能将其涵盖在蒙特利尔公约第17条项下准予赔偿。至于该种评估方式是以化学性、生理性、物理性还是其他特性作为评估标准,这将是医学和司法的一个交叉范畴,需要更多实践予以探索。
三、“伴随身体伤害的精神伤害”的损害赔偿问题
(一)
公约解释倾向于“伴随关系论”
以“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和身体伤害之间的联系”这一路径来澄清精神伤害与身体伤害之间的关联,首先要解决的是蒙特利尔公约第17条规定的“在……情况下”的解释问题,即应当采“因果关系论”还是“伴随关系论”。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第1款的要求,探求公约语义应从最基础的文义解释出发。通过查询牛津英文词典,“在……情况下”的含义为“在……情形下”“如果……”“如果发生……情况”。换言之,该措辞表达的逻辑语境是:如果甲发生,那么乙成立。这只能说明甲是乙成立的一个必要的、伴随的情况,并不要求甲和乙之间具有严格因果关系。因此,公约第17条宜解释为:如果事故造成了一个可准予赔偿的身体伤害,那么旅客有权要求承运人就此伤害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无论是蒙特利尔公约还是之前的华沙公约均使用了“在……情况下”(in case of)或“在……发生时”(in the event of)这类表示伴随关系的短语,所以笔者认为蒙特利尔公约第17条约文本身从未将两者之间的关系设定为“引起”与“被引起”的因果关系。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公约第17条后半句中的措辞“仅在这种条件下”(upon condition only)是公约于蒙特利尔大会讨论时新增的内容,华沙公约的法文本和英文译本中都没有此种表述。这个新增短语与前文的“在……情况下”形成呼应,清晰地传递出精神伤害与身体伤害之间的伴随关系。
(二)
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因果关系论”
从一开始仅支持身体伤害赔偿,到如今纯粹精神伤害以外的精神损害赔偿被大量认可的演进过程中,虽然公约本身并没有在事故造成的身体伤害和精神伤害之间赋予因果条件的限制,但是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往往都要求赔偿精神伤害必须以“由身体伤害引起”为前提。法院之所以形成此种审判逻辑,一方面是因为受到华沙公约带有物理性、身体性倾向用词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因为同期案例实践为了避免旅客滥诉,对“在……情况下”作等同于“由……造成”的解释。
(三)
新近司法实践回归“伴随关系论”
相较于最初一昧地遵循先例,法院现在在认定精神损害赔偿标准时,更加注重发掘约文本身的含义。在2017年美国“Doe v. Etihad Airways案”(以下简称“Doe案”)中,原告旅客Doe女士在飞机飞行途中被椅背口袋中的皮下注射针刺伤手指,要求被告航空公司Etihad Airways对自己因此产生的身体伤害和精神伤害负责。对此,Etihad Airways则主张蒙特利尔公约第17条中的“在……情况下”意味着“由……引起”(caused by),即旅客所受的精神伤害必须是由身体伤害引起的。而本案中Doe女士的精神伤害源于对皮下注射针刺伤手指可能感染传染病的精神恐惧,并非源于刺伤手指这一身体伤害本身,因此无权请求被告承担公约第17条下的赔偿责任。美国密歇根州东部地区法院支持了被告方的观点,后Doe夫妇提出上诉。
同年,美国第六巡回上诉法院推翻了“Doe案”的原审判决,并认为密歇根州东部地区法院对“在……情况下”这一短语的理解有误。第六巡回上诉法院指出,如果蒙特利尔公约的起草者们想对事故导致旅客身体受伤时可准予赔偿的伤害种类进行限制,他们大可以使用一个具有显著因果关系意义的联结词或短语来代替“在……情况下”,而不是表述为含糊不清、似有若无的因果关系。且事实上,在后半句要求事故必须“造成”死亡或身体伤害时,起草者们确实就是这样做的,即使用了“由……引起”(caused)来表达身体伤害和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要求。由此可见,在同一句话中,公约起草者们并没有意图使用“在……情况下”来表达“由……引起”的含义。因此,只要Doe女士的伤口是由飞行途中的事故造成,其无论是基于伤口本身,还是基于惧怕感染风险而发生精神伤害,都属于公约准予赔偿的伤害。
据此,可以看出蒙特利尔公约第17条中事故、身体伤害和损害赔偿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即公约仅对事故与身体伤害之间施加了“引起与被引起”的因果关系要求,而对身体伤害和损害赔偿之间则没有因果关系的要求。那么对于伴随身体伤害的精神伤害行为旅客可能受到的损害后果之一,理应准予赔偿。
四、“与身体伤害无关的纯粹精神伤害”的损害赔偿问题
(一)
公约议定时并未排除纯粹的精神损害赔偿
1999年的蒙特利尔会议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承运人赔偿责任问题上的一场交锋,蒙特利尔公约第17条下旅客所受伤害的赔偿范围是否包含纯粹的精神损害赔偿也是这场交锋的争议点之一。当时,德国、法国和沙特阿拉伯的代表认为法文原文“lésion corporelle”(身体伤害)或者英文译文“bodily injury”(身体伤害)已经包含了精神伤害;以美国、巴西为代表的航空业发达国家则希望能够将术语“mental injury”(精神伤害)明确写入公约第17条中,或是使用含义更宽泛的术语“personal injury”(人身伤害)替代“bodily injury”(身体伤害)一词。而印度、埃及等国家则担心“精神伤害”一词的内涵和外延在当时极为模糊,将精神伤害纳入第17条下的赔偿范围会使国内本就羸弱的航空业雪上加霜。前来参会的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代表也表示,“精神伤害”的范围过于广泛,加之难以认定,把“精神伤害”作为单独的赔偿项无疑会增加法院的诉讼压力。会议最后,为了平衡承运人在其他赔偿责任规则方面作出的让步,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仍然保留了“bodily injury”(身体伤害)这一笼统的表述。
尽管交锋的结果兜兜转转回到原点,但会议磋商的过程透露出:持反对意见的代表们并非反对纯粹精神伤害的可赔性,而是担忧发展尚未成熟的航空业及承运人能否负担纯粹精神伤害可赔后的一系列后果。因此,对于纯粹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的争论,不应停留在与身体伤害之间是何关系这一层面,而应进一步探求剥离身体伤害后的精神伤害的可赔范围与程度如何与航空业的发展水平和消费者权益保护需求相匹配。
(二)
承认纯粹的精神损害赔偿利于实现公约宗旨
也许在当前将全部精神痛苦都纳入蒙特利尔公约准予赔偿的范围还为时尚早,但在有条件的国家和地区逐步建立纯粹精神伤害的赔偿标准,既是公约实现承运人赔偿责任规则统一化的需求,也符合公约保护旅客利益的价值目标。一方面,在其他运输行业,包括2002年旅客及其行李海上运输雅典公约、1976年的国际内河客货运输合同公约和1999年修订的国际铁路运输公约附件A《国际铁路旅客运输合同统一规则》,均使用了“人身伤害”(personal injury)一词来形容旅客所遭受的伤害,其中囊括了精神伤害的赔偿。也就是说,几乎所有主流运输方式的国际公约都规定了对旅客遭受精神伤害的赔偿规则。而另一方面,就民用航空运输行业而言,2009年关于因涉及航空器的非法干扰行为而导致对第三方造成损害的赔偿的公约和2009年关于航空器对第三方造成损害的赔偿的公约直接明确了“精神伤害”(mental injury)应当准予赔偿的情形,其中也包括对“可以辨认的精神疾病”这一纯粹精神伤害的赔偿。因此,蒙特利尔公约作为统一航空私法的重要文件,有必要考虑将纯粹的精神损害纳入承运人赔偿责任范围,以此实现“一体化”的目的。
另外,进入21世纪后,心理健康甚至比身体健康更令人关注。现代医学也表明,精神痛苦的危害有时候远大于身体痛苦。临床研究发现,精神伤害所造成的痛苦不仅可能延缓身体伤害的治疗进程,同时也是与自杀行为联系最为密切的因素之一。医学的发展让精神伤害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逐渐为人所知。既然蒙特利尔公约在议定之初就“认识到确保国际航空运输消费者利益的重要性”,那么理应注重旅客遭受纯粹精神伤害的损害后果,要求承运人对此承担赔偿责任。
五、公约项下精神损害赔偿认定新进实践对中国的启示
(一)
中国法院适用公约认定旅客精神损害赔偿的建议
根据“约定必须信守”原则,中国作为蒙特利尔公约的主要缔约国和民用航空运输大国,中国法院对公约的适用与解释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应当充分发挥示范与引领作用。以中国过往的案例实践为指导,法院认为事故造成的身体伤害属于侵权损害赔偿的一种,而侵权损害赔偿既包括身体伤害赔偿也包括精神损害赔偿。根据2005年“某女士诉美国西北航空案”中“一美元精神抚慰金”的主张获得法院的支持可知,精神伤害在中国司法实践中可以作为单独的损害赔偿理由,这些实践均为法院认定纯粹精神损害赔偿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但从近两年中国民用航空局发布的民航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来看,承运人实现营业收入方面有所回暖,较上年增长13.3%,但亏损仍然高达670.9亿元。并且当承运人对旅客伤亡存在过错时,蒙特利尔公约对赔偿数额未设限,支持纯粹精神伤害获得赔偿是否会成为疫情下压垮部分航空承运人的最后一根稻草,也值得法院考量。
因此,考虑到支持纯粹精神伤害获得赔偿可能是未来的发展趋势,通过司法实践发展精神损害赔偿的认定标准,既需要满足当前旅客精神损害赔偿的迫切需求,又需要兼顾承运人一方的利益,避免因疫情因素而加剧其亏损。鉴此,建议法院在适用公约第17条审理精神损害赔偿纠纷时可以考虑如下因素:其一是身体伤害。存在身体伤害仍然是精神伤害获赔的重要依据,但身体伤害与精神伤害之间不必要求具有严格的因果关系。借助“将伴随身体伤害的精神伤害纳入赔偿范围”这一过渡阶段,在保障旅客权益需求的同时给予承运人一定调整缓冲的时间。其二是医学鉴定。确定纯粹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时,以医方出具的精神伤害鉴定书为判断依据,引入医学标准划定纯粹精神伤害的入赔门槛,起到防止旅客滥用求偿权的作用,减轻法院的诉累。其三是实际损害。确定纯粹精神损害赔偿的金额时,在承运人对旅客伤亡无过错的情形下,仍然以12.8821万特别提款权为责任上限;而在承运人对旅客伤亡存在过错的情形下,对于超过12.8821万特别提款权的部分,应当以旅客遭受的实际损害为基础确定赔偿额度。当然法院无论是在何种情形下都不得判给惩罚性或者任何其他非补偿性的损害赔偿,以免违背公约要求的损失补偿原则。
(二)
中国关于旅客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完善建议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在1993年8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第一次回应了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但直到30年后的2021年我国民法典的正式生效,中国才首次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可见中国立法上对此十分谨慎。针对航空运输领域,我国民用航空法在描述承运人赔偿责任时同样使用了“人身伤亡”一词,这表明中国国内法中同样没有关于旅客精神损害赔偿的明确规定。若未来纯粹精神伤害被纳入赔偿制度,承运人与旅客对赔偿标准的意见必然各执一词,此时国际公约与国内法在该问题上的缺位必将导致法院面临大量的争议诉讼。因此,提前总结包括我国在内的主要缔约国法院适用蒙特利尔公约项下对旅客人身伤亡损害赔偿制度的经验,通过国内立法的方式制定纯粹精神损害赔偿的认定标准,确有必要。
目前,现存的侵权类人身伤害精神损害赔偿的国家标准比较笼统,赔偿数额方面仅列明了以下影响因素——侵权人的过错程度、获利情况、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侵权行为的目的、方式、场合等具体情节及所造成的后果、受理诉讼法院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未对各因素的权重系数作出说明。而从各省(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标准来看,通常按照侵权行为的严重程度、是否造成损害人伤残或死亡、损害人的精神损害严重程度划分三个赔偿级别,但公布的标准中未对限定各个级别的“一般”“严重”“特别严重”等用语作出解释,需要法官自行甄别本案适用的是何种级别下的赔偿标准;且就同一级别内赔偿标准的数额上下限而言,各地也并不一致,比如以造成公民死亡的精神抚慰金数额为例,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一般不高于8万元,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一般不得超过北京市城镇职工上年平均工资的10倍,即一般不高于44.62万元,其中差异不可谓是不悬殊。故在制定旅客精神损害赔偿标准时,建议注重具体的赔偿数额计算细节,有效防止旅客赔偿请求权和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进一步督促国际运输中精神损害赔偿认定标准的规范化。
另外,乘坐国内航班与国际航班的旅客在受到同种程度的伤害时,可能因法院适用不同法律而获得不同程度的赔偿。为避免该种情形的出现,国内立法制定的规则也应当尽量与各国法院适用蒙特利尔公约的实践结果保持一致,实现国内与国际的统一。
结语
针对当前适用蒙特利尔公约第17条而引发的精神损害赔偿认定分歧,分三种情形建议如下:针对“体现为脑部伤害等身体伤害的”精神伤害,可以借助现代医学鉴定技术对精神伤害重新评估划定为特殊的身体伤害,将其纳入公约关于身体伤害赔偿项下;针对“伴随身体伤害的”精神伤害的赔偿认定,无须达成完整的“事故造成身体伤害后再由身体伤害造成精神伤害”的因果关系逻辑链,仅要求事故分别造成身体伤害与精神伤害即可;针对“与身体伤害无关的”纯粹精神伤害而言,将其纳入赔偿范围符合公约议定时的初衷,并且有利于实现蒙特利尔公约保护旅客权益的目的和统一民用航空运输规则的目的。中国法院在认定公约项下的纯粹精神损害赔偿时,可以考虑采用医学和法律的双重认定标准,始终围绕旅客所受实际损害划定赔偿范围,避免引发国际承运人的不满。最后发挥中国作为公约主要缔约国的示范性作用,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率先实现民用航空运输行业运行规则在国内层面、国际层面以及国内与国际层面的多维度一体化。

原标题:《钮笙佳|蒙特利尔公约项下精神损害赔偿认定的新近发展与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