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王嘉珂 上海市法学会 东方法学 收录于合集 #法学前沿 10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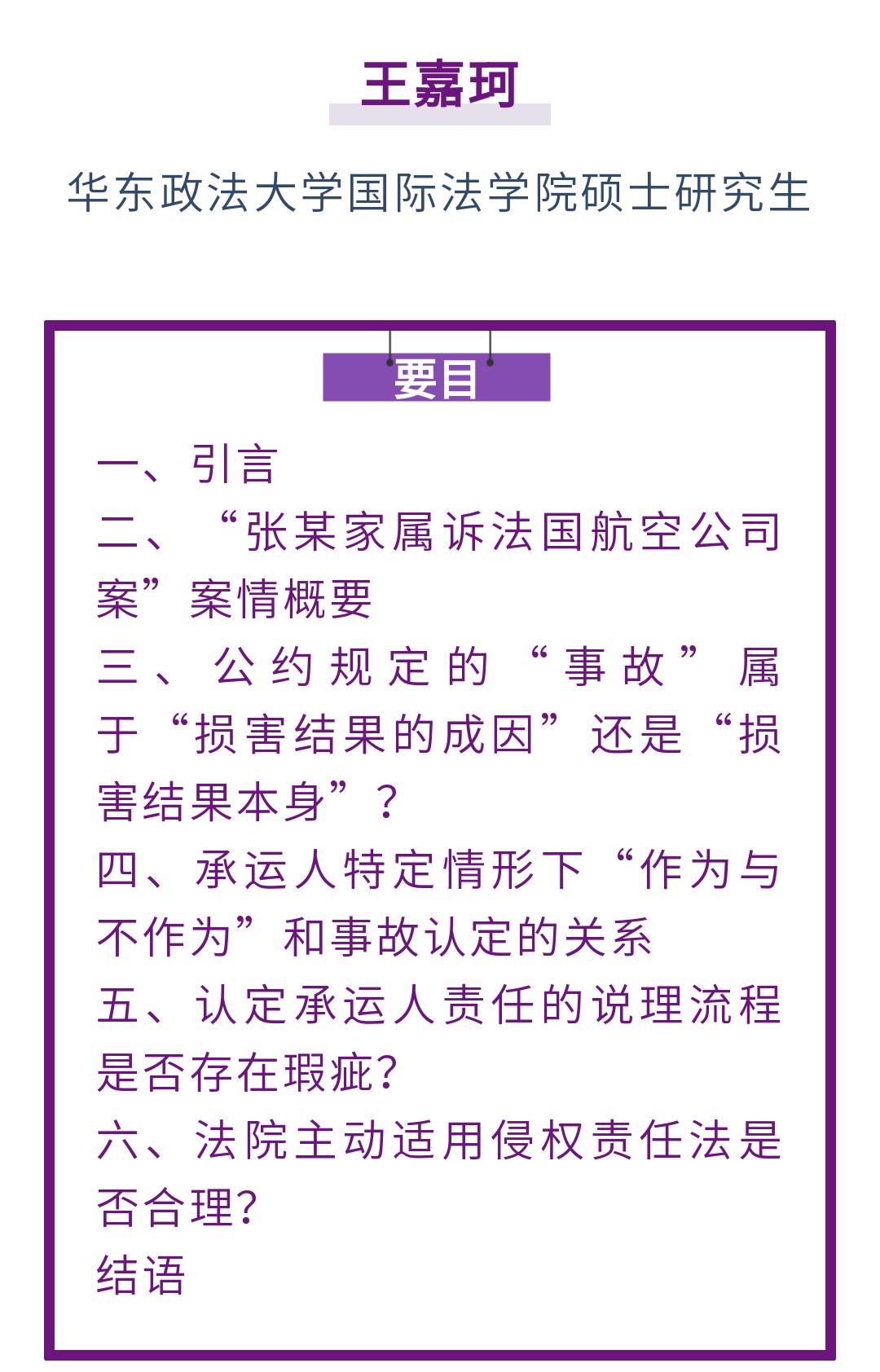
1929年华沙公约和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均未对条约术语“事故”进行定义,故实践中“事故”的含义主要由各国法院予以认定。1985年,美国最高法院将“事故”认定为“意外的、不可预期的、异常的且与旅客自身无关的事件或情势”,已构成事故认定的国际惯例。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法院并未完全接受这一标准。通过分析2015年“张某家属诉法国航空公司案”,指出中国法院在适用蒙特利尔公约审理航空旅客人身损害责任案件过程中,还存在“回避说理”的问题,如未明确“事故”属于“损害结果的成因”还是“损害结果本身”,承运人何种程度的“作为与不作为”构成事故,存在受害人过失情况下如何认定承运人责任,以及法院为何主动适用侵权责任法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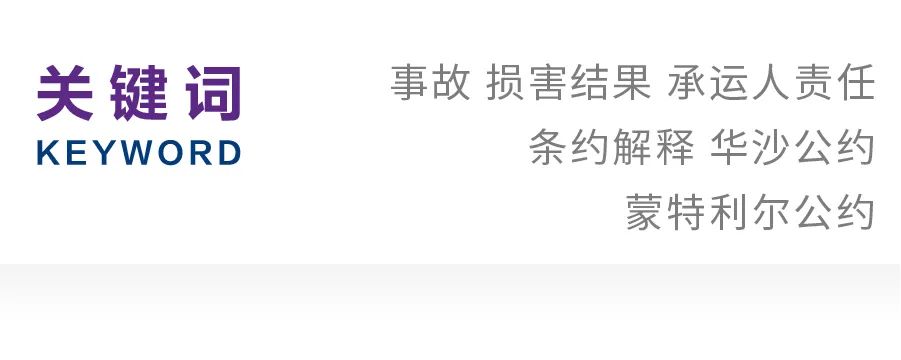
一、引言
为推动早期航空业发展并确保旅客与托运人能够于国际航空运输活动中获得公平赔偿,国际社会于1929年在华沙通过了《关于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简称华沙公约),是航空私法领域制定统一实体法规则的成功范例。然而,随着航空运输业发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的提升,经历了多次修订、补充后形成的“华沙体系”逐渐走向规则的碎片化。1999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通过的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简称蒙特利尔公约)旨在以缔结新条约的方式整合与取代“华沙体系”下的公约文件,以促进承运人责任规则的统一。蒙特利尔公约已于2003年11月4日生效,经批准后于2005年7月31日对中国生效。
“事故”认定是承运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然而华沙公约和蒙特利尔公约均未对“事故”进行定义。因此,通过考察各国法院适用公约的具体情况,有助于明确“事故”的内涵。2015年“张某家属诉法国航空公司案”(以下简称“张某家属诉法航空”)是中国晚近司法实践中的典型案例,但其中对事故的认定与解释仍存在尚未澄清的问题。鉴此,本文首先梳理了“张某家属诉法航空”的案情和双方的主要争议焦点,然后研讨本案“事故”认定涉及的四项主要疑难问题,以期为司法实践中明确承运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界限,平衡承运人与旅客之间的利益提供建议。
二、“张某家属诉法国航空公司案”案情概要
(一)
主要案件事实
旅客张某于2009年4月23日乘法国航空公司(以下简称“法航”)AF883航班自中非共和国首都班吉返回中国,在中非班吉机场登机过程中,张某突发心脏病死亡。被告法航发给家属的书面邮件陈述显示,张某是第一批登机的旅客,他在入座后起身去卫生间,随后突发心脏病倒地,经机上三名医生抢救无效后死亡。家属认为张某的死亡原因没有充足、科学的证据,因而法航得出因病死亡的结论依据不足。家属同时指出,证据中没有法航进行急救情节的任何表述,故法航在推卸责任,因此向法航提出50万元人民币的赔偿请求。法航则援引蒙特利尔公约第17条的规定,指出张某在当日登机时已经存在病症,他的死亡不是由任何“事故”引起,因此拒绝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二)
一审法院裁判要点
关于法航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证据证明张某是在登上AF883航班后死亡的,虽然法航组织了航空器上具有医生职业资格的乘客对张某进行了救治,但法航联系的医生在从到达现场至宣告张某死亡的这40分钟时间内采取了何种措施并没有任何记录,对于张某死亡原因也没有客观准确的结论。因此,依据蒙特利尔公约第17条,法航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赔偿原告43.0352万元人民币。张某家属根据蒙特利尔公约第21条,主张法航在10万特别提款权(SDR)(约110万元人民币)限额内赔偿100万元人民币。法院认为,虽然本案张某家属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所遭受的具体损失数额,但是依据侵权责任法第16条和《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27条的规定,对张某家属要求被告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的请求予以支持。
法航辩称,一审裁判由其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首先,一审法院认定法航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事实理由之一是法航联系的医生在40分钟的时间内“没有作为”导致了张某死亡,但法航认为其已经毫无懈怠地采取了必要措施。法航强调,“事故”的存在是承运人承担责任的前提,张某家属对此应负举证责任,但其并未提交任何能够证明当时发生了事故的证据支持其主张。法航认为张某是因疾病死亡,而疾病事关乘客自身的身体健康状况。乘客因疾病死亡与航空器的运行没有关联,不能归结于意外的、不可预期的、异常的事故。本案中也无任何证据证明发生了这样一种“事故”。其次,即便死亡原因是因“事故”引起,法航根据蒙特利尔公约第20条主张,张某在订票时、登机前均没有请求帮助,法航对张某的身体状况一无所知,故张某存在未向法航告知其身体状况的过失,应全部或部分免除法航的责任。再次,法航主张对张某的救助是基于合同义务,并非基于侵权责任,本案案由不应定为侵权性质的“航空运输人身损害责任纠纷”,而应当认定为“航空旅客运输合同纠纷”。
张某家属不服一审裁判适用国内法确定赔偿数额,并根据蒙特利尔公约第21条第1款,主张在此限额内提出的人身损害赔偿,不承担具体损害的举证责任。张某家属请求二审法院依据公约公约第21条第1款的规定依法改判,以约110万元人民币进行赔偿。
(三)
二审法院裁判要点
二审法院认为,张某在登机过程中死亡,虽经飞机上具有医生资质的乘客对张某进行了救治,但法航联系的医生在到达现场后至张某死亡前这一段时间内,无任何记录证明其采取了救治措施,法航主张其毫无懈怠地采取了必要的措施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根据蒙特利尔公约第17条,被告应承担赔偿责任。针对张某家属提出的约110万元人民币损害赔偿的主张,二审法院并未支持,并认为张某家属未能提供110万元人民币损害数额的证据,支持原审法院依据侵权责任法和《人身损害赔偿解释》计算出的法航应承担的赔偿数额。
(四)
案件中的主要争点
比较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的裁判,法院均以缺乏法航联系的医生从到达后至死亡前对张某进行救治的客观记录为由,要求法航承担赔偿责任,且均未对法航的行为是否构成公约第17条规定的“事故”开展说理。同时,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也都主张依据侵权责任法和《人身损害赔偿解释》计算赔偿数额。通过梳理案件事实以及法院裁判要点可知,该案主要涉及的法律争议体现如下。首先,张某“因自身原因猝死”的情况可否依公约规定认定为“事故”,继而要求承运人承担赔偿责任;其次,张某家属主张在张某发病后40分钟内,法航机组人员的不作为导致张某死亡,该“承运人受雇人的不作为”是否构成公约项下的“事故”;再次,若事故确实存在,法航可否主张张某在整个登机过程中未及时告知身体状况存在过错,进而以共同过失进行抗辩来减轻其责任;最后,在张某家属未能依据蒙特利尔公约提供相应索赔证据时,法院主动适用中国侵权责任法是否合理。
三、公约规定的“事故”属于“损害结果的成因”还是“损害结果本身”?
华沙公约第17条与蒙特利尔公约第17条均规定了承运人对旅客人身伤亡损害所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对于旅客因死亡、受伤或身体上的任何其他伤害而产生的损害,如果造成此种损害的事故是发生在航空器上或上下航空器的任何作业过程中,承运人就应当承担责任。由此可见,两公约均强调,旅客死亡、受伤或身体伤害的损害赔偿责任必须源于“事故”,该事故须发生于航空器上或上下航空器的任何作业过程中。因此,“事故”的认定是承运人对旅客人身伤亡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华沙公约英文文本所载“事故”表述为accident,《布莱克法律词典》将accident解释为“一个无意的、不能预见的、不通常发生或不能被合理预见的损害性事件。该事件不能归因于错误、疏忽大意或不当行为。”而在华沙公约的作准文本法文文本中,“事故”在《拉鲁瑟法文大辞典》中被定义为“偶然发生的、不能预见的、不寻常的对身体或物品造成损害的事件。”
根据条约解释通则,对“事故”理解需要依其用语按其上下文并参照条约之目的及宗旨所具有之通常意义,善意解释之。与规定承运人对旅客伤亡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不同,华沙公约和蒙特利尔公约规定的承运人承担行李灭失与损害责任的前提是“事件”(event or occurrence)的发生。这明显表明公约有意区分“事故”与“事件”这两种原因。尽管公约对“事件”也未作出解释,但一般而言,事件的范围比事故宽泛。任何事故都属于事件,但并非任何事件都构成事故。这意味着与旅客行李灭损所能获得的赔偿相比,公约制定者倾向于为旅客伤亡损害获得赔偿设定更严格的范围,这与华沙公约对承运人的倾斜保护立法理念有关。
由于公约缺少对“事故”的定义,事故的认定就需参考各国法院在司法实践中的解释,因而各国法院在事故认定过程中的裁判理由构成了公约规则的重要补充。美国最高法院对“事故”的认定与解释得到了较多缔约国的认可,可以构成关于事故解释的国际惯例。民用航空法184条第2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因此,笔者援引美国法院关于事故认定的典型案例进行进一步分析。
关于华沙公约第17条项下“事故”的认定,最重要的案例是美国1985年“法航行萨克斯案”(Air France v. Saks,以下简称“萨克斯案”)。该案中,原告萨克斯(Saks)女士在航空器降落过程中感到左耳十分疼痛,最终被医生诊断为左耳永久失聪,故以航空器降落时舱压变化导致其左耳失聪构成华沙公约第17条下的“事故”为由向法院起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萨克斯案”的判决中将事故定义为“意外的、不可预期的、异常的且与旅客自身无关的事件或情势,不包括旅客自身对常见的、正常的、可预料的航空器运行的内在反应。”法院在判决书中强调了以下几点:(1)华沙公约第17条项下的“事故”应结合旅客受伤时周边环境情况予以灵活认定;(2)引起旅客受伤的“事件或情势”(event or happening)必须是意外的、不可预期的;(3)事件必须是与旅客自身无关的情势,而非旅客因自身原因在正常飞行过程中的反应。
在“萨克斯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还指出,损害本身不是事故,原告应证明航空承运人的行为是其遭受损害的近因,应就引起损害发生的原因进行分析。换言之,事故应当是导致旅客受损害的“成因”,而非“损害结果”本身。该标准首次将旅客伤亡这一损害结果与导致旅客伤亡的事故区分开来。区分两者,有利于防止“事故”和“事件”混同,防止过于宽泛认定“事故”,还可以避免出现承运人责任的绝对化倾向。
“萨克斯案”中的事故认定标准随后发展成为美国的法院解释事故的权威标准,众多公约缔约国也在实践中予以适用,例如,美国1993年的“格兹诉英国航空公司案”(Gezzi v. British Airways PLC)、英国2010年的“巴克利诉英国航空公司案”(Barclay v. British Airways PLC)、澳大利亚2009年的“林德航空有限公司诉帕特森案”(Air Lind Pty Ltd. v. Paterson)等都采取了类似的事故认定方式。如今,此定义已经成为判断事故的一项通用标准,并被认为是解释实践对公约的恰当补充。
除此之外,赵维田指出,英国的林德利勋爵曾于1903年表示,“事故这一用语在法律与技术上含义尚无明确定义。一般来说,就其在法定赔偿责任方面,事故是指引起伤害或损害的意外且未予料及的事件。然而,事故也常用以指称任何意外与未料及之损失或伤害本身,而并非指其原因;在引起伤害或损失的原因不明时,其本身肯定会被称作事故。”然而针对公约第17条项下的“事故”,不论从其公约约文措词、立法背景还是法院判决来看,均应将事故理解为特指作为事件或情势发生原因的“事故”,而非事件或情势的发生本身。
根据上述司法实践可知,完全由于旅客身体原因导致损害的情势,不属于事故。按照这种解释,在“张某家属诉法航空”中,张某“因自身原因猝死”的情况不可认定存在“事故”,因此无法要求承运人承担赔偿责任。然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并未完全接受这一认定标准。在“张某家属诉法航空”中,当引起张某死亡的原因不明时,也可能会被中国法院认定为“事故”。当旅客在飞行过程中出现健康问题时,承运人往往需要履行一定的照管义务,防止旅客病情的恶化,若承运人未及时履行该义务导致旅客伤亡,此时该如何理解承运人的行为与事故认定的关系呢?
四、承运人特定情形下“作为与不作为”和事故认定的关系
(一)
承运人不能凭借“与旅客自身因素有关”完全免责
根据目前广泛适用的事故的认定标准,事故必须是由与旅客自身无关的因素所导致。但还有许多国家的司法实践表明,只要某种损害可归因于旅客自身因素,承运人就无需承担责任。例如,在1997年“克里斯诉德国汉莎航空案”(Krys v. Lufthansa German Airline,以下简称“克里斯案”)中,美国第十一巡回上诉法院认为,原告病情恶化的原因为航空器按照航班时刻表飞往既定目的地,而这并非“意外的、不可预期的、异常的且与旅客自身无关的事件”,不构成“事故”。只要导致旅客伤亡的原因为自身健康状况不佳,即使承运人完全消极的不作为,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旅客健康状况恶化,法院也仍认为损害是由旅客自身因素造成,承运人无需承担责任。事实上,该判决完全忽略了承运人对旅客的照管义务。承运人提供的服务是综合的,不是简单地将旅客运送到目的地,而是需要保证以一种安全的方式完成运输。因此,在考虑旅客自身因素问题时,分析在航空旅客运输中承运人的行为对旅客健康状况的影响变得十分重要。承运人不应该变成旅客的保险人,但是承运人也不应该无条件地对旅客因自身健康原因受而到的损害免责。
(二)
承运人的“故意不当作为”导致旅客伤亡构成事故
承运人明知行为可能造成旅客损害而故意采取的行为,或者是基于疏忽大意而故意采取的行为,若符合事故认定的通行标准,则同样构成公约项下的“事故”。例如,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在2004年“普雷斯科德诉AMR公司案”中(Prescod v. AMR,Inc.)认为:(1)承运人的雇员在明知旅客需要随身携带装有应急医用设备的手提行李的情况下,拒绝旅客携带并将其扣留托运,同时反复保证行李不会与旅客分开、不会迟延到达,却发生转运中的行李丢失事件,构成“不可预期的、异常的”且与旅客自身无关的外部事件;(2)承运人的行为是旅客死亡因果关系的一环;(3)旅客之前的身体状况同样是造成其死亡的原因,但这并不影响承运人的责任。因此,承运人拒绝旅客携带装有应急医用设备的随身行李,并对该行李进行扣留与托运的行为同时构成华沙公约项下的“事故”与“故意不当作为”。
(三)
承运人未及时提供协助的行为导致旅客伤亡构成事故
承运人的不作为导致旅客损害的情形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公约项下的“事故”,但任意扩大事故认定的范围会违背两个公约有意限缩“事故”范围的初衷,应明确承运人何种程度的不作为会构成“事故”。承运人的“故意不作为”构成两个公约项下的“事故”。根据美国最高法院2000年对“侯赛因诉奥林匹克航空公司案”(Husain v. Olympic Airways,以下简称“侯赛因案”)的判决,法院援引萨克斯案中对“事故”的定义,认为乘务人员拒绝协助侯赛因(Husain)先生换座位的行为是“不可预期并且异常的”,属于导致旅客死亡的因果关系的一环,因此承运人的行为符合“萨克斯案”中“事故”的定义。法院否定了奥林匹克航空公司关于不作为不能构成公约第17条的“事故”的观点。法院认为,“侯赛因案”中的“故意不作为”与“故意作为”一样足以作为认定故意不当作为的基础。在2000年“兰加迪诺斯诉美国航空公司案”中(Langadinos v. American Airline),原告在排队等候使用卫生间时,遭到一名男性旅客的袭击,于是向乘务人员寻求帮助,但乘务人员没有理会原告的请求,甚至在发现袭击者已经喝醉、行为异常后继续向其提供酒精饮料。法院指出,在普通法上承运人有保护旅客不受可预见损害的义务,当承运人没有履行这种保护义务,对乘客来说将是“不可预期并且异常的”,构成蒙特利尔公约第17条下的“事故”。
承运人未履行“适当”救助措施导致病情恶化的情况构成两大公约项下的“事故”。在2000年“塞古瑞坦诉西北航空公司案”(Seguritan v. Northwest Airlines,Inc.)中,原告诉称乘务员对其突发的心脏病没有提供适当的救助行为,恶化了原告的病情最终导致其死亡,构成公约下的“事故”。法院认为旅客心脏病发作本身并不属于事故,但承运人未提供应有的医疗救助恶化了旅客的病情,则构成了事故。根据“侯赛因案”的判决,“判断承运人拒绝对乘客进行医疗救助的行为是否属于不可预期的、异常的事故,主要是看乘客的健康状况是否因为正常的机舱环境而恶化。”如果在正常飞行过程中旅客突发疾病,虽然承运人有救助的义务,但是只有在承运人实施了不合理的救助措施或者救助过程有疏忽才可以构成公约意义上的“事故”。
需要注意的是,承运人的主要义务是运送旅客到达目的地,不应要求其对所有突发病症都能及时并且有效地提供救助。换言之,并非所有承运人未及时提供救助的行为均构成事故。以下是通常被认为不构成两大公约项下“事故”的典型情形:(1)未能立即将旅客运送至医院;(2)机上缺少足够医疗设备,航班继续飞往目的地,随后旅客心脏病发死亡;(3)机长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符合公司程序和行业惯例的情况下作出不备降决定,导致旅客病情加重;(4)机上发生紧急医疗情况,未能提供充分医疗救助或协助的。
由此可见,承运人故意的作为及不作为在符合事故认定通行标准下构成公约项下的“事故”;承运人未履行“适当”的救助措施,恶化旅客病情的情况下,可能构成公约项下的“事故”。此外,黄力华从同时保护旅客权益和促进航空旅客运输业角度出发,主张对调整关于旅客和承运人的义务分配,将“不可预期”这一判断标准修改为“正常的承运人能否预测”。如果某一承运人能够预见到某行为可能会导致旅客受到损害,而承运人一方又未采取相应预防措施或未向旅客作出相应说明的,则该事件应当构成“事故”。
(四)
中国法院强调承运人的积极协助义务
根据中国的既有判决,中国法院强调承运人在旅客运输中的积极协助、救助义务。若承运人未及时对旅客采取适当救助措施,那么该“事件”就可能被认定法院为“事故”。例如,在2020年“卡某某航空集团与赵某等航空运输人身损害责任纠纷案”中,二审法院指出,机组人员没有第一时间采取紧急措施履行救助义务,承运人对其主张的遭遇气流与颠簸也未能证明,因此该事件属于事故。又如,在2018年“符某、海某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航空旅客运输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中,因海某航空公司在旅客运输过程中履行了合理的注意义务,其索赔人也无证据证明符某死亡与海南航空公司的行为具有关联性,故不属于事故。
综上,在“张某家属诉法航空”中,法航联系的医生在到达至宣告张某死亡的这40分钟内,采取了何种措施并没有任何记录,对于张某死亡的原因也没有客观准确的结论,即证据不足以显示法航已经充分履行其救助旅客的义务,则其未及时提供适当救助的行为对于张某来说是属于“意外的、不可预期的、异常的”,因而法航的受雇人未积极履行救助义务的行为可以被认定“事故”。但中国法院在强调承运人对旅客的积极协助、救助义务的同时,也应当注意救助义务有其合理的标准与边界。承运人不具有专业性医学知识,不能要求承运人提供如专业医院那样设施齐全、技术先进的医疗救助服务。承运人无法对所有的急发病症提供及时有效的救助,切忌对其设定过重的义务,迫使承运人会通过限制乘客年龄、挑选健康旅客等方式来降低其运输风险。
五、认定承运人责任的说理流程是否存在瑕疵?
(一)
公约项下认定承运人责任的一般说理流程
法院要根据索赔人的举证来认定是否发生了蒙特利尔公约第17条项下的“事故”,“事故”是否造成了“身体伤害”或者“死亡”,“事故”发生在“航空器上”或者在“上、下航空器的任何操作过程中”,以及索赔人是否因此遭受了损害。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原则,索赔人的举证责任在于证明符合公约17条规定的引起身体伤害或死亡的“事故”以及由此所致的损害数额。已证明损害中12.8821万特别提款权(约119万元人民币)以下的部分,承运人应承担严格责任,除非其证明损害完全或部分地由旅客或通过旅客进行索赔的人的过失或者其他不当作为或不作为所致;12.8821万特别提款权以上的部分,承运人证明有以下情形的,不应当承担责任:(1)损害不是由于承运人或者其受雇人、代理人的过失或者其他不当作为、不作为造成的;或者(2)损害完全是由第三人的过错或者其他不当作为、不作为造成的。
在“张某家属诉法航空”中,法航主张一审裁判由其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第一,依据公约要求承运人承担责任前提是索赔人张某家属应有证据表明航空器上发生了某件“事故”导致张某死亡;第二,就算存在事故,法航可依据蒙特利尔公约第20条,主张损害是由受害人过失所造成从而减轻或者免除责任。法院应根据索赔人张某家属的举证对是否存在一个“事故”进行回应,张某“因自身原因猝死”以及法航的机组人员未及时履行救助措施导致张某死亡的事件是否构成公约项下的“事故”。除此之外,若法院认定“事故”存在,其应根据法航的举证来认定受害人张某未及时将身体状况告知法航的行为是否符合公约项下承运人法定免责事由,进而裁判法航是否能够因此予以减轻或免除责任。然而法院在裁判中均未正面回应以上两项主张。可见,在“张某家属诉法航空”中,承运人责任认定的说理步骤是存在瑕疵的。
(二)
公约项下承运人免责事由中的受害人过失
商用航空器事故的历史表明,在事故引发旅客受伤或死亡时,承运人或其受雇人、代理人完全没有导致或者部分导致事故的“过失或其他不当作为或不作为”的情形是极少的。问题在于,假设旅客知道或应当知道其身体状况不适宜搭乘航空器,承运人是否可以基于此提出共同过失的抗辩。如果存在共同过失,法院则可以在旅客的过失范围内免除承运人责任。在前述“侯赛因案”中,法院认为侯赛因先生没有为自己寻找一个远离吸烟区的座位,对其后因对烟雾过敏而哮喘发作死亡有共同过失。蒙特利尔公约在国际航空旅客运输中采用双梯度责任制度,区别于华沙公约采用的推定过错原则,在12.8821万特别提款权以下,承运人承担严格责任,无法援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或“不可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免责抗辩事由。但蒙特利尔公约于承运人免责事由上保留了“受害人过失”一项,即公约第20条。因此,在双梯度责任制度下,承运人仍可基于旅客过失免责抗辩。
在“张某家属诉法航空”中,法航抗辩称张某在订票时、登机前均没有请求帮助,因此对张某的状况一无所知。法航认为张某未及时将身体状况告知法航的行为,符合蒙特利尔公约第20条。因此,即使其死亡是由“事故”所引起的,法航也不对张某死亡承担责任,更何况本案中就没有发生任何事故。对此,法院的说理过程首先应当认定是否存在一个导致张某死亡的“事故”,据此来判断是否要求法航对张某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以及根据索赔人张某家属对所受损害的举证来确定承运人赔偿数额。之后法院宜根据承运人对法定免责事由的举证,来认定是否存在受害人过失。若法航能够证明存在受害人过失,则应按照双方共同过失的程度来判定承运人应承担的赔偿责任,而不是简单以“张某的死亡原因没有客观准确的结论”要求承运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六、法院主动适用侵权责任法是否合理?
根据蒙特利尔公约的强制性和排他性,在公约缔约国内,就公约适用范围内事项,公约优先于缔约国国内法的适用。我国民用航空法第184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都明确了国际民用航空条约在中国的优先适用地位。根据蒙特利尔公约第29条,在旅客、行李和货物运输中,有关损害赔偿的诉讼,不论其根据如何,是根据本公约、根据合同、根据侵权,还是根据其他任何理由,只能依照本公约规定的条件和责任限额提起。“无论其根据如何”表明了蒙特利尔公约适用的排他性,即凡属于旅客、行李和货物运输中有关损害赔偿,无论是基于合同、侵权还是其他理由提出索赔,均只能适用公约,从而排除了另外适用国内法规则的可能。由此可见,索赔依据不影响公约规则的统一适用。换言之,不论索赔人基于合同之债还是侵权之债起诉,最终关于赔偿的归责原则、免责事由以及责任限额等问题都由公约统一调整。因此,在“张某家属诉法航空”中,法航主张的案件由应由侵权部分的“航空运输人身损害责任纠纷”调整为“航空旅客运输合同纠纷”并不影响蒙特利尔公约的统一适用。
在张某家属未能提供相应证据支持其要求的约110万元人民币的赔偿额时,法院主动适用中国侵权责任法和《人身损害赔偿解释》来计算赔偿数额并未违反蒙特利尔公约适用的强制性和排他性。实践中很多人对承运人承担第一梯度责任仍存在一些误解,认为只要发生航空事故,旅客就自动获得第一梯度的赔偿数额。然而,公约只是规定了双梯度责任制度,但对旅客具体能够获得的赔偿数额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必须根据有关国内法予以计算。于中国旅客而言,计算赔偿数额时必须参考侵权责任法与《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的规定,只有当赔偿数额超过第一梯度的限额时,才应考虑是否应当承担超过限额部分的赔偿问题。“张某家属诉法航空”中,索赔人张某家属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具体损害额度。换言之,其证明的索赔数额并未超过蒙特利尔公约规定的第一梯度的限额,对于张某家属能够获得的具体赔偿数额需要法院根据国内法予以确定。因此,法院在认定索赔人张某家属主张的约110万元人民币索赔的请求时,因其未能依据公约提供相应证据而主动适用了中国侵权责任法第16条与中国《人身损害赔偿解释》来计算承运人的赔偿数额是合理的。
结语
华沙公约和蒙特利尔公约均未对条约术语“事故”进行定义,故实践中“事故”的含义由各国法院予以认定。一般认为,“事故”宜解释为“损害结果的成因”而非“损害结果本身”。在特定情况下,当飞行途中旅客出现健康问题,承运人故意不当作为以及未及时采取“适当”救助措施导致旅客伤亡,承运人的行为可能会法院被认定为公约项下的“事故”,继而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在中国,若承运人未积极履行救助义务导致旅客伤亡,该行为会可能被法院认定为“事故”。2015年“张某家属诉法航空”在“事故”认定方面值得商榷,宜考虑完全由于旅客身体原因导致其损害的情势,不可依公约规定认定存在“事故”。承运人的受雇人未积极履行救助义务导致旅客死亡的情势,可依公约认定存在“事故”,但也应注意承运人的救助义务有其合理边界。“事故”的存在是承运人赔偿责任承担的前提,法院应合理把控承运人赔偿责任的认定流程,首先应是索赔人证明存在引起其身体伤亡的“事故”以及由此所致的损害数额。若“事故”确实存在,法院宜根据承运人对法定免责事由的举证,来认定是否存在受害人过失,尤其是当旅客知道或应当知道其身体状况不适宜搭乘航空器仍搭乘航空器的情况。若承运人能够证明存在受害人过失,法院宜按照双方共同过失的程度来判定承运人应承担的赔偿责任。由于“事故”一词未被赋予明确的定义,在平衡旅客与承运人的利益的前提下,法院审理过程当中应对“事故”的认定及相关规则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这不仅有利于在实践中完善和发展“事故”认定解释实践,明确承运人责任的界限,亦有助于提高司法审判的说服力与影响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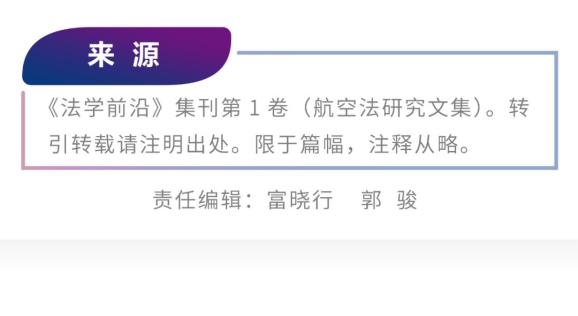
原标题:《王嘉珂|从中国新近案例看航空旅客运输中“事故”的认定——以2015年“张某家属诉法国航空公司案”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