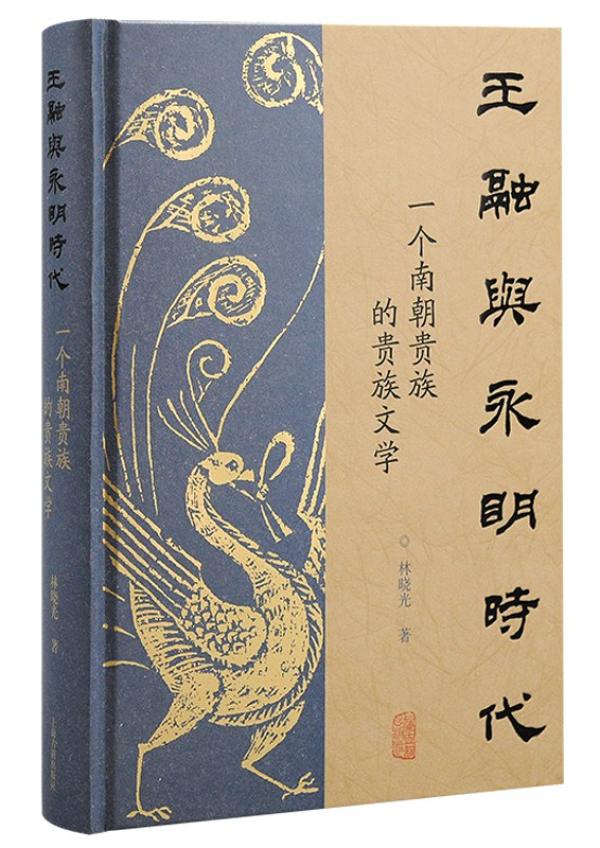本篇所塑造的王融像是否符合历史真实,自当敬候读者批判,但至少这一王融像,在学术史上从未被塑造出来过,则为我所自信。而为总结起见,则自不可不先对历代史家所观察评判之王融形象作一梳理。
首先,作为同时代友人的追忆,有沈约《怀旧》九首的第一首《伤王融》:
元长秉奇调,弱冠慕前踪。眷言怀祖武,一篑望成峰。涂艰行易跌,命舛志难逢。折风落迅羽,流恨满青松。(《文苑英华》卷三一,第1534页)
对王融评价的点很是集中,一是弱冠有奇才,追慕祖先功业,志向高远;一是命途不济,功败垂成。不过,此作是富于感情色彩的追怀之作,或未可视为史笔。相比之下,萧子显《南齐书》本传史臣论:
晋世迁宅江表,人无北归之计,英霸作辅,芟定中原,弥见金德之不竞也。元嘉再略河南,师旅倾覆,自此以来,攻伐寝议。虽有战争,事存保境。王融生遇永明,军国宁息,以文敏才华,不足进取,经略心旨,殷勤表奏。若使宫车未晏,有事边关,融之报效,或不易限。夫经国体远,许久为难,而立功立事,信居物右。其贾谊、终军之流亚乎!(《南齐书》,第82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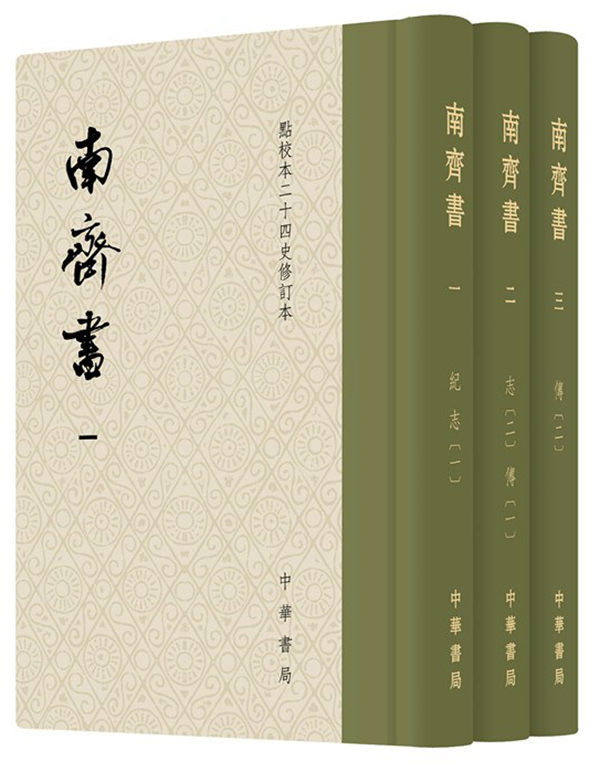 《南齐书》
《南齐书》
则称得上是对王融最早的一次“盖棺论定”。所述当然比沈约的诗性语言要冷静全面得多,但评价指向却并无二致,都在于对其志向不遂的惋惜。不过,沈、萧所注目的王融之志则有所不同,沈约所叹息的“一篑望成峰”无疑是指拥立竟陵政变,换言之,维护修复贵族政治之志;而萧子显所重视的则是北伐收复之志。这种区别的原因,也许因为沈约本人是政变的经历者,时代记忆至为惨痛;而对于下一世代的萧子显而言,政变就只是一种历史档案而已,反不如殷勤北伐这一点来得鲜明了。(萧子显生于永明七年[489],政变时只有五岁。)萧子显的评语颇有值得玩味之处。王融屡屡上表求北伐,在熟悉了后世主战论的今人眼中看来,毫不稀奇;然而萧子显却是将其置于“人无北归之计”,“虽有战争,事存保境”的时代环境下看待的。东晋落难,南渡建国;刘裕北伐,功成而旋败;元嘉北伐则大败亏输。这三类历史记忆各有不同,色彩却一次比一次黯淡,导致南朝政坛对于收复中原再无兴趣。在这种历史环境下,王融的“殷勤表奏”其实是一种特立独行的表现。而萧子显在王融传中三录其所上之疏,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此其一。其二,这里指出了王融命运中的一个关键,就是个人命运与时代命运的差错。所谓“生遇永明,军国宁息”。和平繁盛的永明时代,对于期待重振家声的王融来说,是显得太安静,太无聊了,缺少兴风作浪的契机。萧子显已经看到了王融的北伐要求是存有自己谋求进取的私心,并非出于“民族大义”——然而他对王融的评价却依然是相当正面的。将自我价值的实现置于一切价值之上(也许只有家族荣誉能与此相埒),正是中世贵族时代的强烈特征。而从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具有“六朝性”的并非仅仅是史书中记载的人物事迹,同时也包括了在那个时代中对历史进行记载者的记录视角和评价尺度。
有趣的是,王融、谢朓同传,萧子显的史论却单为王融而发,全然不及谢朓,显示出二人在其心目中的分量不同。这也许是由于谢朓在政治上的表现乏善可陈?和沈约的史论不一样,萧子显显然更偏向政治方面的评价。尽管无法断定王融的行动是否确实能够拯救萧齐王朝的衰亡,但其失败却无疑直接导致了齐末的大混乱,这对作为皇族子孙的萧子显来说自当深有感触。曹道衡、沈玉成先生认为:“子显之称王融,疑自伤家世之祸,故颂之不遗余力。”(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学史料丛考》“《南齐书·王融传论》”条)这是颇有道理的。
此外,萧子显将王融与贾谊、终军相比,这一评价是否恰当?也是个问题。周一良先生曾批评萧子显“未免过高估计王融之经世才能”,曹道衡、沈玉成先生又从而引申此说。(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王融谢朓同传”条;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学史料丛考》“《南齐书·王融传论》”条)然而萧子显对王融的评价,是建立在“宫车未晏,有事边关”的时代假设上的,武帝既崩,北伐成空,王融的壮志再也没有实现的一天,萧子显是否高估了他的经世才能?谁也不知道。在无从对证的问题上纠缠,论证出来的充其量不过是论者基于自己立场所猜测的可能性罢了。但是,王融生于疲弱不振的南朝,诚所谓“时代所压,不能高古”(米芾评怀素书语),汉初雄朝始创,百废待兴,贾谊乘此时势,逞其天才,遂能定四百年天下制度。要将王融与之相提并论,本就是缺乏可能性的事情。不必说王融,遍数五朝人,又有谁能与贾谊匹敌?萧子显原文其实是很清楚的,所谓“贾谊、终军之流亚”,着眼点本不在将王融本人的功业与贾谊、终军相提并论,而是从人物类型的角度给予归属,将其列于贾谊、终军系谱的末裔。这种说法本身,却是毫无问题的。这一系谱人物的共通特征,就是有志于担当朝廷政制,以军国立功,而不甘于文士终老。毋宁说,这一点在作为南朝当代人的萧子显眼中,才是王融最为特殊的闪光点。
无论如何,在南朝史家的眼中,作为政治人物的王融无疑是一个正面形象。他的缺点在于“功败垂成”,而并非“倒行逆施”。换言之,齐梁时代的王融,是一个“失败的英雄”形象。这一点,与政变当时各种记载中透露的舆论也是一致的。在时人眼中,王融也许能力不足,但他的行动本身却不应被指责。而这种形象随着时代的远去,就越来越趋于淡漠。在自南入北的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文章篇》中,王融的形象开始发生变异:
自古文人,多陷轻薄……王元长凶贼自诒,谢玄晖悔慢见及。(《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第237、238页)
这条线延伸下去,到了六朝与隋唐交错的点上,在王通《中说》卷三《事君篇》里,对王融的评价方向就完全改变了:
谢庄、王融,古之纤人也,其文碎。(王通《文中子中说》,《四部丛刊三编》本)
值得注意的是颜、王两种记载都有一个共同语境,就是“古往今来文人皆不足道”,他们是将王融置于历数古今文学之士缺陷的系谱中进行批判的。王通也是像颜之推一样,将古往今来的文人骂了个遍,各有不同的恶谥;唯独对颜延之、王俭、任昉大加赞美,称之为君子。这与其说是对王融个人的否定,不如说是对整个不符合儒家政治伦理和社会道德的六朝世风的否定。脱离了具体时代空气以后,抽象的“温柔敦厚”、“忠君事亲”伦理逐渐占据了批判者的视野,历史就在这样的过程中发生了转变。第三章中引用过的刘知幾《史通》对史书所记王融外交表现无足轻重的批判,也不妨纳入这一系谱当中理解。
因此,在这一时期对王融的否定,还不足以说是他本人形象的真正反面化。不过到了北宋,王融的反面形象就被定型了,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九《齐纪五》:
臣光曰:孔子称“鄙夫不可与事君,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王融乘危侥幸,谋易嗣君。子良当时贤王,虽素以忠慎自居,不免忧死。迹其所以然,正由融速求富贵而已。轻躁之士,乌可近哉!(《资治通鉴》,第4353页)
司马光所论,似完全依据《南齐书》文字所记,认为永明十一年政变是王融一手造成,萧子良只是单纯的受害者。这一立场与今天学界的基本判断相去甚远。但是,对司马光而言,这恐怕无足轻重。从儒家的圣人之道来看,作为政变作乱者,王融的反面性质在这一基本点上已经被定性了,并不需要问什么具体理由。(同样是北宋人的胡寅《致堂读史管见》驳司马光此论曰:“武皇不豫,融欲矫诏立子良,而子良不知。戎服绛衫,断东宫仗,而子良不知。上殂,融以子良兵禁诸门,而子良又不知。诚不知邪?是不智也。佯不知邪?是不忠也。危疑之际,间不容穟,而一听融诪张为幻,略无可否,至于迹涉疑似,恐惧而殒,乃自取之,安得独罪融哉?”[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宛委别藏》本,第749页]其意见与现代学界颇有相通之处。但具体到对王融的批判则与司马光一致,只是为其增加了一名共犯而已。而在另一处,他更严厉地批判王融“三十内望为公辅”违背圣人之教:“富贵人之所欲,然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故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圣人不以富贵为荣,而以道义为重……如王融辈胸中无物,则八驺是营,反而求之,于我何有?”[第747页]与六朝人的观念相比,这些言论无疑是我们更容易理解和接受的;虽然在真实的生活中,大多数人和王融一样地“八驺是营”。)或许正是由于司马光的巨大影响,王融在那以后就很少得到正面评价,甚至渐渐沉到历史深处去了。——或者应该说,永明十一年政变甚至整个永明时代,都在不断膨胀的历史中比重缩水了。在黯淡的背景之前,只有少数几个标志被凸显出来,而王融是不在其中的。
不过,与作为政治人物的王融相比,作为文学家的他总算还借着“竟陵八友”的名头保留了一张交椅。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之《王宁朔集》题辞:
齐世祖禊饮芳林,使王元长为曲水诗序,有名当世……其焜耀一时,亦有繇也……而伧楚入幕,戎服灾身。兰室栴崖,岂宜若是?夫南齐王业,太孙坏之;孝武多男,西昌贼之。设元长志遂,竟陵当阳,萧氏福祚可世世也。谋败狱死,天即恶槌车之躁,其不祐齐则久矣。但见王郎年未三十,心热公辅,并笑其断仗一举,偾取瓦裂,犹然成败之见乎!……夫穰侯相印,不可遽得,终子云、贾长沙之才则自我有也,又曷不少从容引分,资成不朽哉!(殷孟伦《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第193页。按《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凡与张燮《七十二家集》重出者,皆直接抄自《七十二家集》,然而张燮之名往往为其所掩,从文献价值而言其实颇不公平。唯有张溥为各集所撰的题辞,确实是汉魏六朝文学批评中极有见地的重要文献。)
可以看到,张溥的意见又再一次跳过唐宋,回接了南朝。对王融才华的赞赏和惋惜,对南齐政权命运多舛的感叹,都与沈约如出一辙;而“终子云、贾长沙之才则自我有”的评价,则正是出自萧子显所谓“贾谊、终军之流亚”。对汉魏六朝造诣湛深的张溥会对六朝人的意见更加敏感,也是顺理成章的。其所嘲笑的“成败之见”虽然未指名道姓,其批评对象即为宋人一路议论,殆可无疑。而王夫之的意见就大不一样了,《读通鉴论》卷十六齐明帝条论谢朓曰:
夫朓直未闻君子之教,立身于寡过之地而已,非怀情叵测、陷人以自陷之佥人也,而卒以不令而死。……荣不得而加,辱不得而至,福不得而及,祸不得而延,庶其免夫!朓之不能及此也,名败而身随之,宜矣。虽然,又岂若范晔、王融、祖珽与魏收之狂悖猥鄙乎?谚曰:“文人无行。”未概可以加朓也。(王夫之《读通鉴论》,中华书局1975年,第472页)
王融虽然没有得到专论的资格,却荣幸地作为谢朓的反面陪衬登了场,获得了“狂悖猥鄙”的历史最差恶评。从王夫之所举诸例来看,都是在个人品德上属于飞扬跳脱一类,有违温柔敦厚的忠恕君子之道的人物:范晔自怨不得国婚,图谋造反;魏收轻薄无行,以作史资格欺人;祖珽豪纵淫逸,常云“丈夫一生不负身”。(《北史》卷四十七《祖珽传》,第1737页。然而史书多载魏收、祖珽薄德无行事,如魏收贿史、使南时遍奸婢女;祖珽偷盗、赃污、与寡妇通奸等;范晔也曾因国丧期间违礼纵乐而获谴,自奉奢侈而事母甚薄。王融却绝无这类可以指实的犯法败德之行。)这三人与王融的共同特征,是均为狂狷自大,自以为能够压倒天下人的名士。换言之,他们的悲剧有着“自作自受”的性质。而与之相较,谢朓虽然出卖岳父王敬则,向来被评价为人品不佳,但谢朓性格柔弱,其行为属于无法承受时代压力而导致的悲剧,在王夫之看来就较为可以原谅了。因此王夫之的人物论,归根到底与司马光是属于同一方向的: 王融的“轻躁”是其人品败坏的关键点。而这一点,在六朝史论中却完全无关紧要。从这种反差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对自我才华和独特性(无论其在道德上是好是坏)的高度意识,放在六朝的大环境下是并不那么特别的一种表现,甚至毋宁说是精英主义的贵族风的一种典型性质;而近世以后,随着向民本主义的儒家伦理的回归,这种贵族风也就越来越变得令人嫌恶,凸显为王融受批判的主要原因了。
以上总结了历代史家对王融的评判。随着历史变迁而变迁的王融像,既是从正面逐渐转向反面,也是从清晰逐渐沉入模糊。而本书所完成的王融像,则如前几章所考论,并不打算在对其的评价上作出什么辩论,而是希望从历史合理性中给予符合因果关系的塑造,从时代与个人命运的交织中透视其生命形态之由来。
南朝贵族社会,是一个由士庶天隔规定了的重层构造。这种构造并不是无可奈何、不得不被动地无意识接受的现实,而是当时每个人都清晰地意识到,并且各自在其中占据一定位置的体制。时人或者安居于其中,希望永久维持这种现实;或者不安于本位,希望促进社会潜流的涌动,冲破这种既成的秩序。在个体与个体的协作及对抗中,辐射出的能量如同浪潮此起彼伏。由理念与体制所筑成的堤坝反复抵御着浪潮的冲击,也一次次地被毁坏重建。王融的一生,就在这样的构造与反构造中被塑造定型。琅邪王氏的最高贵门第,以及祖父的悲剧,使他的生命从一开始就具备宿命论般的色彩。在被排出了都城贵族圈之后,王融的命运出现了歧路。他或者甘于沉沦无为,在地方上终老一生;或者追怀着昔日的光荣而振起。面对着歧路,个体能量开始突破既存的秩序。母亲的教育使他获得了完整的贵族素养与知识结构,借着家族的余光,更凭着个人的才华,他踏上一条并不那么完美的道路,最终回归到体制内部。经历过拼搏奋起的他,性格中不可避免地呈现出锋芒毕露、桀骜自负的特征。家族荣誉的失而复得更强化了他对于贵族文化的维护爱惜之情。这种才华与性格使他得到了时代的热烈承认,也增长了他对自身能量的信心。而这又决定了他在最后捍卫体制的行动中的勇于自任,最终一步步走向毁灭。
王融的一生,有着极其典型的南朝贵族性的侧面。他门第高贵,才华出众,依据着贵族官僚体系出身升进,成为贵族文化的代表人物,并最终在维护贵族政治的斗争中殒身。但与此同时,也有着由于个人际遇而带来的非典型性。急于功名、越级晋升,不肯“随流平进”,是由于其家门中落;积极筹策伐边,则是基于其少年时的边缘人经验。他一生的剪影,正是被时代潮流拥卷吞裹,同时也以他个人的行动影响改变了时代的、真实的一幅南朝贵族像。
本文选摘自《王融与永明时代——一个南朝贵族的贵族文学》,林晓光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8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