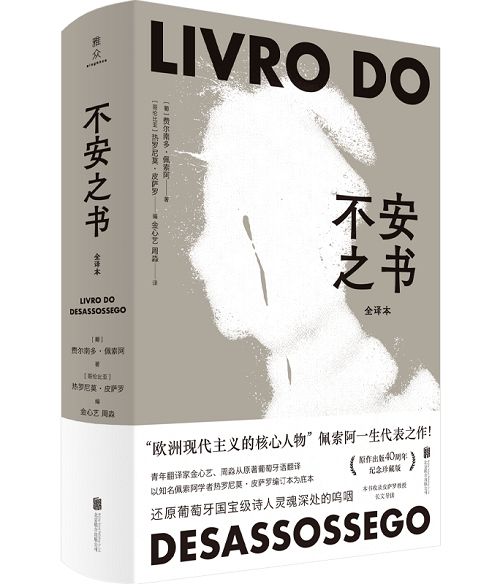【编者按】
《不安之书》是葡萄牙国宝级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用二十余年以不同异名创作的百余篇日记体散文随笔,由后人收集编纂而成的一本奇书。最早曾由作家韩少功于20世纪90年代从英语译为中文,书名叫《惶然录》。
本次出版的《不安之书》以著名佩索阿学者热罗尼莫·皮萨罗的编订本为底本,从葡萄牙语全文译出,还原了佩索阿创作的阶段性特征和这位文学巨匠的人生心路历程,写出了现代人内心的种种感受,展现了人性的孤独和决绝之美,以动人的诗意和哲理引起我们的共鸣。本文摘编自热罗尼莫·皮萨罗为该书所作的导读,澎湃新闻经雅众文化授权发布。
在以“旋涡,旋风,在生活流动的肤浅中!”(第246篇)开头的篇章里,一个由池塘、河流和小溪组成的“水之意象”在我们面前构建起来,这个意象的出发点,是视野中的人群,他们“在(里斯本)市中心的大广场上”穿行,像“多彩而庄重的水”一样。对叙述者而言,这个由人群组成的“水之意象”在“大广场”流淌着——他还补充道,“因为我想到快要下雨了”——与“这一不确定的来来往往”巧妙契合,也就是说,与生活如水流和回流的感受相契合。复数形式的“来来往往”?是的,对此他这样解释:
在写最后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它准确地说出了它所定义的东西,我想也许有必要在我的书出版时,在“勘误”下面加一栏“非误”,然后写上:“这一不确定的来来往往”,第几页,的确如此,形容词单数搭配名词复数。(第246篇)
佩索阿终究没有写下这些“非误”,但是,如果他真的写出来,我们会更容易明白《不安之书》究竟是怎样充满这些能够引起陌生感的语句——并不仅仅因为语法上的搭配——同时也能明白,《不安之书》是如何得益于作者的语言意识,从而形成富有音乐性和梦幻感的散文风格的。在本文中,我并不想证明《不安之书》的伟大在于它有一定数量的、不那么正统的语句,也不想证明这些语句必然提升了某些篇章的价值(正如若热·德·塞纳所说,“有些篇章是最优美也最有穿透力的葡萄牙语散文”)。我想说的是:“非误”计划表明了本书语言的一种高深意义;《不安之书》的散文值得研究,因为是它定义了这部作品,并彰显出作者的特色。福楼拜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佩索阿则通过(或不通过)半异名作者贝尓纳多·索阿雷斯宣称:“很大程度上,我就是我写的这篇散文。”(第322篇)此外,任何对《不安之书》文本的反思(越来越以创作计划和“非误”概念为引导)都包含对该书的编订工作进行审视,因为很多时候,编订者除了确定文本,还会修改原文。
在写下“这一不确定的来来往往”的同一天(1930年4月25日),佩索阿还创作了另一段文字,其颠覆程度不亚于前者:
广场东边比另一边有更多的外地人。好像铺着地毯的闸门,那些波浪状的门向上降下,不知为什么,正是这样的一句话向我传达了那个声音。也许因为门降下的时候才更能发出那个声音,但是此刻它们正在上升。一切都是可以解释的。(第246篇)
可以注意到,那些门(窗?)不但反逻辑地向高处降下(佩索阿还用铅笔加了一条注释:“也许因为门降下的时候才更能发出那个声音”),而且是“波浪状的”(onduladas),一个出人意料的形容词,和“铺着地毯的”(alcatifadas)一样,两者还押韵。《不安之书》的语句寻求贴合并传达多重感受,常用一种有韵律的散文来表达,与诗歌建立了明显的一致性。让我们在同时代的一段笔记中(1930年3月23日前后)回顾《不安之书》的诗艺:“把马拉美的感性放在维埃拉的风格中;在贺拉斯的躯体中像魏尔伦一样做梦;在月光下成为荷马。”(第230篇)也可参见《不安之书》五篇中的第一篇,“贝尔纳多·索阿雷斯著”,由佩索阿于1931年发表在《发现》杂志上,开头如下:
作为艺术形式,比起韵文,我更偏爱散文,理由有两个。其一是个人原因,我没有选择,我无法用韵文写作;其二则是放之四海皆准,而且我完全相信,这不是前一个理由的影子或伪装,所以我有必要将它拆解,因为它触及艺术全部价值的深层意义。
我把韵文看作一种中间性的东西,一种音乐向散文的过渡。和音乐一样,韵文受到韵律法则的限制,即使不是规律韵文那生硬的法则,也仍有着类似谨慎、强制、压迫和惩罚的自动装置。在散文中,我们自由说话。我们可以添进音乐节奏,但还能思考。可以添进诗性节奏,但还能处于它们之外。一个偶然的韵文节奏不会阻碍散文;一个偶然的散文节奏则会将韵文绊倒。
在散文中囊括着整个艺术——一方面因为在言语中包含整个世界,一方面因为自由的言语包含说出和思考这个世界的全部可能。(第331篇)
异名作者里卡多·雷耶斯和阿尔瓦罗·德·坎波斯在其他文字中延续了这场争论,佩索阿生前未曾发表这些文字,他去世之后,它们才在《私密笔记和自我阐释》(1966年)和《有待认识的佩索阿》(1990年)中得以发表。我不参与这场被《不安之书》扩展并复杂化的争论,但我想强调的是,对佩索阿/索阿雷斯来说,散文是获得自由的化身:“在散文中,我们自由说话”;“自由的言语包含说出和思考这个世界的全部可能”。这种自由,不管真实或是表面,都是《不安之书》试图要推向极致的。在与上述引文同年代的一个文本中,作者尖锐地回应了“没有人读我写的东西,那又怎样?”这个问题,他说:“我写我自己,是为了从生活中散心”,其中,“我写我自己”(escrevo-me)用的是动词“写”(escrever)不寻常的反身形式。而他怎样写作?在怎样的散文中散心?
佩索阿以一贯的清醒认识到,一个作者的创作部分地取决于一种心理特征和风格的创造——就像后来福柯理论化的那样。
如果我们从语言学的角度审视《不安之书》,它就是一部前所未有的“创作中的作品”(work in progress),类似詹姆斯·乔伊斯那些最伟大的作品。在现代主义著作的“勘误”下面,存在着多少个“非误”呢?
在用打字机写下“这一不确定的来来往往”的同一天(1930年4月25日),佩索阿为他的散文,即本书作者的散文,留下了一段深思。此处作部分摘录:
今天,在感受的间隔,我对我使用的散文形式进行了深思。事实上,我是怎么写作的?[……]
下午我分析自己,发现我的风格系统有两个原则作为支撑,于是我立即以正宗优秀古典作家的样子,将这两个原则定为我整个风格的总体性基础:完全准确地以感受到的东西来描写感受——如果感受是清晰的,就清晰地写;如果是隐晦的,就隐晦地写;如果是混乱的,就混乱地写;理解语法是一种工具,而非法律。
假设我们面前有一个男子气的姑娘。一个普通人会这样说她:“那姑娘像个小伙子。”另一个普通人,离意识到说话即是表述要近那么一些,会说:“那姑娘是个小伙子。”再来一个,同样意识到何为表达的义务,但又更倾心于准确性(这可是思想的放荡),会说:“那小伙子。”而我则会说 “她那小伙子”,打破语法规则中最基础的那条,即名词和形容词性单词的性数必须一致。[……]
语法上的分类虽然是正当的,但也是虚假的。比如,它把动词分为及物和不及物;然而,懂得表述的人,很多时候需要把及物动词转化成不及物动词,才能将他所感受到的东西拍照下来,而不是像普通的人形动物,只会在暗处张望。如果我想说我存在,我会说“我是”。如果我想说我是以单个的灵魂存在,我会说“我是我”。但如果我想说我是以指向自身、塑造自我的个体而存在,与自身一道,行使自我创造的神圣职责,我怎能不立刻将动词“是”转化成及物动词呢?这样一来,我将以胜利的、反语法的姿态,至高无上地说出:“我是着自己。”(Sou-me)仅凭两个小词,我可不就说出了整个哲学。这难道不比连说四十多句废话要好很多吗?还能对哲学和语言表达提出比这更苛刻的要求吗?
让不懂得如何思考所感的人去遵循语法吧。[……](第247篇)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佩索阿很早就设定了这两个原则。第一,“完全准确地以感受到的东西来描写感受”,这也是他在《颓废文学》(1909年前后)一文中提出的观点之一,该文的副标题为“关于马克斯·诺道[《退化》]一书的笔记”,文中写道:“正如埃德加[·爱伦]·坡指出和践行的那样,有必要区分隐晦的表达和表达的隐晦。为隐晦的事物提供清晰的表达是一种艺术,不是将事物本身变得明白,而是将事物的隐晦性变得明白。”第二,“理解语法是一种工具,而非法律”,这是在未来主义宣言中被强化的一条原则,也是葡萄牙现代主义第一阶段(1909—1915)的精神,虽然佩索阿在《不安之书》中从“沼泽主义”和其他现代主义文本风格演变成办公室小职员的晚期散文风格,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阿米耶尔和马拉美,塞萨里奥·韦尔德和卡米洛·庇山耶,荷马或贺拉斯,以及安东尼奥·维埃拉神父(“葡萄牙语之皇”),或者,如果我们想一想《弗拉迪克·门德斯书信集》的话,也得益于埃萨·德·凯罗斯。
《不安之书》中围绕1930年这个轴心的文章是那么多,佩索阿也似乎感到有必要解释他为什么以这种方式写作:
归根到底,所有文学都努力使生活变得真实。众所周知,哪怕当人们行动而不自知时,生活在其直接现实中,是彻彻底底不真实的;田野,城市,概念,都是彻底的虚构物,是我们那复杂的自我感知所生的女儿们。所有的印象都不可传递,除非我们将其变成文学性的。小孩子是非常文学性的,因为他们说的是自己感受到的东西,而不是根据他人所说的、人应该感受到的东西。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小孩子,他想说自己在哭泣的边缘,他说的可不是“我想要哭”,那是成人才会用的表达,是愚蠢的;相反 ,他说的是“我想要眼泪”。这句话完完全全是文学性的,如果一位著名诗人说得出这句话,一定也会引以为傲。它是如此毫不犹豫地提到热泪的出场,那即将冲破意识之眼睑的、化成水的痛苦。[……]
表达!懂得如何表达!懂得通过书写的声音和智识的图像来存在!这一切才是人生的意义所在:此外都不过是男男女女,假设的爱情和虚构的骄傲,消化和遗忘的托辞,蠕动的人类,好像昆虫,当石头被抬起时,暴露在没有意义的蓝天那抽象的巨石之下。(第266篇)
“表达!懂得如何表达!”,佩索阿如此呼吁;懂得通过“书写的声音”存在是如此重要,此外还要加上懂得通过“智识的图像”存在的价值。《不安之书》充满了这样的图像。在本文开头,我提到里斯本的大广场上由池塘、河流和小溪组成的“水之意象”,在同一个片段中,我清晰地记得,视野中的电车好像“可移动的火柴盒,大大的黄颜色的,小孩子会把烧过的、歪歪斜斜的火柴棍插在上面,做成一根糟糕的船杆”(第246篇)。还有很多这样的影像,许多都不可磨灭。因此,《不安之书》是里斯本城最令人惊叹的肖像画,一系列词语和影像叠加累积,在读者的视象中交织、互补。作者在第一阶段的文本中说道:“这本书展现灵魂独特的状态,从所有侧面剖析,从所有方位考察。”(第49篇);这一灵魂状态,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办公室职员的灵魂状态,他的生活和精神以“里斯本”作为“关键地址”,全部“用大写的字母”写成(第248篇)。
在《不安之书》中,几乎所有事物都指向新的、暗示性的现实。作者解释说,“每一件事物向我暗示的,并非它是影子这一现实,而是它是通往现实的道路”;以午后的星星公园为例,它让作者想到“一座古老的公园,在灵魂幻灭之前的那个世纪”(第158篇)。在另一段文字中,作者解释如何努力变换自己所看到的东西,以及如何让风景像音乐般勾起视觉意象:
我使风景产生音乐的效果,唤起视觉意象——这是狂喜状态所能获得的奇妙且最艰难的胜利,因为引发浮想的载体与被唤起的感觉同属一种秩序。类似的最高成就,是在某个景观与光线都不甚明朗的时刻,当我望向索德烈码头,竟清楚地看见它变成了一座中国宝塔,塔顶四角挂着奇怪的铃铛,好似滑稽的帽子。这座奇特的宝塔是画出来的。它高耸于绸缎织成的界面,我不知道这空间如何能长久地存在于可怕的三维世界里。(第61篇)
这个图像和其他类似的图像,由不同元素堆积而成,比作者“不经意的灵魂”中那些消极“展开”(第204篇)的、简单的梦中风景要丰富得多。《不安之书》似乎不过是一系列“并不连贯而我也不期望能连贯的印象”(第222篇),图像可以给出这样的印象,作者也频频尝试灌输这种感觉。然而,有时候,《不安之书》显得更加不连贯,组织更松散;这时尤其不应该忽略那个赋予作品整体性的运作机制:通过无数图像来完成叙述,而不是通过相对罕见的事实或事件(比如理发师“右手边椅子上工作的同事”之死)。在《不安之书》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图像挥洒,通常这在诗歌中更加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