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松亚 Life and Arts集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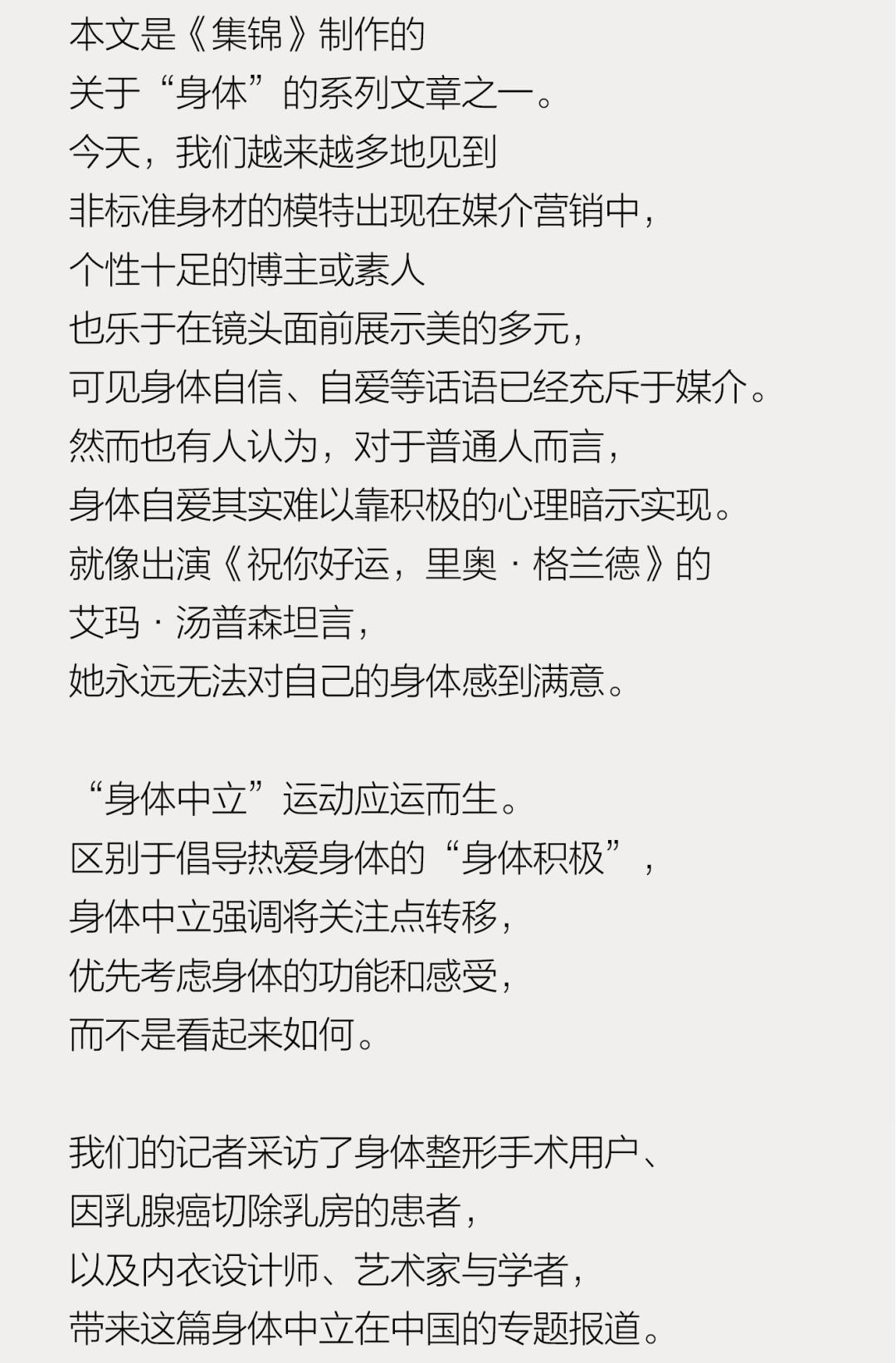

27岁的张小姐匀称、高挑、面貌姣好,走在繁华街头可以轻松加入争奇斗艳的一景。从小到大,张小姐对自己的外表基本满意,除了一个部位——小腿。由于曾经是体育生的缘故,她的小腿坚实有力,但腿肚子上“非常大”的肌肉块,却让她觉得自己似乎拥有“异于常人”的小腿,没有想象中女性的柔美感。
这一心结不断在心底生根,变成生活里挥之不去的“苍蝇”。她不敢在夏天穿短裙短裤,担心露出粗壮的小腿会让别人对她的印象减分。“男生女生都会喜欢腿好看。”张小姐说。这大概是一个基本事实。在厦门念大学时,一位要好的男性朋友曾当面取笑她,小腿“怎么像炸弹一样”。这句有些刺耳的话她记了五六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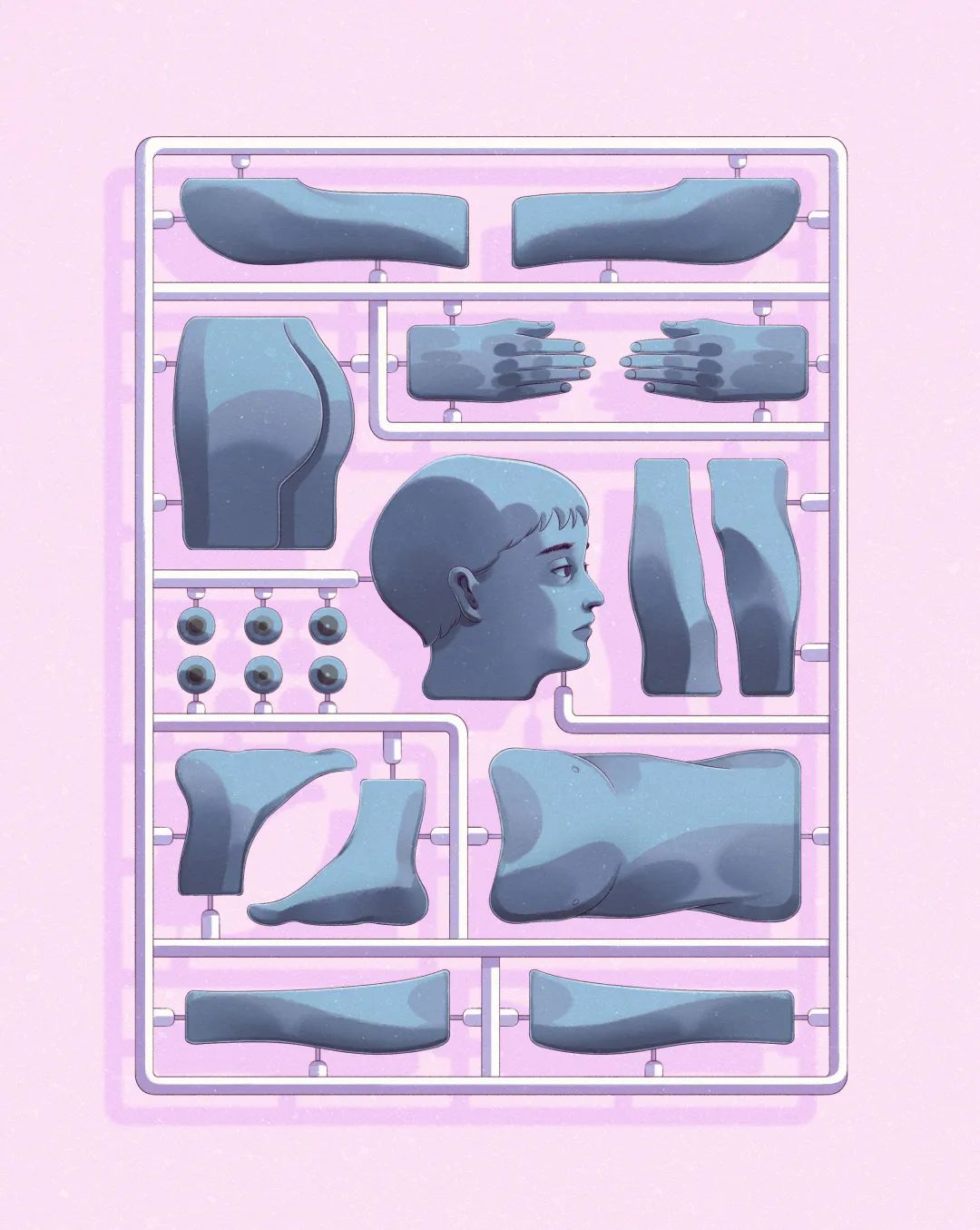
身体的抽象表现。
对身体的别扭与不满日渐积累。她尝试改变腿型,希望补上身体的“短板”,一度考虑做神经阻断手术。这本是一种为了治疗马蹄内翻足瘫痪的手术,通过切除部分小腿神经,让肌肉失去活动能力而自然萎缩。因其间接的“瘦腿”功能,在国内变身为一种高危却受追捧的整形手术,也一度在社交媒体上受到追捧。了解到手术对身体带来的不可逆的损害后,她最终放弃了这一想法,转而选择瘦腿针。这似乎是更可靠也更经济的选择。
2020年春天,张小姐走进手术室,看着医生将肉毒素注射入腿部肌肉。忍受着酸胀感,耐心等上一个多月,小腿终于如愿以偿瘦了下来。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她回忆起来,庆幸自己做了个非常正确的选择。“它不是让我从A变成B那种程度,没有那么夸张,”张小姐对笔者说,“只是说在人际交往的一些环节、一些小时刻,它会给我自信。”她说,自己还会继续打下去,直到腿型固定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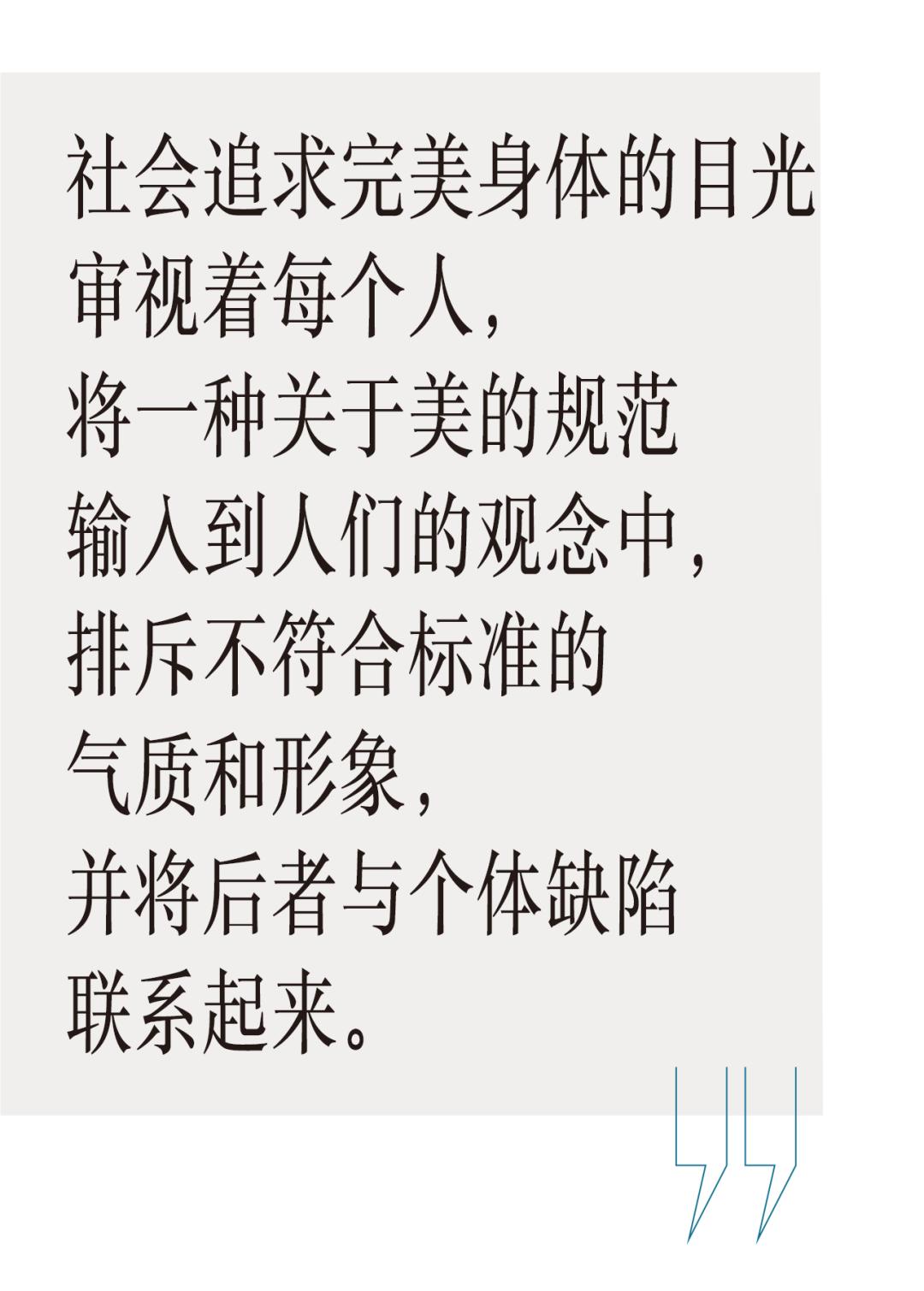
张小姐的经历是当代日渐兴起的美容整形生意的一部分。身体消费已经成为今天无可争辩的事实。媒体、短视频与广告中出现的名人模特不断描绘着理想身体,与女性气质、男性气质等名词一起,制造出身体的习俗样板。社会追求完美身体的目光审视着每个人,将一种关于美的规范输入到人们的观念中,排斥不符合标准的气质和形象,并将后者与个体缺陷联系起来。如今,审美趋势更是在算法的统治下变得更为复杂和强烈,在瞬息万变的网络世界里不断训练着人们对于身体的印象,将身体外在性的统治推到极致。
当以貌取人成为铁律,任何一点与理想身体的差异都会让人感到不安,甚至成为人们痛苦的来源。一个越发重要的问题是,人们应当如何打破刻板的思维模式,减少来自社会、话语和权力的约束,活出真正的自己?

现代生活中,身体正日益占据我们视野的核心位置。随着身体认同成为自我认同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对于身体的规划和改变也越来越成为一种潮流。为了确立和维持自我价值,身体似乎提供了一个牢固的基础,帮助现代人表达自身存在,构建一种可以仰赖的自我感。
但身体管理的兴起,还面临另一种限制,那就是值得欲求的身体形象也受到既存的社会不平等的约束。
几十年来,西方社会陆续出现了身体积极、身体中立等话语,倡导人们接纳多元化的身体,以此反抗身材羞辱,帮助人们突破结构性束缚。身体运动源自上世纪60年代末期首先出现在美国的肥胖接纳运动(Fat Acceptance),控诉社会对于肥胖的污名化。在“以瘦为美”的风潮下,肥胖不仅被认为是丑的,更与道德品行联系在一起,被视为懒惰、不够自律的表现。“受困于”体重的女性为了拥有被喜爱的苗条身材,要接受无休无止的自我检查和自我惩罚,甚至走上极端。

社会的污名化使女性开始无休止的自我审查。
为了将个体从这种“苗条暴政”中解放出来,“身体积极”(Body Positivity)运动应运而生,强调不论身体的功能性与外表如何,人们应接纳并喜爱自己的身体,而不是被束缚在社会约定俗成的审美观和父权话语中。这一词由两个美国人Connie Sobczak和Deb Burgard在1996年以建立同名机构的形式提出。在个人网站上,Sobczak自述,自己发起“身体积极”的直接原因正是为了纪念已经去世的饱受进食障碍折磨的姐姐。身体积极的实践者提倡接纳自己的身体特征,成为自己身体的主人,反对以身体为手段的歧视行为。
这一“人人平等”的理念也被称为身体自爱,它得以进入公众视野与女性主义运动的推动密切相连。不可否认,社会对于女性外貌的关注远远高于男性,女性不仅是被凝视的客体化对象,这种关注和它所附加的价值也让女性更容易受外貌焦虑的困扰。
在今天,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身体积极运动已经在西方社会得到很高的参与度。很大程度上,关于身体积极的讨论聚焦在个人与低自尊的斗争上,成为积极心理学的一部分。与此同时,相关话语也被纳入商业轨道。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是,时装界推出了越来越多的“大码”服装,大众传媒中也出现了更多的“大码”明星和模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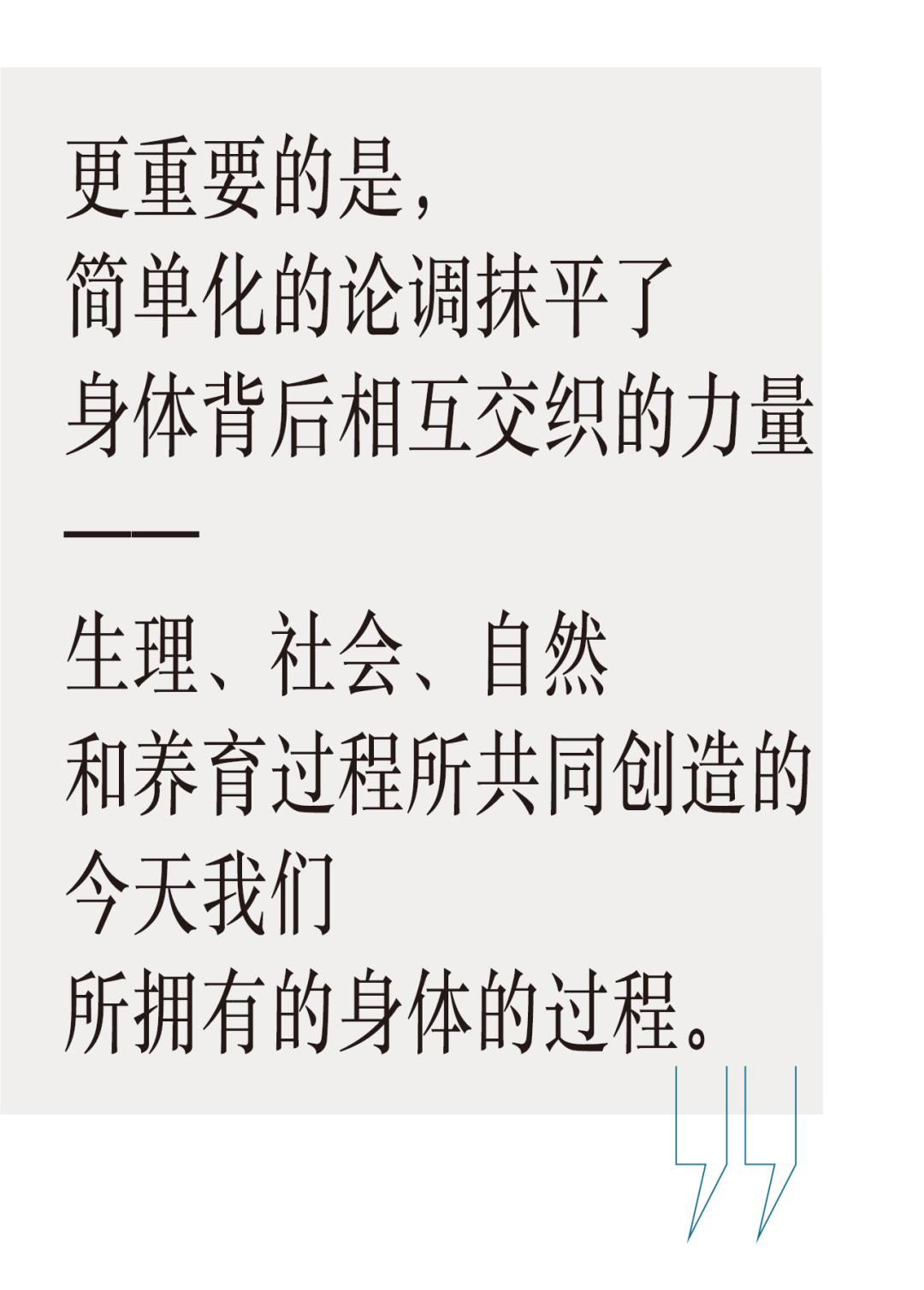
不过,即使身体自信、身体自爱等话语已经充斥于媒介营销中,身体积极运动尚未重塑社会对于美的标准,在流行文化里反而常常沦为商业噱头,被批评落下了少数群体。更重要的是,简单化的论调抹平了身体背后相互交织的力量——生理、社会、自然和养育过程所共同创造的今天我们所拥有的身体的过程。
身体自爱真的可以靠积极的心理暗示做到吗?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民安在《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一书中写道,身体的内部战争,某种意义上,就是身体内在性和外在性的战争。好看、漂亮、青春、性别气质等,都是外在性的基本标准,从属于社会观念并规训着身体。在这个意义上,对身体的塑造也是社会身体的塑造。
主流身体积极话语与商业活动、网络媒介等消费文化机制紧紧联系在一起,人们在Instagram或推特上传自拍并打上身体积极的标签,表达对于身体的自爱。不过,这些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身体仍然是“可接受的”,商业公司也很少展示残障者、性少数或非主流肤色人群的身体。美仍然被视为核心价值,是身体自信的来源。批评者认为,图像化的身体积极运动似乎也陷入了它所希望颠覆的审美规训中,而忽视了身体所处的社会语境。实际上,并非所有人都能如愿接纳自己的身体——考虑到社会压力、歧视、文化约束等因素。

《冒牌人生》剧照。
戏剧导演、小说家陈思安曾在《冒牌人生》中描述了一位等待手术的性别不安者所感受到的与身体的割裂。主人公的生理性别是女性,但内在宇宙并不认同这副躯体。面对一副不想要的身体形态,主人公感到强烈的羞耻感和厌恶,对于丘脑发出的信号和调整行为,身体也有种种排异反应,以疼痛或肿胀宣告存在。身体是诚恳的,但在性别气质的约束下,身体成为痛苦的来源,让主人公为了求得自我和解而选择手术。这像是“一种指向自我的酷刑,也是一种无比坚定的身体规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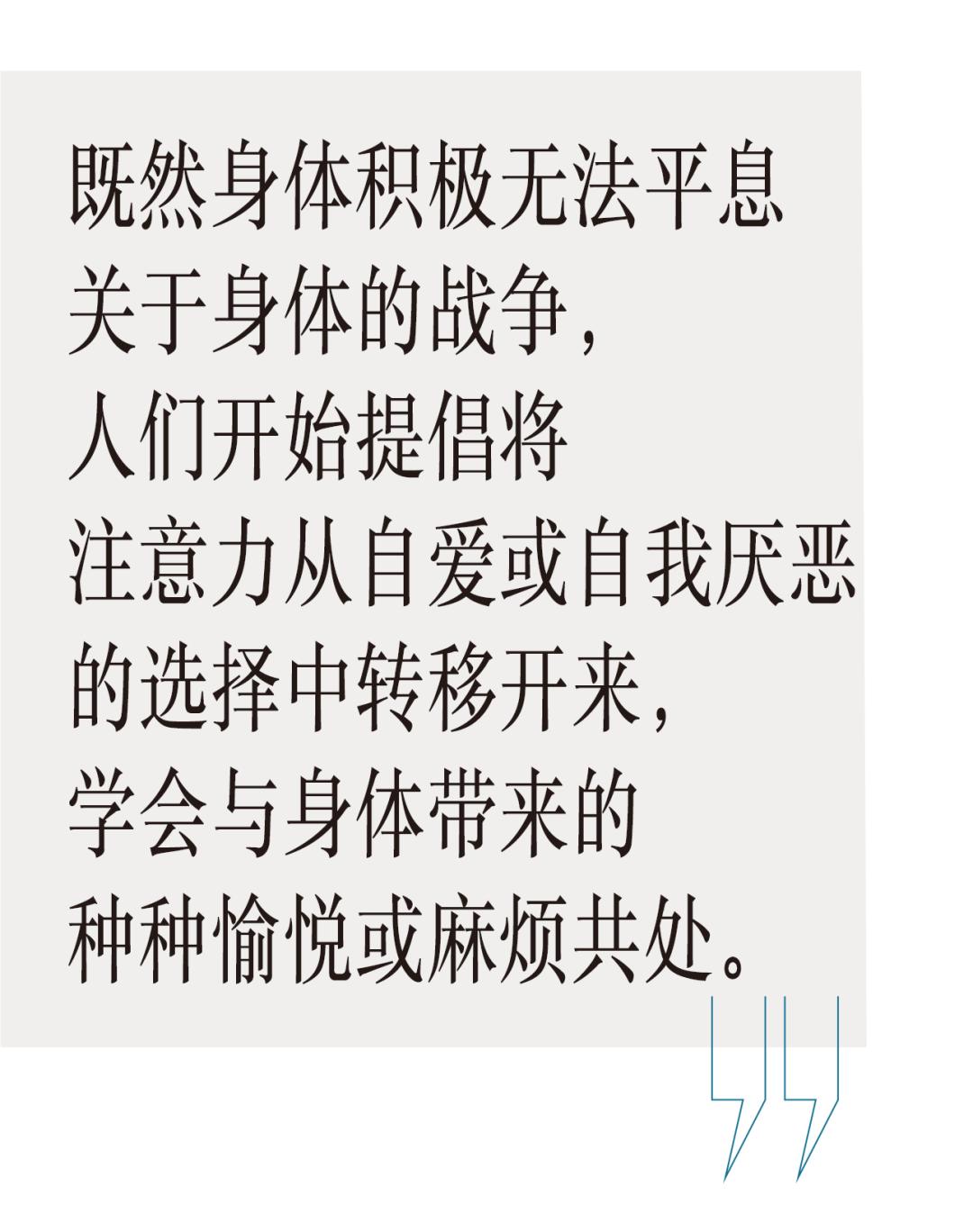
拥有不符合主流身体形象的人所面对的社会和心理压力是一件无可争辩的事实,具身体验中不愉快的经历让自爱变成一项困难的任务。身体中立(Body Neutrality)正是在这样的不满中出现。这个词是由身体形象教练、《身体的快乐》(The Body Joyful)一书的作者安妮·波里尔(Anne Poirier)于2015年提出。既然身体积极无法平息关于身体的战争,人们开始提倡将注意力从自爱或自我厌恶的选择中转移开来,学会与身体带来的种种愉悦或麻烦共处。
作为身体积极理念的延伸派系,身体中立理念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身体积极的内涵,但出现了一些细微层面的心理上的分野。它的倡导者尝试回应身体积极所受到的批评,将视野从身体的外在形象中收回,强调感知身体自身的能量和功能。接纳身体并不必然意味着去喜爱身体,更重要的是不要漠视身体。人们应关注身体的能动性,与身体形成对话,而不是将身体形象作为自我认同的核心。它所代表的主体意识的回归赢得了许多女性博主的青睐。自2015年以来,身体中立也渐成风尚,探索人们如何调和与身体的关系,在身体体验中丰富自己的生活内容与社会空间。

即使尚存在诸多疑虑,身体积极与身体中立运动仍然多少打开了关于身体的讨论面向,在反歧视运动中提高了对于不同人群的保护。不过,相比于欧美社会关于身体议题的开放讨论,东亚社会对多元身体信息的接受度还远远不足。
2020年,问答网站知乎上曾出现过一个提问:亚洲何时才会出现“形象自爱”运动(Body Image Campaign)?其中一个高赞回答不无悲观地表示:近十年也不会有。
在中国,注视身体的目光是强烈的,健康与形象更是文化关注的焦点。在这种社会文化中,女性和少数群体是不可否认的身体压迫的主要对象。一位罹患乳腺癌、今年春天刚刚做完左侧乳房切除手术的患者告诉笔者,失去乳房对她而言就像“被判了死刑”。她害怕在洗澡时看到自己的身体,似乎自己不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她无法向两个女儿解释自己的身体变化,也不敢在母亲以外的家人面前袒露自己改变后的胸部。她只敢在佩戴上义乳后才愿意出门,也担心身体的变化会为婚姻带来的危机。此外,一系列化疗为头发、面色等身体特征带来的变化都是她不得不咽下的苦果。只有想到未来有机会通过乳房重建手术恢复正常的念头,她才能撑下去,将心理创伤压在心底。


上图、下图:经历18个月的打磨修改,于晓丹的内衣品牌姜好设计出了适合乳腺癌术后不同阶段、不同诉求女性的内衣款式。
制作面向乳腺癌术后患者的内衣的设计师于晓丹说,这样的心理感受在患者群体中几乎是共通的。“身体的缺失让她们自卑,还有对死亡的恐惧、压力,以及面对婚姻中规定她所要承担的角色。”没有乳房的女人,不仅要面临来自社会观念的压力,也被审美文化的目光所压迫。东亚传统文化讲究平衡对称之美,失去了一侧乳房,就像失去了这种平衡。于晓丹说,来自社会关系的种种暗示都可能强化这种心理暗示。而且,“除了身体的不对称,她最害怕的其实是被区别对待”。
周雯静《红色系列N°6》,尺寸可变,陶瓷,2016-1;周雯静《红色系列N°6》,尺寸可变,陶瓷,2016-2。
对不同身体的反应和归类,会在实践中促进社会不平等的合法化和再生产。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教授熊欢认为,国内的公众宣教系统还未能提供足够多元化的身体信息,以丰富有关身体的审美规范,教导人们接纳不同的身体,而公共尺度上单一的身体形象正是助长身体歧视的因素之一。从福柯提出的身体与权力的关系来看,身体承载着各种社会权力关系。位于主流的身体对少数身体实施权力作用,这种不对等的关系正是一种建立在身体上的话语权。
长期关注身体经验的艺术家周雯静曾围绕妊娠中的女性身体创作一组作品。她谈到自己所观察到的美化母职的现象,例如,在前期搜索孕期女性形象的过程中,她在网上搜罗得到的结果往往都是非常漂亮的写真照,展示着精美的腹部曲线和光滑的皮肤,“就是那个完美的S”。而当她开始查询有关怀孕的创伤痕迹,却发现能够读到的中文资料很少。另一方面,即使是身边生过孩子的亲密朋友,也不愿意开口谈论孕期的身体变化和产后抑郁等故事。“没有人告诉你怀孕后的妊娠纹长什么样子、肚皮的褶皱什么时候消失。”周雯静说,“在怀孕这件事情上,(社会)一方面美化它、理想化它,一方面又神秘化它。”
周雯静《红色系列Nº3》,200_120_100cm,石膏,2021-1;周雯静《21天避孕药》,12_17cm,综合材料,2020-2;周雯静《女人系列·节育环》,140_120cm,铜_PVC_硅胶,2014-4;美丽坏东西展览现场。
为了解构被工具化的身体,她创作了一组概念化的女性石膏,剥离头部、手、腿,只留下最赤裸的生育特征。这个洁白无瑕的妊娠中的身体被放在红色墨水里,任红色逐渐浸染开来,象征着女性在生物层面最频繁遇到的经验——流血,不管是来自经期,还是生育、疾病、受伤。这具身体如今被放置在周雯静的个展中,伴随着节育环、手术刀一起,展示社会对于女性身体的规训。她将展览主题命名为“美丽坏东西”,以此表达社会中与身体相关的种种具身体验的矛盾性。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身体中立所倡导的回归身体的理念与中国传统哲学养护身体的观念有共通之处。现在,全民健身已经成为新的风潮,但在更美、更强、更壮等符号性的身体要求之外,如何更丰富全面地理解健康还未得到充分挖掘和讨论。
熊欢说,中西方传统哲学对于身体的认知有所不同,中国古典文化里有天人合一、身心平衡的思想,认为身体是经过调和而逐渐养出来的,而西方文化里则更多将身体视为一个可以去塑造的对象。不过,在全球化的消费文化机制的影响下,工具化的身体意识也在中国延续下来,将身体视为一个处在成为(becoming)过程中的、应当努力实现的规划项目。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健身、塑形、整形手术等身体管理等方式才为个体——尤其是年轻群体——提供了机会,以更加彻底的方式,依据某种理想化的自我观,让个体投入对于自我的认同劳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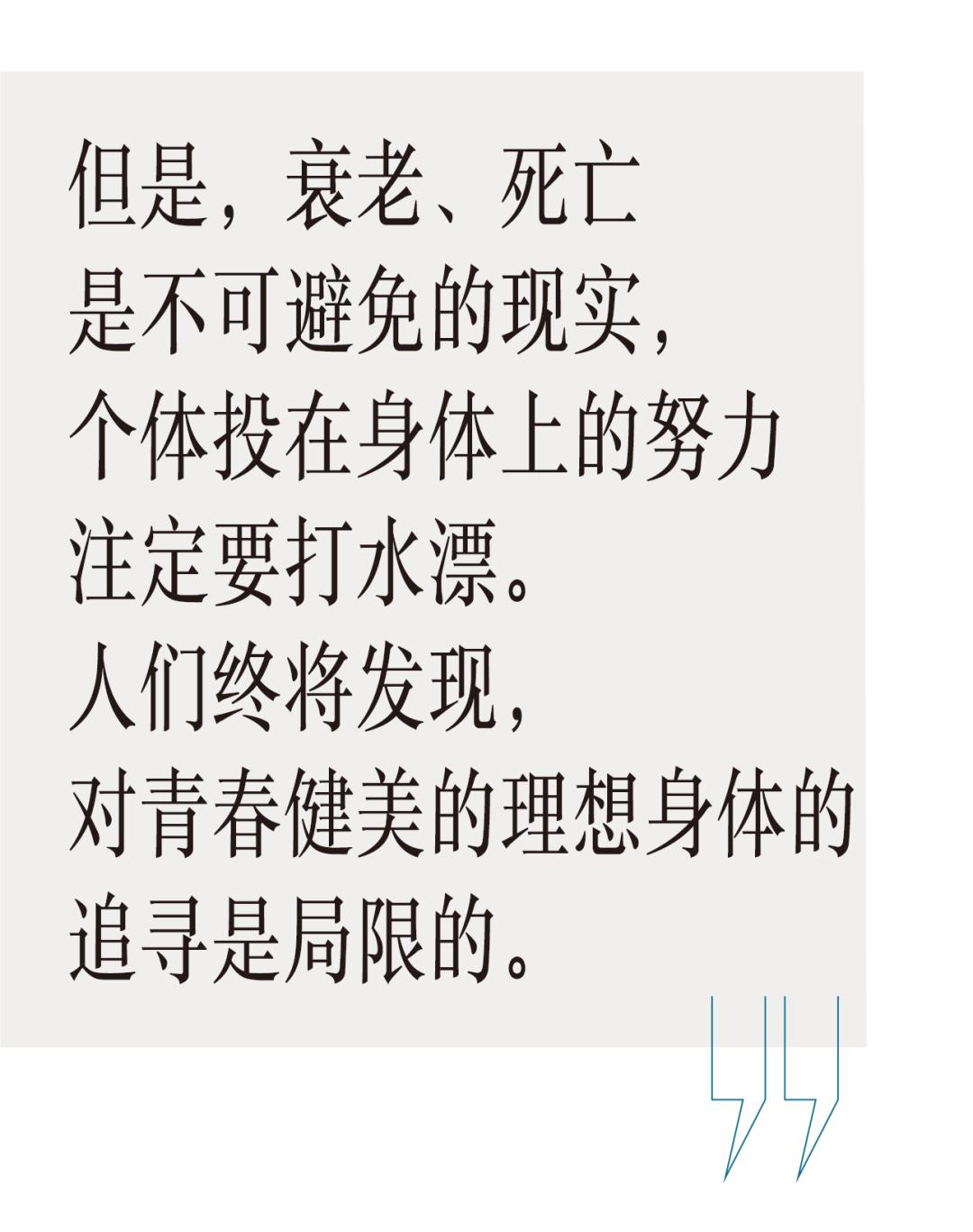
但是,衰老、死亡是不可避免的现实,个体投在身体上的努力注定要打水漂。人们终将发现,对青春健美的理想身体的追寻是局限的。
围绕身体的当代研究常常有两种借鉴和回应的思想传统:生物性的身体和被社会建构的身体。不过,为了达成对身体的充分分析,具身体验也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毕竟,即使在网络社会,推动着我们的体验的,依然是我们的感觉。正如克里斯希林在《身体与社会理论》中所说:“我支持说心与身不可分离,因为心寓于身。”一个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在对身体的检查和管理上投入太多的精力,却丧失了曾经从欲望的满足中获得的惬意?

关注自我才能开始唤醒主体意识。
熊欢曾对国内女性健身人群做过研究,讨论女性在运动中的身体经验。在《凡身之造:中国女性健身叙事》一书中,她发现,许多人可能是出于瘦身塑形或维持身材的目的才开始锻炼,但在运动过程中,疼痛、酸胀、疲累等感官体验让个体意识集中在身体上。运动迫使身体出场,她们也在出汗中开始真正喜爱上这种释放身体天性的方式,从而找到了自我的主体性。
熊欢感叹,中国社会尚且缺乏一些休闲精神,人们在高强度的工作文化下不断消耗身体,没精力养护身体,这也是阻碍人们建立身心连结的一个因素。“如果你一直在用身体干活、熬夜、消耗它,而没有养护它,那你就没有给它一个轻松的环境去放松。这是我觉得很可悲的一件事情,因为即使你去旅游,可能也在想着回来要干个什么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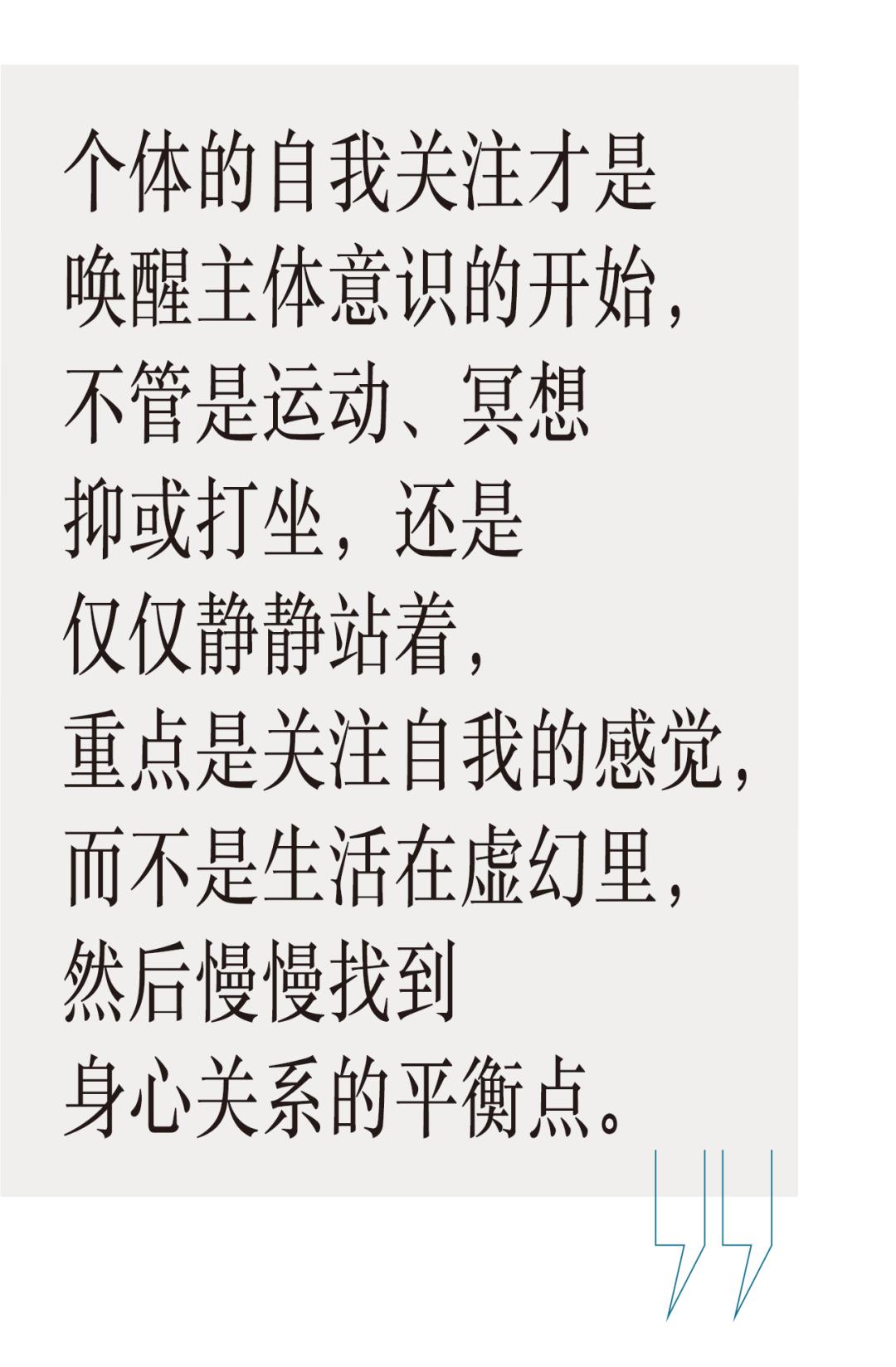
她认为,为了真正建立与身体的认同,人们有必要回到身体本身,认识身体,感受身体的存在和它能带来的愉悦感。很多时候,个体的焦虑反映的是高度同质化和竞争性社会下的集体性焦虑。因此,个体的自我关注才是唤醒主体意识的开始,不管是运动、冥想抑或打坐,还是仅仅静静站着,重点是关注自我的感觉,而不是生活在虚幻里,然后慢慢找到身心关系的平衡点。
此外,社会也需要创造更包容的环境来接纳不同的身体,让不同群体有机会真正获得自爱。但如果社会尚且做不到,熊欢说,社区、家庭和个人都是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提供支持性力量的存在。“就像如果一个孩子出去指着一个人说哎那个人真胖,如果当时那个家长说其实胖也挺好看的,你也可以胖。就这么一句话,也许他以后对这种胖瘦的这种概念就不会这么强烈。”
插画:Mojo Wang
原标题:《「身体」,想说爱你不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