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国学大师。毕生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高举现代新儒家旗帜,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国史大纲》《朱子新学案》等。
(一)
一个人在一个百年的岁月里独自拥有96个属于自己的生命年轮,并在漫长而持续的读书、教书、著书之中渐成一道历史风景、一座文化坐标、一帧世纪背影,这是十分罕见的。
这个人,如果放在生活的户口本上去检索,他叫钱穆,出生于江苏无锡一个叫七房桥的小乡村;如果走进当代学术的牌坊里去拜谒,他居于牌坊的醒目位置,上书“一代儒宗、历史学家钱穆先生”。
说起钱穆先生,我真正静下心来凝望那帧属于一个历史世纪的文化背影,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那时,国学热、文化热正渐次升温,钱穆的名字经常出现在报端和一些专家学者的评论文章里。作为一个曾沉潜于历史云烟深处打捞过诗词歌赋的码字人,我不想也不愿错过这次文化寻根、历史寻根的机会。新千年的前夜,我参加完国画大师李可染先生徐州故居藏品展开幕仪式后,一次非正规的文友相聚,一位历史学博士的一番宏论,加快了我走近钱穆先生的步伐。

(二)
书是钱先生的命,是钱先生输入脉管的血。走近钱穆先生,当从走近钱穆先生的书开始。
在钱穆先生卷幅浩瀚的著述里,《先秦诸子系年》是不可不读的一部。《先秦诸子系年》的成书时间长达十年。十年的风雨兼程换来了钱穆的一鸣惊人。
1923年秋天,已有十年多家乡小学教龄、近一年厦门集美中学执教经验的钱穆,经著名学者钱锺书的父亲、国学大家钱基博推荐,入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讲国文,在讲授《论语》的同时,开始考订孔子生卒行事,启动《先秦诸子系年》的写作。在此后四年的时间里,钱穆一边教学,一边向同为三师教员的钱基博等大家问教学术,开始了早期的教学、研究、交流、著述生涯。
1927年秋天,在无锡三师同事胡达人的推荐下,钱穆转入苏州省立中学任最高年级的国文老师。学术氛围甚浓的苏州中学,鞭策钱穆在著述上更加勤奋,先后写出了《国学概论》《墨子》等不俗之作;与此同时,《先秦诸子系年》所涉及的诸子考辨各篇,也在授课讲义的基础上先后梳理成章。
1929年,就在《先秦诸子系年》初稿基本完稿之时,钱穆与当时学术界、史学界的两位泰斗级人物相遇了。这两位人物分别是:古史辨派领袖、史学大师顾颉刚,经学奇才、著名历史学家蒙文通。
1929年9月,刚刚受聘燕京大学教授的顾颉刚回苏州省亲,在陈天一的促成下造访钱穆。在苏州中学并不宽敞的宿舍里,顾颉刚把目光投向了钱穆刚刚完成的《先秦诸子系年》初稿。面对这个中学教师的心血之作,一向身居学术高位的顾颉刚惊诧佩服不已,诚索此稿带回家中阅读。几天后,钱穆回访顾颉刚,顾颉刚对钱穆的考据功夫和史学才华大加赞赏,当即决定推荐钱穆到中山大学、燕京大学任教。
顾颉刚离开后的那个冬天,虽然寒冷异常,但钱穆却感到非常温暖。一则顾颉刚的慧眼识人,让钱穆增加无穷暖意;二则著名历史学家蒙文通的专程到访,让钱穆遇见了难寻知音,迸发了灵感火花。在历史文化名城苏州,两位神交已久的朋友俯仰湖天,畅谈今古,自然把话题集中到了《先秦诸子系年》上。一向褒言吝啬的蒙文通,对钱穆的奖掖之词如滔滔江水。经其推荐,《先秦诸子系年》初稿中的墨学诸篇,公开发表于南京的一家杂志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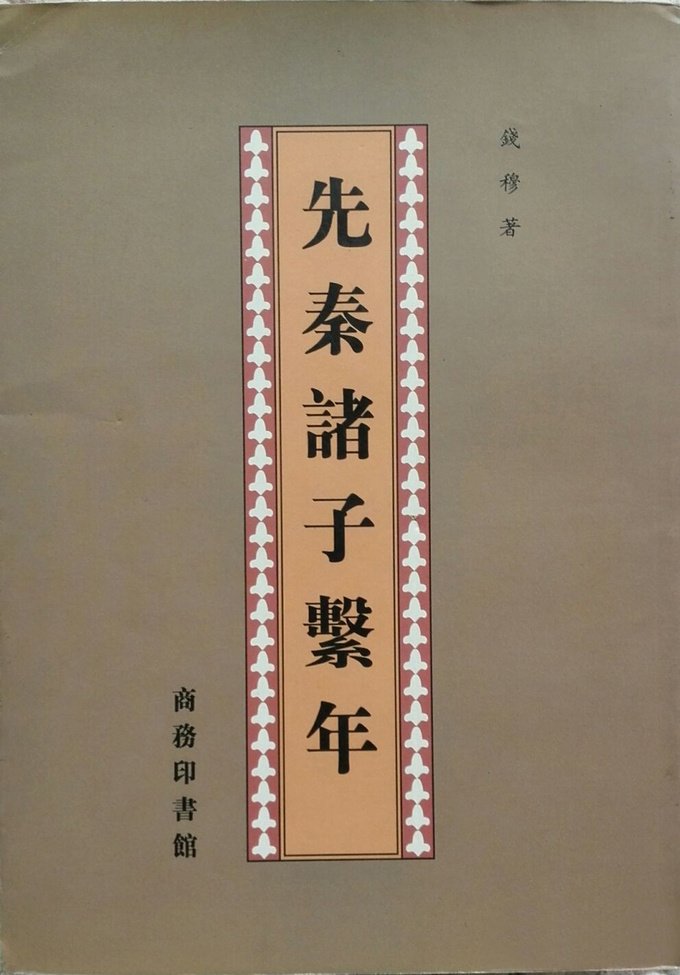
这就是冥冥之中的命运安排:钱穆与顾颉刚的相遇,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改变了他的学术人生,使他从苏州中学一步登入中国学术的最高殿堂,并从此牢牢地站在20世纪中国学术的制高点上,风光无限,辉耀群伦;钱穆与蒙文通的相遇,为我们研究和了解钱穆的早期学术活动、阅读钱穆的早期著作,尤其是客观评价《先秦诸子系年》的历史价值,找到了被官方最早认可的学术文献。1929年之于钱穆,乃新生之年,转折之年。
在顾颉刚的大力推荐下,1930年9月,钱穆辞别苏州中学,前往古都北平,在学者荟萃的燕京大学任大一大二国文课讲师。在未名湖畔,钱穆犹如龙入沧海,驰骋遨游于中国学术的心脏之地。他在教学之余,全身心地浸泡在燕京大学的图书馆里,利用其丰富的藏书资源,除逐字逐句修改《先秦诸子系年》在引述、体例、考辨等方面的错误外,还写出了《周官著作时代考》等在北平学术界有一定影响的著作。
1935年12月,《先秦诸子系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成为民国时期学术界的一件盛事。在这部书中,钱穆对中国学术的卓越贡献在于:以比较权威的《竹书纪年》订《史记》之误,填补了中国历史重大转型时期的研究空白,重建了先秦诸子的学术气脉。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中说:“钱穆先生的《先秦诸子系年》,虽名为先秦诸子的年代作考辨,而其中对古本《竹书纪年》的研究,于战国史的贡献特大。”
(三)
1924年,《东方杂志》摘要发表了史学大家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部名著;此时的钱穆正在无锡三师任教,通过杂志阅读了梁著的一些章节。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以清代汉学为宋学的全面反动为基调来谋篇布局,重点阐述的是清代汉学与宋明理学的对立面。
钱穆敢于向权威挑战,从梁著一发表就不赞同这一在当时很有影响很有市场很有地位的学术观点。20世纪30年代初以后,他拥有了阐述自己的学术见地、全面批驳梁论的舞台和机会。
1931年夏天,钱穆在苏州西花桥巷28号的家中等到了北京大学的聘书,正式出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当年秋,钱穆在北京大学主讲中国上古史和秦汉史课,为正面交锋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做铺垫。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通史课成为大学必修课。北京大学据此提出由钱穆和陈寅恪分别主讲该课的前后半部。钱穆认为,通史要体现一线贯通的气韵,就不能分而授之,遂毛遂自荐,要求一人独立完成全部。1933年秋天,北京大学接受了钱穆的请求,聘请他一人讲授中国通史课。至此,钱穆登上了中国史学讲坛的最高端,在以后四年的通史讲授生涯里,他创造了一个时代的辉煌,铸就了一个时代的华章。
北大的学术风气,让钱穆如鱼得水,使其在书山史海中尽情遨游。他在讲史的同时,以讲义的形式把标靶一点一点地指向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由于当时梁启超去世没多久,钱穆的这一指向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钱穆在此时完成的名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虽与梁著同名,但观点却有很大差别。钱穆把视野放置于宋明理学的传统要义在清代汉学的继承与发展上,提出清代汉学渊源于宋学,“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也”的著名论断。应当说,这个论断与当时居于主流思想的梁论是背道而驰的,但就绵延了五千多年的中华文化而言,它似乎从未产生过断层,即使史上几个外族问鼎华夏,一统河山,其文化也是兼容并蓄,不断前行的。因此,就是从今天的视角去审视钱穆,他的见解仍然掷地有声,振聋发聩。
当然,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部名著,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仅有这些是不够的,提纲挈领地去解读去考察,它的思想精髓在于:高扬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宋学精神,彰显明清诸儒不忘种姓的民族气节,为增添国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送一洪钟大吕,点一指路灯火;它的卓越见地在于:以明清时期的黄宗羲、王夫之、曾国藩、康有为等51位学术人物的思想承袭为核心,把学术思潮的发展变迁放置于思想史本身的矛盾运动中去分析评判,从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和思想资源中寻找思想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力量,为后世论人写史建筑了标志性物什,为开史学研究之先吹进一股强劲的东风,提供着方法论的借鉴。
(四)
国运不昌,战乱频繁,这样的舞台给战士提供了谱写革命英雄主义史诗的机会;而对于钱穆先生这样的纯粹学者,则是提供了面对破碎河山,生忧患意识、扬民族精神的生动教材。他的传世名作《国史大纲》就是在这样的人文环境里孕育的。
“卢沟桥事变”后,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北平沦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合并,在湖南长沙组建临时大学。随着日军的战火烧进南京、武汉和长沙,长沙临时大学只好入滇转进昆明,改名西南联大。由于校舍不足,文学院设在远离昆明的中越通商口岸城市蒙自的海关内。钱穆、朱自清等人经过68天的跋山涉水,行程1700多公里,于1938年4月先后抵达昆明和蒙自。
蒙自山清水秀,环境幽雅怡人,着实是高士寄情山水、放飞理想、著书立说之世外桃源。1938年5月,钱穆开始在教书之余卜居宜良岩泉寺整理旧稿,正式写作《国史大纲》。1939年6月,《国史大纲》全稿杀青。在经历重重审查后,直到1940年6月才获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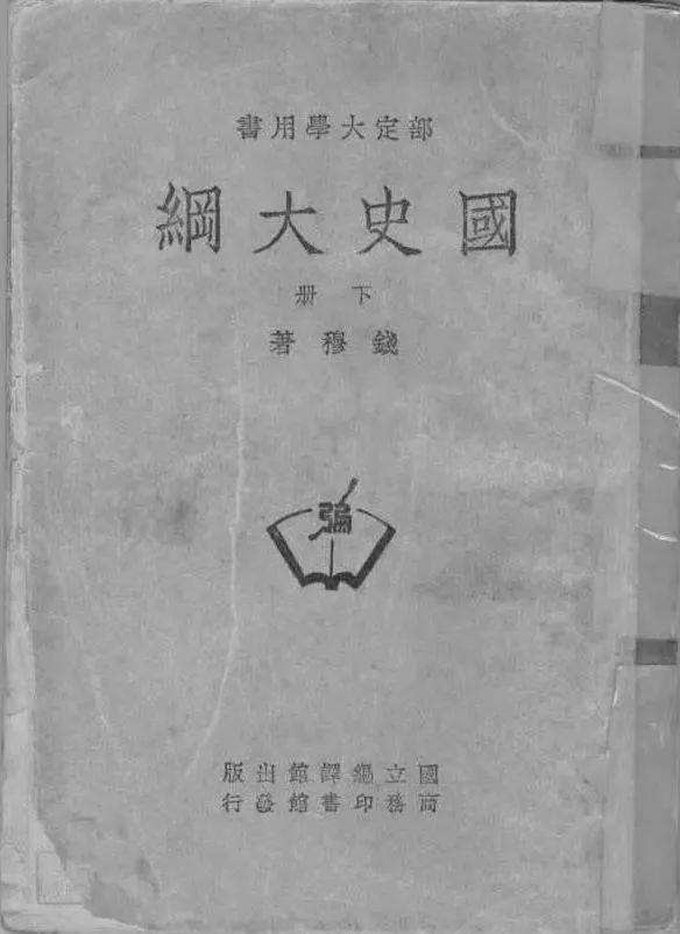
《国史大纲》我系统地读过两遍,与钱穆先生的跨时空心灵碰撞持续了半年之久。最明显的感受是觉得《国史大纲》至少在五个方面作出了开创性建树:其一,标志着钱穆史学体系的形成,实现了他从疑古到信古、从考据到义理、从历史研究到文化研究、从考史到著史的历史性转变。其二,钱穆第一次明确地把文化、民族与历史三者联系起来考察,成为20世纪文化民族主义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其三,钱穆从强调文化是民族国家认同的基础出发,对新考据学派所持的史学观进行了批评,集中彰显了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这对抗战期间以史为鉴,从民族的记忆中找回自尊和自信,激发国人的民族意识,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四,作为一部章节体兼顾纲目体的通史著作,突破了传统史学著作只重政治制度的纲目体例,全方位展示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宗教等社会生活的全貌,这种全新的著史方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治史人。其五,以史学为路标拓展新儒家思想,既突出儒学精髓,又接扬春秋传统,建立了一柱擎天的新儒家史学。
时光如水,悄无声息。《国史大纲》在时间和读者的长期考验里,已经化作一座文化的坐标。由此,我想到,钱穆如果没有开放的眼界,没有强烈的民族文化意识,仅仅局限于古史考辨,在历史的断壁残章里绕弯弯、求余韵、找枝叶,他的文化高度、历史成就断然不会这么高。钱穆是历史和时势造就的领一代风骚的史学大师。
(五)
钱穆一生对朱子情有独钟。幼时读朱子,开启懵懂心智;年轻时教朱子,传播先贤思想;中年和晚年时写朱子,解剖和阐发新儒家真谛。
我曾读过多位学者撰(编)著的《中国思想史》,大致的意见是,在儒家思想的流变史里,经历了两次高峰。一次是以孔子思想为主要代表的儒家思想创制时期,一次是以朱子为代表的宋理学集大成时期。在朱子的理学体系里,孔子的思想得到了传承和发展,为儒学重获新生机,发挥新精神,矗立了八百年不倒的精神雕像。
秋阳绚烂,秋水苍茫。钱穆向朱子迈开的最关键一步是在他的晚年时期。而在这之前,他为治朱子学所做的准备和尝试,占据了他生命中的一半时光。
1949年,钱穆随任教的广州华侨大学迁往香港,“希望在南国传播中国文化之一脉”,从此开始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漂泊生涯。在客居香港的16年里,钱穆以教育家和学者的双重身份活跃在教育及学术舞台上。他与唐君毅、张丕介等历尽千辛万苦,一同创办新亚书院,亲自担任院长,直到以新亚书院为主体之一,成立著名的香港中文大学,才辞职赴台,为香港教育史留下了光辉一页;他继续主讲中国通史课,为弘扬国学精粹,传播传统文化,担当先锋,为人师表,培养了一大批国学通才;他时刻不忘朱子,在紧张的办学教学之余,仍潜心朱子的研究,先后完成了《宋明理学概述》《朱熹学述》《朱子泛论心地功夫》《朱子的史学》等全方位扫描朱子的著作,这些作品为钱穆晚年归宗朱子、“综六艺以尊朱”铺设了道路,埋下了伏笔。
1965年6月,钱穆正式卸任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校政职务,携夫人胡美琦于7月赴马来亚大学中文系讲授中国学术思想课程,专读《朱子语类》,八个月后返回香港。1967年7月亲赴台北,寻觅新居。新居位于台北市郊区士林外双溪。1967年10月,钱穆夫妇正式迁居台北,1968年7月入住古朴而典雅的外双溪素书楼。在此后的20多年里,素书楼见证了钱穆晚年生活与学术活动的点点滴滴。
往事如烟,先贤如梦,缠绕了钱穆的大半生。现在终于有了全身心投入朱子的机会,几十年的日积月累,使《朱子新学案》呼之欲出。1969年11月,钱穆以三年之功,在素书楼完成了他一生中最长的单部著作《朱子新学案》。
《朱子新学案》皇皇五大卷,逾百万言,1971年9月出版后,立刻在海内外汉学界引起广泛共鸣,成为一部享有世界声誉的中国文化名著,不少学者据此把钱穆尊称为“当代朱子”“新时代的新朱熹”,是能够经受住考验和推敲的。
我读的《朱子新学案》是汉字简体版本。读它,我读得很辛苦很投入很亢奋,常常随着钱穆的情感一同律动,随着钱穆的笔触一同悲喜,随着钱穆的思索一同凝重。在钱先生的学案里,八百多年前的朱子活了,朱子的思想活了,正统的儒学活了。
当然,一部深奥玄妙的《朱子新学案》,光粗枝大叶地翻阅,寻找点毛皮,是不会有多少收获的,它需要心无旁骛,虔诚地走近、走进,才能真正把握其思想内核,真正感受它的无穷魅力,进而理解它,读懂它。在这里,有几个问题希望引起读友们的关注:第一,冠于篇首的长文《朱子学提纲》要细读精读。这篇提纲集全文论点、思想之精粹,以诗化的语言,对儒学史、中国学术史进行了简明扼要的归纳与概括,其匠心其凝练其深刻,举世无二人能及。第二,全书的框架设计要仔细咀嚼回味。《朱子新学案》分五卷两大部分。第一、第二卷为思想之部,由理气和心性分而承之,妙论宇宙本体之形上学;第三卷为专论,详析详解详察朱子思想之发展及其在当时理学界之地位;第四、第五卷为学术之部,以经、史、文学三足而辉映成章。此种架构,条分缕析,贯通了朱子思想之渊源之要义之演进,为全面认识朱子儒学上升一新高度。第三,作为集大成者的朱子要重新认识。在《朱子新学案》里,钱穆颠覆长期定位于朱子身上的哲学家、思想家之限,以思想、经学、史学、文学之四脉,全方位还原朱子的哲学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本色,大力彰显朱子纳吐百家、博采众长之儒宗气魄,使其与孔子呈双峰对峙之势。

就钱穆先生同时代的国学大家而言,他的书是较为好读好懂的,是最为中国化的。原因很简单,他没有正式留过洋,没有接受过正统的洋文化教育,不会轻易把洋主义、洋文字拿到书中贴标签、兑水分;他一生钟情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生耕耘和收获于中华历史文化的肥田沃野。他一路行走在经史子集之间,兼收并蓄,和而不同。他用近乎一个世纪的时间,开辟了一块广阔无垠的精神大陆,点亮着中华文化的长天厚宇。钱穆是中国历史文化造就的继往开来的一代儒宗。
(六)
钱穆一生执着于中国历史文化,为弘扬中华文化殚精竭虑。
晚年的钱穆在怀旧与展望的时空里踽踽前行。和他同居一岛的余光中先生,早年以《乡愁》一诗名播海内外,他的“乡愁”在煎熬了近半个世纪后,终于有了登上大陆化解离愁的机会。而那“一湾浅浅的海峡”之于钱穆先生,却只能梦里神游,魂里飞渡,乡愁至死未曾消融。他在《八十忆双亲》里,情真意笃,尽情怀恋和追忆早年时光;他在最后完成的《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一文里,用毕生体悟,对“天人合一”提出新解,认为“天人合一”观,是中国古代文化最古老最有贡献的一种主张,认为此下世界文化之归趋,恐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1990年8月30日,钱穆带着对故乡的依恋,带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敬意,在台北无疾而终。1992年1月9日,钱穆的灵骨越过海峡,安葬在他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苏州。
钱穆走了,他一生以历史人物为主要研究和著述对象,他最终也走进了这个不朽的队列里。他用一千多万个汉字为中国文化画出了一道美丽的钱氏弧线,一步一步地到达了中国20世纪的文化峰顶。
2005年一个暑气未尽的夏日黄昏,我在苏州出差之余,专程来到苏州吴县西山俞家渡,拜谒钱穆先生的墓地。在西南太湖的这片浩淼烟波里,那块风景秀丽的石坡地成为钱穆先生魂归大陆的最后归宿。站在写有“无锡七房桥钱穆先生之墓”的墓碑前,千言万语竟不知从何说起。那就对钱先生的坟冢深深地叩个头吧,在我弯下身子的一刹那,我看到,埋葬先生的山坡,也埋葬着一段文化的历史,陪着先生入眠的书籍,也记录着先生一生的精神苦旅。那条从坟冢曼延开去的小路,宛如一道清晰的背影,宛如一条铺满鲜花的神道,从20世纪一直通向先秦诸子。
起雾了,那不是雾啊!那是无锡七房桥慢慢升起的炊烟,那是北大未名湖悄悄涌起的波澜,那是香江新亚书院轻轻散落的云雨,那是台北素书楼缓缓垂落的旌帆。
雾像一个惊叹号,感动着钱穆先生给予我的那个北方少雪而南方雪灾、冻雨肆虐的漫长冬天。
作者简介:胡正良,1969年12月出生,江苏徐州人,研究生学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书法美术评论家,康德哲学研究学者,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