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二月
星期三
成为“华族”虽然看起来毫无规律可言,实际上却存在一定的政治逻辑支持,而这种政治逻辑则与日本近代的历史有着密切的关联。对于华族的论述,实际上也是对“日本近代的意义”的论述。
—— 《华族:日本近代贵族兴衰史》
鹿鸣馆开馆
现在人们谈到“华族”的时候,脑海中会浮现出他们穿着华丽服装翩翩起舞的样子。在明治初期激进的西化运动中,肩负“皇室之藩屏”使命、拥有特权地位的华族,也曾像西方诸国的特权阶层那样穿着洋装参加舞会。他们的舞台便是“鹿鸣馆”。鹿鸣馆于1883年(明治十六年)开馆,在那之后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在此举办的社交舞会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时任外务卿的井上馨(后荣升伯爵),为了达成修订不平等条约的目的,在日本推行欧化政策。坐落于东京麹町区内山下町(现日比谷公园附近)的鹿鸣馆,作为社交场所也是其中一环。
鹿鸣馆的建筑面积为440坪,是一座砖结构的二层洋楼,设有客厅、台球室、女宾化妆室、舞厅以及休息室等。鹿鸣馆由英国建筑师约书亚·康德尔(Josiah Conder)设计,建筑费用据说高达14万日元,也有人说是18万日元。鹿鸣馆从破土动工到竣工花了两年半的时间,是当时日本最为奢华的欧式风格建筑,由时任外务省委员的松平忠礼(原信浓尚田藩主,后荣升子爵)担任第一任馆长。
鹿鸣馆的开馆仪式在1883年11月28日举行,现场聚集了国内外千余名来宾,由井上馨致开馆辞。会场由30余名警卫负责巡查,晚间舞会的乐曲由陆海军军乐队演奏,宫内省的音乐人则负责宴会时演奏的音乐。
开馆仪式结束后,鹿鸣馆连日举行舞会,参加者包括明治政府的高官,如外交官,还有所谓的“受聘外国人”以及他们的夫人和女儿。1884年7月7日,明治政府颁布《华族令》,制定了将爵位分为“公”“侯”“伯”“子”“男”五个位阶的“五爵制度”。从那以后,新获得爵位的华族成员也开始经常出入鹿鸣馆,成为这一国际社交舞台的一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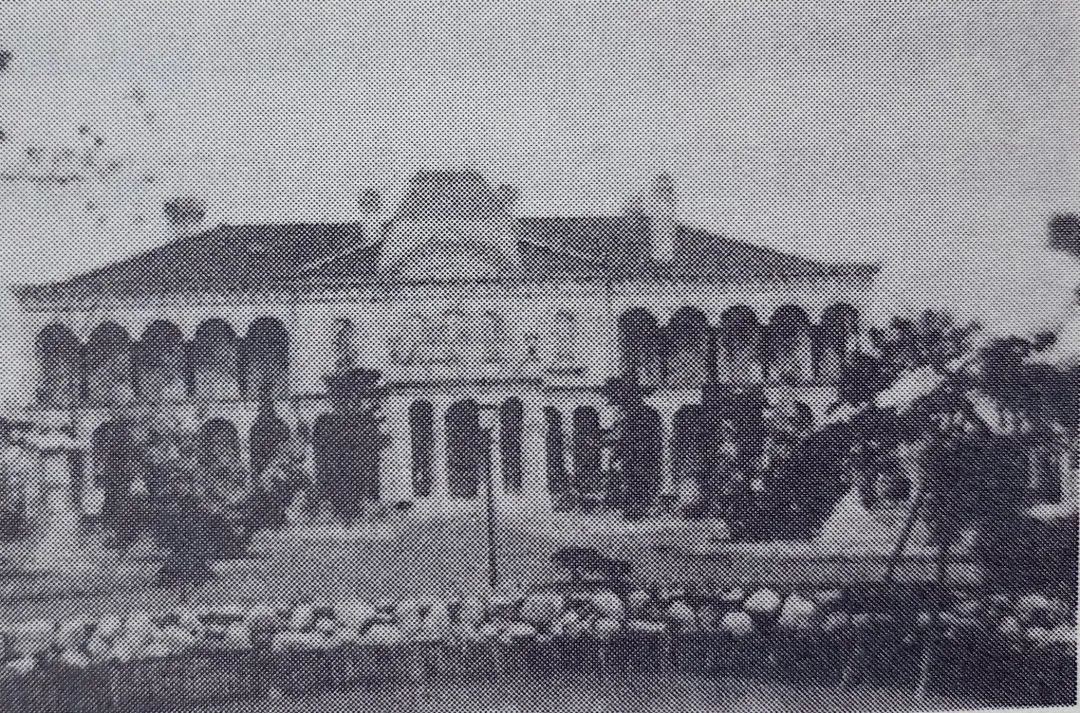
鹿鸣馆外观
不会跳舞的华族夫人们
当时的日本,会交际舞(dance)的人并不多。1880年(明治十三年)11月3日是天长节,当时鹿鸣馆还未开馆,这一天在“延辽馆”(即现在的滨离宫外国人接待所)举行了一次有500多人参加的晚会。由于当时没有一个日本人会跳交际舞,上场跳舞的无一例外是外国人。第二天《东京日日新闻》感叹道:“虽说我国风俗如此,也难掩不甘之心。”
在1883年鹿鸣馆开馆仪式的晚间舞会上,日本女性中只有有着留美经历的大山严夫人大山舍松以及津田梅子、永井繁子,有着海外游历经历的井上馨夫人井上武子及其女井上末子,还有就是刚从意大利回国不久的锅岛直大夫人锅岛荣子以及从俄罗斯回国的柳原前光夫人柳原初子等几个人上场跳舞。包括伊藤博文夫人伊藤梅子和佐佐木高行夫人佐佐木贞子在内的大部分政府高官的夫人自始至终游离于舞会之外。
为解决这一问题,1884年(明治十七年)10月27日在鹿鸣馆举办了交际舞练习会,专门教授华族夫人们跳舞。练习会由刚刚通过《华族令》荣升为侯爵的锅岛直大担任干事长,时为海军军乐队钢琴教师的德国人安娜·蕾尔负责伴奏。
交际舞种类较多,主要包括方阵舞、华尔兹、波尔卡、苏格兰方块舞、玛祖卡以及加洛普等。想要学会这么多种舞蹈十分不易。在华族夫人们刻苦学习的同时,外务省和宫内省有爵夫妇之间也掀起了一股“交际舞热”,在天长节晚会这样的场合,穷尽盛会之极。

鹿鸣馆的舞会
逐渐流行的裙撑款式
鹿鸣馆的影响力虽然并不长久,但不容小觑,就连学习院的女学生(1885年学习院废除女子教科,成立华族女子学校)也穿上了鹿鸣馆特有的撑腰式洋装。当时总理大臣每个月的工资只有500 日元,但据说这样的一件洋装就要400日元,可见其人气之高。
穿洋装与跳交际舞成了女子的必修课。据说,当时的东京女子师范学校(御茶水女子大学前身)要求学生“必须穿着洋装”,就连校长都得穿着燕尾服在讲堂中跳舞。
除服装外,音乐会以及妇人慈善市场(旧货市场)等西方事物也流行开来。当时有人绘制了一幅名为《鹿鸣馆贵妇人慈善会图》的锦绘,描绘了身着和服或洋服的妇人们在鹿鸣馆内聚会的情景。画中还附有一个一览表,表中出现了总长“一品炽仁亲王御息所”有栖川宫董子(沟口直正伯爵妹)、副总长“三品威仁亲王御息所”有栖川宫慰子(前田立嗣侯爵妹),以及会长大山严伯爵夫人大山舍松、副会长伊藤博文伯爵夫人伊藤梅子、副会长井上馨伯爵夫人井上武子、副会长森有礼(初代文部大臣,1887年荣升子爵)夫人森宽子等华族夫人及其女儿的名讳。据说这次旧货市场持续了三天时间,卖出了7500多日元的货物。
这一时期,新获得爵位的政府高官以及他们的夫人、女儿在“为了修订不平等条约而为国家进行努力”这一大义名分之下,频繁地出入鹿鸣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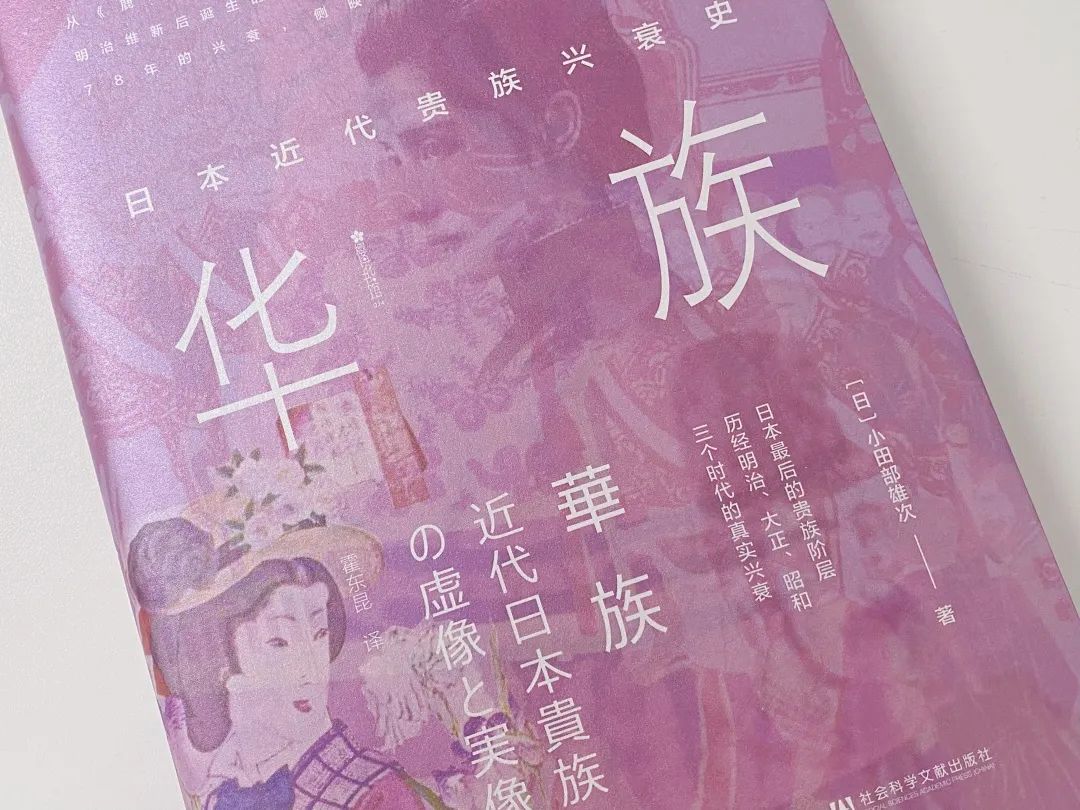
毕戈的讽刺
将鹿鸣馆中上演的这种“异常现象”巧妙地描绘出来的,是法国的讽刺漫画家乔尔吉·斐迪南·毕戈(1860~1927)。毕戈对日本平民女性颇有了解,从他所作的画中也能感受到女性的温柔。然而他对权力的批判十分猛烈,对鹿鸣馆以及华族的态度也并不友善。
毕戈为讽刺鹿鸣馆所作的画非常有名,在其1887 年(明治二十年)连载于讽刺杂志TO ̂BAE ́的一系列画作中,他毫不避讳地描绘了鹿鸣馆中男女装模作样的姿态。
例如,在一幅名为《出入上流阶层的绅士淑女》的画作中,身着正装的男女在镜子中却变成了类人猿。在《鹿鸣馆舞厅》这幅画中,他将日本人描绘成了猥琐无品的乡下人。在《鹿鸣馆的礼拜一》中,毕戈又描绘了身着洋装的艺人,在一个看似休息室的地方用烟管抽烟的场景,其中有人把烟灰弄到了地上,还有人蹲着抽烟。《晚餐会之后(等候室)》则描绘了“绅士们”脱去鞋子在长凳上盘腿而坐,而“淑女们”坐下时把腿伸出去老长的样子。

《出入上流阶层的绅士淑女》
G.F. 毕戈作

《鹿鸣馆的礼拜一》
G.F. 毕戈作
当时对鹿鸣馆进行揶揄讽刺的并非只有毕戈一人。曾为幕臣的小林清亲(1847~1915 )师从英国新闻特派员查尔斯·沃格曼(Charles Wirgman,1832~1891)等讽刺派画家,1885 年(明治十八年)在《团团珍闻》上登载了名为《云之上与泥之上》的画作,讽刺鹿鸣馆中人不顾贫民疾苦之行径。
首相官邸的化装舞会
人们对以鹿鸣馆为代表的“欧化”的批判,因1887 年4 月20 日伊藤博文在永田町首相官邸举办化装舞会一事而达到顶点。
这一天,伊藤博文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位威尼斯贵族,井上馨、山县有朋以及三岛通庸等人也各自进行了装扮。身为帝国大学教授的法学家穗积陈重、植物学家矢田部良吉则分别扮成了惠比寿和大黑天。三岛通庸的两个女儿园子(1869年出生,当时18岁,后成为外交官秋月左都的夫人)和峰子(1870年出生,当时17岁,后成为宫内大臣牧野伸显的夫人)扮成了汐汲。这场晚会近乎疯狂,直到第二天凌晨四点左右才结束。
这场化装舞会显然已经脱离了修订不平等条约的目标。因此,迫切希望早日修订条约的日本民众对这场舞会的批评格外猛烈。随后不久,关于伊藤博文当天的丑闻以小道消息的形式扩散开来。
所谓的丑闻说的是,报纸上有篇文章描绘了参加晚会的一位伯爵夫人在深夜时分赤裸着双足从虎之门仓皇离开,并跳上人力车直奔骏河台地区的情形。人们私底下说,这位夫人正是户田极子。
户田极子是岩仓具视的二女儿,也是户田氏共伯爵的夫人。她生于1857 年(安政四年),当时30 岁,因容貌甚美而被称为“日本之花”。舞会当天,户田氏共扮成了太田道灌,户田极子为配合丈夫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位为其献上棣棠花的妇人,可以说这正是贤淑妻子的典型装扮。然而,据说装扮成威尼斯贵族的伊藤博文首相按捺不住好色之心,竟向美丽的户田极子求爱。
这件事众说纷纭,真相不得而知,但这种流言蜚语的背后,是国民对于此种行为的强烈不满。在修订不平等条约这一大义名分下发起的“西方化”运动,显然已经偏离了初衷。同年9 月17 日,井上馨因“外国人法官任用问题”辞去了外相职务,此后欧化政策也逐渐走向衰退。
从鹿鸣馆到华族会馆
随着欧化政策的衰退,日式传统服饰得以“重生”,但鹿鸣馆与帝国酒店等处依旧歌舞升平。
然而,鹿鸣馆在1894 年6 月20 日发生的地震中遭到破坏,舞厅摇摇欲坠,非常危险。最终鹿鸣馆被变卖,改建成了华族会馆。
1927 年(昭和二年),随着华族会馆迁移到麹町区三年町(现千代田区霞之关)处的新馆,颓败的鹿鸣馆成了日本征兵保险公司的所在地,最终于1940 年(昭和十五年)被拆除。拆除后的第二年,在其原址建立了商工省别馆。当时的《朝日新闻》写道:“在文明开化风潮下绅士淑女们曾经的社交场所,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已经成为统制经济的主城。”
鹿鸣馆的楼梯、试衣镜、花瓶和茶壶等一部分物品仍被保存在东京大学以及作为华族会馆后身的霞会馆内,只有它们似乎还在叙述着彼时华族奉行欧化主义的历史。
鹿鸣馆随着欧化主义的衰退而走向了落寞,曾让鹿鸣馆繁盛一时的华族们后来又如何呢?
这些人也如曾经的公卿、诸侯等江户时代的特权阶层一样,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有军人、财政界人士加入其中,却也难免迎来同鹿鸣馆建筑物一样的命运——走向衰落。
(本文节选自《华族:日本近代贵族兴衰史》序章 大众印象中的华族——点缀鹿鸣馆的人们。)
书籍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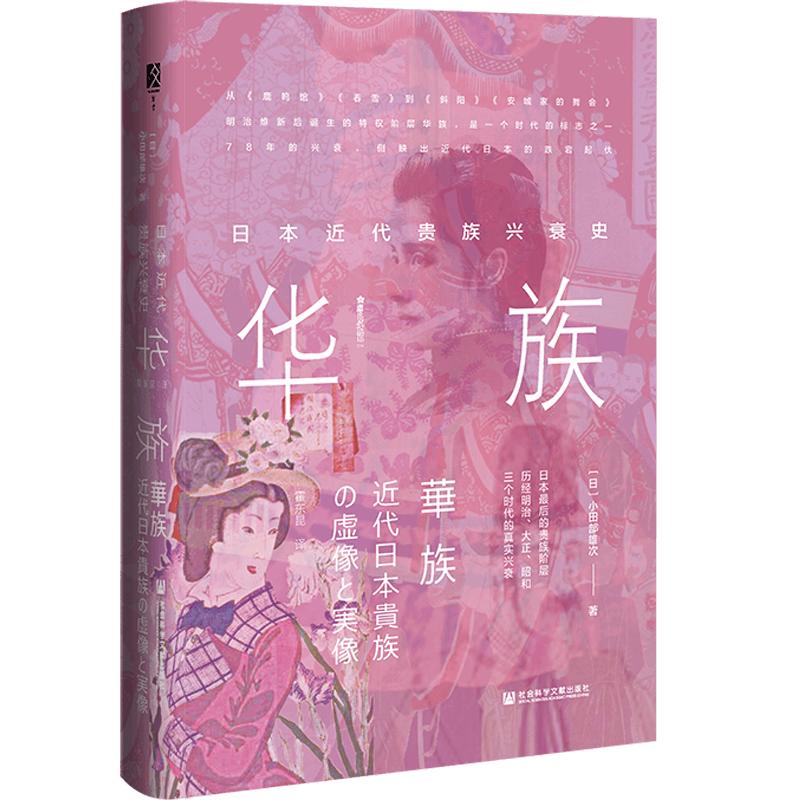
华族:日本近代贵族兴衰史
[日]小田部雄次 著
霍东昆 译
2022年1月出版/79.00元
978-7-5201-9166-1
内容简介
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颁布《华族令》,宣布由公卿、诸侯和维新功臣等家族共同组成新阶层“华族”。华族拥有封爵,世袭地位与资产,是日本近代史上特殊的贵族阶层。
在长达78年的时间里,华族作为“皇室之藩屏”,对日本近代各方面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主要由华族议员组成的贵族院,是日本近代政治体系中重要的一员;华族投资的银行、矿场、海运和铁路公司,在近代以来的社会生活中留下了诸多痕迹;因自身地位和受到的良好教育,华族中还诞生了鸟类学家山阶芳麿、文学家武者小路实笃等活跃在时代前沿的人物。然而,随着日本走向战争,这一贵族群体最终在1947年因华族制度的废除而消失。
在文明开化和大正浪漫的光环里,华族给世人留下了许多旖旎的想象。什么样的人是华族,华族有何特权和义务,华族怎样生活……本书从文献史料出发,揭开朦胧表象,讲述华族历经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代的真实兴衰。
书籍亮点
★ 一部华族概览,展示华族在三个时代、78年间对日本近代历史的影响
★ 三岛由纪夫《鹿鸣馆》,太宰治《斜阳》,以及电影《安城家的舞会》等文艺作品中展现的华族,其真实面貌究竟为何?
★ 本书以华族后裔团体霞会馆编纂的《平成新修 原华族家系大成》为基础写成,作者小田部雄次多年来专注日本近代皇室及旧华族研究
★ 择重点介绍了著名华族成员的社会影响与个人成就。卷末附全1101家华族一览,收录封爵者姓名、爵位、出身与功绩、家族延续时间等详细项目
书籍目录
序章 大众印象中的华族——点缀鹿鸣馆的人们
第一章 华族的成立
1 从公卿、诸侯到华族
2 《华族令》与“公、侯、伯、子、男”爵位的制定
3 作为上流阶层所拥有的特权及所尽义务
第二章 “天选阶层”的基本结构
1 华族之全貌
2 华族会馆与学习院
3 第十五国立银行的建立与华族农场
4 明治时期对华族的批判
第三章 过度膨胀的华族——从明治到大正
1 日清、日俄战争与华族的“军人化”
2 从无业者到女电影演员——多样化的职业
3 朝鲜贵族们的苦恼
4 贵族院
第四章 通向毁灭之路——从大正到昭和
1 经济基础的瓦解
2 西园寺公望与“改革华族”的崛起
3 丑闻
4 日中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时期
终章 日本式“贵族”的终结——战败与战后
后记
史料及参考文献
附录 华族一览
原标题:《『方寸』新书速递 | 《华族:日本近代贵族兴衰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