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梁冰清 颜旭 零度往上
她回看了自己从乡村到城市的成长过程,
发现最令她挂怀的
还是那些生为农民的亲人和曾经的工厂同事。
她再次确认了一个事实:
“我的生命无法与这群人割舍,
他们是我的亲人。”

▲黄灯
黄灯,湖南汨罗人,作家,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现于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任教。主要从事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著有非虚构作品《大地上的亲人》《我的二本学生》等。2016年,黄灯发表《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引发春节期间全国乡村话题大讨论,首发公号阅读人数228万,各大公号阅读量过千万。2017年出版的《大地上的亲人》获得“第二届华语青年作家奖”非虚构类主奖,并入选新浪十本好书、新京报书评周刊“2017年中好书”等。2021年黄灯凭借《我的二本学生》,获南方盛典“年度散文家”。
总策划|何兰生
监制|李 炜
张凤云
编辑|巩淑云
刘自艰
美编|刘 念
出品|农民日报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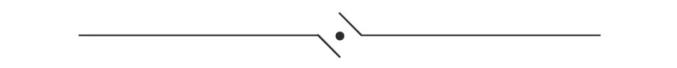
2021年12月,黄灯在甘肃陇东学院开了一堂讲座,主题是“看见他们——光环以外的二本生”。自从《我的二本学生》这本书出版以来,每隔一段时间她都要飞往其他城市,与不同地域的学生进行类似的交流座谈。
密集而匆忙的行程让她略感疲惫,但她却很坚持。除了分享观点,她更想亲自确认一些事实,看到她所书写之外的更多可能性。就像甘肃之行,她希望了解西北和南方的二本学生之间到底有何差异。
“所以要到现场去体验,我不喜欢二手经验,不喜欢那种隔膜的不可靠的东西。”黄灯说话依旧带着汨罗老家的乡音,她用手向上托了托眼镜框,从镜片后面露出一双真诚的眼睛,似乎想通过视线让我们感受到她的坚持。
“我的童年是一颗没有被破坏的种子”
一条长长的看不到尽头的路,两边是比自己还高的庄稼,只有当风吹过,低头的庄稼才能让视野变得开阔。
黄灯到现在也忘不了这个场景。那时她7岁,从汽车站去往外婆家的路上,总会经过这样一片田野。“那个时候你就会有种感觉,人是渺小的,而你跟这个世界之间是有一层明确的关系的。其实并不能得出什么明确结论,但这种场景却会吸引你去尝试思考一些东西。”黄灯认为,正是成长路上无数个这样的瞬间,滋养了她的童年,并让她学会了思考。
1974年的正月十五,黄灯出生于湖南汨罗凤形村。因着家乡有“三十的夜,十五的灯”的说法,她便被取名为黄灯。
她的妈妈是个普通的家庭农妇,“活得虎虎生威,平凡又充实”,父亲是一名乡村教师,“一辈子处于燃烧和付出状态”。家里一共四个孩子,黄灯排老三,还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因为孩子比较多,黄灯从2岁开始,就被父母送去湖南汨罗隘口村的外婆家,一直到12岁才重回父母身边。
虽然不缺爱,但与父母聚少离多的事实还是在她的心底投落下了一道落寞的影子,以至于到现在,黄灯对于留守儿童学生都会多出几分特别关注。
隘口村历史文化传统悠久,民俗“故事会”闻名三湘,每年正月十五,村里人都会用独特的表演形式比赛讲故事。日常时,人们也爱好“打讲”(闲聊),黄灯外婆人缘好,哪里都能找到打讲的人。从小,她便跟着外婆走街串巷,话家长里短。

▲冬日故乡的田野
她脑海里极具象的一幕是,火塘上锅子冒着徐徐热气,姜盐豆子茶异香扑鼻,随着茶水入杯的一声声“嗞”“嗞”,一段又一段的人生故事便从老人们的嘴里流淌出来。
让她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关于福奶奶的故事。福奶奶这一生共生了12个孩子,但最终成活的却只有一两个。因为和外婆同龄,去福奶奶家闲坐,是幼年黄灯的日常。在外婆和福奶奶的聊天中,她对福奶奶的生产之痛难以忘怀。最艰难的那次,外婆强调,福奶奶一边生产一边纺纱,孩子前后生了三四天,生存的艰难与女性的隐忍在黄灯的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对他人的看见和感知,仿佛从童年阶段,就有了天然的开始。“7岁以前,我没有任何阅读经验,更不认识一个字,但从小,不同时代的人就在我脑子里走来走去。”她觉得正是这种原生态生活场景和最本真生活经验的积累,给予了她感知人生苦楚的能力。
她也会一个人安静地待着,在青山草木间长时间地去审视自己,在一种模糊不可言语的个人情绪中,慢慢察觉出人和环境的亲切关系。
而更多的时候,她的童年长在田间。捉鱼、放牛、养鸭、捡柴、疯耍……没有任何一个乡野项目在她的生命中缺席过。她的同伴很多,“没有几十也有上百”“大的带小的,一群一群的就是这样疯耍着长大了。”
乡村的生活经验涂绘了她的性格底色,也让她从中汲取到足够多的生长力量。“我的童年像是一颗没有被破坏的种子,既没有被外来的书本知识介入太多,也没有被条条框框的价值观破坏。生命历程是自由自在的,所有的认知都来自于生活经验,这种没有知识干预的童年是特别美好的。”说着,她的两只手相向而合,正是一个呵护的姿势。
她认为每个小孩的内心都有一颗种子,保护种子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它埋在土壤里,给它提供必需的阳光水分。“种子保护得越好,它以后就越有力量。”
“我的生命无法与这群人割舍”
“鲜活”“事实”“体验”是她口中的高频词,这种对事实现场笃定的确认,起源于她“有机的”童年,也一直潜藏于她起伏命运的草蛇灰线中。
1995年从岳阳大学毕业后,黄灯进入一家国营工厂做文秘、会计、组织干事,之后在国家“减员增效”的倡导下,直接到生产一线当起了挡车女工。
从大学生到工厂女工的身份变换,让她深感了巨大落差,但是奇怪的是,她却生出一种坦然的感觉。“以前在机关的时候,做的那些工作比较虚,但是在车间里,我从事实实在在的生产,虽然过程特别劳累,但是不能否认这种快乐的真实性。”
1998年从工厂下岗后,她考取了武汉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后来又考上了中山大学的博士生。
因着命运改变而带来的欢欣显而易见,但她也在无尽的书本知识、概念、理论中失望地发现,她身处的学术环境已经离现实生活太远了,这种知识的空虚感跟她一直尊崇的踏实而鲜活的生命体验背道而驰。
“尽管学院经验改变了我的生存和命运,但这种改变的路径却同时将我的精神推入了虚空,让我内心几乎找不到安宁,并产生一种真实的生命被剥离的痛感。”她期待中的知识分子,本应该是关注底层、有社会责任感的,而不是封闭在固定圈子里只关注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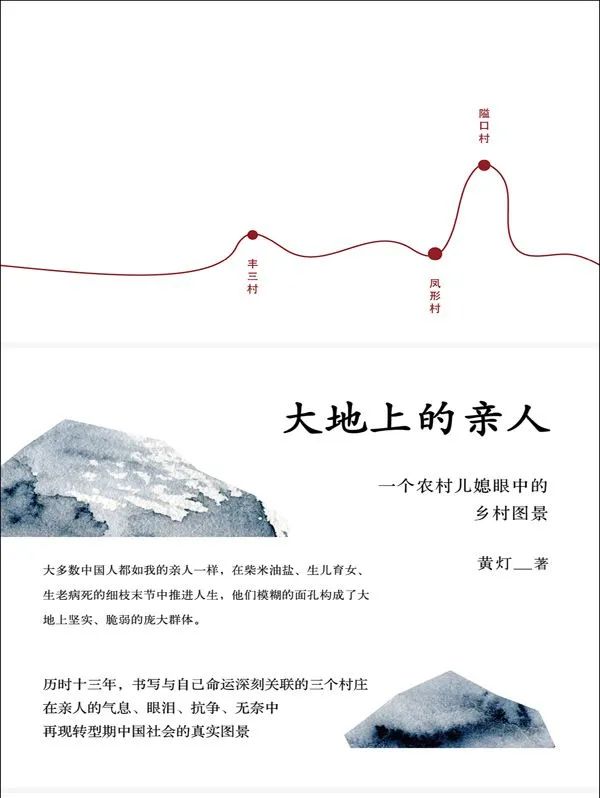
她开始了长久地自我审视,并在这种情绪里,敲出了二十多万字的思想随笔,在这次“放血式”书写中,她回看了自己从乡村到城市的成长过程,发现最令她挂怀的还是那些生为农民的亲人和曾经的工厂同事。她再次确认了一个事实:“我的生命无法与这群人割舍,他们是我的亲人。”这个“精神还乡历程”,她坦然接纳。
从那开始,她主动联系在广州打工的亲人和同乡,就在城中村棠下村,她穿梭于“一线天”的犄角胡同里,在陌生的空间听亲人们讲家乡土话、吃家乡菜,也更加真实地了解到亲人们在大城市打拼的真实处境。她加入到中国人民大学温铁军老师所带领的乡建团队中,进行了大量实地调研。调研期间,她吃住在村中,走访大量乡民,对三农问题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
她的笔触也更加精准地对准中国现代化浪潮中被裹挟改变的农村、农民。一方面,她对童年乡村保留有美好回忆,一方面现实农村的处境又让她觉得痛楚。她觉得有义务把她看到的思考的书写出来。2016年,她的一篇作品《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经由新媒体的裂变传播,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并触发了一波返乡手记热潮。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她又完成了《大地上的亲人》这本书。书里,她将目光对准与她有生命关联的三个村庄,通过对亲人命运的透视,将个体家族的悲喜放置到宏大时代背景下去叙述,“勾勒出中国农民与命运抗争的复杂图景”。
有批评家指出,这本书太过于个体化,有一定的偏颇。对于这个说法,她的回应是:“当然了,任何一种书写都具有局限性,它基于个人经验所写,难免带有一种价值观。”
而在黄灯的丈夫杨胜刚看来,这本书最值得肯定的地方反而在于,它“动用了文学最原始的力量:情感和真实”,而这一切,都建立在黄灯“回归更广大群体的生存现实、主动建立起与现实的深刻关联”基础上。
“教他们观察自己也观察世界”
在离广州城市中轴线不到十公里的地方,龙洞街道如同一块碧玉横卧群山之中,这里藏匿了很多不起眼的学院,黄灯毕业后任教的广东金融学院就在其中。
2005年,黄灯开始了她的教师生涯,在学校里她遇到了数不清的学生。老师的身份为她提供了一个观察个体生命的隐秘路径,也让她清晰地看到,社会时代发生变化后,应试教育在孩子身上留下的烙印:“在应试教育和对分数的疯狂追逐中,孩子们的个性、天性和生命活力,被磨灭得无影无踪,他们的面目越来越相似,早已成为工厂的标准化构件。”
黄灯回忆说从教十几年来,没有一个学生因为坚持自己的想法而与她发生过争吵,他们“中规中矩、老成持重”,被裁剪地规规整整,“像一个空心人来到了你的身边”。
这显然与她上学时期的飞扬放肆大为不同,她不禁思索:现在教育和年轻人命运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她更疑惑于:这么重要的一个话题,为什么一直没有合适的契机引起大规模谈论?

▲2005年拍摄于家乡
基于与学生们的日常交往和写作沟通,黄灯于2020年出版了《我的二本学生》这本书。书面世以后,“二本学生”这个群体获得了很多社会的关注和讨论,但是黄灯告诉我,她并不是单纯地在写二本学生,这个群体只是她观察这个社会和时代的切入口,书中提到的群体困惑也存在于重点大学的学生中。更确切地说,她写的是一个时代的切面。
而在教师的试验场里,黄灯的努力还在继续。她说相对于作家,自己更看重教师的身份,她也不觉得引起“二本学生”大讨论的意义比教好学生更重要。
她总是试图去消除流水线学习带给学生的“电子产品味儿”。“对于一个大学生而言,更重要的是精神成人。如果他的精神世界不够广阔,那以后的发展后劲是很有限度的。”秉持着这个观念,黄灯上课,从来不进行硬性地知识灌输,她爱跟学生互动,不同的班级总能激发出不一样的火花。
她跟学生们聊海子的诗歌,聊“五四”那代人的情感如何外露,也喜欢讲《春江花月夜》,那种借由文学而生出的辽阔时空感和形而上的思考,令她无比着迷。她说,一个年轻人不应该被琐碎的事物捆绑住,他们的生命中都应该有这样的时刻——去面对那种特别虚无的问题,去独立思考、想象,他们的精神应该是时刻飞扬的。
在课堂上,黄灯会拿出来两三个小时跟学生们讨论人生话题、读书意义,让他们抛弃掉学业生涯中那种程序化的语言套路,“用自己的语言去表达自己”。
2019年,黄灯辞去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与新媒体学院院长一职,选择去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当了一名普通老师。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她在名声大噪后没有选择一个知名院校,在他们看来,这是“人往低处走”的表现。
黄灯说她只是想要了解专科院校。本科院校的专业设置、文化氛围、生活方式她了如指掌,反而是职业院校带来的陌生感更能让她兴奋,这是一种边界的突破。况且深圳这座城市,也承载了她对南方精神的想象:年轻的、活力的、敢闯敢干的。她希望通过亲身体验,去了解一个群体和城市。
在深职院,黄灯和几名老师还开设了非虚构写作工坊,共有三十多个学生报名参加。除了字数5000字以上,黄灯不对他们做出任何要求。去年,学生们共完成了近二十万字的作品,最多的一名学生写了三万字。
“写作和思维是紧密链接在一起的。”她坚定地相信,相较于写作这件事,引发学生的思考和自我认知,才是它真正的意义内核。“要唤醒他们,教他们观察自己也观察世界。”
前段时间,有学生跟她说,自从接触了写作,感觉一些看不到的障碍被克服了,世界的维度变得丰富起来,连人也自信起来。她觉得很欣慰。
私下里,学生们叫黄灯“灯哥”,形容她“理想主义”“上课很真诚,直剌剌地什么都讲”。遇到难题,也会找她去纾解郁闷。
“除了表达和看见,更需要的是行动。”她也注重教学生一些实用性的经验,或是待人接物的细节,或是为人处世的道理,去帮助他们“做好起跑动作”。
有的学生用邮件提交作业,附件里带个文档,正文却没有一个字。黄灯会特别严肃地告诉学生:“虽然我不会介意,但是这样的行为放在职场里是非常不妥当的,正文至少应该说一句‘请查收’。”
“作为老师,要有一定的预判性,去思考一个学生进入社会以后会面临什么样的困难,然后尽可能多地把这些困难提前排解掉,这样才能避免他们以后被撞得灰头土脸。”
她甚至想写一本书,去观察那些已经在社会上立足并取得一定成绩的学生,总结他们身上可复制的成功要素。比如,一个孩子需要自信到什么程度,一个毕业生怎么去和周边社群融合,什么样的品德是工作时特别需要的。
“让他们接纳自己”
或许是与乡村天然的亲近感,黄灯接触最多的还是农村的孩子。农村学生与城市学生的区别,她看得异常清晰。“对于农村的学生而言,负载在家庭之上的生存挣扎是他们内心深处最大的困境。”
王国伟(化名)是黄灯2006级的学生,他有着典型农家子弟的“务实”特质。虽然对武侠小说创作抱有热情,但他却清楚地知道现实与梦想的距离:“我很清楚地认识到,大学毕业后,我的首要任务是要解决我和我家人的生活问题。”毕业后,他顺利地找到了一份银行的工作,后因不喜应酬交际,又参加了全省公务员考试,成为了一名狱警。
十几年来,黄灯接触了很多像王国伟这样的农村学生,他们的命运走向反复验证了她的判断——相较于家境良好的城市孩子,对广大寒门子弟而言,生存的压力和家庭的重担降低了他们承担风险的能力,也因此在择业的选择上少了很多。
黄灯喜欢将个体命运放在大的时代背景下去考量。她将自己上大学时的情景与自己执教的2006级学生进行对比,发现自己上大学时农家学生占到了60%,通过国家分配工作的比例高达97%。
而十几年后,她观察到因为失去了国家兜底的庇护,农家学子的就业去向也越来越呈现出不确定性,她将此称为“时代的裂变”。
在与农村孩子相处中,她认为更重要的是帮助他们平缓度过情绪低落期。“在短暂的大学生活新鲜感后,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往往会对农村孩子产生冲击。要让他们真正打开自己,就得让他们学会接纳自己,这是个漫长的过程。”在她看来,这是每个农村学子的必修课。
“作为过来人,我的真实体会是,坦然面对这些事,承认并接受,反而能融入得更快一些。”黄灯说,作为一个乡下孩子,她对此感同身受,过去她也因自卑选择逃离故乡、远离亲人,自欺欺人地将这些“不体面”涂抹成“模模糊糊、忽略不计的背景”,这种撕扯令她难过,她希望学生们能绕过这些弯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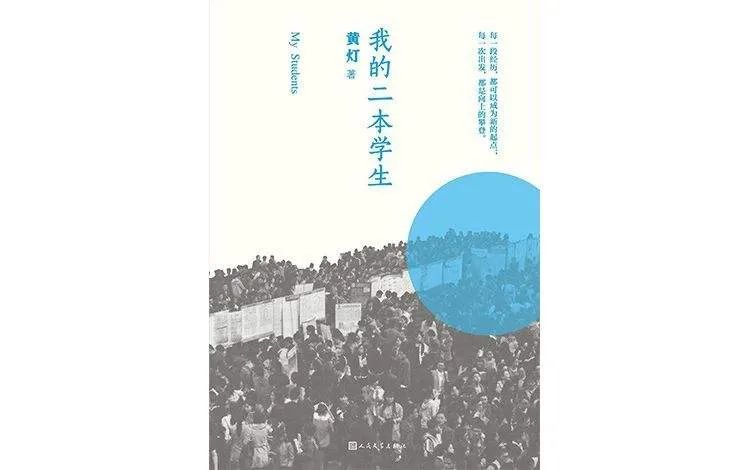
聊到这里,她自然而然地提起了李沐光(化名)的名字。他是黄灯执教的2012级中文班的学生,来自广东省一个普通的村庄,父亲近几年在外打工,母亲则在家操持家务,干点简单的农活。家庭的困窘让他对外面的世界很是向往。来到大学后,他悄悄观察城乡学生的差异,惊异于城市同学良好的综合素质。他们有的会弹钢琴,有的会拉小提琴,有的会跳舞,有的会唱歌——这些他从前只在电视上见过。
失落和敏感是必然的,而真正改变他性格的转折点来自于一次钱财被骗事件。他联系了辅导员,并因此获得了在学生会工作的机会,性格也因此变得自信起来。大学毕业后,李沐光找到了一份在当地著名地产公司做党务的工作,收入不错,家庭状况也得到了改善。
“正是因为接纳了自己,沐光的整个人生才改变了轨迹,从他身上,我看到农村学生改变自己所带来的可能性。”黄灯总结说。
尽管黄灯总会不自觉流露出一种知识分子特有的悲观态度,但跳出书写范畴,她还是觉得年轻人的命运是一个动态的起伏过程。《我的二本学生》出版两年后,当她再去看书中的一些人物原型,发现命运已在不知不觉间,对他们原有的路线进行了纠偏。“他们有的考上了研,有的找到了满意的结婚对象,很多人都是在往好的方向去发展。”
黄灯无法否认属于过去的普惠性时代红利正变得越来越稀少的事实,但是她也看到这个时代正在不断释放其他的机会。
“其实时代的红利一直都在,只不过有心的孩子才能抓得住。”黄灯说。
采访结束,正好碰到黄灯上初中的儿子杨力行考完试回到家中。“考试很简单,哪怕作文扣20分、三道选择题全错,我也能考100分。”语气里都是自信与少年人的张扬。黄灯边笑边摇头说他“迷之自信”。
对于儿子的教育问题,黄灯一直秉持着“散养”的理念。相较很多人强调阅读的必要性,她认为在孩子理解能力有限的情况下,日常生活经验的获取来得更为重要。
黄灯喜欢带着儿子“疯跑”,他们的足迹遍布街角小巷,特别是那些逼仄又富有生活气息的胡同,他们总能体会到更多的烟火日常,这是属于母子两人心照不宣的隐秘乐趣。每年寒暑假,她也会带儿子回家乡,为的是让他跟故乡亲人建立起一种亲密关系,她反复跟儿子强调:“你是一个有生命来路的人,不是突然之间在广州出生长大的没有根基的人。”
临告别时,我在杨力行的书桌上,看到了一张便利贴。黄色的纸上用彩笔写了6个词语,“远见、果断、大度、责任、沟通能力、公平”,不知道这是不是黄灯对孩子的期待。

往期
回顾
原标题:《黄灯:“体验”大地上的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