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舒少环 新周刊

2019年11月22日,厦门,戴荃在第28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演唱。/ 视觉中国
侠之风骨,客之柔情,行之洒脱——戴荃借着新专辑《侠客行》也找到了自己内心的侠之大义。

音乐人戴荃的发型从前往后看,是个普通的短寸头,但一扭头,脑后藏了条辫子。他的眉角微微上扬,辫子一甩过来,俨然一个在林间执剑习武的侠客。
那条辫子跟了戴荃十几年:“头发在古代有很多意味,我留辫子,单纯为了纪念我考上大学。”生于1979年的他,青春期撞上了中国摇滚乐的黄金时代。高中毕业后,他组乐队玩了10年,玩摇滚、玩Funk。“我们当年玩的,都挺‘地下’(underground)的。”
25岁那年,即2004年,中国摇滚乐逐渐低迷,多数转入“地下”音乐。戴荃也突然转向,连考了两次大学,最终考入南京艺术学院(简称“南艺”)音乐学院。戴荃走上一条更正统的道路,做音乐制作人、参加音乐综艺,当歌手、出专辑。
但戴荃内心那股江湖侠义气没被丢下,正如他最新一张专辑《侠客行》,“侠,是人在江湖、行侠仗义;客,是江湖中的人情,有友情、爱情等;行,是放下,放下江湖、潇洒自如”。

戴荃近照。/由被访者提供
以下为戴荃自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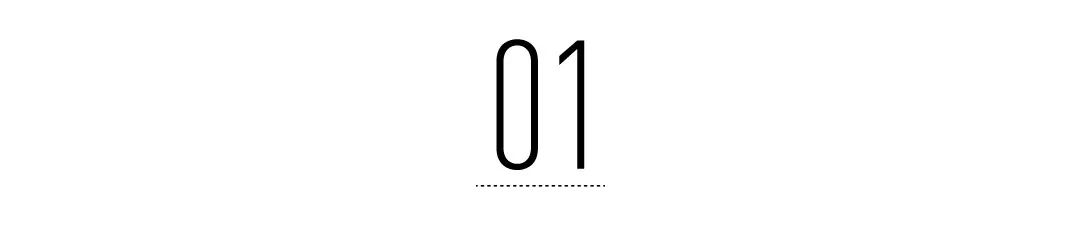
没被五指山压住、
没戴上紧箍咒的“野猴子”
我从小一直很皮,朋友都管我叫“猴子”。我以键盘专业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安徽黄梅戏学校。入学后我就当上了班长,但第一学期就被班主任撤职了。老师觉得我太皮,没法给同学当表率。当时,我喜欢闷在琴房里练琴,正常的课也不去上,经常在学校里养各种动物,也常被班主任逮个正着。
我的同学基本都是学民乐的,比如二胡、竹笛、唢呐、古筝等。我当时迷恋摇滚乐,90年代,在我最躁动的年纪遇上了中国摇滚最好的年代。我在艺校组了支乐队,大家一块儿唱Beyond的歌。回想起来,我挺享受那个阶段的,感觉很自由,是种自我释放。艺校毕业后,我正式组乐队了,没考虑上大学。当时,我们乐队玩摇滚,风格很硬。到现在为止,唐朝乐队都是我最喜欢的一支乐队,他们区别于任何一支摇滚乐队,是我心目中最诗意的“中国风”摇滚。

唐朝乐队。/视觉中国
那些年,我一直是乐队的键盘手兼主唱。键盘手在摇滚乐队的存在感很低,只能站在舞台的一角一动不动。但我也是主唱,表现欲很强,所以我就很着急。我一直幻想有一天能给键盘架上四个轮子,这样我就能在舞台上自由活动了。过了很久,我买了一种挎在身上的键盘,跟吉他似的,终于得偿所愿。玩了几年摇滚,我又开始组乐队玩Funk。它更强调技术,编排也更精致。
但90年代,像我们玩的那种硬摇滚乐、Funk,都属“地下”音乐。我大部分时间待在我的故乡——安徽芜湖,也去西安待过两年。由于年龄小,我也碰到过那种演出之后人家不给结账的情况。独在异乡也没有办法,只能忍气吞声,那时多少也吃了些苦。我们单靠乐队收入还不太够养活自己,所以基本都有别的工作。
当时,很多玩乐队的挺瞧不上流行音乐,感觉自己做的音乐才更有深度。但为了生计,我也会给一些流行歌手伴奏,也是从那时开始接触流行音乐。靠着这些工作,谈不上挣大钱,但我养活自己没有问题。我也没什么野心,哪怕别人赚十块钱,我只能赚三五块钱,也不羡慕别人。干自己喜欢的事最重要,所以我一直挺开心的,就这么玩了十年。
那时的我,挺像那只没被五指山压住也没戴上紧箍咒的“野猴子”孙悟空。

戴荃童年照。/微博@我是戴荃

被箍住,从野生江湖回归正统
我父亲一直觉得我太野,需要拿个“紧箍咒”紧一紧。在他的坚持下,我突然萌生了上大学的想法。
我考了两年,25岁那年才考上大学。这意味着我从野生江湖回归正统,到了一个能约束自己的地方。我特意留了一条辫子,头发在古代有很多意味,长辈会给小孩留“长命辫”,女子也会剪一缕头发送给心仪的男子等。那我就留一条辫子,以表纪念。
到了南艺,我真正开始学习作曲。4年间,室内乐、管弦乐、器乐曲等,什么作曲风格我都练过。因为有长期玩乐队的经验,跟同学相比,我学习的进度要快得多。大学第二年,我被招进江苏省演艺集团工作,进入了专业艺术团体。
2013年,恰是国内音乐综艺大热之时,我被选中参加了音乐综艺《中国好声音》,2015年又参加了《中国好歌曲》。刚创作《悟空》这首歌时,我给朋友听,他们也并没觉得它有多好。我此前为《中国好歌曲》还准备了一首轻摇滚的歌《有时》,但当时的导演吴群达最后选定了《悟空》。所以,音乐很玄,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悟空》当时就踩在了那个点上。
创作《悟空》之后,我正式确立了“中国风”的创作风格。相比以前玩的音乐,这是一种新的融合,例如,《悟空》这首歌也有摇滚的元素。这个时代已经不存在所谓的纯摇滚乐、纯Funk、纯Blues了,更多的是各种风格的融合。你可以判断出一首歌更多是偏什么风格,但风格绝对不单一。
创作中国风音乐,是我内心的一种回归——我学西方古典音乐出身,长大后玩乐队,但回过头来发现中华文化对我个人是一次重塑。新专辑《侠客行》,讲的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侠义精神。“侠客行”这三个字代表三个部分:侠之风骨,身处江湖、行侠仗义;客之柔情,人在江湖中碰到的友情、爱情等;行之洒脱,是一种放下的状态,放下江湖、潇洒自由。

戴荃新专辑《侠客行》封面。/微博@我是戴荃
我心目中最符合侠义精神的形象,是古典名著《三侠五义》中的展昭。展昭生在民间,他跟着包拯一起办案、惩奸除恶,并被朝廷赐以高官。展昭不是高高在上的,他很贴近民间。白居易也是我心中符合侠义精神的人物。他既不像杜甫那么苦大仇深,也不像李白那么身处云端。白居易能很好地平衡宫廷与民间的关系。当年他创作《卖炭翁》时,还会跑去问街头老太太能不能听懂。这是艺术家深入民间的一种姿态。
侠义精神说出来简单,但要融在音乐里,考虑的因素却非常多。我对中国风的要求相对苛刻。我不太喜欢拼接式的中国风。来一段戏曲、加一段流行乐,就是中国风了?这太流于表面。我理解的中国风,是字里行间的那种韵味,编曲、作词、唱腔等,缺一不可。那是一种整体上的化学反应,不是元素的拼贴。
平时我出门,特别爱去有山有水的地方,比如北京怀柔的青龙峡。南方有桥的地方就有水,北京却不是这样,桥下有水的地方不多。所以,青龙峡简直是我心目中的江南,有山有水有长城。这里甚至会让我有一种归属感,像古代的隐士,把自己藏在山林间,想下山时,再下山。我也领略过沙漠、戈壁、海洋的美,但真正的归宿只有一种,那可能就是山水之地。

失落感
前几天,我在朋友圈分享了迈克尔·杰克逊的We Are the World(1985年版),又跑去翻看那首歌的MV。我止不住地感叹,里面的45位歌手,每一位歌手的声音、气质、长相,包括动作,都风格迥异,但当他们合在一起,又特别和谐。
现在很难再看到这样的景象了。你去听一些合唱,歌手们唱得好像都差不多,个性也没那么突出。单靠听声音,你很容易疑惑:这究竟是两个歌手还是一个歌手唱的?之前,我跟北京一个著名的调音师聊天,我俩聊起现在很多歌曲的后期修音,都希望将声音调成一种风格,最好跟抖音上一个样。打个比喻,市面上“绿色”很受欢迎,所以我就把自己的声音也调成“绿色”;而不是我的声音是“红色”的,那就接受它是“红色”的。
以前我们听歌,也跟现在不太一样。我可能顶风冒雨去买了一张CD或一盒磁带,但转头一不小心可能会失手掉在地上再踩上一脚,这些意外我都经历过。那时,谁要买了一张新CD或一盒新磁带,同学间就借来借去、互相分享。那种感觉真的不一样。

戴荃全身照。/由被访者提供
如今,大家听歌更方便了,想听什么听什么,各种音乐风格全都分好类任你挑选。然而,大家对音乐的感情却不一样了。现在大家听音乐更多是一种功能性的需求,累了、乏了就想听点开心的、上头的。不像我们当年,对听音乐是有很多追求和情怀的。
短视频的兴起,更让大家对听歌变得没有耐心。一首歌,通常只听15—30秒。这么短的时间,你又能对一首歌了解多少呢?也有人觉得音乐不重要,我只需要听听歌、看看视频,笑一笑就好了。这种观点也反映出一个社会问题:大家都过得比较累,你还要让他们去完整地听完一首歌?他们不要思考,只要这个音乐让自己开心就行了,至于它是什么音乐、谁唱的,跟他们没关系。
除此之外,我还曾在知乎上回答过一个问题——“中国音乐圈最痛心的一刻是什么时候?”我实名回答:“要说最痛心,那就是它变成娱乐圈的那一刻。”
不过,我骨子里是个乐观的人。对于整个华语流行音乐,我还是乐观的。毕竟,从听众角度出发,他们听歌的渠道越来越多,市面上越来越多的风格也在涌现,百花齐放。或许,再次认真审视一首音乐,只是还需要一些时间罢了。

✎作者 | 舒少环
✎排版 | 玉子烧
原标题 | 戴荃,内心住着一个侠客
欢迎分享到朋友圈
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本文首发于605期
《恋爱困难症》
原标题:《“音乐圈变成娱乐圈,最让人痛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