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洁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的重要代表性作家,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沉重的翅膀》《无字》《爱,是不能忘记的》《祖母绿》《森林里来的孩子》等作品具有广泛影响。曾获第二届、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多次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部分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并获意大利骑士勋章及德国、奥地利、荷兰等多国文学奖。
张洁的小说《幸亏还有它》《日子》《祖母绿》《七巧板》《波希米亚花瓶》《漫长的路》曾首发于《花城》,其中《七巧板》于1984年获首届花城文学奖,《祖母绿》于1985年获第二届花城文学奖、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今日,我们分享这两篇的精彩内容给读者朋友!
本文约8500字,阅读需10分钟。


祖母绿(节选)
张洁
黄昏像一块硕大无朋的海绵,将白昼的炎光,慢慢地吮吸渐尽。喧嚣的市声,也渐渐地低落下去。城市像一锅晾凉了的稠粥。房间里已经暗得不辨西东,只有墙角那盘燃着的蚊香,信号灯似地亮着暗红色的光。
浅色花布的窗帘,在习习的晚风中轻拂,玻璃窗在轻风的摇曳中微微作响。就是在不刮风的时候,每逢有人在地板上走过,这些窗子,也会咔啦啦地震响。这是栋老房子啦,灰黄色的墙壁古色古香;地板上的每条木板,中间早已磨出凹槽,却还是被路阿姨擦得一尘不染,油光锃亮;红木家具,以及家具上的棱棱角角,依旧硬得人;窗子也很像教堂里的格式,又窄又长,顶部还是—块拱形……
二楼朝南的那一排窗前,有一棵叶子阔大的老核桃树,一棵海棠,还有两棵老也不见长的日本松。打从卢北河笫一次迈进这个院子到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它们还是那么高。不过,看得出来,它们苍老了许多。人会苍老,树又何尝不会老呢?
夏天,核桃树和海棠树的浓荫,不但会滤去阳光的炎热,还遮挡着窗子里的人,和窗子里发生的事。到了冬天,海棠树的叶子,核桃树的叶子虽然掉光了,可是,谁还会有瘾头站在冷风地里,窥视别人的窗呢?屋外四周的青砖墙上,爬满了青藤。本來就不敞亮的窗户,深深地陷进那厚密的藤叶里,像边沿铺满厚厚的青苔,极少有人来汲水的一口古井 如左家与人极少交往的家风。而在卢北河嫁给左葳之前,左家似乎还不这么冷森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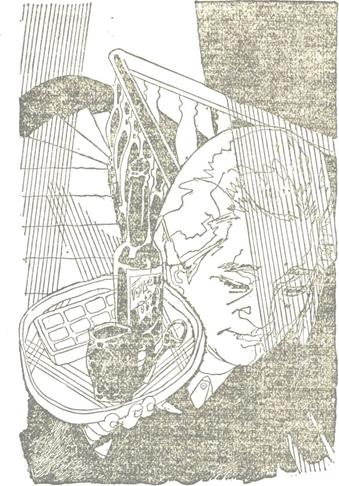
因此,卢北河爱这老房子的幽暗。
……
灰砖墙有什么不好?
她从不和别家的保姆来往,不像她们那样,抱着主人家的孩子,坐在树荫下,或朝南的大墙下,抖落主人家的老底儿,编排主人家的不是。
不对她说的事情,她绝不打听。只要不是对她发的话,别管大家在她面前说什么,她都像没听见一样。要是偶尔来个客人,又碰巧主人全不在家,谁也别想从她那儿打听出来,家里人上哪去了,去干什么。问撾什么,她全会木无表情地摇摇头,说:“不知道。”哪怕这位客人是常客,她给他上过多少次茶,备过多少次饭,她也跟不认识一样。
客人们不断向卢北河告她的状,卢北河听后,只是抿嘴笑笑。
这哪儿是保姆?分明是个宝物。不像左家原来那个保姆,太爱说话,太爱串门儿,太爱管闲事。卢北河嫁过来不久,就找了个理由,让左葳把她打发走了。那保姆走的时候,还拉着卢北河的手,泪流涟涟地舍不得分手,弄得卢北河心里也很不好受,一直把她送到长途汽车站呢!
卢北河和左葳就这么一个孩子。左家两代都是单传。
偏偏这孩子来的个晚,结婚好几年之后才有他。头几年,婆婆在她那瘪肚子上扫来扫去的目光,简直像一条鞭子抽打着她的神经。她恨不得自己的肚子,一夜之间就隆得像扣着的一个面盆。
她甚至在婆婆的眼睛里,看到过几许懊恼的神色。婆婆懊恼什么呢?难道懊恼左葳没有和曾令儿结婚,而终于娶了媳么?
既然如此,为什么利用曾令儿对左葳的爱,去暗示她替左葳戴那顶右派帽子?又为什么任曾令儿像流放一样,分配到边疆,而左葳不随她去呢?在左家,好像世界上从来没有过曾令儿这个人……老太太的懊恼,就跟《雷雨》中的周朴园一样,几十年来供着鲁妈的照片、一丝不走样地保留着鲁妈的一些生活习惯……其实不过都是一种无比真诚的伪善。
向东是他们心上的肉,掌上的珠。可是疼孩子,不是这么个疼法。得让他自小便练就能在政治上立于不败之地的硬功夫,这才是真格的。就连给儿子起名字这件事,卢北河既看得很淡,也很有用心。姓左,名向东。什么时候往深里想想这个名字,什么时候她身上便会乍起一层小小的鸡皮疙瘩。但是,在这个名字里,不管是谁,再也嗅不到左家世世代代的书卷气,也嗅不出卢北河家的铜臭味儿了。
……
她一面轻摇着靠在她身上的新娘,一面想着生和死,这个自有人类以来,便已然存在的老题目。
靠在她怀里的新娘,已经嚎不动了。她全部的精神、力气都已耗尽。似乎只有一双眼睛还在活着,死死地瞧着在海面上搜索的那两艘快艇。
曾令儿不忍心告诉她,这实在已经没有意义。要她接受曾令儿已经做为合理而领略的意义,还必须她亲自将那通往透彻的道路走上一遍。那是一条唯一的,却又充满泥泞的道路。
天就要亮了。大海渐渐地从黑暗中显出它无比庄严的雄姿。使大海得以显出轮廓的光亮似乎不是来自天上,好象有一股巨大无比的暗黄色光柱,从海的深处透出,将海水映得一片昏黄。渐渐地,又从东方的云层里,透出瑰丽的朝霞,然后是一片金光从海面耀出。这金光将海面染成金红,远处的渔船在金光的照耀下,像金箔折出的小玩艺儿。
退潮了。海浪不停地、哗哗地响着。每响一次,便向海的深处,退去一步。而将昨夜的暴雨,抛进海里的浊物,一口一口地吐出。那些树枝、木板、空酒瓶子、罐头盒子、塑料口袋……重又回到海滩上、陆地上来。
海,越走越远了,越来越干净了。碧澄澄地、清澈澈地在朝阳下闪着宁静的光辉。
曾令儿惊喜地呼出:我智慧的海啊……
忽然,打捞的人们向着一处海滩迅跑。曾令儿搀起新娘,也向那方跑去。
果然是他!永远不再醒来。大海连他也吐出来了,它不肯接受这陆地上的一切。
新娘已是欲叫无声,欲哭无泪。她只是用双手,抚摸着他。从他的头发摸起,一寸一寸地,摸过他的全身,直至他的脚尖。仿佛在验证,这面目浮肿,遍体鳞伤的男人,究竟是不是她挚爱的丈夫?然后她厉叫一声,向大海跑去。人们拖住她,把她抱回旅馆。
曾令儿为她脱去已经撕成碎条的衣裙——不知是她在昨夜的疯狂中自己撕碎的,还是乱跑中让海滩上的灌木丛刮破的。又在浴池里放了半池热水,连搀带抱地把她浸在那半池热水里。那可怜的人儿,血液好像都已冻结,全身显出乌紫的颜色。曾令儿守在浴池旁边,直到她全身的肤色恢复正常。
她给她擦干全身,又换上了干净的衣服,迫她服了两粒安眠药,抱她躺在床上。
她睡了,像死亡那样安静。
原载《花城》1984年第3期
七巧板(节选)
张洁
橡皮管扎在了左胳膊的上端。带来一阵酒精味的实习护士小严轻轻地拍打着尹眉肘窝旁边的肌肉。尹眉听见她悄声悄气地咂着嘴,大概她的静脉血管不那么清晰。
“你们在护校学习的时候没学过吗?应当尽量节省使用病人的血管。谁知道以后根据病情的发展,她还要有多少次静脉注射,或者是不是需要长期打点滴?”
有谁带着那样不容置疑的权威的口吻在说。尹眉不由地睁开眼睛看了看。她原以为一定是位倒背着手,站在一旁指点的医生或者是护士长。不是,既不是医生也不是护士长,而是对面病床上的那位病人。垂着双脚,坐在高高的病床的床沿上。那双秀美而丰腴的脚,却趿在一双粗糙的、男人穿用的棕包塑料拖鞋里——真可惜了那双脚。
说着,她滑下了床沿,走近来,拿起尹眉的手,用手指——个个都像“孔雀东南飞”里描写过的:“十指如葱心”——沿着尹眉手背上的每一条血管划动着。她接着对小护士说:“你看,她小拇指内侧的这条血管就很表浅,也很清晰。试试看,可以从这里开始扎。当然,细了一点。要是你觉得有困难,那么就扎手腕上这一条。”

小严似听见又没听见,认真又不太认真的样子,把橡皮管从尹眉的肘部取下,扎在了她手腕的上端。
小严为什么会用这种态度来对待她呢?好象对待一个惹不起、摆不脱的累赘。
难道她说的不对么?当然是对的,小严已经开始在尹眉的手腕上涂碘酒,然后又是酒精。
那张面孔,尹眉分明觉得在哪儿见过。在哪儿呢?尤其是那双眼晴,太特别了。不论谁,只要见过一次,就不会忘记。它真美,虽然被包围在一簇皱褶里。
渐渐地,那双眼睛膨胀起来,越变越大,而后又变成成千上万只,在尹眉的眼前闪来闪去。尹眉赶紧把自己的目光移向窗外。外面是满眼的绿树。她看见一棵玉兰树上绽着大朵的、白色的花,还有一棵松,就贴近病房的窗口。然而,那松针似乎瞬时变得好长,根根都向尹眉伸过来、伸过来,好像要刺进她的脑袋。她的眼前变成一片漆黑,两个大头针的针头样大小的金色的亮点,像荧光屏上心电图在显象那样无声无息地滑过去、滑过去。脑袋又开始疼了,疼得好象要裂开来。要是真裂开可能就不那么疼了,顶好拿个撬杠,从太阳穴那里把脑壳撬开,把脑袋里面压得她疼得要死的那股力量释放出来。
“哎哟一”尹眉忍不住大声呻吟起来。
“疼吗?”小严赶紧按了按血管四周已经有点发红的皮肤。断定没有什么异样之后,对尹眉说:“这葡萄糖浓度大了一点,百分之五十,对血资有点刺激,但可以吸收一些血液中的水分,为的是减轻你的颅压,一会儿你的头就不会疼得那么厉害了……”小严悄声细语地安慰着尹屈。
尹眉真希望小严再说点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小严的声音显得是那么动听,柔美,简直像在地狱的熬煎里,听见了来自天堂的音乐。难怪过去有人把护士称做“白衣天使”。真对!真对——
对面床上的病人,开始用力地用手掌一下又一下地按摩着尹眉的额头,像一架精密的、由电脑控制的仪器,随着任何一根神经最细微的不适所发出的信息而立刻移向那个部位。
有多久了?她的手不累吗?一定很长时间了。想想看,小严已经推完了那一大管葡萄糖。
“谢谢。”尹眉从咬着的牙齿缝里挤出这两个字。
“你别说话,休息吧!”对面床上的那位病友说。
尹眉心里充满了感激,毕竟萍水相逢啊!可是尹眉渴望着在额头上按摩的,是丈夫那双大手。鲁莽的,不知轻重的,带着浓重的烟草味儿的大手。丈夫什么烟都能吸,尹眉相信,要是没有什么可吸的时候,他一定连树叶子都可以拿来当烟吸,像象胃口极好的那些庄稼人一样,哪怕是天天大葱蘸酱,吃起来也津津有味。就凭这一点,他也不像个卫生局的副局长。世界上的事怎么那么怪,这个一点官瘾都没有的人,却偏偏当了官儿。当然,这足这几年提倡干部知识化、专业化的结果。尹眉常常带着奚落的口气对丈夫说:“你这个官儿有点像人家小姐在绣楼上拋的彩球,怎么就落到你头上来了?!”
他呢,一点也不懂得玩笑,死板板地说:“抛彩球总比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多点自由的味道,但难免不带有极大的盲目性。”下面还有一句,“何况人家是官宦家的小姐,不从命,行么?”
袁家骝不再往下说。他是个豁达而冷静的人,什么事都看得很淡。从猿到人用了多长的时间?几千万年,对不对?对尹眉的揶揄他只是憨厚地笑笑,像年长的人,带着宽厚的微笑,看那些淘气的孩子。
一年多来,尹眉的头常常疼,而且疼得越来越厉害。昨天晚上,尹盾的头突然剧疼,夹着喷射性的呕吐,简直要把胃都吐出来了,浑身抽搐,打着寒战,把牙齿嗑得哒、哒、哒地直响,不得不送到医院急诊,值班大夫立刻收她住院。
安排尹眉住进病房之后,袁家骝就被关在病房外面了。尽管头疼欲裂,在护士关上病房的房门之前,尹眉还是勉强从枕头上挣扎着抬起头,看了丈夫最后一眼。当然,她不会死。可是对平常不大生病的人来说,住医院总有一种不清不楚的、失去自主能力的惶然。
与其说尹眉爱袁家骝,还不如说是她依恋他。他们之间的感情和一般年龄相当的夫妇不大一样。也许因为袁家骝大着尹眉几岁。尹眉常问:“你爱我吗?”
“爱。”简单极了,前头连个表示程度的定语都不加。
“爱得要死吗?”尹眉实在不甘心。
“……”袁家骝想了想,很认真地。然后说:“死亡是一种生理现象,爱是一种心理现象。怎么能够这样比拟呢?”
气得尹眉用拳头在他的胸口上擂。袁家骝抓住她的两个小拳头,依次在每个拳头上吻了吻,说:“是这样的。”
……
“你是说‘庸俗社会学’?”尹眉深信,他感兴趣的,不过是她在言谈话语中,那像闪电一样耀眼的、转瞬即逝的、什么痕迹也不会留下的机智的闪光。然后她友善地问:“你也是哲学系的毕业生?”
“不,我是生物系的。”
尹眉的父亲说过:“爱情的开始常常是在莫名其妙之中。比如,在不该笑的时候,笑了一下;或应该看一眼的时候,看了两眼。”
等到裳家骝向她求婚的时候,她想起父亲说过的这段话,才意识到这两者她都兼而有之。于是她觉得嫁给袁家骝是有根有据的。她是哲学系的毕业生,研究社会学的,喜欢有根有据,引经据典。别看她耍起贫嘴来洋洋洒洒,可是真要办起什么事来的时候,却死钻牛角尖。
又来了,那种寒战,半分钟一次。在半分钟之间的间歇中,是明知对疾痛躲不过的、恐怖的等待。
“谢谢,请不要再弄了。”尹眉觉得烦躁。
“这样你会好些。”对面床上的那位病友深信不疑地说。依旧固执己见地、坚定不移地一下又一下在尹眉的额头上按摩着。
“不,我不要——”
“要的,你需要。”
尹眉简直想要发火,她需要安静。她闹不清对面床上的这位病友为什么非要把她的关切强加于她。这种强制的关切究竟是为了减轻尹眉的痛苦,还是为了她自己的某种信条?
“不——”尹眉几乎是哀求地大叫了。
“你需要,你绝对地需要。”平板的声调里,透着死也不肯罢休的顽强,并不因尹眉的抵触愔绪而受到丝毫的影响。
在脑袋难耐的剧疼里,还得忍受这种不让她独处,妨碍她调动自己的意志,自己对自己的适应能力进行调整的干扰,尹眉愤怒了。她想起念高中她当团支部书记的时候,班上有位女同学,也是这么强加于人地做好事,明明别人自己可以做的,压根儿不需要任何人帮助的事,那家伙非死乞白赖地争着去做。死乞白赖到令人生厌、令人不能安宁、令人不得不怀疑她的动机的地步——真是为了帮助别人,还是为了別的什么?班上的同学没有一个说她好,反倒都带着一种又是鄙夷,又是怜悯的态度对待她。而且,整整三年,尹眉她们那个支部硬是没有发展她入团,大家不通过,你有什么办法?怎么在这里竟也碰到这么一个死缠着人不放的人,生病也不让人得安宁,啊?!她气得一把推开她按在自己额头上的手,几乎是用一种恨恨的眼光朝她望去。尹眉看见,那双美丽的眼睛惊诧了,睁得圆圆的,两颗黑黑的子,像从未有人探测过的、神秘而不可知的洞穴。你不知那里边有什么,或是压根儿什么也没有。然而那惊诧是真诚的,绝不是假装出来的。尹眉不禁想:有这双美丽的眼睛不就得了,她还想要什么啊?
但是,这似曾相识的眼睛……究竟是在什么地方见过?
“哎哟——”她疼,她无法回忆。于是紧闭着双目,无力地呻吟着。
即使闭着眼睛,尹眉感到对面床上的那位病友还在紧紧地牢盯着她,说不定一会还会扑上来按摩她的额头。她觉得额上一阵麻簌簌地发紧。由于成了被人穷追不舍的目标,她感到一种被监禁的拘束。她开始讨厌这医院,这病房,这到处令她感到刺眼的、生硬的白色。她使气地、示威似地连蹬带踹地翻过身去,不再面对对面床上的病友。毛毯掀开了,她感到立刻有人上来给她掖好。没错,这还是她。尹盾使气地又狠狠地蹬了一下腿,她感到蹬在一个什么东西上,软软的,可能是她的手。但尹眉并不打算道歉,只是装着不知道的样子,依旧闭着双眼,发狠地叫着:“哎哟——”
对面这个人到底生的什么病?她自己又究竟要住多久的医院?要是这么面对面地和她并排躺上几个月,她的病不但好不了,兴许还得添上点什么病。这可怎么得了,能不能换个病房呢?

尹眉觉得自己倒霉透了。于是头痛显得更加难以忍受。
“打饭啦,打饭啦!”送早饭来了。送饭人操着一口的湖南口音,在走廊里一分钟也不肯再等似地吆喝着。
病房里立刻手忙脚乱,盘磕着盘,碗磕着碗地一阵丁当乱响。
尹眉饿了,从昨天下午开始头痛起,她滴水未进,而胃里的东西早已吐得一干二净。可她无法起床去打饭,也不好求病房里的谁——新来乍到的。只好巴巴地听着送饭人那刻不容缓的吆喝。但她又着实怕对面的病友给她打饭。
没有,她不但没有张罗着去替尹眉打饭,自己也没去。尹眉没回过头去看她,反正她那里是一点动静也没有。她怎么了?难道她生气了,不高兴了,因为尹眉刚才那样对待她?
小严来了,把一碗牛奶、两个油盐小花卷放在尹眉的床头柜上。“我给你领了碗筷,饭嘛,你昨天没订,我随意给你领了两样。”然后又附在尹眉耳边悄声说:“牛奶底下有个荷包蛋,你快吃,省得一会儿送饭的查出来少了个蛋。”她低声笑着,孩子气的脸显得更圆了。
“那,合适吗?”
“没事儿。”小严又趴在尹眉的耳朵上,“你不吃也浪费了。”她向对面床上努努嘴,“这是她订的。”
“那怎么行呢?这——这不是——”尹眉想说,“这不是胡闹么?”又怕这话说的太重。而且小严是带着对她的明显好意。
“她不吃这湖南人送的饭。”
“哎哟——”头还是有点疼。
“怎么,没觉得好一些吗?”
“好象是好一些了。”蹊跷。尹眉忍不住
又问,“她为什么不吃这湖南人送的饭呢?”
“她说这湖南人会在她的菜里下毒药。”说完,小严从尹眉耳旁直起身子,嘻开嘴巴,就跟对别人说她发现谁头上忽然长了个犄角,或是谁屁股上突然长出了条尾巴似的。
“那怎么可能,再说她怎么会认识这送饭的湖南人呢?”
“当然认识。她就是我们这个科的大夫啊!”
对面床上有了动静。小严转了话题:“你自己能吃吗?”
尹眉抬起身子试了试,头果真不那么痛了。“可以。”便斜倚着床头坐起来。小严把一个枕头拉起来,垫在尹眉的背后。
对面床上的人显然已经不再注意尹眉,她的注意力仿佛被一件非同小可的事占据了,神色庄重地打开自己床头柜上的小门,跟教徒领圣餐似地从里面捧出一个挺讲究的饼干筒,又拿出一瓶麦乳精,放在小柜上,然后拎起暖瓶出去打开水了。
瞧着她走出病房,尹眉又问:“她跟那个湖南人有仇?”
“没有!因为那湖南人跟她爱人很熟,她爱人也是这个医院的大夫。”小严一面说,一面频频地回头望着。
“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她有病,精神病——”
对面床上的回来了。她谁也不理地走回自己的床前,从床下拖出白色的小方凳,端端正正地坐下,开始调冲麦乳精。
小严笑笑说:“我该下班了,你慢慢吃吧。”说着,便走出了病房。
她有病?!
有病怎么不去住精神病院?小严说的是真话,还是一般意义上的、对性情乖僻的人的一种貶称?
尹眉看不出她有病。她一点也不像尹眉心目中精神病患者的样子。不哭不闹,不撕扯衣服、被褥,也不摔盆摔碗,更不语无伦次。而且,从早晨她在小严给尹眉注射葡萄糖时所发表的意见来看,她的思维逻辑还相当清楚。想到这里,尹眉禁不住侧过头去看她。她正安安静静地吃饼干,带着一种若有所思的样子。当然,时不时地还不忘记掸去掉在膝头上的饼干渣,以及用小勺搅一搅杯子里的麦乳精。
“哗啦啦——”四十三号床那位病人的饭盒被碰掉了。尹眉看见,对面床上的仿佛受了惊吓,立刻盖上她的饼干盒子和茶杯上的盖,回头朝四十三号床望去,发现并没有什么。于是开心地笑了笑。可是这一吓,倒把她从若有所思的、迷迷怔怔的状态中吓醒了,加快速度地吃完了她的早餐。她拿起自己的杯子,又走过来拿起尹眉用过的碗筷,说:“我替你涮涮去。”

尹眉轮流地在另外两位病人的脸上,搜索着她们的表情。她们谁也没有反应,仿佛年这本是一件天经地义、早已司空见惯的事情。
四十三床一面用牙签剔着牙缝,一面在看一本《大众电影》。她的胃口真好,尹眉不能想象,那么小的一张嘴巴,怎么会吃进去那么多东西。一个早餐便吃掉两个茶叶蛋,一包牛、肉干,一碗牛奶,一个花卷,一块蛋糕。她那个床头柜像个袖珍的食品商店,应有尽有。难为她怎么把那么多盛食品的罐子、盒子、瓶子塞进那么小的一个柜里。
原标题:《纪念作家张洁 | 《祖母绿》《七巧板》,无数人文学阅读的新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