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世纪,正值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痛苦转型之时,音韵学作为中国学术中的一支,自然同其他学科一样,步上了转型之路。所谓“转型”,其最核心的标志在于研究范式的转变。之于音韵学来说,便是“考古”、“审音”的研究范式转变为历史比较法。这里对相关名词略作解释:“考古”是说利用《诗经》、《楚辞》及其他古书上的韵语(例如《老子》中的韵句),加上形声字、通假字乃至读若字等材料来研究古音的声类、韵类。“审音”则是利用蕴藏于宋代韵图里的等韵学知识来研究古音的系统。历史比较法除了要利用前述的文献材料,还要利用各地的方音来探究古音演化与发展。
《切韵汇校》(中国古代语言学基本典籍丛书)
于当时而言,历史比较法是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风雨飘摇之际,是一批西方学者将这种方法带到了中国语言学研究的领域里来。这些西方学者有钢和泰(Staël-Holstein)、马伯乐(H.Maspero)、珂罗倔伦(B.Karlgren)等人。这之中最有成绩的,即属于珂罗倔伦,或者我们应该用他最为中国学者熟知的译名称呼他——高本汉。
高本汉是瑞典人,少年时代在瑞典延雪平(Jönköping)度过,其父约翰纳斯(Johannes)是一位高级中学教师,能熟练地使用拉丁语、希腊语和瑞典语——这正是高本汉父亲要教授学生的科目。从高本汉日后要从事的事业来说,高本汉的父亲对他影响最大。但是在高本汉的成长之路上,他的中学教师卡尔·列毕(Carl Rebbe)——撰有《瑞典语言学》——对高本汉的影响同样不能忽视。正是在父亲和老师的言传身教下,高本汉在1904年就着手对瑞典的方言进行调查。从高本汉将来从事的学术研究看,这个调查可以说是打下了高本汉后来调查中国方言的基础。

1907年,高本汉进入乌普萨拉大学学习。在那里,高本汉立下了学习汉语的志向。1909年,高本汉去了俄国的圣彼得堡学习。作为与当时中国接触最为频繁的国度,圣彼得堡有一大批高水平的汉学家,例如瓦西里·瓦西里耶夫(Vasilij Vasil’ev,1818—1900)、普什丘洛夫(Pesjtjurov,1833—1913)以及高本汉的老师伊万诺夫(A·Ivanov)等。在圣彼得堡的学习无疑对高本汉的帮助极大,老师们在中国的亲身经历更是频频吸引这位以无限热情投身于语言学研究的青年。于是当高本汉回到瑞典以后,他立马谋划起去中国的旅程。
尽管略有波澜,高本汉最终还是在1910年4月底抵达了上海。在圣彼得堡学习时,高本汉就听老师介绍过山西曾有一位从事语言研究的同乡人新常富(原名Torsten Erik Nyström,地质学家)教授。这次到访中国,高本汉最想拜访的就是居住在太原的这位新教授。不过,当1910年6月高本汉到达太原时,这位新教授已经离开了中国返回了瑞典。幸运的是,高本汉得以“接过”新教授居住的房子,这或多或少解决了高本汉生活上的难题。

在太原,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创办的太原大学堂成为了高本汉的工作地点。尽管1911年年初高本汉曾从太原到北京略作停留,但他不久就返回了太原。这是因为1910年年末发生在东北的鼠疫,似乎有传染到北京的可能(见1911年1月27日高本汉致妻子茵娜的信件),为了避祸,高本汉就着急从北京回到了太原。在太原的日子里,高本汉得以调查甘肃、陕西以及晋南晋北的方言。去北京前,他还调查了西安和开封的方言。甚至,在西安的时候,高本汉去了一趟碑林,获得了不少珍贵石刻的拓本。
1911年10月29日,辛亥革命的炮声响彻太原城,待在城中的高本汉随即把自己的亲身经历撰写成《每日新闻》报的通讯稿。——为了保持在中国生活的费用足够,还为了能补贴家用,高本汉担任了《每日新闻》的海外记者。11月中旬,高本汉离开太原到达北京,随后他乘坐火车由西伯利亚大铁路返回欧洲。1912年,积累了不少调查材料的高本汉从伦敦——回到欧洲后,高本汉曾到伦敦待了一些时日——到了巴黎。在这里,他旁听了法国汉学家沙畹(Emmanuel-èdouard Chavannes)开设的相关课程。1915年5月,在巴黎学习了2年时间的高本汉开始了他的博士论文答辩。这篇博士论文后来构成了高本汉的代表作——《中国音韵学研究》第I卷。
答辩结束后的高本汉,先是去哥德堡大学任教。到1920年时,他计划要再去一次远东。两年后,这个计划成功了,高本汉顺利地访问了上海,而后去了日本东京。在日本待了近4个月之后,高本汉回到了哥德堡大学。此后到1939年高本汉担任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博物馆馆长前,他一直在哥德堡大学完成他对于汉语的研究。
从1915年开始,高本汉先后发表了《中国音韵学研究》(分为四卷出版)、《中国语与中国文》、《中日汉字分析字典》、《左传真伪考》、《汉语词类》、《中国语言学研究》、《汉文典》等成果。当然,这些成果无一例外都是用外文写作。这对于中国学者而言,实在是非常不便于利用,故而有一大批中国学者投入到译介这些成果的工作中。参与这些工作的有张世禄、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贺昌群、陆侃如、冯承钧、王静如、董同龢等人。
《汉语音韵学》(音韵学丛书)
董同龢 著
从历史角度看,高本汉无疑是一个被运气钟爱的人。前举张世禄、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等人,均是在学术史上留下大名的赫赫人物。由他们来翻译高氏的著作,真可以说得上是“同类相求,同声相应”了。自然,高本汉的学术理念乃至其学术范式,就更为后来的中国学者所理解、所接受。我们不妨看两段评价。第一段是张世禄先生在《音韵学》(1932年)一书里说的:
他(指高本汉)对于中国周汉时代的古音,也曾有过几度的试探,以为中国过去古音的研究,运用材料实在笨拙得很,现今应当重新的来做一番考证。他对于隋唐以后的语音已正式的建立几个系统。高本汉的结果,固然还未能完全可信任。但是,单举他所应用的方法的细密而说,已经可以推为现今最进步的中国音韵学了。
第二段是著有《等韵源流》的音韵学家赵荫棠说的:
等韵图的编制,至劳乃宣已走到穷途;宋元等韵的解释,至黄季刚亦陷入绝境。设若没有新的血液灌输进来,恐怕我们中国的音韵学永永远远停留在株守和妄作的阶段里。幸而我们借着创制注音符号与国语罗马字的机会,激起来新的趣味,于是近代语音学的知识和比较语言学的方法,以及国际音标的好工具,都从美欧介绍到我们中国。这种介绍,自然对于中国音韵全体都有大的帮助,而等韵学的研究亦因此而开辟新的纪元。在音韵学的新运动之下,有新的贡献的,是赵元任,钱玄同,林语堂,李方桂,黎劭西,刘半农,高承元,魏建功,罗莘田诸位先生。他们或介绍,或发明,或补苴,共成音韵学的新园地。所以我们现在叙述起来,很难确定他们各人学说的来源和相互的影响的脉络。但是,我们从何处叙起呢?我们现在只能以高本汉(B.Karlgren)所研究中国音韵学的结果为起点,然后叙述国内各家之补充与修正。
从这两段话里,我们便能晓得对于中国语言学研究来说,高本汉及其代表的研究范式究竟占了一个怎样的地位。
在高本汉逗留中国的时候,研究音韵学尚且还可以借助高氏的新方法把清人使用的老材料再翻新一遍。但是在高本汉到达中国前,河南殷墟的惊天发现——“甲骨文”的现世,就已经暗暗要求喜欢赶新鲜劲的学术研究要尽早用上这批出土材料。自然,高本汉对于这些材料有所注意。在完成《中国音韵学研究》之后(四卷本。第四卷于1926年出版),高本汉花费了14年时间来把他研究上古汉语的结晶从学术研究的溶液里析出。这部结合了出土的甲骨文材料、金文材料,又以汉字的谐声关系编排字头顺序的字典,便是《汉文典》(1940)。
《汉文典(修订本)》
如上所述,《汉文典》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对于甲骨文材料和金文材料的使用。试想一下,如果高本汉对这些材料的了解是欠缺的话,很难想象他是如何在《汉文典》里把这些可爱的小东西排好位置的。从相关的材料记载看,高本汉在编著《汉文典》前,已经发表了《中国青铜器中的商与周》(1936)、《中国青铜器的新研究》(1937)和《中国青铜器的年代》(1937)等与金文研究相关的成果。这正说明了他是在充分掌握这些“三代”材料的基础上展开工作的。

除了金文之外,高本汉注意到使用中古成书的韵书(如《切韵》等)将对研究上古汉语语音造成干扰,所以在考察具体字的语证上,他总是以汉代以前的文献材料作为最开始的出发点,进而一步步去梳理字的字义。
《汉文典》无疑是高本汉重要成果之一,在1940年版告罄之后,他投入到对此的修订工作之中。于是在1957年时,一个彻底修订过的《汉文典》面世了。这个版本较之前的版本要来得更为全面,最大的变化便是把他自己对于《诗经》、《尚书》两部经书的研究成果都吸收了进来(这两部成果分别是《高本汉〈诗经〉注释》、《高本汉〈书经〉注释》)。某些意义上,这书是一部检索高本汉古汉语研究成果的引得(index)。

1978年,高本汉逝世。作为一个研究汉文研究了一辈子的外国人,高本汉除了留下大量的学术成果之外,他还留下了对于汉文的赤忱。或许这正像他的中文名意指的那样——本是汉人。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高本汉的研究成果对于整个中国音韵学,乃至整个中国语言学的影响都是巨大的。从李方桂先生起,不少研究就是建立在对高本汉的成果的批评上的——这正是学术发展自我深化的要求。无论如何,当后人阅读一个现代的音韵学的著作而在首章(或者其他溯源的地方)发现高本汉时,我想,那正是在提醒后人不应忘记这位伟大的学人在学术上的那些影响巨大的贡献。
《汉文典(修订本)》
[瑞典]高本汉 著
潘悟云、杨剑桥、陈重业、张洪明 编译
繁体横排
16开 平装
978-7-101-1518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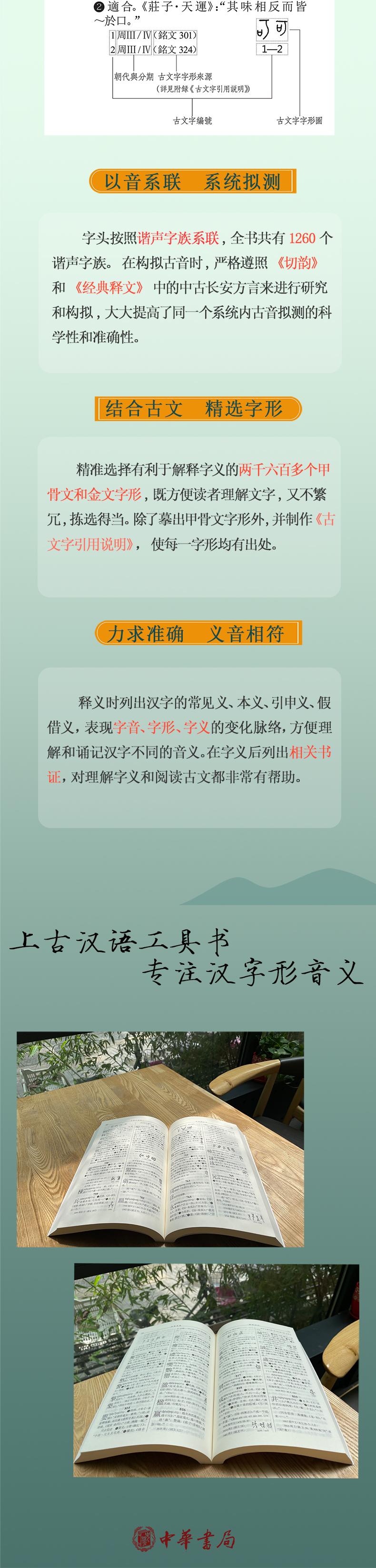
原标题:《高本汉与中国语言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