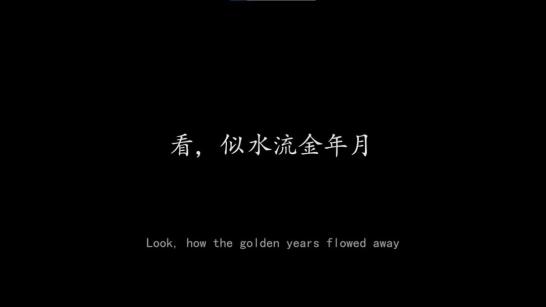导语:作为首部入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斩获最佳剧本奖的中国动画电影,杨凡导演的《继园台七号》呈现了60年代旧香港的点点滴滴。
影片聚焦动荡年代下的个体情感,在重绘那段逝水流金年月,延续其东方式的古典审美的同时,为观众营造了一出虚实之间的奇旖梦幻。
威尼斯颁奖典礼上,杨凡说,“有人批评我的电影很drama,但是我现在做到了,我拿到了奖杯!”

文/编辑:骑桶飞翔责编:刘小黛
策划:抛开书本编辑部
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一、动画形式的情书封存
“因为摄影并不是像艺术那样去创造永恒,它只是给时间涂上香料,使时间免于自身的腐朽。”
安德烈·巴赞在《电影是什么》中阐述了一个关于电影本体的“木乃伊情结”。在此,巴赞借助精神分析,研究电影起源,上溯到雕刻和绘画的起源。在巴赞看来,为了战胜时间,克服死亡,人有永久性保持自己尸体的驱动。人们相信,“人为地把人体外形保存下来,就意味着从时间的长河中攫取生灵,使其永生。”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渐渐明白,艺术并不总能战胜时间,它无关乎人们生命的延续。但是,相对的,它创造的是一个“符合现实原貌、而时间上独立自主的理想世界。”
在《继园台七号》中,有这样一句旁白:“那个年代,朴实中呈现着繁华,繁华中又带着些真诚。实实在在,绝不炫耀,却是一个永远逝去的盛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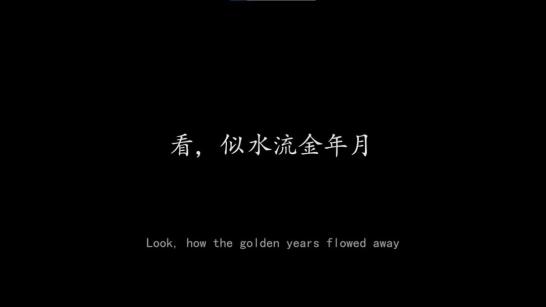
从这个角度回望这部电影,便不难理解,杨凡导演创作这部电影的初衷。杨凡志于为旧香港这具木乃伊涂上香料,使其免于腐朽。这是一部送给旧香港,送给文学,送给电影的,以动画形式封存的关乎时光的情书。十年辛苦不寻常。杨凡导演采取动画电影的形式,梦幻般地还原了20世纪60年代“六七运动”时期下的香港,连诸普鲁斯特、《红楼梦》、好莱坞电影等文化元素,展现了殖民地背景下的中西方文化融合,这种动画电影的形式无疑地给予了观众一种对于过去时代的自由遐想,更拓宽了创作者广阔的创作边界。

在此,我们可以看到杨凡对历史记忆的还原。处处是亚热带的木棉树,春天来临,片片雪花般的棉絮飘荡。低空驶过的飞机,投射下巨大而不无象征意味的阴影,遮蔽了狭窄低矮的楼房,也遮蔽了行人车子。伴随着六十年代知名歌星潘迪华《Ding Dong Song》歌声下的,是熙熙攘攘的街边杂货店和食肆,是形形色色而富于质感的一个个广告牌,是电车上西装革履的扒手,是偶然能遇到的说着上海话的美丽的问路的小姐。
杨凡集合两岸三地近百名工作人员,终于为旧香港的众生像,涂上了一层香料,妥帖讲究地留住了旧时光。二、动乱年代的个体表达
影片的背景是香港英国殖民时期,但杨凡并未花费过多笔墨去描绘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地区人民,在这种压迫与被压迫的情节隐居电影深处的同时,杨凡倒是对混乱年代的个体表达更感兴趣。

在电影院一段,偷窥的女儿美玲看到了虞太太与子明的吻戏,失魂落魄地走到街上,这是“毕业生”式的道德困境,同时也是“倾城之恋”般的浪漫。游行的人们在大街上挥舞着旗帜,哨声飘荡,爆炸纷起,而后是一段以木版画形式连缀下,群众高声呼叫与美玲行走的蒙太奇。在这里,“爱国无罪”等旗帜与汹涌的游行场景倒成了揭露美玲心境的背景,香港这座城市仿佛因美玲低沉的情绪而倾倒。
然而,这首先是一部矛盾的电影。正如杨凡所说,影片的主题关乎战争与和平,关乎邪恶与美好,关乎精神与肉欲,关乎痛苦与释怀。在这一部绝望的电影中,在繁华、优雅与暴动的年代之下,每个人都渴望驯服和占有别人。就像许鞍华在《天水围的日与夜》系列电影中刻画出一个地方的一体两面一样,杨凡将香港旧时的美好,感动,连诸其妖艳,阴暗的一面一同献到了观众面前。杨凡导演的作品从来都不乏对女性意识的关注。从第一部电影《少女日记》中,杨凡便热衷于拍摄文艺爱情,到后来的作品中,更偏睐女同性恋等异色边缘主题。在《继园台七号》中,他再次延续对女性境遇的关怀与书写。

杨凡导演作品《流金岁月》这种主题投射到电影中,首先展现在观众面前的便是虞太太这个人物形象,虞太太年轻时作为“进步青年”,也曾积极地投身过社会浪潮,如今与女儿美玲相伴为命,却与女儿的老师子明,产生了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情感纠葛。

虞太太就像是那个时代香港的化身,优雅、素净,家里的装饰也是明亮干净的。可是深究其背后呢?手中的《呼兰河传》,墙上的鲁迅的书法立轴。在这之下隐藏着的是虞太太被压抑的情欲,和不无畸恋的情感。三、虚实之间的奇旖梦幻
杨凡毕竟是个惯于发挥其东方式美学底蕴的人,在他表现那个不平凡年代下个人情感的奇情诡谲时,仍然懂得在虚虚实实间为观众营造一场盛大的奇旖梦幻。
大学生子明打网球的一段戏,足以媲美《卧虎藏龙》中的竹海交战。在《卧虎藏龙》中,李慕白说,“我们能触摸的东西没有永远。把手握紧,里面什么也没有。把手松开,你拥有的是一切。”在竹林戏中,李慕白与玉娇龙一来一回间,哪里是在打斗,那分明是缤纷的情欲。

李安导演作品《卧虎藏龙》同样,在《继园台七号》中,子明和他的朋友打着无形的网球,中间是残破的球网,周边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小孩、女人。在这里,摄影机在凝视,人群在凝视,观众也在凝视。这哪里是子明在打着莫须有的网球,这分明是杨凡在营造一种溢满在空气中的情欲味道。

在电影中,杨凡用《红楼梦》中妙玉的判词“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来暗示虞太太备受压抑的情欲。以两人谈话《红楼梦》中妙玉被掳时的细节,借“如痴如醉”几个字,挑出虞太太内心渴望解脱的真实想法。
在展现虞太太浮想联翩的春梦时,杨凡先以黑猫作引,黑猫代表轻盈的虚境,犹如其缤纷的情欲,随时而来,倏忽而逝。在这次炽烈的性幻想中,杨凡融合开花、泼墨等形式为陪衬,为观众呈现了一出不可言语的东方式的超现实画面。在金黄的月亮下,匪徒绑走妙玉,于檐前屋后起舞回荡。在深幽的竹篁林里,虞太太的化身妙玉赤身裸体,唇红齿白,肤若凝脂。
在东方,古人对蛇多敬畏,蛇冷血喜阴,身段柔软,代表了女性的柔软与曲线美,同时阴者淫也,因此蛇往往有淫邪之意。在西方的创世神话中,蛇是引诱人类犯罪,被逐出伊甸园的元凶,因此往往同样是欲望的象征。在此,杨凡以蛇为喻,盘旋虬曲,交尾蔓延。在作为虞太太汹涌而不可抑制的欲望象征的同时,为观众营造了一出虚实之间的奇旖梦幻。
杨凡说“我爱电影,但电影爱我吗?不管电影爱不爱我,我爱电影。于是我勇敢的写,把这一生的情信拿出来与众分享,希望这段看似缠绵却无可厚非的爱情,仍然真挚。对不起,别误会,是与电影恋爱的一生。”也许这句话就是这部电影,同时也是他热爱电影纯粹一生的最好的注脚吧。
《继园台七号》电影分镜剧本
《继园台七号》原著小说《芳华虚度·继园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