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blank 三明治 收录于话题#短故事学院176个
对于女性来说,堕胎是对心理与身体的双重打击,它是可怖,是痛苦的,同时还面临社会道德的全面围剿。blank在犹疑中写下了这个故事,像是一场平静的风暴,作者用克制冷静的笔触书写了一场只有自己才知道的失去。一个大都市的现代的女性,在失去时,只能选择维持内心秩序,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文 | blank
编辑 | 胖粒
“明天去买验孕棒吧。”我终于下定了决心,转身推推他。
“没必要吧,应该不会中的。”
是啊,应该不会。我点开手机日历,那个小红点的标记依旧停留在上次姨妈走后的第一天,按理说是再安全不过的安全期了。
但这次的姨妈已经推迟十天了。
这十天里,我眼看着自己的焦虑像个越来越涨大的气球,对每一丝迹象疑神疑鬼和心怀希冀。内裤上出现的几丝血迹让我欣喜若狂,早晨刷牙时的偶尔反胃让我一整天都寝食难安。我故意骑自行车、吃冷饮,敲打和揉捏自己的小腹,妄图改变一些不知道是否已成定局的事情。
他当然也不能好过,我每天都在他耳边喋喋不休自己的焦躁和不安,频率从一天八十次向一天八百次进发。他尽力安慰,却很难感同身受。
时间一天一天流过,我知道,我不能再逃避一个结论了。
无论是什么,总得有个定论。
01
药店的店员把我们带到一排货架旁,从几块钱的试纸到几十块钱的验孕笔应有尽有。我一边猜测她的礼貌之下是否藏着鄙夷,一边拿起比手掌还大的长条盒子,假装淡定地付款,然后落荒而逃。
我把说明书来回读了两遍,才小心地撕开盒子里的防水锡纸袋,仿佛动作轻一点就能得到想要的结果。但这根验孕棒的包装就像它即将呈现的结果一样,严谨而不近人情。
看着尿液从塑料棒一头露出的试纸浸润进去,我把验孕棒放在洗手池的台面上,等手机上的时钟走过两圈,才回头去看。
两根红线。
我翻来覆去看了几遍,又找出说明书看了一回,妄图找出一点翻盘的可能,但没有。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我该怎么办?要因为这个结婚吗?堕胎是不是很危险?会不会被人指指点点?妈妈会怎么说?朋友们会怎么看我?被同事们知道了怎么办?
无数个问题在我的脑子里搅成了一团乱麻,哪个都想不出答案。我觉得自己好像掉进了一个狭小的洞里,只能盯着头顶指甲盖大的天空,那里一点阳光都没有。
02
“姐妹们快来接血气!”
“提心吊胆,安全期内射会不会中啊?”
“姨妈推迟了二十天终于来了,来还愿!”
我拿过手机,页面还停留在豆瓣的“大姨妈”小组,大多数帖子都已经变成了已读的灰色。这个标签为“女性”、“月经”和“情感”的豆瓣小组有近四十万成员,我不知道其中有多少人正在与我共享类似的困境。
据说,只要每天早晚诚心回帖,就有可能得到“姨妈神”的眷顾。这样的规则听起来荒诞,却是许多女孩试图抓住的救命稻草。她们在这里倾诉自己的故事,虽然未必会得到回应和安慰,但至少让那些羞于启齿的慌乱和惶恐得以安放。
我也曾是其中一员。
小组里经常分享各种“催姨妈”的偏方和小妙招,比如掐拇指上的穴位,或是喝熬得浓浓的桂圆红枣水。也许有心理作用的成分,但这些方法的确在过去帮我“催”来过大姨妈,虽然代价是手指上的指甲印一碰就疼,牙龈也实打实地上了火。
然而事到如今,它们已经无法再帮助到我了。
03
把手机和验孕棒推到一边,我们面对面坐下,预备一场严肃的讨论。
“你怎么想?”我先开了口。
“看你怎么决定,我都听你的。”他毫不犹豫地说,像是早就想好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觉得太早了。”我看着他的眼睛,“但是你是怎么想的,如果不考虑我的想法的话?”
“我……”他有些吞吞吐吐,像在斟酌语句:“我也觉得,有点早。”
“真的吗?”我再三确认。
“真的。”他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就像我想要的那样。
那时我们刚认识一年多,还没想过要很快结婚,生孩子则是更加久远的事情,也许远在天边,但绝不会近在眼前。
做出这个决定之后,事情并没有顺理成章地变得容易,我的生活就像一辆在分叉口前徘徊的列车,终于选择躲过一种改变,而进入另一种改变。
04
“真的要告诉他们吗?”我拉住他拨电话的手,内心有些忐忑。做惯了“报喜不报忧”的小孩,我下意识抵触把这件事情告诉双方家长。但我那时还住在家里,妈妈那边是不可能瞒过的。至于当时只见过一两次面的准婆婆,我完全无法预测她怎么想这件事和我们的决定,以及,会因此而怎么看我。
“肯定要让他们知道的。”不同于我的反复犹豫,他在这件事上早早做好了决定,“没事,待会我来说。”
婆婆是那种对孩子不愿放手的母亲。因此他在成长过程中受到了事无巨细的关心。从高中的陪读,到大学的隔三差五电话联系。直到现在,每到换季,婆婆依然会发微信来絮絮叨叨地嘱咐他记得更换衣服被子,避免着凉,也不要太热。
而我常常自得于自己跟妈妈的关系像朋友一样,调侃自己是被“放养”长大。谈恋爱之前,我从来没有下了飞机要报平安的概念,出去玩只有拍到了好看的照片,才会在给妈妈的对话框里唰唰唰发上一串。
但再像朋友的妈妈,遇到女儿未婚先孕的事情,还能够保持冷静吗?
“妈,我爸在吗,你打开免提,我跟你们讲件事。”我在这边胡思乱想,他已经拨通了婆婆的电话。
“xx怀孕了。我们商量过,决定不要这个孩子。”
电话那端一阵长久的沉默,婆婆叹了口气,说:“这么大的事,你们得给我们点时间接受啊。”
相比起隔着一根电话线的坦白,与我妈妈面对面的开诚布公更加让人难熬。他做好了比跟婆婆打电话时更充足的准备,以真诚的道歉开场,再从我们的决定讲到以后的计划。我坐在一边低着头听,不时抬眼偷看妈妈的表情。她的眉头皱得越紧,我的心里就越发虚。
屋里的空气仿佛被冻结了,轻轻一碰就会掉下冰碴子来。一阵难捱的沉默过后,妈妈转向我,说:“你长大了,我也管不了你了。你们自己想好就行。”
无论是妈妈还是婆婆,在这件事上,她们从未真正表达对我的责备,甚至没有说过一句“为什么这么不小心”。但我相信对她们来说,未婚先孕和堕胎这两件事放在自己女儿和未来儿媳身上,大概是令人羞耻的。就连我自己,有时也会在心底赞同这样的说法。
两周后的一个晚上,那时我已经预定好了医院的床位,妈妈忽然小心翼翼问我:“真的不考虑把这个孩子留下来吗?”
“不考虑!”我回答得很大声。
她没有追问,这是她唯一一次向我提起这个问题。
朋友也问过我同样的问题。那段时间,意外怀孕是我心中最不可告人的秘密。我只将这个秘密告诉过两个朋友,一个是认识十几年的发小,一个是有过相似的经历的好友。彼时,我们因为距离原因很少见面,但奇怪的是,有些时候隔着屏幕和电话线的倾诉比面对面容易得多,也更具安慰。
她们曾浅尝辄止地问过我,会不会考虑做出另一种选择,在得到我的否定回答后就不再问。无论对我的选择究竟有几分赞同,她们都为我提供了朋友能够给到的最为充足的情感支持。
05
医院从来都不是太容易的地方。
抽血、化验、拿到报告单再回科室。因为是妇产科,周围或站或坐的几乎都是大腹便便的孕妇。她们大多因为冗长的排队时间而满面倦色,有些坐在长椅上闭目养神,丈夫或家人在旁边拿着化验单和提包;有些虽然看起来很累,但依然挺着肚子在走廊里来回走动——我曾听怀孕的同事说过,有时候胎儿的姿势不对,做B超时医生看不清要检查的部位,就需要准妈妈多加走动,来让胎儿调转姿势。碰上肚子里的小家伙不配合,一两个小时都完成不了一项检查。
我并不是完全没想过生孩子这件事。十八九岁的时候,我想以后要生两个孩子,一个哥哥,一个妹妹,要是龙凤胎就更好了。现在,天气好的时候,路过小区楼下的草坪,我也会想,如果我有一个安静的小男孩或者喜欢咯咯笑的小女孩,我们可以来这里铺开野餐垫,拿一本小说或者童话,带上薯片和果汁,躺在草地上看天。
然而,随着对生育的了解越来越多,比起孕吐、阵痛、阴道撕裂、盆底肌损伤、堵奶、产后抑郁、睡眠剥夺、与长辈同住,还有辅导班、学区房、像打仗一样的鸡娃比拼……那些甜蜜的幻想太轻了,不足以让我走进这样令人望而生畏的现实。于是我将它们收起来,下定决心要到自己完全准备好的一天再生孩子。
那么,在这里做检查的这些人呢?她们都是已经准备好了吗,还是顺其自然接受了命运做出的选择?
我低着头,从她们当中借出一条路。我们都徘徊在有很多岔口的迷宫,遇到岔路,就选一个,继续往前走。不能后悔也不能回头。
我穿过岔路,回到给我开化验单的医生那里。
“胚胎很健康,”医生从报告单上方看向我:“真的不要吗,太可惜了。”
这个问题有些尖锐,尤其是在这样的情景下——我的视线往下瞄了一眼,又掩饰般地移回来。面前的女医生白大褂下的腹部高高隆起,目测已经有七八个月的身孕。她的脸颊略显圆润,气色很好,似乎并未由于接连不断的病人而染上倦色。
“我,我还没......”我后悔没想个别的理由,“还没准备好”听起来不太有说服力。
“还没结婚?”她善解人意地帮我补全了后半句话。
“啊?哦对,是的。”我连忙点头,磕磕巴巴地接过她递来的借口。
“现在结婚也来得及呀。”
好在她似乎只是顺口提到,并无意在这个话题上过多停留,也许是见多了像我这样不听劝的病人。她快言快语地结束了聊天,便带着我去做下一项检查。我看着她有些笨重的姿势,心里忽然有点微妙的愧疚。让一位身怀六甲的大夫为了我这个来堕胎的病人忙碌,是我太不应当了吧。
06
那时我才刚工作不久,想做的事情和想实现的梦想在笔记本的dream list里排了一页又一页,而生孩子,无疑是不在其中的。
有时在公司遇到刚休完产假回来上班的女同事,她们大多都面色疲惫、头发凌乱、脸上冒着油光,黑眼圈像要掉下来。我询问近况,她们回给我一声叹息。睡眠不足,每天的生活变成围绕着孩子团团转。
“起码两岁之前吧,就不要想有自己的时间。”一位同事这样感叹,又对我说:“你啊,趁着没孩子,抓紧时间好好玩吧,以后就没机会了。”而昨天她还在劝我:“早点生孩子,恢复得快。”
很奇怪,人们好像习惯把生孩子这件事当作一道重大的分水岭,一面紧赶慢赶地催促着岭那边的人尽快跨过来,同时又把很多事情毫不留情地归为“过了这道线就不能做了”。比如打游戏、旅行、养宠物、认真打扮自己、保持天真和孩子气,我曾从不同人的嘴里听到它们被归到这道分水岭的另一边。
而他们还在疑惑,我为什么不想生孩子。
我不能违心地说我一点都不想生孩子,但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件事好像会把我的生活搅得一团糟,让我的一举一动都成为靶子,让任何人都有资格指摘一二。
07
如果忽略掉可能是我太过敏感的想法,医院的检查进行得还算顺利。我可以住院了,但目前床位紧张,即使是最贵的单人间,也要等一个星期。于是我依旧按时上班、每天吃饭,除了心里多出来的秘密,以及电脑中藏着的下一周的休假申请,我与从前没有任何区别。
直到那个周五,我休假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我正在座位上收尾手头的工作,领导忽然叫我过去,一边整理行李箱一边对我说:“你今天跟我出趟差吧。”
“啊?呃,好......”我心里还在组织着拒绝的措辞,嘴上却鬼使神差地先一步答应了。话说出口的那一秒我就后悔了,可现在再说不去,就更奇怪了。
我懊恼地走回工位,脑子里想着医院那边的说法:“周六必须来办住院手续,不然床位不给保留。”好在要去的城市不远,第二天应该能赶回来。
在邻市开完会打车去酒店的时候,已经快晚上十点了。车子后座挤了三个人,我贴在车门上看了会儿手机,便觉得胃里有些翻腾。可能是晕车了吧,我找出一片强力薄荷糖含着,把那感觉压了下去。但薄荷糖的效力也只维持到了下车。我给司机付完款,刚走了两步,就哇的一声吐在了酒店门口的大理石地面上。
是整个胃袋被头朝下拎起来,倒了个精光的感觉。
08
我趴在房间的洗手池边干呕,好像有股力量要把我的胃推到喉咙口检查一下。我抬头看镜子里的自己,眼睛里布满血丝,脸也有点肿,一团糟。
记不清是这个晚上的第五次还是第八次,我漱了口,把自己扔回床上。被腾空的胃再次针扎似地疼起来。刚才烧的热水还放在床头柜上晾凉,我犹豫一下,还是端起来抿了两口,用最小的动作慢慢咽下去。感受到暖意的胃部几乎立竿见影地停止了刺痛,但与此同时,另一股熟悉的感觉袭来,预示着我的胃即将开始新一轮的过山车之旅。
疼痛和呕吐的间隙,我一边在微信里给他发语音诉苦,一边打开浏览器搜索,按什么穴位能止胃痛。而手机左上方的时间,已经跳到了凌晨三点多。
“你脸色怎么这么白?”
第二天我坐最早班的火车回去,在病房名额没有被取消前赶到医院报到。给我办住院手续的护士看着我的脸色,谨慎地多问了一句:“你是不是贫血?”
“没有没有,”我担心影响住院,连忙摆手:“就是昨天吐了一夜。”
护士了然,低头在办理单上签字,带我去病房入住。
后来我跟他聊起这件事,他说:“可能是它知道它要被打掉了。”我记不得听到这句话时是什么感觉。但如果堕胎这件事曾经让我有过一点负罪感,那么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了。
不是后悔,只是有一点愧疚,如果没有立即注意到就会随风飘散的那种。
“你知道吗,我看过一个故事。”那天夜里我们挤在病房的单人床上,睡在里面的人要紧贴着墙,外面的人要收腹提气才能不掉下去。屋里很黑,我忽然很想把这个故事告诉他。“据说所有的小孩儿在出生之前都要在天上排队,等被天使叫到号了,就会去到妈妈的肚子里。被打掉的小孩儿会继续回到天上排队,直到下次排到了,就再来找自己的妈妈。”
这个故事我忘了是从哪里看到的,大概是一个几岁的小男孩向妈妈描述他出生前的记忆,在天上排队,然后飞到妈妈的肚子里。他说这样的经历他有过三次,前两次的时候,他都是莫名其妙进到一个黑乎乎的管子里,就又回到天上排队了。直到第三次,他终于降临到这个世界上。
我记得这是个温暖的故事,但我组织了半天语言,还是讲得七零八落,甚至有点像个鬼故事。
09
住院的第二天,我去取检查报告。如果一切顺利,就可以开始做药物流产了。
“霉菌感染啊。”医生从一沓报告中抽出一张,指着上面标成红色、后面还带着加号的一项,向我宣布了结果。这种症状并不难消除,只要用一次性塑料给药器把圆形的白色药片推进阴道,连续两至三次就可以。但由于要先解决霉菌,药流时间至少要推迟到三天以后。这意味着我之后在家休息的时间再次缩水。原本以为用上所有的年假,应该能恢复一周再去上班,看来是不行了。
“早晨查房了。”走廊里传来一个嘹亮的女声,然后是敲门和推门的声音:“咦,怎么把门挡住了?病房的门不可以挡住的。”
我连忙下床去开门,这个房间的门有点问题,从外面推会容易卡住。一位银发的老教授带着七八个实习生进来,单人间一下子显得有些拥挤。
“哦,没有挡住,是这个门的问题。”她先是绕到门后面确认了一下,才走到床边,给实习生们讲解起我的情况。她的用词和语气都很平和,不是因为我在场而特意表现出的温和,而是发自内心的不带偏见。她站在那里给学生讲课的样子实在太像我的教授,我忐忑地立在床边不敢坐下,像个要做展示却忘了带讲稿的学生。
“你不用站着。他们站着,你坐下休息就行。”她摆摆手让我坐下,转身继续跟学生们讲:“这个霉菌感染啊,很多人听到霉菌就会觉得,肯定是不讲卫生啊,不自爱,但其实不是的。霉菌感染可能有很多原因,比如自己的内裤不小心和老公的臭袜子放在一起啦,或者游泳池的水不够干净等等,都是有可能的。”
我不知道她的这段话是不是特意说给我听的。无论是不是,我都很感激她。
后来去科室挂号、复诊没再碰见过这位老教授,她也许不知道,她的这番话在之后的日子里帮了我很多,帮我抚平自己,也应对别人。尤其是当婆婆在电话里用疑惑的、在我听来稍带一点质疑的语气问:“怎么会有霉菌呢?”我可以压下内心的羞耻感,理直气壮地告诉她:“医生说了,霉菌感染有很多原因。”
10
我接过那片药。
“吃下这个药,就真的不能要了,不能后悔了。”护士尽职尽责地提醒我。
我其实没什么好犹豫的。
我坐在病房的床上,把饭盒里的饭菜吃完。妈妈这两天没有来看我,但做好了饭让他带来给我。我其实庆幸她不来,我不想在这种情况下见到家人。
他把饭盒收好,我看着他。
“那我吃了。”
“嗯。”
我把白色的药片从铝箔里拆出来,放进嘴里。药片外面不带糖衣,碰到舌头就化开苦味。我连喝了几口水,确保它顺着喉咙滑到胃里,愣了一会儿,才扑进他怀里哭起来。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哭。
我一直觉得,当腹中的胚胎还没有一粒小米粒大的时候,应该被优先考虑的是母体——她的健康和她的意志。但我还是哭了,我不希望被认为毫无愧疚。就像现在,我一边写,一边害怕写完之后,我会暴露出自己是个狠心的人。
药物流产要服用两种药。第一种是让胚胎停止生长,我的身体并没有什么实质的感受。第二种药是让子宫收缩、孕囊排出,对我来说,这才是真正的流产过程。第二天早上,我吃第二种药的时候,他请了半天假来陪我,病房的床上铺好了浅蓝色的一次性棉垫,地上摆着医院小卖部买来的塑料盆,都是医生特意吩咐一定要准备的。
药效发作很快,疼痛从下腹尖锐地扎进脑内的神经。太痛了,作为一个经常体验严重痛经的人,即使每个月痛到在床上打滚、眼前发白,全靠布洛芬续命,也比不上现在十分之一的痛。
“好痛啊,好痛,我要死了。”我倒在床上捏着他的手,耳边听到自己的尖叫是破音的,带着嗡嗡的回响。走廊甚至隔壁房间肯定能听见我的声音。但我感觉不到尴尬,只要这疼痛能停下,怎么都行。
他扶我起来,褪下裤子,蹲在塑料盆上,血液和血块从体内坠出,落进盆里。
“不能去厕所,一定要用盆。”护士是这样嘱咐的。这种方式看起来羞耻,但为的是确保能够找到掉落的孕囊,才能确定药流成功。
血水很快积了小半盆,我在里面翻来覆去,也没有找到要找的东西。
“一直没有下来吗?”护士推门进来看我的情况,又看了看盆里的东西,决定让我再补一片药。
然而,直到时钟转到午后,我还是没有见到那个据说是白色圆形、上面有绒毛的孕囊。
他接了几十个领导催促的电话,说了两百多遍“马上就到”。没有将意外怀孕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人的一个不好的方面,是不能拥有正大光明的请假借口。于是他不得不赶去公司,而我被护士带去做B超确认情况。
“卡在宫颈口了。”护士看着屏幕上的影像,对我说:“你放松。”
她拿出一件工具,也许是镊子,或者钳子,从我的阴道伸进去。明显的异物感让我想要躲避,但又不能躲,只能忍着那工具在里面寻觅了片刻,夹住什么东西,抽离出来。
“好了,出来了。”护士宣布。她手中夹着的东西血淋淋的,我分辨不出是不是白色,也看不清有没有绒毛。
回到病房,还有几袋消炎药要输。护士帮我打上针,嘱咐我换药的时候叫她,就匆匆出去了。我躺在床上看架子上的输液袋,里面透明的液体一滴一滴往下滑,滑过长长的管子,流进我的手背。
11
出院的前一天,我去医院大厅办手续。
“可以刷医保卡吗?“我站在缴费窗口前,把捏在手里的医保卡和就诊卡递进去。“流产的费用不能用医保报销,这一块是走生育保险的。”窗口里的工作人员推回了我的医保卡。
“啊,生育保险……要怎么走?”我对这个词语的了解,仅限于大概知道它是五险一金中的一项,但从未想到用到它的一天会这么快到来。
“要拿着你的病例、收据这些材料去你们单位申请,然后去社保局报销就可以了。你可以回去问一下,你们单位肯定知道的。”工作人员放下手里的单据,向我仔细解释。
“好的,谢谢您,我回去再问一下。”我努力让自己的语气显得诚恳,递过银行卡付款,心里想象着单位同事听说我要报销生育保险时脸上会出现的神情,以及这个消息将会以什么样的速度传遍公司,忽然觉得有点好笑。设立这项制度的人怕是想不到,有人会觉得同事的八卦比信用卡账单更可怕吧。
出院那天早上,我刚收拾好东西,门就被敲响了,是一对年轻的男女。女孩是入住这间病房的下一位病人,不过看到我一个人和地上的大包小包,便主动说可以先在走廊上的休息区稍坐,让我留在房间里等家人来接。
这栋妇产科楼坐落在医院最深处,外面的树都有些年头了,从窗户看出去,不远处就是高耸明亮的新门诊大楼。那天听我说起病房所在的楼有些老旧,妈妈立刻说:“最里面的那栋楼嘛,我知道,当时我生你的时候就是在那里。”我才知道这楼原来比我的年纪都大。
妈妈打来电话,说已经到了医院门口。我拎着东西走出病房,路过刚才来敲门的男孩和女孩,他们正凑在一起看着手机。我不知道,那个女孩也要经历我经历过的事情吗?她看到我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
回家的路上,我跟妈妈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我们聊到生育保险报销的流程有多离谱,说到医院的新门诊楼,还有我昨天叫的汉堡王外卖。但我不会把在这里真正发生过的事情告诉她,她也不会问。
从得知怀孕到我完全恢复回去上班,妈妈对这件事的态度始终是有一点冷漠的。她当然是关心我的,会询问我的进程,会帮我做装满整个饭盒的三菜一汤,会开车来接我出院,会让我在家多休息,给我准备营养的饭菜。但她没有紧张兮兮地冲去医院看我,每天在微信和电话里的关心都是点到为止,甚至没有试图在要不要留下孩子这件事上左右我的意见。
即使她尝试了,我多半也不会改变主意,但我很感激她没有。就像我感激她的冷漠,这让我真切地感受到被放在平等的、互相有分寸的成年人位置上。做错了事情不受责怪,是因为责任和后果都要自己承担。但妈妈不是别人,她嘴上说得再果决,手里依然默默帮我担起了一部分包袱。
我从没问过她那一点冷漠的原因,以后应该也不会问。如果她觉得女儿未婚先孕有些羞耻,我也完全能理解她的感受。否则,我怎么会把这件事对身边的几乎所有人瞒得密不透风?
我有时会想,如果我有个女儿。我当然不希望她经历这样的事情,就像妈妈也不会希望我经历这样的事情。但我阻止不了她,就像妈妈阻止不了我一样。可是我很想给她讲讲我的故事,比如不小心弄破避孕套,半夜跑去买紧急避孕药的那天有多狼狈;比如吃短效避孕药真的可以治痛经,而且祛痘,但心情不太好,每天都提心吊胆害怕漏服,终于决定停药的那天觉得天空都格外明亮;当然,还有意外怀孕和流产的故事。
我有好多故事想告诉她,即使她选择的路上必定会有很多坑需要她自己去踩,我还是想把这些都讲给她听。让她知道,无论将来做了什么傻事,都不会比妈妈当年做过的更傻啦。所以,都不用太放在心上,会过去的。
后来的事情平平无奇。
我在家里躺了快一周,按照医生的指示去复查——如果子宫内还有残余的组织没有排出,可能需要再次清宫。我忐忑地坐在圆凳上,担心听到不好的结果,但医生拿着我的检查结果,露出一个笑容:“很干净,完全没有问题!”
回家的路上,我忽然想到药流那天补服的、让我多疼了好一阵子,却好像没起到什么作用的那片药,也许是因祸得福吧。
12
“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呀?”
后来的后来,大概是在结婚以后,忘记聊起什么,他问我。
“我当然喜欢女孩了,漂亮又可爱,还可以给她买好多小裙子。”我说。
“是啊,”他说:“不过感觉,养女孩要更多操心呢。”
我忽然想起很久前的那个闷热的夏天,医院的单人间很小,门吱呀吱呀地响,窗外的蝉鸣很吵,我白色睡衣上沾的血迹,到现在还没有洗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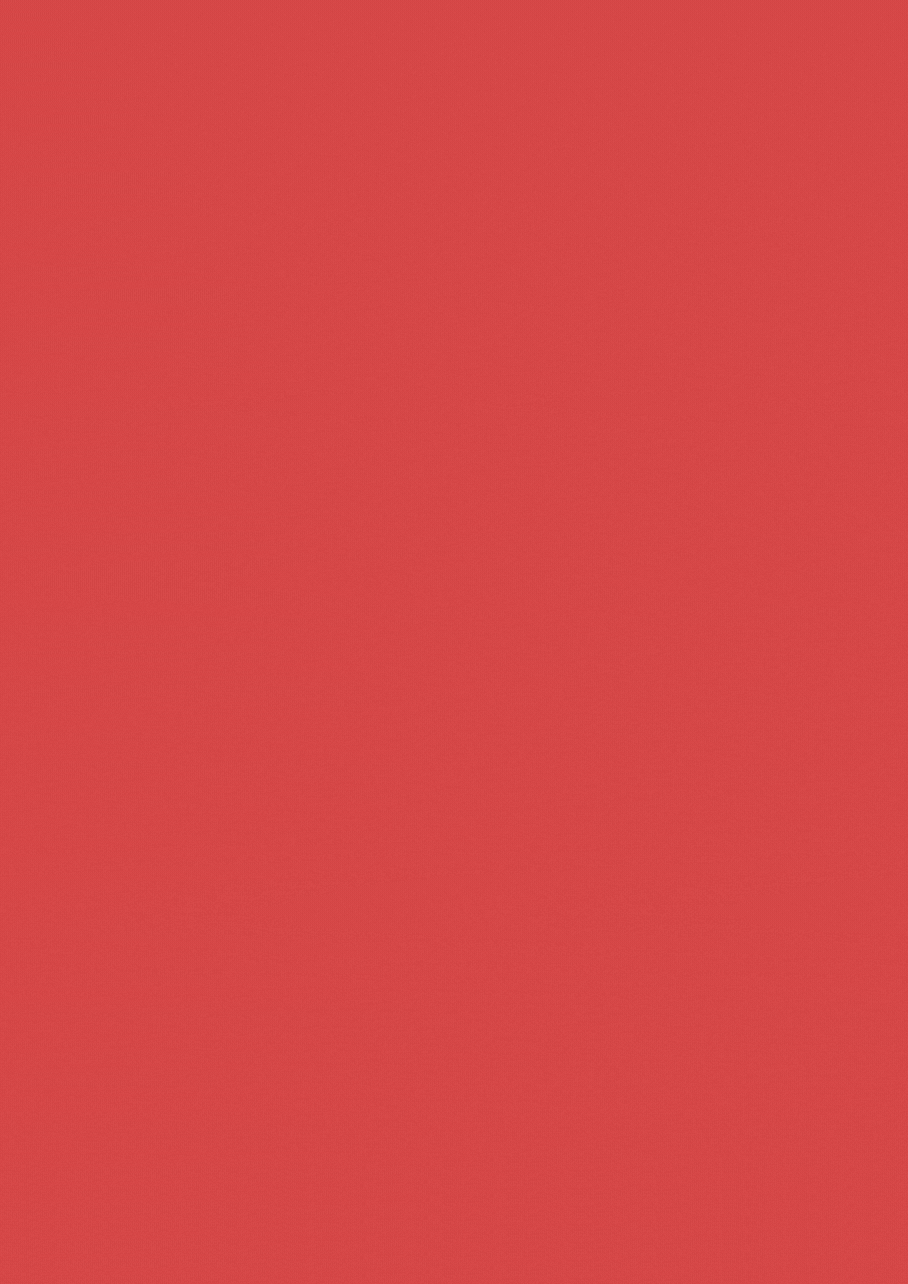
作者后记
这个故事存在心底很久了,我也已经往前走很久了。但真正写完的那一刻,我依然觉得如释重负:终于不用担心会忘记了。
这个题目对我来说还是有一点难以启齿,本来打算降低存在感、默默写完,但短故事的大家真的好好啊。尤其是胖粒老师,她在整个过程中给予我的理解和接纳,比我想象过也许能得到的多太多。她是我这个六月的指路明灯。
我依然不确定这个故事能够带给读者什么,但我记得依蔓在第一节直播课中说,写出来的故事就像一点点光,虽然不多,但能让一些栖息在黑暗中的人聚拢到有亮光的地方。
我也想做一点点光。

把生活变成写作,把写作变成生活
三明治是一个鼓励你把生活写下来的平台
原标题:《吞下那片药之前,护士说,“吃了就真的不能要,不能后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