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硬核读书会 硬核读书会 收录于话题#吾论阅读2个

每一年,都有大量的外文作品被翻译到中国。但人们更多关注作者,译者则隐藏在文字背后。
近些年,人们越来越关注翻译作品的质量。优秀的翻译,需要扎实的外语功底,也需要优秀的母语表达,更需要对翻译文字背后文化的深刻理解。那么,如何才能做出好翻译?什么是好的翻译?
2021年4月23日,后疫情时期的第一个世界读书日。新周刊硬核读书会联合华为阅读,邀请五位文化界的大咖,以“吾论阅读”为主题,聊一聊他们的读书“方法论”。
如果是在十多年前,我们很难想象一位译者的名气会超过原作者,而一位译者凭借翻译历史类非虚构图书走红,更是一种“天方夜谭”。
陆大鹏做到了。
他翻译的“地中海三部曲”收到了如潮好评。他还以惊人的速度每年推出新的译著,流畅、扎实的翻译,以及他时常在社交媒体分享自己的所思所得,让他迅速出圈。
他不仅翻译英语作品,也翻译德语作品。在题材上,他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去挑战文学作品翻译——稳定的产出以及精确的翻译,让他的名字成为了翻译质量的“质保标签”。
一位优秀译者流畅的语言能力是如何炼成的?如何保持大量的产出?如何在新媒体时代,保持自己对文字的敏锐?
2021年的“世界读书日”就要到了,借由这个机会,我们一起走进译者陆大鹏的阅读世界。
Q=新周刊硬核读书会
A=陆大鹏
历史的真相往往复杂得多
Q:最近在读的是什么书?
A:最近在读的两本:德国历史学家格尔德·海因里希(Gerd Heinrich)的《普鲁士史:国家与王朝》(Geschichte Preußens. Staat und Dynastie),我对德国历史一直很感兴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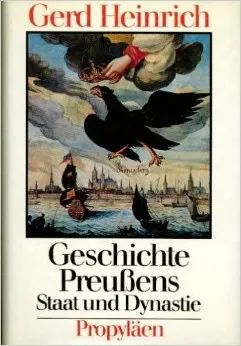
海因里希的《普鲁士史》打破了很多刻板印象。
海因里希是研究柏林和勃兰登堡历史的大师。这本书写得比较早,是1980年的,但今天读起来还是很有意思的。由于二战的影响,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普鲁士这个概念与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甚至与纳粹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历史的真相往往比刻板印象复杂得多。海因里希举了个例子:在希特勒任命的纳粹党和党卫军的大约500名最高级官员当中,只有3.4%是普鲁士人,而普鲁士人口占德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二。这500名最高级官员大多来自波西米亚、巴伐利亚、奥匈、波罗的海地区等。
海因里希甚至说,大批外地官员涌入普鲁士,所以对普鲁士来说,纳粹是一种“外来政权”和“占领军”。另外,德国军队当中反抗希特勒的地下运动,是由普鲁士贵族军人集团主导的。
另外还在读的一本书是苏格兰历史学家威廉·达尔林普尔的《白莫卧儿人》,谈的是莫卧儿帝国末期英国殖民者在印度的生活,英国与印度文化之间的互动和交流。英国与印度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征服与被征服,英国人自己也深受印度的影响,甚至是一定程度的同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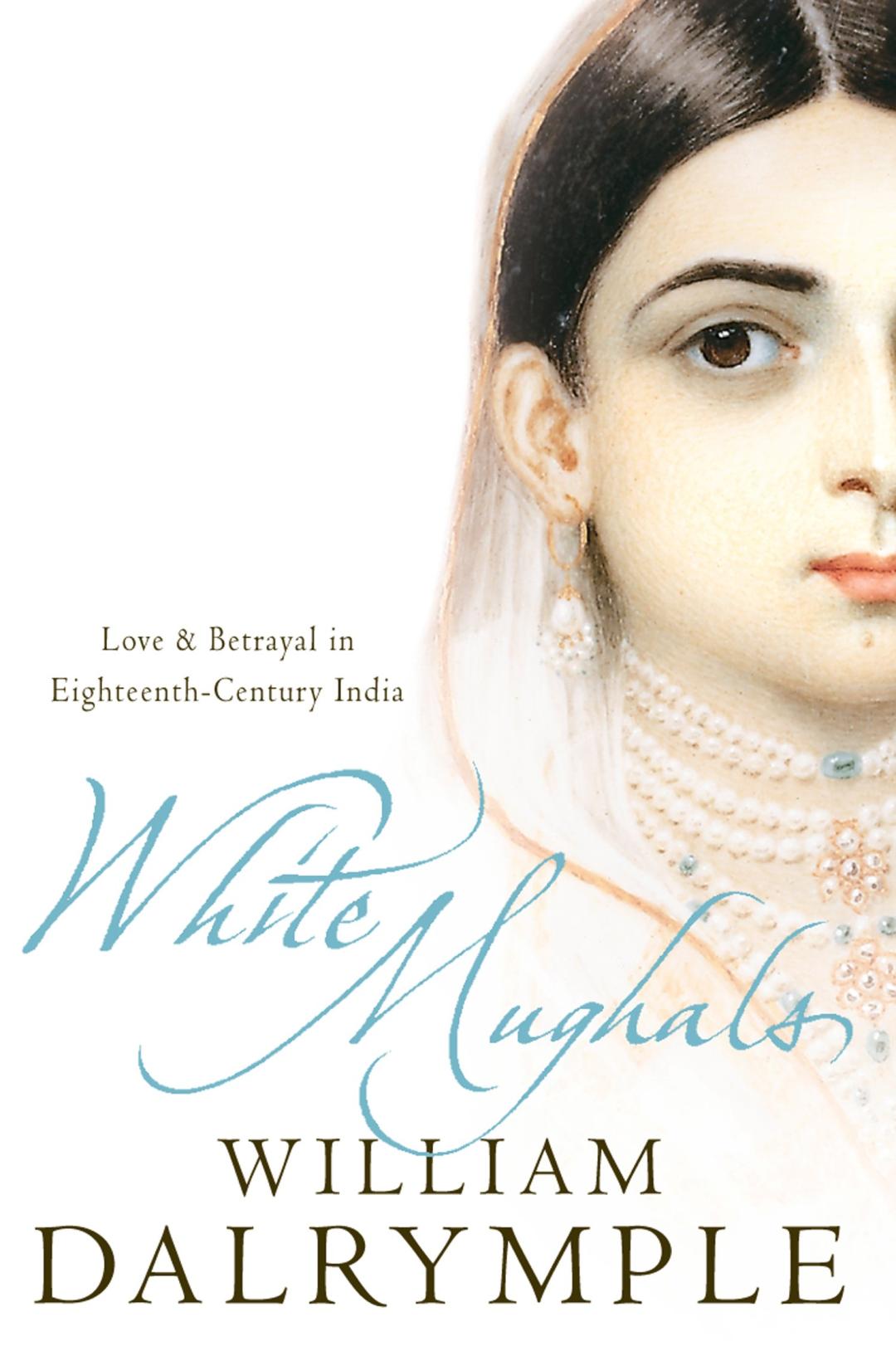
威廉·达尔林普尔的作品从另一个角度还原了大英帝国的历史。
Q:这段时间有读到让你眼前一亮的书吗?能否跟大家分享?
A:眼前一亮的感觉已经很久没有了,大概是随着年岁增长,我变得迟钝了。
最近读的书当中,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安德”系列科幻小说,尤其是其中的《死者代言人》和《外星屠异》。
这个系列的科幻比较哲学,探讨了很多涉及跨种族、跨文化交流的伦理问题。比如,如果宇宙是一个“黑暗森林”的话,是不是应当一旦发现外星智慧生命就立刻消灭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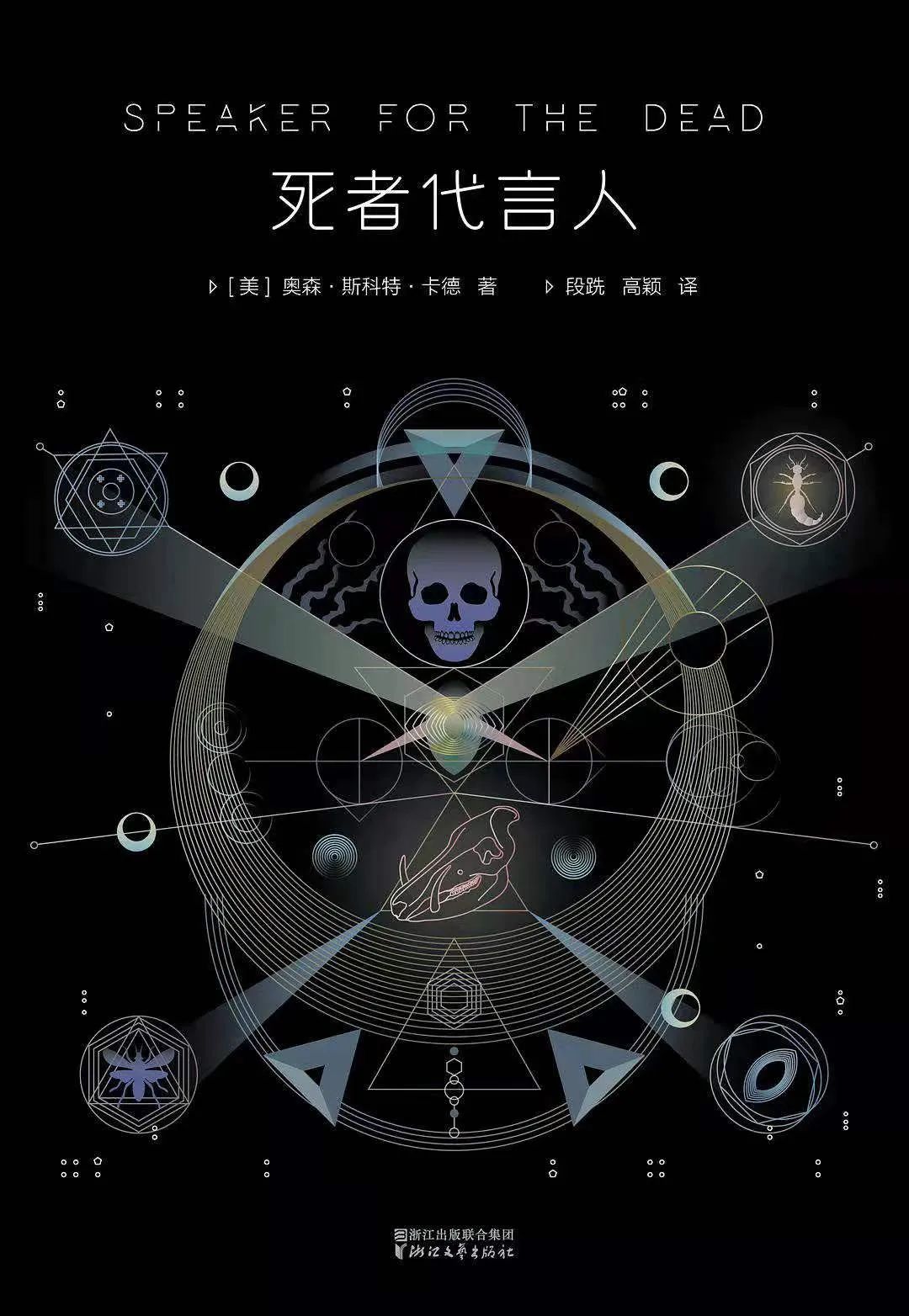
《死者代言人》
[美] 奥森·斯科特·卡德 著,段跣 / 高颖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4
Q:你平时一般喜欢读什么类型的书,是读原版比较多,还是读中文版的作品多?
A:我从小养成的兴趣是读外国文学和外国历史,上大学之后开始读外文书比较多一些。如果一本书的原著是英文或者德文的,我会尽量去找原著来读。最近两年,我也在督促自己多读一些中文原创作品。
我以前读书比较“实用主义”
Q:对比你在大学的时候,这几年的阅读偏好发生了变化吗?
A:最近两三年有很大的变化。以前读书比较“实用主义”,喜欢读非虚构、历史、政治类,觉得这样能获取有用的信息,觉得读文学“无用”。现在我督促自己多读文学,尤其是经典文学。
Q:你现在有了孩子,会和孩子一起读书吗?给孩子选的书都是什么类型的?
A:孩子比较小的时候会和他一起读,有的书反反复复地读了很多遍,比如日本的“小猫鱼”系列和宫西达也系列的绘本,还有“怪杰佐罗力”系列。
现在他已经五岁了,识字量已经比较大,所以大多是自己读了。比如《龙猫》绘本,他一个人读了怕是有上百遍,还读给大人听。
我和妻子给孩子选书的时候会注意各种类型和题材,孩子自己比较喜欢动植物的科普和关于建筑的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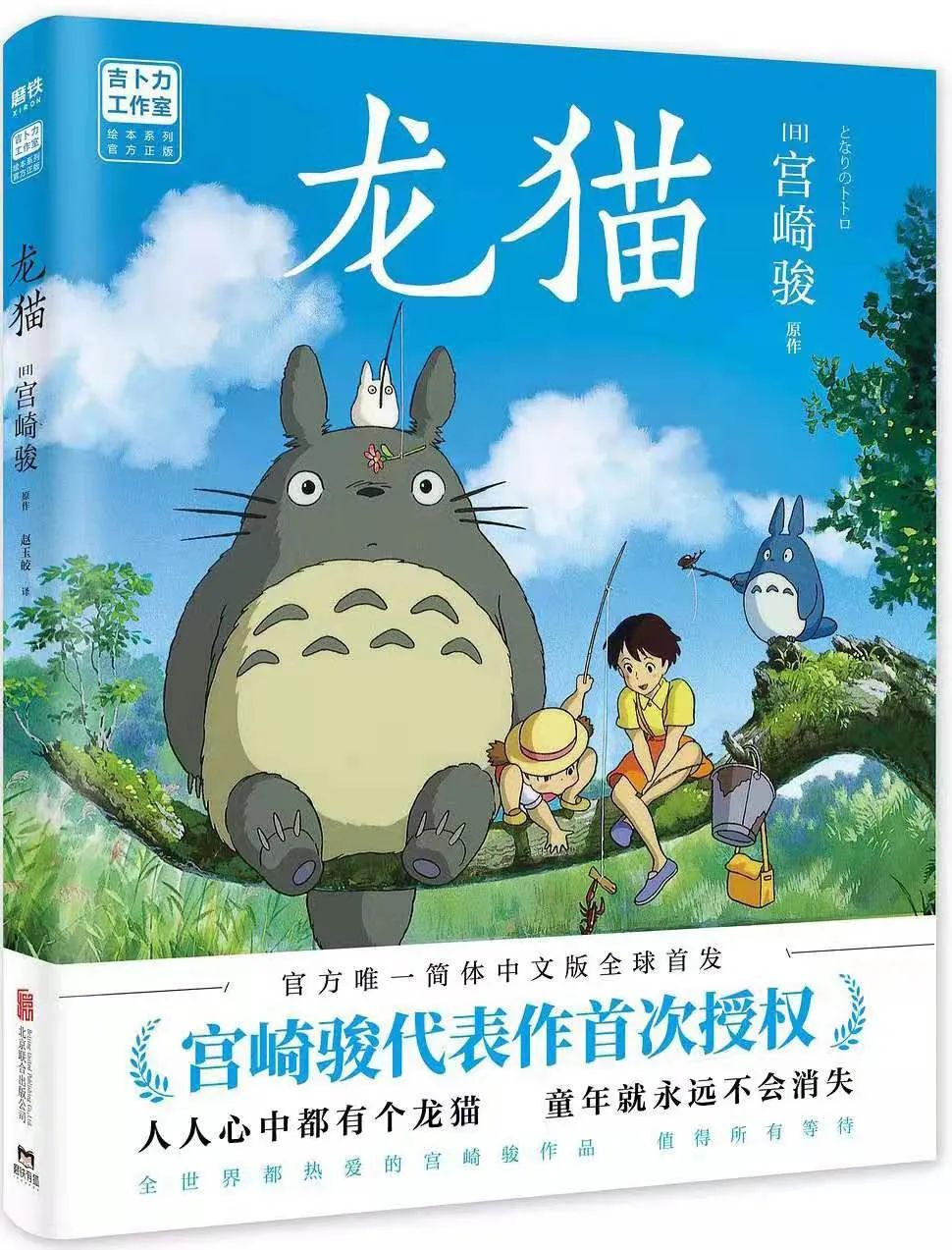
《龙猫》
[日] 宫崎骏 著,赵玉皎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12
Q:社交媒体时代,人们的时间变得更加碎片,阅读成了一件比较奢侈的事。有很多人习惯在屏幕上阅读文字、摄取信息,电子阅读流行起来。你现在会常常用电子阅读器或阅读软件吗?
A:我是80后,属于纸质阅读时代的遗民,喜欢读纸质书。但我相信,没有人会否认电子阅读的便利(轻便易携,容易检索和做笔记),我喜欢纸质书完全是个人的习惯。
翻译需要有纪律性
Q:你翻译的作品很多,并且质量很高。平时翻译的过程是怎样的?每天有固定的时间吗?平时是如何保证翻译的效率的?
A:我的理想状态是每天固定工作几个小时,一般上午2个小时、下午2个小时、晚上1个小时,但实际上很少做到。
我有个习惯是每工作一个小时,会休息十来分钟,躺下休息颈椎,同时利用这个时间听一些东西。
我喜欢听英文的有声书或者podcast(播客),听一些跟我做的主题完全不相干的话题来休息大脑。如果实在太累的话,就走出房门到外面去。我觉得翻译工作要形成一种工作习惯和工作节奏。每个人的节奏不一样,大家需要自己把握,也需要有纪律性。
Q:最近很多人在讨论“机翻”,你认为什么样的翻译才是好的翻译?你觉得最好的翻译作家和翻译作品有哪些?
A:什么样的翻译才是好的翻译,很难一概而论。我觉得一般来讲,是比较准确地传情达意,中文流畅清晰,尽可能地帮助不懂外语的读者。另外一点是,我个人不喜欢在翻译中使用半文言、方言和网络俚语。
中国译者方面,我非常喜欢董乐山先生,他的好几本翻译作品,比如《第三帝国的兴亡》《巴黎烧了吗?》等,原书都是极好的、很有影响力的作品,他的翻译也非常好。
我是在年纪比较小的时候,应该是中学的时候,读到他的好几部翻译作品,对书中涉及的历史尤其是20世纪上半叶纳粹德国历史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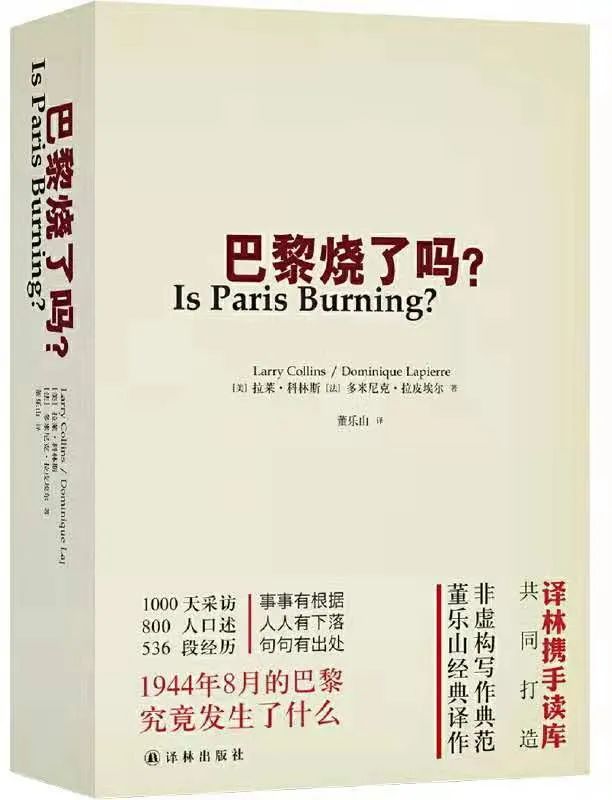
《巴黎烧了吗?》
[美] 拉莱·科林斯 / [法] 多米尼克·拉皮埃尔 著,董乐山 译
译林出版社,2013-3
我中学时代非常喜欢的是草婴翻译托尔斯泰的好几部作品,包括《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等,对我影响也非常大,我从中受益良多。
现在有人批评草婴的译本,懂俄文的人拿俄文版和中文版来对照,觉得他的翻译有很多问题。他的翻译也许是有一些问题,但是,这和草婴译本发挥了很大影响,让许多年轻的读者对托尔斯泰产生兴趣,这两个方面是不矛盾的,所以我还是很感谢草婴对托尔斯泰作品的翻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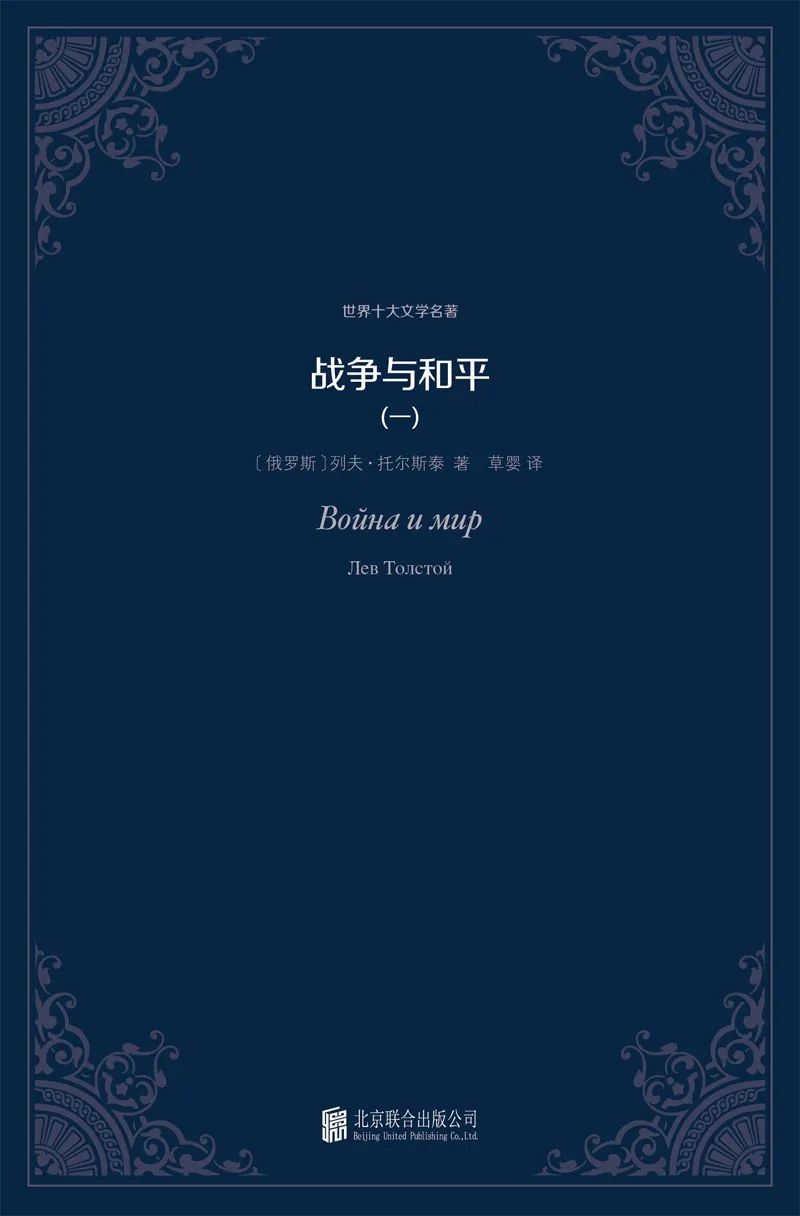
草婴的译作虽然有争议,但是却让很多人爱上了俄罗斯文学。
后来我比较喜欢的译者是一位美国人William Weaver,他翻译了意大利作家埃科、卡尔维诺的大量作品。我非常喜欢他翻译的《玫瑰之名》,这个英译本是一部了不起的杰作。
西班牙语文学方面,我不懂西班牙语,因此主要是通过英文来读。一位翻译西班牙文学的美国人Gregory Rabassa,作品有英译本《百年孤独》,文笔行云流水,对我这样一个不懂西班牙文的人来说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翻译作品。
因为我不懂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但是通过这些译者的英译本,得以管中窥豹,领略埃科、卡尔维诺、马尔克斯等人的大师风采,心满意足,而且这两位翻译家本身的英文文笔就非常棒,所以是一种很享受的阅读体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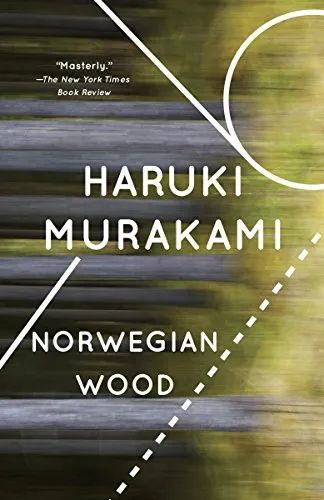
美国翻译家Jay Rubin翻译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的图书封面。
同时我还喜欢另外一位美国翻译家和学者Jay Rubin。他是哈佛大学研究日本文学的教授,翻译日本文学,已经译了好几部村上春树的作品。他的英译本《奇鸟行状录》《挪威的森林》很值得向大家推荐,我读过之后非常难忘。如果你喜欢村上春树或者英语文学,可以读一读Rubin的译著。
Q:有人认为,翻译外文作品应该从原作直接翻译,而不是从英语译本二次翻译成中文,你怎么看?
A:理论上,当然是尽可能直接从原文翻译,那样最好。但实际上很难做到,尤其是小语种。但是,像法语、德语尤其是西班牙语,恐怕也只有我国才把它们算作所谓的“小语种”了,这些语言的作品如果在今天还从英语转译,我觉得是令人惊讶的。
Q:你翻译英语作品,也翻译德语作品,能不能说说,翻译不同的语言给你的感受有什么样的不同?
A:其实没有特别的感受,这个可能要看具体作者的风格。英语作者也完全可能写得佶屈聱牙,德语作者也完全可能写得轻松优美。
Q:你翻译得最为艰难的是哪一本书?为什么那本书会很难翻译?
A:可能要算萨曼·鲁西迪的小说《摩尔人的最后叹息》。一般来讲,小说大多比非虚构作品更难翻译,因为小说文字的“文学性”更强。当然了,什么是“文学性”,就是玄学问题了。
鲁西迪是一位英语语言大师,他的文字密度极大,一句话往往有好几层不同的意思;而且他熟练运用西方经典、伊斯兰和印度教的多种文学与文化传统,对流行文化(比如科幻小说)也很精通,所以对阅读和翻译都是很有挑战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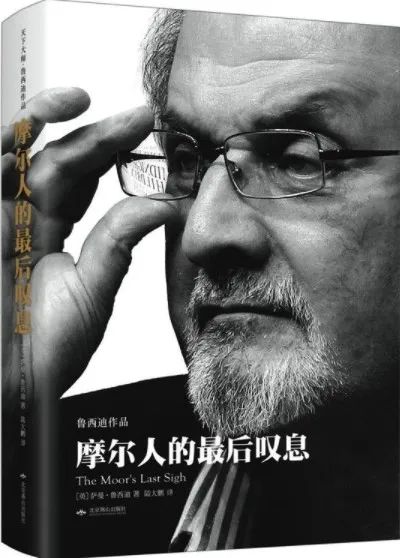
《摩尔人的最后叹息》
[英] 萨曼·鲁西迪 著,陆大鹏 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7-5
Q:历史科普类、非虚构类、文学类的作品你都翻译,但是每一种作品都不大一样,你是如何把握不同类型书本的风格?
A:我个人来讲,我翻译的大部分是历史和非虚构作品,还有少量的文学作品。除了鲁西迪等作品之外,其他大部分作品都没有非常鲜明的风格特色,比如说像丹·琼斯、罗杰·克劳利等等。他们本身的语言是比较平易的,没有非常华丽的辞藻和雕琢的文风,是给大众阅读的作品。所以我也尽量用简单、准确、直白的语言来表达,不会用半白半文的写法。
同时,像这种历史或者非虚构作品,它们的用途是什么?是给大家提供知识、传递信息,与此同时带有一些娱乐功能。所以我觉得这种书既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突出译者的个人特色和个人风格。
我翻译的小说当中,朱诺·迪亚斯的《你就这样失去了她》写的是多米尼加裔美国人,而且是底层平民的生活,语言风格有时比较gansta(帮派气、匪气),这对我是比较难以把握的,我不确定自己处理得是否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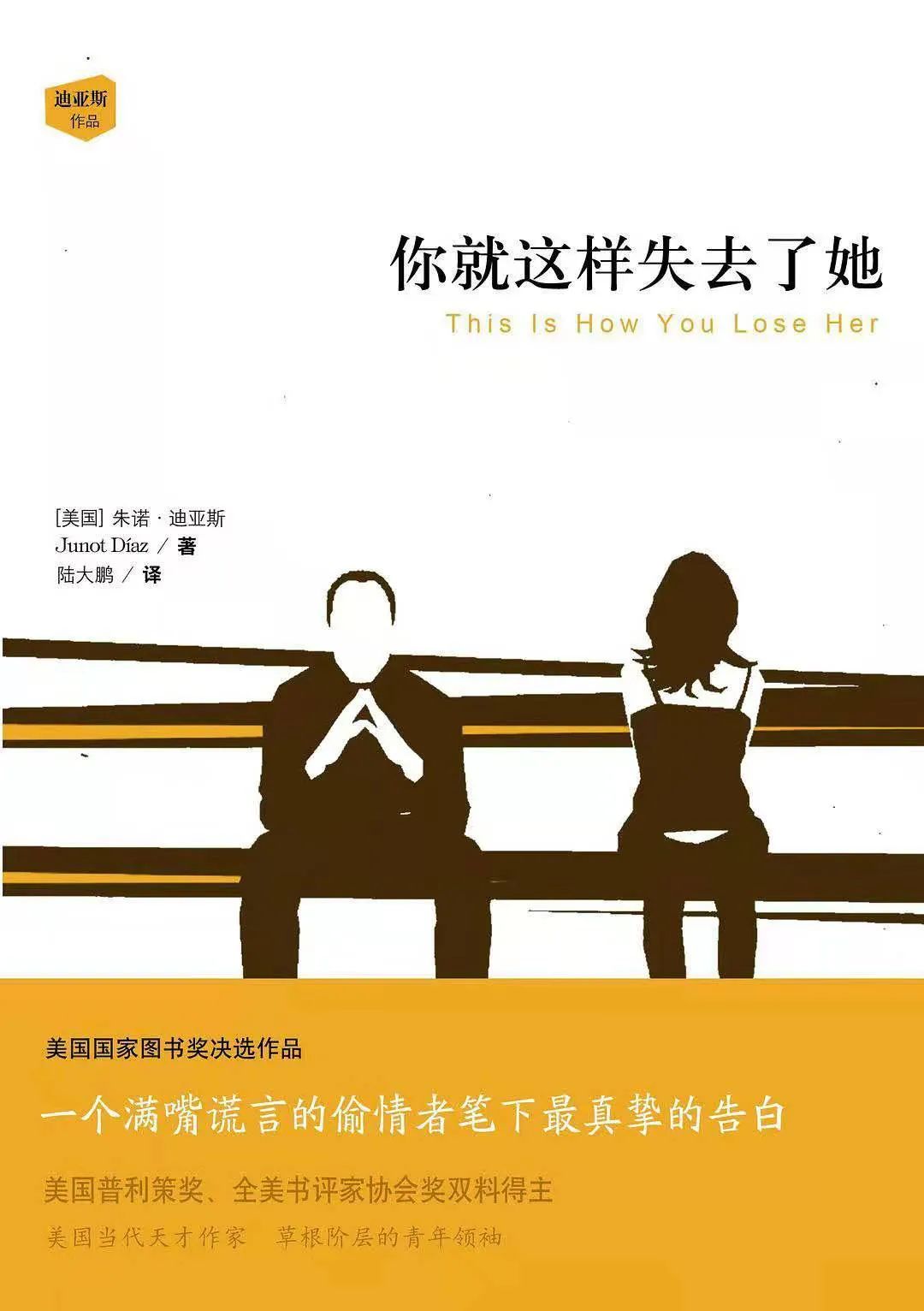
《你就这样失去了她》
[美] 朱诺·迪亚斯 著,陆大鹏 译
译林出版社,2016-4
Q:翻译不仅要求外语好,也对中文能力有很强的要求。你平时会经常阅读中国本土作家的小说吗?是否有推荐?
A:小时候喜欢读近代的白话小说,《说岳》《三侠五义》《包公案》那种。现当代中国本土作家的小说,我读得比较少,现在也开始督促自己多读一些,其实应当请大家向我推荐才对。
那就说说读过的书当中,我比较喜欢的那些吧。比如老舍,他可以说是北京的狄更斯吧?还有王小波,当然他的风格是很“西化”的。还有莫言,姚雪垠的《李自成》与徐兴业的《金瓯缺》。
共 读 时 刻
你最近读到过什么好的翻译作品?
欢迎到留言区分享给大家
出品 | 新周刊·硬核读书会
采写:钟毅
原标题:《陆大鹏:中年以后,我不再觉得文学无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