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独立纪录片导演,魏时煜的三部纪录长片《红日风暴》(2009,与彭小莲联合导演)《金门银光梦》(2014)和《古巴花旦》(2018)多次应邀参加国际电影节,在海内外学界和传媒界受到很多关注与好评。她的电视纪录片有《崔健:摇滚中国》(2006)和《跋涉者萧红》(2019)等。
作为学者,魏时煜近年成绩斐然。《霞哥传奇:跨洋电影与女性先锋》(2016,与罗卡合著)获得2017年“香港书奖”;2018年重出简体字版,标题改为《灿若锦霞:第一代跨洋影人与近代中国》。她的专著《王实味:文艺整风与思想改造》(2016)在2017年首届出版双年奖上,获得“文学与小说”类别的“最佳出版奖”。她的另一部专著《胡风:诗人理想与政治风暴》也获得很多好评。魏时煜2014年首版的《东西方电影》受到欢迎,2016年又出增订本。她更早的著作还有《开始学动画》(2010,与梅凯仁合著)以及《女性的电影:对话中日女导演》(2009,与杨远婴合著)。[1]
《记录之旅:原始档案》是魏时煜的首部纪录长片,制作历时三年多,在这部片子里,她的摄影机对准了自己的恩师司徒兆敦,围绕着他的经历与人脉,如织网一般,将司徒人生中动人的细节织进他所经过的大时代中。为何命名为《记录之旅:原始档案》?“因为发现了片中所有人都在以不同的形式进行记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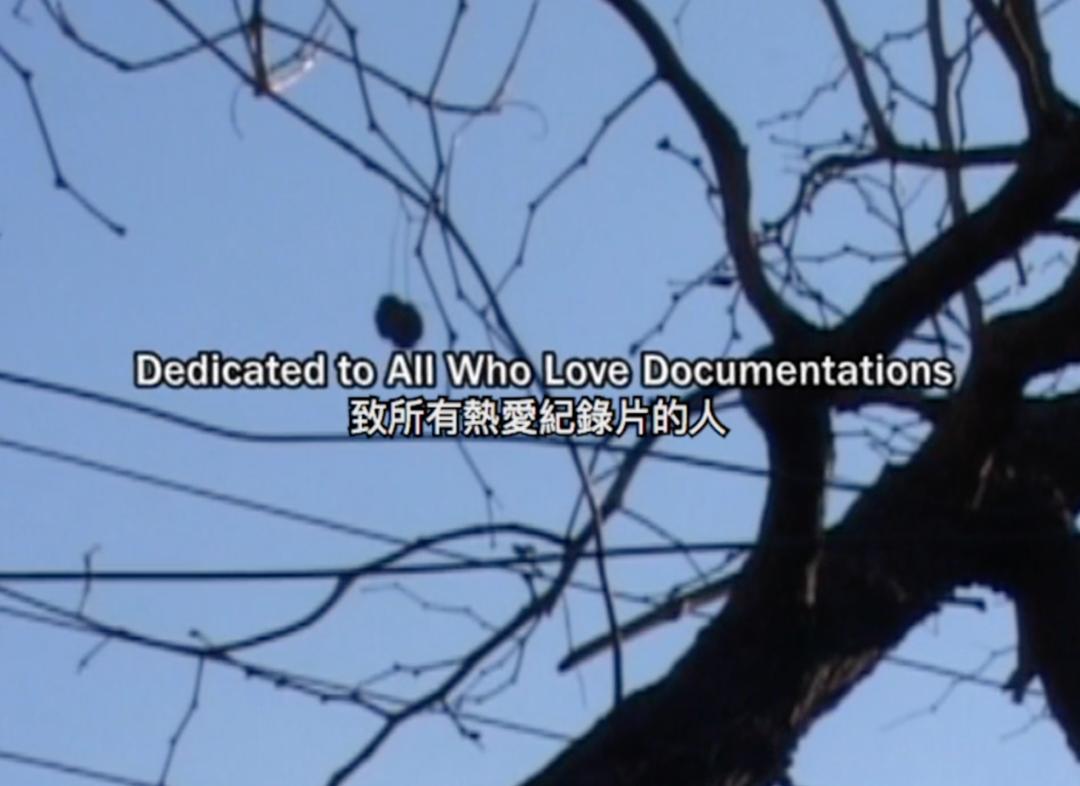
采/文 | 飞檐
编辑 | 杨杨L菲
凹凸镜DOC:在创作《记录之旅:原始档案》的时候,是否有事先构想过想要阐发的纪录片议题?
魏时煜:开始跟司徒老师上课的時候,觉得他讲的都是我沒接触过的,打开一扇大门,想记录他说的每一句話。他备课很认真,手写的讲义,常常誊抄三、四遍,到上课前我去复印给学生。我们是一个学期13节课,他用了1/3的时间在讲怎么处理跟被拍摄对象的关系。开始大家不懂,觉得你教纪录片,总要介绍拍摄步骤吧?第一步、第二步,像在外国还教你怎么找钱,pitching。2003年的时候还不流行,这几年才变得比较流行。后来明白怎么处理关系,其实是怎么做人的问题。我拍他上课、辅导学生,用六个月剪出一个92分钟的版本,被彭小莲彻底否定了。小莲也是司徒的学生,我也告诉司徒老师。
推翻第一个版本,回过头来想,自己究竟要表达什么,就发现他们家的人都跟记录有点缘分。整个都是关于记录这件事情,谁都在记录什么?用什么样的媒介在记录?之前我没有想过,比如雕塑也是一种记录,司徒老师的弟弟兆光是雕塑家,他的记录是可以摸到的雕塑,比如一头牛、一个劳动的人、孙中山等等。之前我没想过这个,然后觉得这个还挺有趣的。
还有司徒的父亲司徒慧敏,就拍过戴爱莲的纪录片。而他本人早在做纪录片之前,曾经在牢里,用特别小的字,在好不容易得到的几张纸上,写听书(是狱友讲给他的)笔记,这种记录,真的是在一个精神荒漠里让生存变得更有意义的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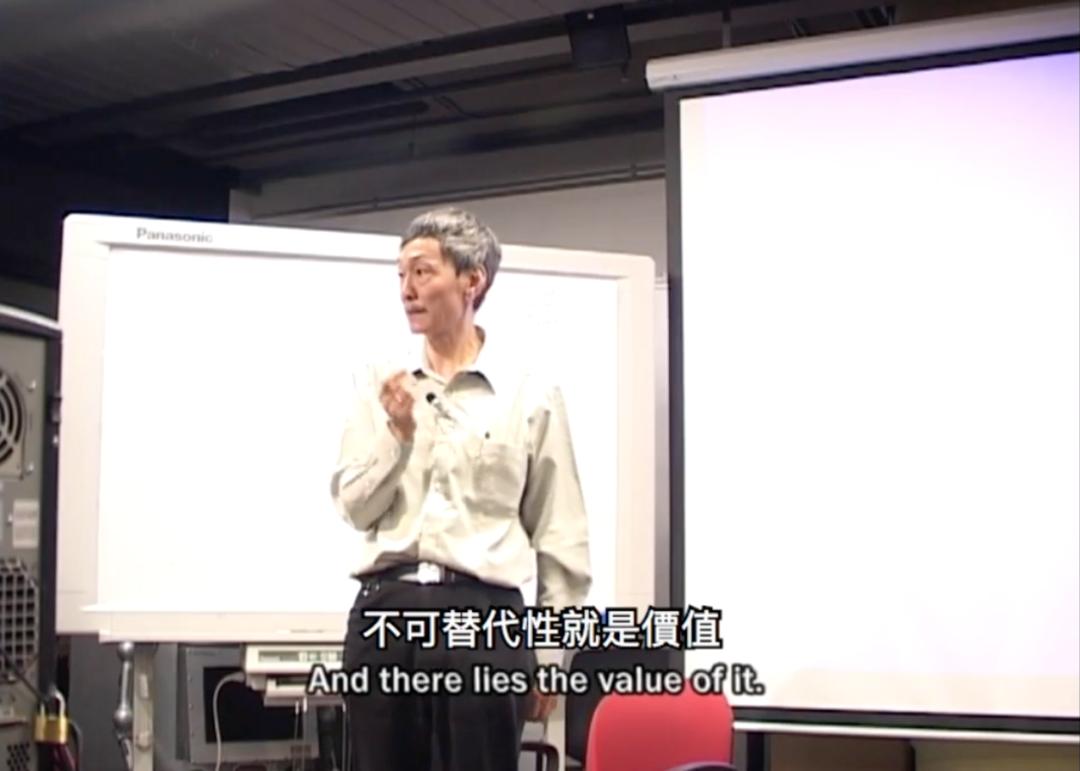
凹凸镜DOC : 司徒老师对您的纪录片创作产生什么影响?
魏时煜:其实我觉得还是和被拍摄对象的关系。我觉得这有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后来我认识好多拍纪录片的人,他们都跟我讲处理不好这个关系。我后来都一直在尝试努力做到司徒老师的要求。
比如拍完片子,你用了别人的材料,会不会去送片子给人家?会不会去邀请别人先看片?是不是真的一家一家去送DVD?然后是不是准备好跟人家做一辈子的朋友,还是拍完片就跟人掰了?
其实是很难的,对于这个关系的重视,限制了我的纪录片选题。比如说我经过思考之后,不会去拍民工、未成年人,主要锁定拍摄知识分子。第一,我要教书,我没有办法从时间上去处理长期跟拍,而且我希望有平等的对话。我希望自己每拍一个东西,都能有所收获,不单是批评社会现实。
去拍中国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命运历史的反思,外国人不一定要看,甚至外国电影节不接受这类片子,可能他们觉得这类历史纪录片应该是BBC的事。但我因为去做这些片子,真的学到了很多。
凹凸镜DOC:如何在历史题材里注入趣味性呢?
魏时煜:怀斯曼他不认同直接电影,他说想用自己的材料做出一个“戏剧结构”。我也想这样,比如我做《金门银光梦》的时候,我比较自觉地运用好莱坞电影那套叙事策略,来构成一个节奏。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被好莱坞电影训练出来的,同时因为好莱坞高票房电影大多有个固定结构,起承转合和大小高潮大概在100分钟的什么位置,都相去不远。我会依据这个结构,揣摩观众可能会在某一个时刻期待一些故事的进展或转折,那我会在这些时间点上给观众一些惊喜,或者介绍新人物出场,或者转场到新的地方,观众在这个节奏里面会忘记自己在看纪录片,会不断有惊喜,恰恰因为纪录片的起承转合不可能像剧情片那么严丝合缝。这种期待和获得不同感受的过程,就是看纪录片的趣味所在吧?

凹凸镜DOC:通过一个人物切入,来回望历史事件的时候,您会去思考这其中的主观性和客观性吗?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魏时煜:其实我这部片子(《记录之旅:原始档案》)里提到过,开头司徒老师讲他的经历的时候,我会觉得都是非常真实的,但有一些他的记忆未必是对的,因为在拍他,又很喜欢他,我就不会去检查他讲的话,记忆是否有误差。当意识到他的记忆开始呈现误差的时候,那一下打击蛮大的,就觉得,你的记忆还有別的误差吗?
当然我没有经验,后来才知道,人的记忆最准确的只有一样东西,就是情绪。对某个事件中的情绪的记忆是基本不会错的,对其他所有事情的记忆都有可能有误差,时间、地点、人物可能都会记错,甚至事件都会记错。我这个片子里,司徒老师把他爸爸的电影记错了,他开始说是《白云故乡》,后来纠正是《游击进行曲》。
像这个信息我做研究时也发现了。但有一些事情是没有办法核实的,比如说,他说伊文思送给他一个磁带,然后里面录的是哪里的民歌,这些东西就无法考证,但是它也不是一个必须弄清楚的历史事实。
我和彭小莲做《红日风暴》的时候,也遇到了很多类似的问题,初剪拿出来给所有的人看,每个人都会讲几个搞错的地方。不出现历史事实的错误,其实也是最难的。但是司徒老师从來没有任何掩饰的,他一开始就提醒我,人的记忆是不可靠的,是我自己开始没有注意到一些历史细节问题,注意到的时候已经是六个月后了。
但是司徒老师那个片子里,他其实是没有任何掩饰的,他一开始就提醒我说,人的记忆是不可靠的。我一开始没有注意到一些历史细节问题,注意到的时候已经是六个月后了。
凹凸镜DOC:在创作《记录之旅:原始档案》的时候,您对于纪录片创作的愿景和现在相比有什么变化吗?
魏时煜:谈不上什么愿景,当时是一种朴实的记录冲动。我总结了一下,因为大家觉得我的片子题材好像很不一样。我记得放《金门银光梦》的时候,就有观众说,我看过你的《红日风暴》,你拍的题材怎么会这么不一样;然后看《古巴花旦》时觉得又不一样了。
我自己总结就是向“优良人类”致敬,包括我拍崔健也一样。像崔健出新专辑,人家就说你这个专辑这么多不同的元素?他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圆的,而不是线性的,创作就应该是多面的。
凹凸镜DOC:您会如何去归纳这些“优良人类”身上的共性特质呢?
魏时煜:其实就是跨越,对边界的跨越。
凹凸镜DOC:可以理解为一种反叛吗?
魏时煜:我觉得反叛是一种姿态,跨越是一个实质。你可以反叛,也可能反叛了什么也没有跨越。其实可以不反叛,就跨越了。

凹凸镜DOC:您之前很多作品是在拍摄人物,拍摄时,您最关注和最关心的是什么?
魏时煜:拍摄的过程当中,主要是能拿到什么料就是什么料。
因为这几个片子很不一样,拍到古巴花旦的时候,我的主角才是活着的,除了司徒老师这个片子,其他的人都是去世的。所以,有什么问题我就可以直接找他。等到拍胡风的时候,胡风是不在的,所以得到他一段声音就已经觉得很宝贵。《金门银光梦》伍锦霞只是照片,没有声音。
凹凸镜DOC:所以您还是先广泛地去收集这些材料,然后再去想会得到什么吗?
魏时煜:是,因为不知道你会得到什么。如果已经有了想法,知道自己要得到什么,那按照司徒老师的话讲,就是你在拍专题片,不是在拍纪录片。因为纪录片就是一个发现的过程,专题片是已经有了框架和想法,然后我就到处找材料来支撑它。
凹凸镜DOC:所以您也不会去提前预设那些东西?
魏时煜:其实没有办法预设。司徒老师跟我们讲说,你不要去预设。我记得司徒老师的课至少用了两三节课讲专题片跟纪录片的区别。专题片的话,在那个框架里面有好多东西,你没办法讲它是真实的。独立纪录片,你怎么预设呢?尤其是当你自己当年那么年轻的时候,对不对?想的基本都是错的。
我对学生说,我说你们可以给我提问,你们把我当成你的访问对象,你可以试一下,看能不能提出什么有趣问题。有个学生问我有没有喝酒喝高的时候,我说纯聊天就可以高的,你知道吗?纪录片中对话的魅力非常大。一个不认识的人,你如何和他对话,让他能跟你分享他的故事?就像司徒老师所说的,你怎么样选纪录片人物?你选的人物,如果他是一直都在做一件事情,你跟这个人物的这个关系就可以长久一点。
对于《记录之旅:原始档案》来说,司徒老师当时教研究生班,我在帮司徒老师干活,想把他说的话记录下来,一开始只是一种记录冲动。

凹凸镜DOC:对于年轻创作者来说,如何从自身的私人议题,更进一步地探索到公共议题呢?
魏时煜:其实,每一个个人议题都是一个公共议题,你在觉得自己还有很私人的议题的时候,就像崔健的那句歌詞:“现在你还太纯洁 现在你的疯狂还是秘密。”实际上是你还没有真正长大的时候,你觉得好多东西只有自己感受到,让你把自己感受到的东西表达出来的时候,其实它已经给了很多人声音。
凹凸镜DOC:一些更个人的东西,比如家庭、成长或是代际之间的议题要如何扩展呢?
魏时煜:一般情况下家庭关系可能也就是那么一两百种,一般人想象得到的也就10种、20种家庭关系。那么实际上,随便家庭关系是怎么样,都代表一群人,都不是只代表自己的家庭关系。所以不必区分个人性和公共性的问题,讲出来的时候已经具备了公共性。
对于年轻的创作者来说,需要分辨自己的片子会和哪些观众发生关系,这一经验是从放映得来的。司徒老师当时会组织放映会,邀请大家一起看片子,这个过程很重要,需要面对观众。
凹凸镜DOC:您曾在海外多地长期学习交流,亲历多种文化背景是否会对自己的创作观念有一些影响?
魏时煜:会,更多的是工作模式和风格,在日本的时候感觉禁锢感比较厉害;在加拿大时,很轻松;现在在香港,好开心,我们学校厉害的女人太多了(笑)。
凹凸镜DOC:作为一名学者兼创作者,对您来说,研究理论和创作之间有怎样的关系,二者之间是否会互相影响?
魏时煜:其实对我来说做理论研究和拍片都是同步的,我一般对于一个题材需要做海量研究。会访问很多人,我每个片子的材料最少都有100多个小时,最多有500、600个小时。像崔健这个片子可能访问了80人,我希望做一本书,对我的受访者有个交代。但是我的片子就只能那么长,一般都有一本书來延伸。
同时,做书的话,尽量把思路理清楚就好,内容纳入一套系统。电影你可以玩的比较多,因为电影不一定依据逻辑关系,只要声音连接的或者画面连接的,就可以连接过去了,电影是视觉逻辑和听觉逻辑不一定要匹配的的一种创作形式,这是电影最好玩的地方。可以带给观众无限的惊喜。
参考文献
[1] 摘自魏时煜的个人主页:https://scholars.cityu.edu.hk/en/persons/shiyu-louisa-wei(067ab9f2-4827-4f80-9b0e-01366947a256).html
采访对象介绍

原标题:《纪录片,一种朴实的记录冲动 | 女性专栏1周年,专访导演魏时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