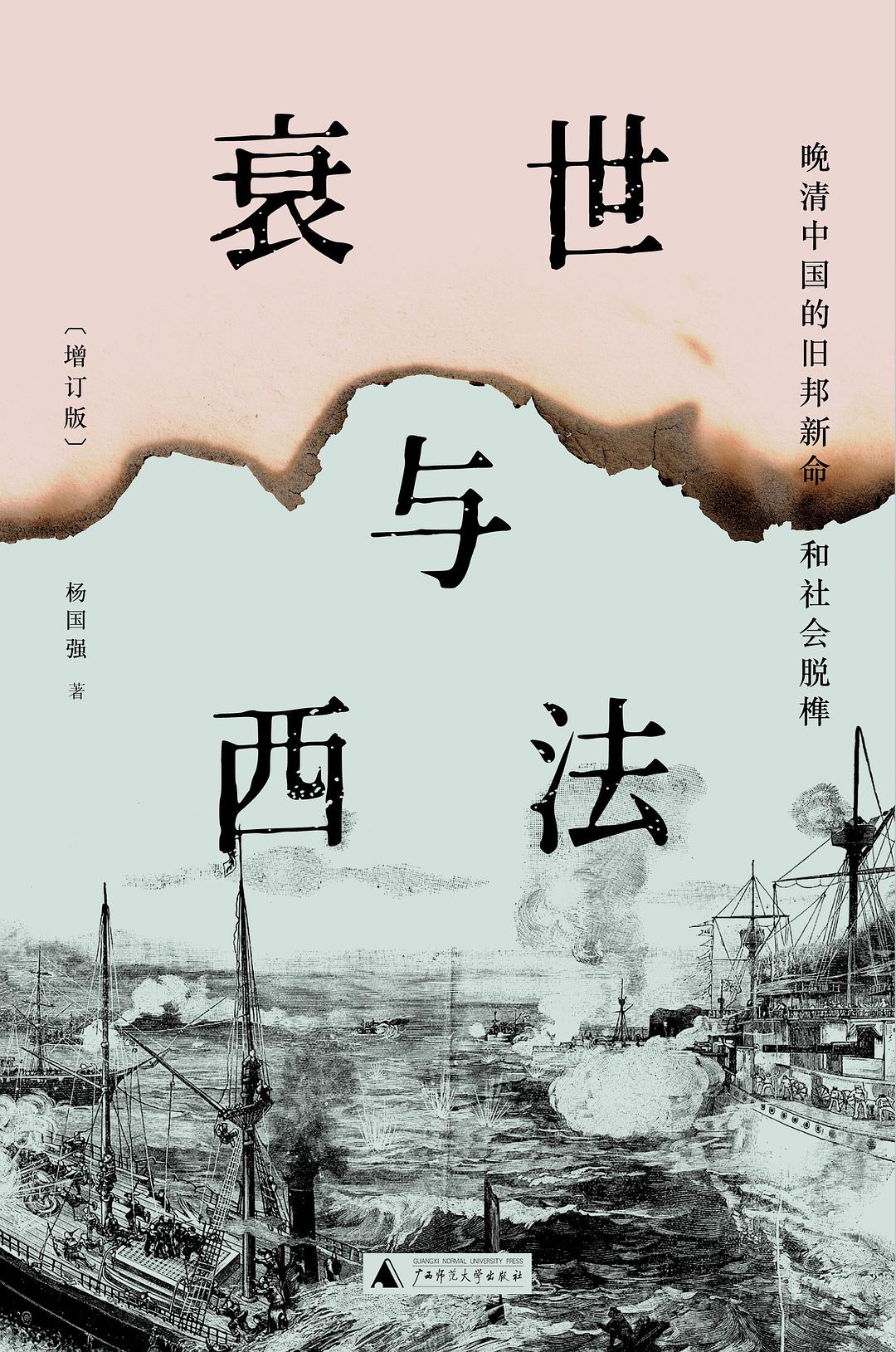光绪元年(1875),英国领事官马嘉理(Margary,Augustus Raymond)被杀于云南。当年二月,英国公使七天之内十多次照会总署,并在此后的一年多里屡次追迫威慑,遂使滇案成为中英之间的巨案。在这种追迫威慑之中,命案从一开始便被用来深作引申,致马嘉理之死实际上已经越出了其一人一身的本来范围,而不可解脱地与英国人谋之既久的商业利益相牵连,并因之而成为英国人商业扩张的一个题目。
 马嘉理事件
马嘉理事件
咸丰八年(1858)的中英《天津条约》列有“税则并通商”各项俟“十年再行更改”一款。而后的中英通商,常常是逐利与纠纷相虬结,从条约中获得了利权的商人又深恨条约空间之太过逼仄,因此,十年期满之日,各个口岸皆群起喧哗。九江的英商要求“外国汽船有权在扬子江和鄱阳湖上航行”;烟台的英商要求修筑通到济南的铁路,以及“获得开采这一地区煤矿的特权”;镇江的英商要求“赋与女王的领事们更大的权力”以对付“中国的官僚”;上海的英商要求“在内地居住和设立栈房的权利”;福州的英商要求“整个中国海岸都对外国贸易和船只开放”;厦门的英商要求口岸外围“免交厘金税”,又要求“关税减半”;天津的英商要求“整个中国都对‘基督教和商业’开放”并“建筑铁路和电报线”,等等。这些主张虽各立名目,但其共有的不肯囿于约章的扩张之势则代表了在华英国商人的普遍意向。因此,同治七年(1868)英国公使阿礼国先后三次向总理衙门送“修约节略”,其中开列的概免厘金,删改税则,内河准行轮船,长江与沿海增开口岸,海关设立官栈,退还洋货厘金,洋盐进口,开采煤矿,以及由此“牵及”的“铜钱(电报)、铁路”,都是这种商人的普遍意向化作了英国使节的外交立场。但在中国人的眼中,西人的扩张已是伸展太过而逼迫太甚。
 《天津条约》签订场面
《天津条约》签订场面
英国人索要的东西,既涉国家财赋又涉民间生理,因此,当日朝廷和疆吏最不能顺受的是这些东西涌入中国之后的伤“国政”和害“民生”。所以,随后八个多月里的中英折冲以“婉商”、“恫喝”、“严辩”、“驳复”相交错为常态,往往“此既舌敝唇焦,彼亦词穷语竭”。然而“其愿未偿,其心未已”,则交涉终无了期。于是,次年折冲再起。最后议定的新约,是中国一方让出了比过去更多的利权;而这些让出的东西在英国一方却是“远不能满足商人的要求”。由此引出的在华英商“对于条约一切细节的反对”和伦敦商界“抗议批准条约”,使英国政府不得不“奏请女王中止批准”这个同阿礼国的名字连在一起的新约。显然,商界之阻止新约,表现的是其扩张意向在积久之后不能自抑的炽盛。而新约之能够被阻止,又一定会使其扩张的意向在后来的岁月里愈益炽盛。在后来的岁月里,这种既存于中英之间而没有借修约获得满足的“要求”,便不能不持续地影响和制约英国的驻华公使,并因之而不能不持续地为历史造因果。阿礼国之后,面对商界并且代表商界的是继任的威妥玛。而他一定会比阿礼国走得更远。
若着眼于一个更大的范围,则与厘金、税则、航运、采矿之类相比,英国人的商业扩张还在于久谋以云南为入口的“中国帝国西南边陲的那条路”,以期由此取径,“可以在那个国家的内地胜利地作一切将来的竞争”。自19世纪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英国人在两次侵缅战争之后已经据有下缅甸。对于中国人来说,英国人在地理空间上的这种移动,是本来的“岛夷”和“海国”最终已变作此日的近邻和强邻。于是,自五十年代后期以来,从缅甸进入中国云南之想便顺次而起,成为英国商界和政府议了又议的题目。与这些群起的议论相匹配的:是六十年代后期接连有过两次由英国政府和印度当局组织的探路,其中的一次已到达中国境内的腾越(腾冲),可谓眼到脚到,节节远伸。而与英国人的节节远伸相仿佛,是相近的时间里法国人用同样的手段占据了越南的南部,并因之而同样由“海国”变成了中国的强邻。之后,当英国人从缅甸向东面的云南探路之日,法国人也在从越南向北面的云南探路。总署在奏报里统谓之“蚕食之谋,匪伊朝夕”。至七十年代中期,滇边所面临的已是法人“窃据越南各省十之六、七,欲由越南溯九龙、澜沧、黑惠、漾濞各江,并沿江各陆路自南而来”;英人“与缅甸立约通商,即由缅境历猛卯、腊撤各土司界,自西南而来”。两者都在为中国造大患。但就英国人而言,一心溯江而上并“在极力和英国竞争”的法国人又是一个使人不能安心的直接的对手。就这个意义而言,法国人在滇边的存在和躁动如同是对英国人的一种催促。除了这一面之外,七十年代中期英国的对华贸易已在“销沉和停滞”之中。随这种变化而来的,是商界为“产品寻找新的市场”的强烈冲动又在使这个议了又议的题目变得日趋急切。因此,同治十三年(1874),在伦敦的提调之下,印度当局再度指定陆军上校柏郎(Browne, Horace Albert Colonel)领队探路,以勘测滇缅之间的陆路交通,同时要求其驻华公使派译员作引导。刚刚调入上海领事馆的马嘉理遂奉命入滇缅,并于次年一月在八莫与柏郎会合。之后马嘉理由缅境返回中国,行至蛮允附近被杀。已在东进途中的柏郎一行也半路受阻,就此折回八莫。在当日的奏议和后来的叙述里,这一段史事便被称作“滇案”或“马嘉理案”。
马嘉理之南行,是由中国政府发给“执照”的。发“执照”的总理衙门同时又曾“函致该省督抚,饬属于该翻译官到境量为照料”。前一面是条约义务,后一面则是不在条约之内的格外当心和格外提防。但彼时云南的回民起事以及牵连弥广的长久动荡甫得平息,滇西犹在不宁之中。对于太过遥远的京城来说,便是当心和提防都只能鞭长不及马腹。因此总署虽已“函致该督抚”,而当马嘉理被戕杀19天之后英国公使威妥玛的照会送到了面前,地方文报还没有说起过这件事。于是在由此开头的中英交涉里,总署便成了后知后觉的一方。对于英国人来说,马嘉理之死直接打断了他们预想中的探路。但当时英国外相德比(15th Earl of Derby)对威妥玛作训示,特别提醒的还是与中国政府交涉之际,要“牢记印度政府派柏郎上校率领探测队去云南的目的”。显见得探路虽然一时中断,而促成了探路的那种商业扩张的意向却仍然支配着英国一方。在同一个时间里,还有过美国的一个外交官站在局外对总署作旁白,说是“英国上下议院绅耆率多巨商,久欲开通云南一路,兹闻马嘉理被戕,群情愤忿,即议请印度总督派兵进滇,藉端用强夺取”。这段话以其同属西方世界的闻见之知为根据,具体地描述了这种扩张之势移入滇案的情节和过程,则意思又进了一层。因此,作为身在这些背景之中的英国公使,威妥玛同总署交涉滇案,从一开始便不肯作就事论事之想。光绪元年(1875)二月,他在送递总理衙门的“备忘录”里开列的是:一、中国政府派员调查,并应有英国官员全程介入;二、准由印度当局再次派队探路;三、赔银十五万两;四、作为《天津条约》给予英国使节的权利,实现“适当的和满意的觐见”;五、“确保”英商免除正税和半税以外的一切征课;六、“立即予以满足”历年累积的“各口未结等案”。其中与马嘉理之死直接相关的有两条,而英国官员介入调查和预先勒取十五万两两节,以当日的万国公法而论,已皆属离奇。余下的四条则同马嘉理个人全无关系,其命意所在大半是英国人的生意,都是《天津条约》之后英国人向中国屡索而不能得的东西。以滇案的本义和范围相衡量,显然太过牵连无度而枝杈旁生,然而按英国人的理路,“备忘录”所开列的六条还意犹未足。
因此,当年夏秋之交威妥玛过天津,同奉命羁縻的李鸿章“叠次”面谈滇案,于六条之外又立“七条”名目。其大端为中国政府须派大员赴英国道歉,以及朝廷明发上谕切责云贵总督岑毓英等等,而其侃侃而谈中所力持的裁撤厘卡、多开口岸和“上谕内所称‘英国’字样必要抬写”以示敬意之类尚不在七条之内。然而滇案没有了结,则七条犹是止境。至光绪二年(1876)五月,英国公使与总署“累经往返议论”而动辄“忿激异常”之后,又有过七条变为六条,六条再变为八条的波澜兴作。由此添加出来的,是“中国人有伤害英国人案件,准英国派观审”;会商“滇省边界商务”;英国派员驻大理(或云南他处)及重庆,并列“奉天大孤山、湖南岳州、湖北宜昌、安徽安庆、芜湖、江西南昌、浙江温州、广东水东、北海等处”为口岸。而赔银之数,又因加上“派兵护送”和“多调兵船”之费,须由英国另作核定。其深作开掘,显然用心都在滇案之外。
这个过程历时一年又数个月,与这种越来越多的指索相匹配的,是代表英国的威妥玛在同中国作交涉的时候始终不懈地施以凌厉激亢。总署当日作奏报,遂于叙事之中不能不累举其“词意极为激切”、“愤激不平之气,狂妄无理之言,殊堪诧异”、“咆哮急迫”的种种脸相狰狞。后来的一个法国历史学家论中英之间这一段史事,用为刻画的也威妥玛“最为好战的意图”。因此,威妥玛的职份虽在交涉,而更喜欢用的则是胁迫。他对总署说的是,“若弗照行,从此绝交”,使馆“各员全行出京”;他对李鸿章说的是,若再拖延,“我只好出京,把云南事交与印度大臣办理,各口通商事交与水师提督办理,英商税饷概不准完纳”,并预言,“那时兵端必开,再议新章断不止此数条”。
在这一类语言胁迫之外并作为这一类语言胁迫的一种实证,英国政府应威妥玛之请,曾于光绪二年(1876)春专门从印度调来四艘军舰进入中国海面,以期用炮口助声势。昭示这种用来打仗的东西,是意在告诉中国人,语言的胁迫并不仅仅止是以口舌作风波,其直露的一派躁急是自额尔金以来所没有过的。但中英滇案交涉的不断延续,以及威妥玛在这个过程里的一再“愤激”和一再胁迫,又说明了英国一方的六条、七条和八条都没有被中国人全部收受。光绪元年(1875)总署概论滇案交涉,曾言之明切地说:“自庚申定约以来迄今十有余年,各使臣觊觎中国,屡欲扩充,均经臣等力持而止。”是以此日英国公使“所求通商等事”皆“蓄谋已非一日而特于滇案发之”。然则“就洋情而论,则所求各节为本图,而滇案其藉端也”。这些话说明了英国人的利害所在和中国人的利害所在。于是英国人要把这些东西同滇案混起来,而中国人不得不把这些东西同滇案分开来,统归之为“一切拉杂之词”,并“叠与相持”而“痛加驳斥”。交涉的过程遂因之而成为一个不断冲突的过程和屡次中断交涉的过程。
然而中英滇案交涉之际,又是中国政府侷促于四面交困当中的时候。一方面,由日本侵台引发的衅端虽然甫得平息,而日本之咄咄逼来则刚刚开始。另一方面,西征在军事上的一路推进已经使中国军队与占据了伊犁的俄国人越来越近,从而与中俄之间的危机和交涉越来越近。而同一个时间里,法国在越南不息的掠取又正日趋日近地化为对于中国持续的冲击和强烈的冲击。这些起于中日、中俄和中法的事端都发生于滇案之外,但由此引发的紧张和忧患悬在头上,则不会不具体地而且直接地制约中国人在滇案中的交涉。因此同“叠与相持”和“痛加驳斥”相交错的,常常还有主事的中国人由四面交困下的一旦“决裂”,而引出“值此饷绌兵单,大局尤可危虑”的涉想和担心。而后,中外关系里的这一面便不会不导致交涉中的“深知事势紧要”而“曲予通融”,从而导致中国一方在这种交涉,冲突,再交涉,再冲突的过程里一边为守护利权作撑持,一边为“力保和局”向后退。所以每次由交涉而中断交涉到再起交涉,英国人都能更进一步。
至光绪二年(1876)七月,发生在土耳其的“大乱”已从远处牵制了英国。之后,是英国外交部“非常希望云南问题从速解决”的训令又实在地牵制了已经“无所借口”,但还“觉得不满足”的威妥玛。而在中国一面,则是出现于华北的旱灾正以其空间上的不断的延展而形成越来越大的规模和范围,使本在四面交困里的中国更深一层地进入了内忧与外患的交困之中。这种内忧与外患交困形成的内外互相牵动,不能不使中国人在交涉中的余地更少。原本的单面制约已演为两面各有各的牵制,因此,在经历了17个月的折冲之后,代表中国政府的李鸿章同英国公使威妥玛在烟台面议约章,以了结滇案。这个过程又费时二十多天。最后签订的中英《烟台条约》分作三部分。第一部分以“昭雪滇案”为总目,大端在遣使谢罪,赔偿白银20万两,商订滇缅通商章程。第二部分以“优待往来”为总目,大端在协定中国官员同各国外交官往来的礼节,以及各口岸事涉中外的“承审章程”。第三部分以“通商事务”为总目,大端在各口租界免收洋货厘金,新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并俟轮船上驶之后再议重庆,辟沿江六处地方停泊轮船并上下客货,进口洋药(鸦片)一并在海关完税纳厘。此外还有“另议专条”名目,主旨在准许英国派员入藏探路。
在这些列入了约章的条目里,英国人不仅可以沿长江一路从下游而至中游,从中游而向上游自如地伸展;而且可以沿滇缅通商一路从西南锲入并且远伸,以经营中国的边地和内陆。由此拓出来的广袤空间,已是大幅度地实现了他们“蓄谋已非一日”的扩张意向。而同时的“承审章程”又别立一种法权结构,使之能够侵入中国政府的司法审判;至英人进西藏一条,则以后来藏地的不宁为中国人带来了历时久远的祸患。这些都说明:《烟台条约》已使英国人获得了影响后来的种种利权。但当时的英国商界经十多年期待悬想之后已所望太奢而不能知足。由此不能知足所催生的鼓噪,尤不满于《烟台条约》的“通商事务”一端。加上法国、德国、俄国、美国和西班牙联合起来,以备忘录方式反对英国“片面行动”,遂使英国政府批准这个条约在时间上比中国政府迟了9年。滇案由马嘉理之死而起,因此在交涉滇案的过程里,中国一方始终以“彻底确查”当日之真相为杜绝彼族“多方逞志”的要义。光绪元年(1875)四月朝旨已令署云贵总督岑毓英“彻查根究”;一个月之后又特派湖广总督李瀚章为钦差大臣“赴滇查办”。朝廷前后相继地驱动一个总督和另一个总督,皆意在先得真相,以势位与责任比,又以后者为重。因此,自当年十一月至次年五月,李瀚章六次奏报“英员马嘉理在滇被戕情形”都被总署引入交涉之中,一以“不法匪徒”与“野人”之“伺隙乘机劫杀”为滇事的因由所在和来龙去脉。“伺隙乘机劫杀”是一种一哄而起和四散而逃,以此立论,显然是李瀚章的查办并没有把云南的官府拖入漩涡之中。但郭嵩焘并不相信云南的官府不在漩涡之中,并在当时就滇案之起因曾另立一说:
臣在闽臬任内屡接云南信报,多云云南抚臣岑毓英探知英官柏郎带有缅兵入境,檄饬腾越厅、镇防备;腾越厅、镇又檄饬南甸一带土兵、练勇防备。辗转相承,浮言滋起,以致无故杀毙译官马嘉理一员,贸焉构难。
继之再劾其事后“意存掩护,又不查明肆杀情由据实奏报,而一诿其罪于野人”,并请“将岑毓英先后酿成事端之处交部严加议处”。比之“查办”所得,这些情节说明了疆吏的识度、判断、意志和权力在当日滇边所造成的骚动和盲动,以及这种骚动和盲动与滇案的因果关系。然则深究始末,从“匪徒”和“野人”很容易推导到官府。但那个时候相信郭嵩焘的人并不多。奉旨“查办”的李瀚章且对郭嵩焘的奏议作逐层指驳,而以“拿获各犯供认抢劫不讳,委非归罪于野人也”为总结之词。迨滇案了结而云贵总督换了刘长佑,则“各犯供认”全变。彼时刚刚与英国人缔结了《烟台条约》的李鸿章在给沈葆桢的信里已说是“烟台定议条款,势迫于不可中止。旋接荫渠、琴轩来函,以岑中丞去滇后,犯供全翻,与威使访查情节一一吻合,足见彦卿手眼神通能障蔽家兄等耳目,而几贻国家之大祸,可不惧哉”。显见得刘长佑和潘鼎新的信所证明的,是岑毓英介入滇案的程度其实比郭嵩焘推断的还要深。
这种迟来的翻供说明的是,在一年又六个月的中英交涉里,总署对于滇案的真相始终没有弄得十分明白。而作为对比,是英国一方曾不断地追究岑毓英的责任,并执意要将岑毓英“提京审讯”。由此造成的压力,成为总署在交涉过程中备极窘迫和苦恼的题目之一。若以刘长佑、潘鼎新信中所说的“与威使访查情节一一吻合”为可信,则英国一方的这种追逼不会全是虚声恫喝。但烟台议约一经开局,威妥玛即收手不再追逼,至中英双方以《烟台条约》议结滇案之后,威妥玛且为“官犯”与“野匪”代求恩典,“以为责其既往,莫若保其将来,请将案内各犯宽免”。其间的直起直落,正说明了同已得的种种权益相比,在英国公使心中,其实“马翻译被戕之事亦算不得什么”。于是中英交涉的最终结果留给这一段历史的,仍然是种种细节上的模糊。
(本文摘自杨国强著《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增订本)》,一頁folio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10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