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鱿鱼游戏》:为了活下去的“失败者”们
和传统“大逃杀系”不同的是,《鱿鱼游戏》设置了玩家知情后离开,却在体验了现实绝望后“自由选择”重新回到游戏这一情节——他们主动自愿进入这个宣称“人人平等”、“机会均等”的弱肉强食的丛林。可以说,这部剧准确地捕捉到了现代社会权力的特征,并不是逼迫,而是煽动、诱惑人自觉地承担风险。同时,几个游戏的幼稚、简单、运气成分高淡化了传统大逃杀系给人的“智斗/武斗”的印象,但却让“平等”本身显得更为荒诞,它完全是一种抽象的、纯粹概率意义上的平等,而且故意无视不同人之间体能、经验等方面的不平等。《鱿鱼游戏》的基本设置与总体规则无疑是对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强烈反讽。
*本文一二部分涉及轻微剧情透露,第三四部分涉及关键剧情透露,推荐看完剧再阅读。
“大逃杀”的谱系与新自由主义丛林法则
近日网飞(Netflix)推出的《鱿鱼游戏》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巨大的关注。这部剧集的基本框架——富人让人在游戏里相互厮杀——并不新鲜,近年的电影《要听神明的话》(2014)、《饥饿游戏》(2012)和上年同样由网飞播出的《弥留之国的爱丽丝》(2020),都证明了这类题材容易获得商业上的成功。于是,观众对这一类型影片经常有两种误解或偏见,一种是把它们当作纯粹的商业快餐爽片,类似于闯关综艺游戏和“吃鸡”(《绝地求生》(2017))等电子游戏,没有什么深度可言,不能企图从中找到什么意义;另一种认为这种题材的作品是对人性的挖掘,通过将人放到极端的环境中来试验平时被文明的面具所遮挡的人性“真实”的一面。本文希望可以通过《鱿》为例澄清这两种误解或偏见,“生存系”/“大逃杀系”也许关注的并不是真空的“人性”,它和其他类型的文艺作品一样,有着反映作品所处的时代下人们的生存境况的功能,就《鱿鱼游戏》来说,除了反映社会的现状,还有改变社会的志向。当然,也有人认为这种剧即使加入了政治性的佐料,它也只不过是资本主义主宰的娱乐工业的一道景观罢了,人们无法从中得到政治教育。确实可能是这样,它们是否真的起到某种政治性的后果,还有待历史去检验。
“生存系”发源于日本,也被称作“大逃杀”系,是因为高见广春于1999年发表的小说《大逃杀》,这一类型在日本有着约二十年的历史。《大逃杀》小说讲述某高中的一个班级的学生在政府的要求下开始互相残杀,直到剩下最后一人,目的是“培养青少年们在逆境中排除各种困难,并由此获得坚韧不拔的生存能力”。本作被深井欣二改编成电影(2000),该片上映后引起了道德上的恐慌,被多个国家列为禁片。日本文化研究学者宇野常宽认为,《大逃杀》“提前预告了新时代的氛围”【1】,开启了2000年代“生存系”作品的想象力。随后2000年代的一系列人气作品也采用了“互相厮杀直到最后”的设定,如《真实魔鬼游戏》(2001)、《Fate/stay night》(2004),还有一些作品虽然没有字面意义的“厮杀”,但是直面了“如果不努力做任何事的话就生存不下去”这一价值观,如以考取东京大学为目标的《龙樱》(2003),描写在极其严酷的老师的主宰下生存的《女王的教室》(2005)等等。

《大逃杀》里的老师
“生存系”的想象力有什么特别之处呢?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还要向前追溯,直到被日本评论家称为“政治的季节”的1960-70年代,这时日本学生响应世界左翼运动的潮流,充满热情地投入到革命运动中。但是日本联合赤军在1970年代走上了恐怖主义暴力行动的道路,最后以失败告终,日本民众逐渐丧失了对革命的“宏大叙事”的信心。越来越多的人不相信能够通过社会来自我实现,相反,他们认为所谓出于崇高理想的大义可能会变成对他人的伤害,所以出现了“不知道做什么是对的、不想伤害别人,所以什么都不做”的御宅族的想象力,其巅峰就是动画作家庵野秀明的《新世纪福音战士》(1995-1996),14岁的主角碇真嗣在故事的中后期因为误伤了同伴,拒绝再驾驶福音战士,封闭起自己的内心,真嗣的形象得到了同时代的年轻人的深刻共鸣。

《新世纪福音战士》里的碇真嗣
然而,根据宇野的观点,随着小泉纯一郎的新自由主义改革,2000年代的想象力环境发生了变化,如果90年代日本文艺界的主调是“什么都不做”的话,那么00后的主调便是“什么都不做的话就会死”,人们开始厌恶逃避现实的青年,认为他们应该为自己的困境负责。随着左翼的普遍衰落以及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这种意识形态不仅在东亚,而且在全世界都变得很常见。在丛林体系日益残酷的21世纪,“狠”成为了生存的法则。“生存系”的作品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应运而生,在这些作品里,只有在残酷的互相残杀中胜利的人才能存活。
在日本的“生存系”作品中,直接描写贫富差距、工人运动等左翼传统题材的作品已经很少,很多作品初看起来和现实世界没什么关系,需要经过评论家的解读,才能看到它们和社会历史之间的关系。相比起日本,韩国近年的作品更加直接地描写了现实社会的残酷痛苦,这和韩国新自由主义近三十年来的迅猛发展以及人们对它的不满有关。当下韩国的左翼政党也非常支持此类“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2020年2月20号,韩国总统文在寅在青瓦台宴请刚获得奥斯卡奖的《寄生虫》剧组成员,感谢导演奉俊昊对韩国电影做出的巨大贡献,并且表示他在努力解决《寄生虫》这部电影里展现出了很多社会问题。官方的大力扶持让韩国描写现实社会问题的作品有资本登上主流影视的舞台,让韩国编导在创作“生存系”的作品时可以更加直白地讨论它的社会性。

文在寅和《寄生虫》剧组
《鱿鱼游戏》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展开的。这部剧的主人翁成奇勋遭遇工厂裁员、工运被镇压,生活惨淡,沉迷赌博,负债累累,靠着年迈母亲的摆摊赚来的微薄收入过日子,但却对他人有着质朴的善意。这样的形象也许一开始会激活一些观众的“穷人原罪论”,是“性格决定命运”——正是因为他不思进取,投机取巧、只想着眼前的日子而没有对未来的打算、还是个“圣母婊”(他的高材生发小曹尚佑也对他说了类似的话),才会沦落到这种地步。但真的是这样吗?

从“规训社会”到“享乐社会”
参加“生存游戏”的都是什么人呢?日本很多的“大逃杀系”作品中角色都是无差别地被卷入生存游戏中的【2】,但是《鱿鱼游戏》里进入游戏的人物是“自愿的”,只要他们进行民主投票,如果有过半数的玩家同意,游戏可以终止。但是即使在第一个游戏后终止成功了,绝大部分的人还是又“自愿”回到了鱿鱼游戏里,因为比起现实生活中地狱般绝望的生活,这个杀人游戏里的奖金更能给他们希望,主办方对这个游戏的定性是“给那些无路可走的人有公平竞争的机会”。这些人之中有被裁员又欠下一屁股赌债的成奇勋、因为炒期货欠下巨款的曹尚佑、逃至韩国后母亲被遣返因而和弟弟一起过着坎坷生活的姜晓、被黑心的韩国老板恶性欠薪的巴基斯坦籍劳工阿里等等。他们的潦倒不一定是因为他们犯的错,比如成奇勋所在的双龙汽车公司搞砸了,并不是员工的错,但员工却被要求承担这个责任。

奇勋在双龙汽车公司的事件是受害者。那么他在之后沉迷赌博是自作自受吗?奇勋的发小尚佑从名校毕业,在证券公司上班,但把自己和母亲的钱都投进去玩期货,这又是一种自作自受吗?确实,没有人逼他们赌博,是他们自己选择的。这是《鱿鱼游戏》里的游戏和大部分同类作品不同的地方,主办方并没有强迫玩家参加游戏,而是煽动、诱惑他们参加,让他们自愿选择参加游戏,自己负上责任的。(有人可能会反驳说,参加游戏的人是走投无路,但没有证据说明尚佑是迫于无奈才去玩期货的,这一点在下一节说明。)这部剧准确地捕捉到了现代社会权力的特征,并不是逼迫,而是煽动、诱惑人自觉地承担风险。
关于这一点不妨参考福柯的研究【3】,在历史上可以区分出两种权力装置:第一种是前现代的君王权力,君主拥有将违反律法的人处死的绝对权力;第二种是在大革命之后的规训权力,它渗透在社会的毛细血管里,在学校、监狱等场所里用规训生产出温顺服从的主体。现代社会有超出两者的一种新的权力装置,德勒兹称之为“控制社会”的装置【4】,这种权力并不禁止人去做什么,反而煽动人去“自由”地冒险和投机,当投机失败的时候,社会机构就会将这批人排除在外,而个人就要承担起这个责任。《鱿鱼游戏》里那些走投无路的人只剩下他们的“赤裸生命”,被迫签订下器官买卖合同,生命(甚至人格尊严)成为了最终的抵押。那个神秘组织仿佛就是一个被社会排除在外“废物回收器”,只保留“废物”们的器官和他们能提供给观众的“乐趣”。
《鱿鱼游戏》的总体规则对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有着强烈的反讽,这个地方是由一个崇高、超越性的“民主公平”的原则所支配的,无论男女老少,都有绝对“平等”的“翻身”机会。里面的工作人员不会无故地杀人,只有当参加者遵守不了规则,或者在游戏中犯错、失败(而且很多时候是运气上的失败)才会死。相信每个人都会看到这里面的“平等”有多荒谬,它完全是一种抽象的、纯粹概率意义上的平等,而且故意无视不同人之间体能、经验等方面的不平等。《鱿鱼游戏》里的几个游戏的幼稚、简单、运气成分高淡化了传统大逃杀系给人的“智斗/武斗”的印象,但却让“平等”本身显得更为荒诞:并不是智力或体力上有优势的强者才能活着,比起所谓的能力,运气更加重要,活下来的与其说是强者,不如说是“幸运者”。
在控制社会中的“自由选择”还有一个与规训社会非常不同的特征。在规训社会中,监狱等惩戒的场所是为了让主体“改过自身”,重新温顺地回到社会中他该有的位置上,这是社会对主体(以及主体对自身)的“长线投资”,希望他们经过规训后能继续被社会输出价值。但在瞬息万变的当代社会里,长线投资失去了必要,社会只需要捕捉主体对社会来说的“最高点”,然后当它处于低位时(不符合某种社会标准时)将他抛弃,然后将责任归到他自身,如同信贷机构在曹尚佑的最暗时刻不会伸出援手。
在失去价值时抛弃不仅发生在社会对待人,人对待他人上,还包括人对待自己生活的方式上。他们已经不再相信“努力就会富裕”这样的观念,即使再努力,取得的成果也会在一夜间化为虚有,所以他们追求的也是最为即时的享乐,沉迷如如酒精、毒品、赌博、性等等的享乐,不去想之后怎么活的事情,甚至有人做好随时去死的准备。
最生动的一幕是韩美女上厕所时在下体里掏出一个胶囊,当我们以为那里藏有什么逃生的法宝的时候,看到里面其实是香烟和打火机。相比起能够让她更好地赢得游戏或者说逃出去的道具,她不辞劳苦地带进来的是几根香烟,相比起长期的利益(努力赢得游戏逃出去),她更加重视短期的快乐。同样,成奇勋沉迷赌博也许和对长期的利益的悲观有关,他所在的公司被收购后全面裁员,而工人联合的抗争也没能有让人满意的成果【5】,在对社会整体高度不信任的情况下,短暂的享乐就成了“活到明天”的手段,日本心理师信田さよ子从各种物质(酒精、赌博、药物、购物等)成瘾者的自述中也找到了这一点【6】。而这一点又和资本主义重合,资本主义既生产这些消费品让人活到明天,又通过这些消费品将人控制住,因此拉康派将这样的社会称为“享乐社会”【7】。

吸上第一口烟的韩美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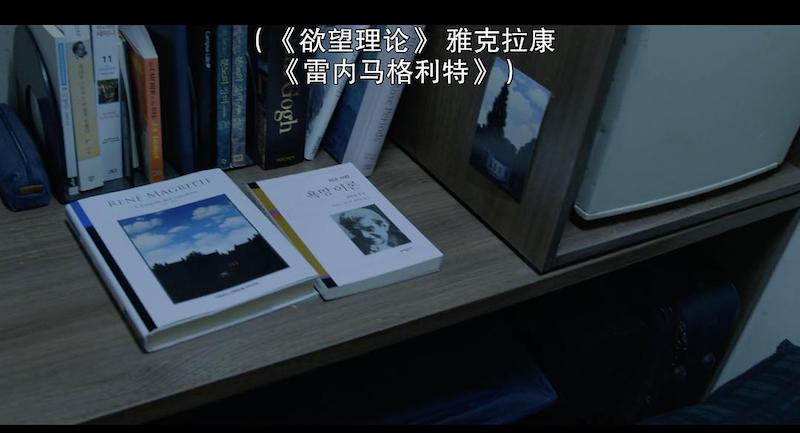
剧中亮相的拉康著作
历史终结后,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值得献身
上节还有着一个问题,参加游戏的人是因为走投无路,但没有证据说明曹尚佑是迫于无奈才去玩期货的,作为一个工作体面的高材生,他并非像那些底层人那样“无路可走”,只能沉迷于酗酒和赌博等的小快乐。《鱿鱼游戏》不仅探讨了走投无路的人,而且还探讨了那些社会意义上的成功者为什么会“冒险”。这个问题在“幕后黑手”那里有提示。
在成奇勋“胜出”游戏,一蹶不振的时候,被游戏的发起人约见,他原来就是游戏中的1号玩家,也是成奇勋在游戏里认识的第一个人——那个老人家吴一男。当吴一男被问到为什么这样做的时候,游戏的真相,甚至这个“社会”的真相被揭晓,他回答道:“你知道,身无分文的人,和家财万贯的人共通点是什么吗?就是人生毫无乐趣可言,如果家财万贯,不管买什么或用什么来满足口腹之欲,最终都会变得了无生趣。”我们不能轻率地认为,这是编剧为了把故事的起因圆了才让角色这样说,如果是这样,这一幕就毫无必要。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吴的话:富人和穷人的共同点,就是“人生毫无乐趣”。
这千真万确,在消费社会/享乐社会,参与有意义的事业、“勤劳致富”(长期投资)的通道破灭,只能追求那些小快乐(短期投资)。生活了无生趣并不等于没有小快乐,穷人能够享受很多简单的快乐,因为他们没有选择,只能靠这些活到明天,“人生了无生趣”反而并不会从他们口中说出。吴一男也是从弄巷里长大的,“用钱滚钱”当了富豪,当他实现阶层跃升,有了选择,有了可以改变自己和他人生活的资源的时候,却对帮助底层人没有兴趣。他发现即使是有了钱,生活依然毫无生趣,他和他的客户依然是选择了“游戏”。像那些参加他们的游戏的穷人一样,吴一男这些富人也并没有看见别的选择。这些富人和穷人一样,对社会和人性都充满不信任,于是还是和像穷人那样选择了“短期”的享乐,哪怕冒着被逮捕、被杀、失去一切的风险。如果说穷人受折磨的是物质匮乏(生命和生活随时无法维持)的痛苦,那这些富人受折磨的是无聊之苦,就算摆脱了前者后者也无法摆脱;对于穷人来说,不加入游戏的结果是生活不能持续;对于这些富人来说,不游戏的后果是陷入存在的无聊。
这剧中,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能够获得的都是短期的享乐,而欲望的维度是缺席的。资本主义用可以快速满足的商品,湮灭了不可能获得的“物”,也就是湮灭了人的欲望——拉康派精神分析认为欲望是建立在禁止和不可能性上的,欲望能让人产生变革的幻想,这让主体可以带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激情朝向不可能性行动。失去了不可能的维度,一切商品都了无生趣。
从黑格尔主义者科耶夫到福山都发表过的“历史终结论”,在20世纪尾声苏联解体后大行其道。福山认为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8】,而科耶夫则认为在历史的终结处,人类作为“否定性”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已经不需要再有战争、革命与哲学,只需要“爱、艺术、游戏”【9】。
在“历史的终结”的论调中,没有什么比自己的享乐更加重要了,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值得牺牲和献身。在大写历史的终结之后,资本主义的丛林法则作为超越性的法则支配着每个人,《鱿鱼游戏》里的三条基本游戏规则——“必须参加游戏、不能妨碍游戏的进行、半数参与者不想参加游戏的话游戏即可终止”,便是超越性的“民主自由原则”很讽刺的体现,规则里的“游戏”都可直接换成“新自由主义丛林法则”。
所以,问题并不只是“穷人如何翻身”——如剧中的高额奖金的游戏所暗示的那样,控制社会煽动着人去积极把握翻身的机会,宣称只要加入新自由主义的“游戏”,人人都有翻身的机会,只是输了之后要自己负责后果——问题还是如果仅仅服从这些规则,争取在这个规则内杀死其他玩家独自存活,之后又会如何呢?吴一男的答案是胜出了只能陷入无所事事之中,靠残酷的游戏来消遣;曹尚佑的答案是会被煽动继续投机,再次掉落深渊;警察的哥哥(阅读拉康和尼采的青年,弟弟黄俊昊调查到他曾是某届游戏的胜利者,我们可以推测它是从玩家变成了管理者)成为新自由主义的祭司,维护着“游戏规则”的神圣性(所以他对“玷污这个世界”的作弊者深恶痛绝);而成奇勋回答是的答案是什么呢?
为了活下去的“失败者”们
“生存系”作品的发展都是从主人翁单纯想活下来,再到因为伙伴的牺牲而悲痛愤怒,最后再到相互结盟推翻这个体系,最终寻找除了上述两种“胜利”之外的别的可能。在这过程中,那些在游戏中偶然结识的伙伴起着重要的作用。
成奇勋两次决定参加游戏都是为了亲人,第一次是女儿,第二次是母亲,在社会的意义上他是个不合格的父亲和儿子,他对她们充满着愧疚之心,社会(尤其是儒家文化圈)为家庭赋予了超越性的价值。但我们不能忘了让他在家庭责任上失败的事件,即以韩国真实事件为基础的被开除的工人的抗争事件,在那里他经历了同事/战友的死亡,在战友受伤时他选择了留在这位战友的身边,而没有选择回到待产妻子的身边。同样在结尾,正要乘坐出国的飞机去美国见女儿的他在地铁上看到了有人和他一样被邀请参加“游戏”,他再次在命运的关节点上背对家庭和自己的利益,没有选择当一个成功的“好父亲”,电影留在了他义愤地转头离开航班的一刻,我们姑且猜测他选择了抗争、站在失败者的一边。
凭借一种朴素的道德直觉,他总是对他所遇见的弱者非常执着:一起抗争的战友、游戏里遇见的老人、孤僻的少女扒手……,即使他们可能会拖累甚至背叛自己,但是他依然愿意相信他们。当姜晓对他说不相信游戏里的人的时候,他说,“人不是因为值得相信才相信的,是因为不相信,自己就无所依靠。”
这句话与控制社会的“游戏”的价值完全相悖,控制社会中会评估每个人的信用等级,如果这个人缺乏信用,就不会给予帮助,强者只和不给自己拖后腿的强者联手。这样的社会撕裂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在这个规则内肯定是人人自危、无所依靠的,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被帮助是因为对方从自己身上有利可图,但是强者不可能一直是强者,在无处不在的风险和诱惑中,他不知道哪一天也会突然变成弱者,这时候就变得无依无靠。剧中的曹尚佑就是这样,他知道遵守这个社会的规则,甚至清楚规则中最为龌龊的部分:当他从强者变成弱者(期货投资失败)的时候,就应该为自己负上责任,穿着体面的西装,孤零零地在浴缸里自杀。这一次自杀是给资本主义的最后的礼物,帮助资本主义清除了对它而言的“废物”。这次自杀没有成功,也只是因为新自由主义给了他多一个机会,仅仅相当于多借他一笔钱去赌,这时候他对于这个社会来说已经是一个“活死人”的状态了。
他的发小成奇勋虽然也面临着巨债,但他仍回到母亲身边当“袋鼠族”(相当于日本的御宅族,都是“生存系”所偏爱塑造的主角),借助赌博的短期享乐“死皮赖脸”地活着。他们的处境并不相同,成奇勋生活困顿的导火索并不是自己,而是双龙汽车公司;而曹尚佑却需要为自己的投机行动负上责任。相比起前者,曹的这种痛苦更加难以诉说,因为并没有“坏人”(至少剧中没有看到)逼迫自己玩期货,曹尚佑只能轻描淡写、毫无怨言地自己负责。在成奇勋那里,他看到了裁员(公司推卸责任)的不合理,可以奋起组织反抗;而在曹尚佑那里,“自我责任”的观念遮蔽了社会权力的淫秽性:它允许、煽动、诱惑人去冒险投机,而最后让失败者自己承担责任。
导演将希望寄托在了选择活着的成奇勋身上。他只有在最终战前夕下过对曹的杀心——认为认可这套游戏规则,杀害无辜者的尚佑不该活着——但这被姜晓所阻止,她告诉他“你不是这样的人”,尽管他对尚佑很愤怒,但最终还是想和他一起放弃奖金走出去,但这对尚佑来说已经为时已晚。
从最后一幕中推测,出去之后的成奇勋在经历完一段忧郁的时间之后,并没有像吴一男那样陷入无聊,因为他有了自己要做的事。这并不代表着他对于这个社会重获信任,他的行动并不需要依赖大写的历史和社会的理念,他只是因看到有另外的“游戏”受害者非常愤怒罢了。这种激情既不同于改造世界的激情,也超越于那些小快乐,成奇勋似乎看到了这一个其他角色没看到的选择:为了帮助活下去的失败者们,在这里他仿佛寻回了欲望的激情,摆脱了作为幸存者的内疚和忧郁。
注释
【1】宇野常寛,《ゼロ年代の想像力》,早川書房,2008. 第一章中译:https://mp.weixin.qq.com/s/Ie8E9QwGrLJ8M_J65lSk8w
【2】但是主人翁往往是社会中比较边缘的角色,如《弥留之国的爱丽丝》的主人翁有栖是在优秀的哥哥阴影下的沉迷游戏的家里蹲(引きこもり)。
【3】米歇尔·福科,《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扬远婴译,三联书店,1999年。
【4】吉尔·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刘汉全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
【5】关于这场真实发生过的韩国工人运动,见《藏在《鱿鱼游戏》背景中韩国工人真实的抗争故事》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689708604325996
【6】信田さよ子,《依存症》,文藝春秋,2000。
【7】松本卓也,《享楽社会とは何か?》,季刊iichiko,2018,p113-127。
【8】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许铭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9】亚历山大·科耶夫,《黑格尔导读》,姜志辉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