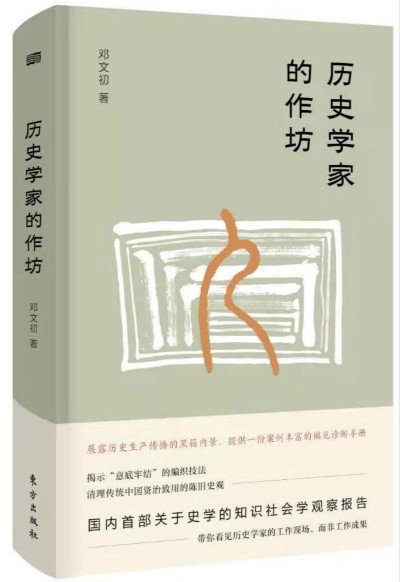石达开的诗名如何得以广泛传播?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第二十五则收有石达开逸诗。任公说:“太平翼王石达开,其用兵之才,尽人知之,而不知其娴于文学也。近友人传诵其诗五章,盖曾文正曾招降彼,而彼赋此以答也。”诗云:
曾摘芹香入泮宫,更攀桂蕊趁秋风。少年落拓云中鹤,陈迹飘零雪里鸿。声价敢云空冀北,文章今已遍江东。儒林异代应知我,只合名山一卷终。
不策天人在庙堂,生惭名位掩文章。清时将相无传例,末造乾坤有主张。况复仕途多幻境,几多苦海少欢场。何如著作千秋业,宇宙长留一瓣香。
扬鞭慷慨莅中原,不为仇雠不为恩。只觉苍天方愦愦,莫凭赤手拯元元。三年揽辔悲羸马,万众梯山似病猿。我志未酬人亦苦,东南到处有啼痕。
若个将才同卫霍,几人佐命等萧曹。男儿欲画麒麟阁,早夜当娴虎豹韬。满眼河山增历数,到头功业属英豪。每看一代风云会,济济从龙毕竟高。
大帝勋华多颂美,皇王家世尽鸿蒙。贾人居货移神鼎,亭长还乡唱大风。起自匹夫方见异,遇非天子不为隆。醴泉芝草无根脉,刘裕当年田舍翁。
梁启超对石达开诗有所品评,说前后四章,皆不免下里巴人之诮;独第三章,“不愧作者之林”,其后还加了一段:“又闻石有所作檄文,全篇骈俪,中四语云:‘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山河。’虽陈琳、骆宾王,亦无此佳语,岂得徒以武夫目之耶?”
柴小焚在《梵天庐丛录》中说,石达开答曾国藩诗四律,《大盗诗》一首,近人笔记往往录之,“予又得其六首,题则亡之矣”。所收之诗,五首与梁启超同,只多出一绝:
吴山立马十年豪,撑柱青天一杵高。今日雄心销欲尽,夕阳红上赫连刀。
“丛录”并加评语云:“语气沉郁,音节苍凉,足以俯瞰燕雀矣。”
石达开诗名,由此得以广泛传播,“诗人石达开”加“英雄石达开”,一个反满革命领袖的形象由此高大丰满且栩栩如生了。
但抱歉得很,无论梁启超还是柴小焚所录的这些,其实都是伪诗。
太平天国研究专家罗尔纲考证:这些伪诗最早见于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不久,南社诗人高旭又刊出《石达开遗诗》,称“残山剩水楼刊本”,其中除“答曾国藩五首”外,另有《途中感怀》等二十首,共二十五首。自此以后,《无生诗话》《龙潭室诗话》《太平天国野史》《石达开诗抄》《太平天国诗文钞》等竞相转刊,石达开能诗之名于是远扬、“喧腾于世”。其中,高旭的伪造由同是南社诗人的柳亚子披露,应可证实。
话说回来,尽管坊间流传着这些伪诗,并不意味石达开就完全不能写诗。在罗尔纲编选的《太平天国诗文选》中,仍然选编了石达开两首遗诗,其一为出自口传的《驻军大定与苗胞欢聚即席赋诗》:“千颗明珠一瓮收,君王到此也低头。五岳抱住擎天柱,吸尽黄河水倒流。”这一首,与天国人物水平相当,虽属口传,大约是真的吧。
另一首诗前有序,不录。其诗曰:
挺身登峻岭,举目照遥空。毁佛崇天帝,移民复古风。
临军称将勇,玩洞羡诗雄。剑气冲星斗,文光射日虹。
这首勒刊在广西宜山白龙洞的洞壁上,其后还有当时天国将领的和诗留存,应该也是真迹。如是,则石达开真的能诗,并不需要他人“越俎代庖”。
历史的合法性在于真实
在天国史上,这个叫“石达开伪诗案”,自然,此“案”早已结案。
其实,天国史上“石达开伪诗案”并非孤例,其余仅如《梵天庐丛录》就还收了忠王、侍王的就义诗。说金陵城破时,忠、侍两王就擒于赣,在囚车中一路慷慨赋诗。侍王有半律“一片雄心终不死,百年杀运未全消。仰天喷出腔中血,化出长虹亘碧霄”,忠王则有一联“自分豹皮同死节,敢将羝乳望生还”。两人还在监押途中互相对诗,仿佛赶考路上。忠王吟句有“报道哥哥行不得,前山现有鹧鸪啼”,侍王则和曰“杜宇不知天意思,不如归去唤声声”……
现在我们知道,这些伪诗大多是那个以反满为宗旨的“南社”文人群体创作的,问题自然就不再是诗品高下,而是,这些民族主义者何以要制造这些伪诗?
有一个说法,叫作“可以无其事,但必有其文”,这是那些小说家生造“赛金花救国”等传奇时的自我辩护,已被历史学家张鸣痛斥为“妓女救国论”。不过痛斥是痛斥,但这样的故事仿佛大有市场,这就需要在痛斥之外,做民族心理的进一步探讨:这样的作伪,究竟意味着什么?
也许,从传播角度看,确实如小说家者流所说,虽事实并非如此,但故事却必须如此。那些盖世英雄、革命将领、民族救星等豪杰之士,怎能无诗如阿Q之临终只哼出半句大俗话“二十年后又是……”?此平民之所以为平民,英雄之所以为英雄也。事实上,《焚天庐丛录》正是如是判分英雄与庸人,说石达开答曾文正公招降之书,“纯是英雄气概”,而程云得刘浔招降之书,“则不免书生气习”。而忠、侍王句亦可说明:“此忠、翼、侍王之所以为王,而程之所以为检点欤?”
英雄故事自有英雄故事的规矩,于是,忠王、翼王、侍王必得有诗,而庸常之人可以不计。如果诗品免不了土里土气,难以入流,则作文者自然有责任替这些豪杰拟就篇什,以增添英雄之光彩、塑造英雄之形象、继承英雄之遗志、传播英雄之事业。伪诗入史,乃是革命之必要,使命何其重大,何得称“伪造”?!
于是,在这样的历史中,革命目标决定事实创造,审美的品位盖过事实的真伪,历史与小说在此终于合二为一了。历史的真实于是转化为一种审美幻境,它让你相信(有时还不得不信)——虚构比历史更真实,虚构就是真实。
中国传统章回小说往往在大段极尽渲染之能事的铺叙之后,加上一句套语:口说无凭,有诗为证。可见,在汉语世界中,诗是真实的见证,甚至,诗就是真实。
历史与虚构,在汉语世界中,原来竟然是等同的。
这个事实,大约是现代中国人,尤其是那些接受了现代史学思想——历史合法性在真实——的人忽视了的传统吧?
然而,如果不把这种传统纳入考量之中,我们不仅无法读懂国史,更无法理解国人心中的历史。
历史的撰写总要加入这种审美的味素,这才是国史得以流传千古的秘籍。而读者在阅读这样行之有文的精彩汉语时,其历史体验也就成为一种充满激情的幻觉之旅。
较之历史真实的枯燥,幻觉总是更有魅力。相比于历史,我们更喜欢心中的幻觉,因为幻觉能激活我们疲软的神经,而历史,有时显得过于沉重、过于理性,对于理性被遏制生长的汉民族来说,有时还确实显得过于艰难。
伪造历史与政治合法性
历史学的正统解释是:作为革命团体,南社伪造石达开诗乃是一种革命宣传,并非历史研究。此说事实俱在,不必否认。且政治行为中利用历史乃是最正常不过的事,尤其是在一个历史资源丰厚到令人窒息的文化中。不过,既然将话题转入政治与历史之关系,则无妨就此话题略作申述。
政治宣传的目的在动员,在此动员之中,历史人物或事件被当作政治动员的手段,这乃是常态。但动员要有效,不管是社会革命还是国家治理,都需要动员对象的接受、理解、服从与配合。因此,动员过程必定要政治领导集团与普通群众之间达成某种共识,某种具有法律关系的认可、契约或协议。从此角度看,历史主要不是作为一种知识、记忆媒介在起作用,而是一种特殊的政治约定,是政治领导集团对于民众的某种赞画文本、某种口头许诺。民众正是基于对此文本的信任,才会响应领导集团的号召,投身其中,甚至牺牲性命亦在所不辞。在政治动员中,历史类素材之所以常常被采用,就因为对于未来政治,我们很难有确切的认知,但对于历史,我们却始终抱着一种确信的态度,始终存有一种特殊的温情。以历史为动员,事实上就是对我们的集体记忆、对民族温情的征调。这种征调如同征税,既构成了政治动员中双方的法律关系,也构成了此后领导集团的合法性基础。
政治革命与国家治理,确乎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利用历史的效果。然而,这并不能证明历史可以被滥用、被伪造,可以是虚构的神话——如果说,仅仅作为历史知识的伪造还能原谅的话,作为政治行为的历史一旦伪造,事实上就构成犯罪——伪证罪,至少也是对政治道德的玷污。政治行为人如果连历史都敢伪造,则何事不能伪造?这也意味着,这些政治人物可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对于民族记忆、对于民众情感不负责任。由此可以推断,这些人在政治上是不可信任的。虽然,那些成功者因为控制着权力与历史书写而能逃避审判,但逃脱是一回事,逃脱并不能解除其犯罪嫌疑,反而将证实并加重其罪责。
政治行为中的作伪必然影响此后的政治行为,行为逻辑表现为谎言逻辑——谎言体系的自我生成——为维护一个初始谎言需要制造一系列的谎言;而谎言之间又总是自相矛盾、漏洞百出,于是,为了掩盖真相,需要建立一种谎言理论,这就是“意底牢结”产生的背景。但“意底牢结”并不能做到逻辑自洽,总需要镇制性力量来保护自己,谎言与威胁的孪生结对由此形成,这也是一切极权政治的运作逻辑。
在《捍卫历史》一书中,英国史学家艾文斯说:介入政治一直是许多历史作品的源泉,过去如此,未来依然。可历史对权力提供支持的前提是它的真实性,史学必须抛弃那些已经证明是无效的政治理念,同时不得歪曲和操弄过去的事实,“若是刻意歪曲、操纵或混淆历史事实”,它就会作法自毙,自作自受。史学为此将丧失存在的依据,而政治也会因其合法性的丧失而分崩离析。
(本文摘自邓文初著《历史学家的作坊》,东方出版社,2018年11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