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晔旻评《骆驼与轮子》|技术“退化”背后的征服者逻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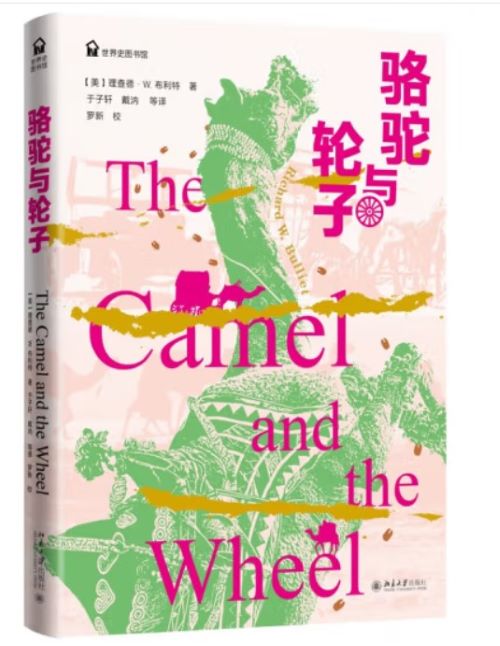
《骆驼与轮子》,[美]理查德·W.布利特著,于子轩、戴汭等译,罗新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8月出版,310页,66.00元
提到如今司空见惯的轮子,相信很多人都会认同,它的发明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使陆路交通和运输状况大为改观。这方面的反例就是点错了“科技树”的古代美洲印第安人,他们能够制定出惊人精确的历法,却一直不知道使用轮子,更没有车,结果陆上交通工具成为了空白……然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理查德·W.布利特(Richard W. Bulliet)却在《骆驼与轮子》一书里告诉读者,在中世纪的中东与北非地区,曾经出现过一场技术“倒退”,当地几乎完全废弃了作为交通工具的(车)轮,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种纯粹的畜力——骆驼。
说起来,这倒也不是布利特在当下这个互联网时代故作惊人之语以吸引眼球。《骆驼与轮子》中译本称得上是一本“迟来”的新著。此书的英文原版面世于半个世纪之前,以至于读者可以毫不费力地在书中发现早已“过时”的专有名词——比如将1977年成立的吉布提共和国继续称为“法属阿法尔与伊萨领地”,而1993年已经成为独立国家的厄立特里亚在《骆驼与轮子》里也仍旧是“埃塞俄比亚属”。但这并不意味着布利特在书中的论点过时了。这方面的一个例证就是,英国学者布莱恩·费根(Brian Fagan)在《亲密关系:动物如何塑造人类历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12月版)里就引述了布利特的相关看法,足见此本《骆驼与轮子》虽然已经比许多读者的年纪还大,但阅读价值至今仍在。
作为布利特笔下的主角,“骆驼”自然是一种人们很熟悉的家畜。身体强健的骆驼,可负重近三百公斤,中等者亦可负重一百四十公斤有余。而且,骆驼足蹄特殊,适于行走各种地形,又极其耐渴,在夏季可三至七日不饮水,在冬季,若草料含有水分,甚至可以完全不饮水,因此也有个“沙漠之舟”的雅号。需要说明的是,当今世界上其实存在三种骆驼:单峰驼、双峰驼与野生双峰驼。后两者虽然形态相似,但源自不同祖先,因此基因不同。《骆驼与轮子》着重讨论的,是其中的单峰驼。

单峰驼
书中引用公元301年罗马皇帝戴克里先的价格敕令证明,相比古代的有轮(畜力)车,驮运骆驼的成本更低:一辆(至少两头牛牵引的)四轮车运输一千两百罗马磅商品,一英里的费用是二十第纳尔,而同等距离下,一头骆驼驮运六百磅商品只需要八第纳尔——折算下来,用骆驼运货比用四轮车节省百分之二十的费用。可以说,这就是能够使用骆驼代替轮子的一个经济原因。
但仅此一点,并不具有说服力。古代中国在“丝绸之路”的货物运输里也使用骆驼,但骆驼从未取代中国的马车、牛车乃至驴车。就像《骆驼与轮子》告诉读者的那样,这样的技术“退化”仅仅发生在中世纪的中东(与北非)地区。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因首先在于,这里正是骆驼的驯化地——最早驯化骆驼的人是生活在阿拉伯南部海岸的狩猎族群,在起初的很多个世纪里,骆驼是阿拉伯半岛南部人群唯一的家畜。但这块土地并不贫瘠,盛产乳香树,人们从中可以获得乳香——价值极高的芳香树脂。进入文明时代之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整个西南亚对乳香近乎永无止境的需求创造出利润丰厚的国际市场,也因此形成了一条经由阿拉伯沙漠的“乳香之路”,而骆驼正是商人在这一地理条件下最理想的驮运畜力。如布利特所言,“至公元前7世纪,已存在大量的骆驼可供利用”。然而,也像《骆驼与轮子》紧接着提到的那样,“轮子在交通运输上的主导地位仍继续了八九百年,之后才慢慢衰弱”,因为在此之前,“骆驼饲养者,即游牧人”,并未“充分融入中东社会与经济”。

骆驼商队
转折时刻是如何到来的呢?答案很有趣:驼鞍的形式发生了改变。对国人熟悉的双峰驼来说,骑在哪里是根本不需要考虑的问题:双峰之间。但单峰骆驼的骑法变得多样化了。最早出现的驼鞍是放在尾部的垫子,用一根向前延伸的肚带固定。有了这种鞍垫,驼夫就能骑着骆驼行走很远的距离。接下来出现了“南阿拉伯驼鞍”。它是一种围着驼峰放置的马蹄形鞍垫,上面的鞍穹和水平横杆可以用作捆绑货物的支架。但真正具有革命意义的是最后出现的“北阿拉伯驼鞍”:两个倒V字形的巨大拱架被置于两块鞍垫上,驼峰前后各一个,用横杆连接,形成一个驼峰居中的坚固框架。骑手坐在架子上的衬垫上,重量不是压在驼峰上,而是均匀地分布到骆驼两边的肋骨部位。如果驮载的是货物而不是人,只要将两袋货物放在架子的两侧即可。
在“北阿拉伯驼鞍”出现之前,“不能指望坐在不稳定的环装垫上的骆驼骑手使用这样的武器:用长矛戳刺或用剑重击的任何努力,都有可能像伤害敌人那样使骑手自己衰弱”。就像马镫的发明成为冲击力惊人的“甲骑具装”诞生的先决条件一样,正是“北阿拉伯驼鞍”让骆驼骑手得以牢牢固定在坐骑上,使得骆驼骑兵终于成为一个具有相当威力的兵种。阿拉伯游牧部落正是凭借配备了“北阿拉伯驼鞍”的骆驼骑兵收取路过商队的保护费,从而捞取了“第一桶金”。而“阿拉伯各部落一旦拥有了军力和财力,就再无可能被隔绝于沙漠之中了”。

骆驼骑兵
不过,这样的论述很容易让人产生错觉,即公元七世纪阿拉伯人的突然崛起,主要归功于骆驼骑兵。《骆驼与轮子》里简要否定了这一点:相较骆驼而言,阿拉伯部落民更重视的是马。这也很容易理解:骆驼的绝对速度虽然不慢,但是由于骆驼的高度,上下骆驼都得要骆驼卧下才行,这就令骑士的反应能力大打折扣。另外,骆驼脾气很坏,有体臭的毛病,智力也比马低很多(因此训练时间更长)。骆驼作为骑兵载具的话平台又略高,对阵步兵反而不利。所以经典游戏《帝国时代2》干脆设定骆驼兵面对(克制骑兵的)长枪兵更加不堪一击。因此,就算是盛产骆驼的阿拉伯半岛一带,骆驼骑兵也非首选。阿拉伯帝国初兴时,号称“安拉之剑”的名将哈立德·伊本·瓦利德用十八天时间横穿沙漠奇袭敌后。这被看作一个用兵经典。只不过,虽然哈立德所部行军的确是骑骆驼,但作战时还是用的马匹(过沙漠沿途宰驼供膳,用驼胃里的水饮马)。《骆驼与轮子》认为骆驼骑兵对阵马骑兵属于劣势似乎有些问题,从生物习性上来说,马匹不喜欢骆驼的气味,因此在《帝国时代2》的设定里,骆驼骑兵对战(马)骑兵有加成。当然,这只是一个与《骆驼与轮子》主题不太相关的话题。
但阿拉伯人惊人的扩张征服,又的确是骆驼得以取代轮子的关键原因。一些地中海城市,早在希腊-罗马时代就开始使用四轮车,却在阿拉伯征服后改用骆驼作为运载工具。沙漠征服者带来的不仅有自己的语言(阿拉伯语)与信仰(伊斯兰教),还有对骆驼的习惯性使用——对四轮车的弃用使得“无轮社会”成为现实。可以说,这本质上就是武力征服者在所征服的土地上推行了自己熟悉的生产生活方式——与十三世纪蒙古人征服中亚地区之后,察合台(成吉思汗第二子)强迫当地人按照“札撒”以蒙古方式宰羊别无二致。但骆驼驮运毕竟在经济性上更胜一筹(甚至优于骆驼拉车),因此在中东的主要城市一直延续到了近代“西风”东渐之时。《骆驼与轮子》同样提到,在诸如水利灌溉、磨坊、制陶等需要使用轮子的行业,在阿拉伯帝国的历代哈里发统治时期都经历了技术改进。因此,骆驼取代四轮车所体现出的技术“退化”,着实是要打上引号的。
以此看来,布利特的主要论点不失为有理有据、逻辑自洽,但这并不等于《骆驼与轮子》就是不刊之论。虽说书中主要以单峰驼展开论述,但也提到了单峰驼与双峰驼的消长。简而言之,两者分别适应炎热与寒冷气候。而气候适中的伊朗地区原本分布着双峰驼,但单峰驼最终在竞争中取胜。作者认为这是因为可以牧养其他牲畜的地区,一般都不将双峰驼作为主要的畜种(骆驼的生长周期很长,经济账算不过来),而在阿拉伯沙漠,单峰驼牧养规模很大,构成纯游牧经济的基础,因此单峰驼凭借规模优势取胜。这一说法的问题在于,在靠近阿拉伯沙漠的地方,马、牛、羊这样的家畜也很常见(《圣经》里有不少宰羊的记载),在牧养双峰驼的地区发生的事情(“骆驼对他们来说从来就不是生活必需品,其产品与劳作潜力相对也没那么值钱”)为何不曾在牧养单峰驼的地区同样出现呢?

唐三彩双峰骆驼俑
另外,《骆驼与轮子》也提到,随着骆驼驮运战胜四轮车,中世纪中东地区的一个特征是“不修路”。这自然是因为骆驼对地形的适应力远胜过四轮车的缘故。这一论断本身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说过,“与距离作斗争,仍然是费神的问题”(这是他在名著《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里论及十六世纪西班牙帝国的统治与帝国幅员之间的关系时所讲的)。极盛时期的阿拉伯帝国领土西至西班牙,东到中亚河中地区,几乎横跨半个欧亚大陆——对帝国决策中心而言,如何让政令达到如此遥远和广大的地区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此前的几个帝国,譬如波斯帝国与罗马帝国,为此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邮驿系统,并修建了大规模的道路网。为何阿拉伯帝国却能够“不修路”呢?古代最快捷的传递文书的交通工具是马匹。要发挥马匹的速度优势,驿道也是一个必备条件,比如云南驿现在保存的一千七百米长的青石板路,就是封建时期的官道,按一丈左右的标准建成,可以保证两匹马相向而行,通行无阻。阿拉伯人对马匹的重视不言而喻,难道会没有考虑到路况的重要意义?抑或,阿拉伯统治者对道路的不重视,也是造成哈里发政权在八世纪中叶的极盛时期后很快陷于四分五裂的一个原因呢?

波斯帝国时期的道路
与道路相关的问题还有中世纪城市里的街道规划。布利特显然是反对“西方观念中普遍以为规整的城市布局才是好的,不规整的就是坏”这一观点的。因此他在书中为中世纪中东狭窄蜿蜒的街道辩护:容易适应地形变化;可以提供荫凉,可以挡风,可以提高居住密度……总而言之,这被作者看作“无轮社会”的特征,在不需要“车辆紧身衣”的情况下,“这些城市逐渐发展出更适用的街道类型和布局”,“由于只供行人和驮畜往来,街道可以变成露天集市”。
这样的看法,恐怕也有些失于偏颇。与其说布利特罗列的这些特征属于“无轮社会”,倒不如说是前近代城市的共同点更为贴切,与轮子的使用与否没有太大关系。比如,古代的东亚显然属于“有轮社会”,人力车、马车、驴车都不罕见。政治意味浓厚的古代中国城市,以隋唐长安与明清北京为代表,的确是“一个矩形的宫城包含在一个完美的矩形外城之中”这样完美的几何形状。但另一些自然形成的城市街道布局,就远没有这样整齐,比如上海县便是如此,众多狭隘蜿蜒的街道,甚至成为如今老城厢(旧南市区)交通的一大顽疾。至于商业集市更是与车辆通行与否无关,哪怕是清代帝都北京,一样流行着一首御史巡城诊语,所谓“中城珠玉锦绣,东城布帛菽粟,南城禽鸟花鱼”,可见其商贾辐凑,店铺林立的景象,与中世纪中东城市的“露天集市”又有什么区别呢?可以说,在这一点上,挑战“西方刻板印象”的布利特似乎有些“矫枉过正”了。

乾隆年间的上海县城
当然,在进入近代社会之后,随着有轮车辆成为城市的主要交通工具,即便是中东社会也在逐渐告别骆驼主宰下的“无轮社会”。因此,在《骆驼与轮子》的结尾,布利特对在现代社会渐无用武之地的骆驼的命运感到忧心忡忡。从生物学上讲,这也不是没有道理。比如,要不是早期人类驯养了马匹,这种一度被视为“线性进化”典型的动物恐怕就有灭绝之虞(现在只有很小的野马种群)。相比之下,骆驼同样是一类处于衰亡状态的有蹄动物,而且情况比马更糟。现存的两种家畜,单峰驼与双峰驼的野生亲属早已灭绝殆尽,如果人类不再需要这种家畜,骆驼的前途可想而知。

野生双峰驼群
有趣的是,布利特对此提出的解决办法之一是将骆驼从驮运家畜变成肉用家畜。对此,国人或许是会赞成的。毕竟清代的“山八珍”说法里早有“驼峰”,而当代新疆的“烤全驼”也正在变成一个旅游卖点。只不过,布利特对此提出了自己的忧虑:“仍然不清楚的是,今日的骆驼商人也许只是对正在逝去的游牧经济进行最后的收割。”而这,就只能让时间去给出答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