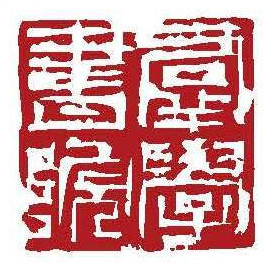第三帝国时期,普通德国民众如何一步步成为纳粹分子?

今日推荐
《第三帝国的生与死》
弗里切著
社科文献出版社2021年
坎迪尔历史奖、古根海姆奖获奖作者、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二度奖励作者彼得·弗里切关于纳粹意识形态研究的佳作。
纳粹意识形态如何逐渐主导德国社会?
普通德国民众如何一步步成为纳粹分子?
1933年1月30日,当听到希特勒掌权和民众的欢呼声时,埃里希·埃伯迈耶在日记中悲痛地写道:“我们是失败者,绝对的失败者。”得知1935年出台的《纽伦堡法令》剥夺了犹太人的公民权后,他愤怒地说:“仇恨被播种了100万次。”然而,1938年3月,他却为德奥合并喜极而泣:“如果仅仅因为成果是希特勒取得的便加以拒绝,这种想法是愚蠢的。”
以上是一个普通的德国市民在20世纪30年代心态上发生的极大变化。在《第三帝国的生与死》中,彼得·弗里切用冷静且客观的笔调,为纳粹的意识形态如何一步步在德国占据主导地位进行画像和分析。纳粹的基本诉求的核心是民族共同体,它呼吁所有日耳曼人纠正《凡尔赛和约》的错误,努力让国家变得强大、充满活力,消除体制中的“不健康”因素。德国要生存,其他人(特别是犹太人)必须死。弗里切披露的日记和信件揭示了德国人的恐惧、欲望和疑虑,也展示了纳粹概念如何渗透普通德国民众的日常生活。这部作品充满力量和启发性,从全新层面探讨了德国人如何努力适应新的种族身份、相信战争的必要性及接受无条件破坏——简而言之,如何一步步成为纳粹分子。
《第三帝国的生与死》引言(节选)
文 | 彼得·弗里切
在第三帝国,生与死密切地纠缠在一起。纳粹党向民众宣传理想生活的方式与他们认为的1918年的德国灭亡危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纳粹党要把德国人将面临的灭国命运加诸敌国身上。纳粹的暴力手段如此极端,他们的良心如此不受传统道德准则的谴责,以至于他们的任何解释都显得苍白无力。然而,在德国灭亡这种可怕预感背景下,作恶者思维(mindset of perpetrators)就显得很容易理解了。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纳粹党发动了一场几乎与其极端理论完全一致的战争。它用最激进的语言,提出了生与死、国家生存与灭亡的问题。然而,在第三帝国存在的12年里,军事征服与危险可怕地如影随形。政治活动建立在极端自信和可怕的担心上。这两种心态同时存在,让纳粹党的各项政策越来越激进。“可以如此”被“必须如此”掩盖起来。随着数百万德国人参与修复、保护和维持国家等公共事务中,这种结合释放了巨大的能量。同时,纳粹党的迫切心情增加了这些政策的破坏性,因为他们认为,保护“有价值”的生命的唯一途径就是消灭那些他们认为“没有价值”的生命,包括那些基因上“不健康的人”、“反社会者”和犹太人。在接下来的篇幅里,我们将探讨纳粹复兴德国的决心,以及他们相应的信念:复兴德国,就必须以持续递增的规模消灭生命。
阿道夫·希特勒和他的纳粹追随者发动了一场血腥的世界大战,逐渐扩大它的规模,直到1945年5月以惨败告终。纳粹党承诺给德国人安全富足的生活,试图通过灭亡其他国家,判决其他国家民众死刑的方式来实现这一诺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4000万欧洲人死亡,相当于这个洲总人口的10%。死亡的这些人中,半数以上是平民,主要是东欧的平民。死难者包括600万犹太人,大约占1940年欧洲犹太人总人口的三分之二。虽然这些数字很难精确统计,但它可以说明纳粹党要实现建立大德意志帝国的目标就是通过暴力手段,将“土地和民族”改造成“空间和人种”。纳粹思想之所以这样血腥,不是因为它掌握了现代杀人工具,或者行事效率高,或者已经形成了一套官僚制度,而是它将自己看作解决德国历史问题的具体方案。依据这个方案,深陷危机的德国人一定要让自己坚不可摧。
作为一个社会修复和帝国征服项目,纳粹要求德国民众付出极大代价,这不仅仅体现在征税和征兵上。纳粹党设法动员德国民众争做具有自我意识的民族统一体。纳粹党致力于改变民众审视彼此的方式,希望他们认识到,作为世界历史的积极参与者,他们都是这个民族共同体(national community)的一部分。实际上,德温格尔写作那本书的一个目的就是通过揭示波兰让德国走到了生死存亡关头,宣扬德国命运高于一切。在很多方面,纳粹党在政治上的胜利取决于作为个体的德国民众是否透过“种族同志友谊”这一“棱镜”看待这个世界。因此,这不可避免地引出这本书的另一个目标,即探索德国民众认同纳粹这种新型种族秩序并在这一秩序下相互合作的程度。换句话说,在1933~1945年,德国人以纳粹党徒的身份走了多远?

“德国民众”和“纳粹党徒”这两个集体名词之间关系的本质虽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书写问题。很长时间以来,历史学家用这两个词来表示相互排斥的程度,而不是相互等同的程度。虽然历史学家一直承认确实存在一批狂热的死忠纳粹核心分子,但历史研究也确实发现,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选举中,德国民众对纳粹党的政治支持是很随意的,1933年之后纳粹关于建立民族共同体的要求也很空洞。学者们认为,关键的选民群体,如工人、农民,甚至是中产阶层的一部分,对新政权没有表现出什么热情。他们承认希特勒很有声望,但同时也认为纳粹党自身和纳粹党的很多社会、经济政策缺少基本的合法性。从这个角度来看,纳粹党很像是掠夺者,而大多数德国民众似乎只是想借机获得政治上的好处,或者说他们的道德水准较低,但总的来说并不存在思想上的共谋。一直为历史学家不感兴趣的政治模式,如极权政治,从另一个方向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最近对纳粹时期德国社会的研究,尤其是有关“日常生活历史”的研究,表明德国民众在与纳粹当局谈判,要求获得福利、资源、喘息空间(breathing space)的过程中,二者之间会出现积极但仍旧很有限的合作。即使从这一角度来看,纳粹独立于德国民众的程度也令人惊讶。纳粹领导者推行战争计划,而普通民众为自己的生活担忧。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作为人类行为研究领域“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的一部分,历史学家重新思考了“德国民众”和“纳粹党徒”在思想意识方面的联系。他们指出,二者之间共同的文化、政治倾向可以上溯到19世纪某些职业人群(尤其是生物医学领域的从业者)的自我动员、民族共同体及其种族理念的合法性。最近的研究还更加关注基层民众积极建设国家社会主义的各种方式。德国社会各个群体广泛参与纳粹项目,形成了各种同谋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辩论相当于将视角从杯子是半空的转变为杯子是半满的。虽然,纳粹成功的有限性不应该遮盖他们推动下的民众政治立场的重大改变,或短时间内民众中产生的忠诚,但是,很少有学者接受这一论据充分的说法:在“灭绝性”的反犹态度上,大多数德国民众和那些敢于实施先入之见的纳粹党首领享有共识。
我倾向于上述观点的后一部分,不过,我的目标不仅仅是证明更多的德国人是纳粹分子,德国人身上的纳粹信仰比先前人们认为的更为执着。另外,也有必要分析这一时期的德国民众对纳粹革命既期望、着迷,又感到沮丧的复杂感受。作为有关社会、种族、种族复兴(racial renewal)的庞大计划,纳粹为德国民众提供了很多参与方式。除了出于对纳粹思想体系不同程度的信仰,德国民众还可能出于恐惧、投机心理和想要做一番事业的考虑,接受了纳粹政策。还可以找到很多原因,比如说民众懒惰、冷漠、无知。我们不能忽视这些动机。然而,纳粹对德国民众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要求他们信仰纳粹,相信民族共同体的优点,将彼此视为“种族同志”。纳粹党还通过制度上的安排,尤其是让数百万德国人通过集体营(community camps)的生活产生思想上的认同。这其中的作用是,他们必须自己考虑该做何改变——是否做一个纳粹党员、他们的同志、具有种族思想的德国人;是继续坚持原有的思想,还是拥抱新的转变。他们苦苦权衡随大流的重要性、附和他人的便利性、个人对集体应尽的责任。历史学者对这些动机严格区分,因为这些动机本身就是纳粹德国仔细审查的对象。对于反犹政策、安乐死、战争方式是否符合道德准则,民众中间的讨论也很多。虽然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结果个体之间差异很大,但是这一过程让他们的思想意识发生了转变。第三帝国的民众一直都为这些问题所困扰。

另外,魏玛共和国末期严峻的经济形势(600万人找不到工作,或者看不到任何稳定的未来),再加上军事失败和《凡尔赛和约》(民众普遍将该条约与德国一系列经常复发的大灾难联系在一起,如1922~1923年的“大通胀”,1930~1933年的“大萧条”),让德国民众很容易接受新的观点体系,愿意相信新的开端可能需要动用暴力。在1933年之前,已经不断有人用要么走向新生,要么灭亡这样的灾难性语言提出他们新发现的德国的两条出路。1933年之前,就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德国选民投票支持纳粹党;其他很多人参加了针对魏玛共和国的各种国家主义叛乱活动。数百万人愿意接受国家复兴的理念。
很多信件和日记为我们了解德国民众如何接触国家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资料。这些资料不具有代表性,但是很能说明问题。我在研究中广泛运用了这些信件和日记,因为它们体现了德国民众之间某些很有意义的日常交流。这些信件和日记流露出那个时代人们的恐惧、渴望和内心的想法,表现出人们怎样将那些纳粹词语和概念用在日常生活中。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日记相当于纳粹在全国各地的集体营里倡导书写的自传作品。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加强了自我审查。写日记或私人信件有助于强化每个人自由主义思想的“前哨站”,或者可以形成和强化心中的国家社会主义信仰。依托纳粹的政治理念,写日记和信件可以让人们进入一种可能的区域。在这方面,卡尔·杜克费尔登(Karl Dürkeflden)介绍了下萨克森州(Lower Saxon)派纳市(Peine)的社会民主党工人怎样在信中说服自己“调整”思想,信仰国家社会主义。洛尔·瓦尔布(Lore Walb)在日记中讨论了“同志”的含义。伊丽莎白·布拉施(Elisabeth Brasch)在1940年写的自传里深入分析了帝国劳工服务局的工作给她带来的好处和坏处。在给女儿的信中,伊丽莎白·格本斯勒本(Elisabeth Gebensleben)试图向持有怀疑态度的女儿解释迫害德国犹太人的“合理性”。她自己的儿子竭力说服自己,国家社会主义信仰与他和一个“半犹太”(Mischling,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有一方是犹太人)女孩之间的爱情并不冲突。在日记里,埃里希·埃伯迈尔(Erich Ebermayer)解释了为什么德奥合并让他激动。弗朗茨·格尔(Franz G)在日记中记录了他在柏林参观“堕落的艺术”(Degenerate Art)展览时,奥托·迪克斯(Otto Dix)创作的三幅一联的《战争》(Der Krieg)组画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西线无战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一书的上市引发了人们对战争性质的无数争论。来自前线的信件确认了那场全面战争的残酷,比如长官命令士兵向无辜平民开枪。在战争结束之际,莉泽洛特·G(Lieselotte G)在日记中竭力控制自己,不让自己流露出对希特勒的不满。这些自传文字表现出各不相同、差别细微的个人观点,反映出这种思维过程怎样让人们不断出现相反的看法。这些日记表现了人们思想转变的纠结之处。
德国人进行的有关战争与和平的讨论尤其有趣,因为他们和那些纳粹理论家思考的是同样的历史问题,只不过是他们想到的不一定是国家社会主义这一解决方案。朋友、家人关于《西线无战事》一书的认识分歧巨大,这既说明他们怀疑雷马克关于战争残酷的描述是否依然适用(虽然纳粹已经禁了那位“和平主义者”作者出版的书),同时也说明他们渴望给以德国战败收场的那场战争找到一些救赎的含义。每当德国违反《凡尔赛和约》的某一项内容,如控制萨尔河、扩充国防军、侵略奥地利、占领苏台德地区,民众狂热的庆祝活动并没有减少民众对另一场欧洲冲突的厌恶之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民众迫不及待地希望战争迅速结束,但又不得不坚持下去,为的是避免类似1918年11月那样的民族浩劫。从人们的日记和信件中我们明显感觉到,尤其是1943年,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战败后,人们交流的内容频繁提到1918年的可怕结果。然而,人们之所以总想到1918年,是因为纳粹历史观的影响,而不是当年心理创伤的遗留影响。纳粹党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统一了德国民众对“背后插刀”之说的看法。

从德累斯顿一家牙医诊所候诊室里的摆设就可以看出人们关于德国历史观点的游移不定:“在被强制悬挂的希特勒画像下面的书架上,摆放着一整套海涅作品,以及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上大学时参加的联谊会的花名册、一本有关某个步兵团历史的书。”在日记里记下上述场景的是犹太人维克托·克伦佩雷尔(Victor Klemperer)。他随后给出的结论是,那名医生“肯定不是纳粹党人”。不过,关于画像和书籍的摆放,实际情况可能与克伦佩雷尔说的不一样,希特勒的画像可能不是被强制悬挂的,但是,真实的一战历史和雷马克小说里的描述一样惨烈。这里以小说家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 ll)为例。作为一个二十几岁的魏玛共和国士兵,伯尔虽然反对安乐死,但是相较于雷马克,他更支持信奉国家主义的作家恩斯特·荣格尔(Ernst Jünger)。虽然他厌恶希特勒将他变成一个杀手,但是他仍然希望德国能打赢那场战争。1918年11月的革命、《凡尔赛和约》、德国扩军、希特勒发动的战争、战争的胜负未卜形成了一条特殊道路(Sonderweg),即1933~1945年让数百万德国人的人生被彻底改变的那条民族苦难的“特殊道路”。他们找到的解决方案并不总是与国家社会主义思想一致,但是,他们提出的问题表明他们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集体命运、集体审判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认同为纳粹有关民族共同体的主张提供了相当程度的合理性。
谈到1933年形势的德国人经常提起纳粹的暴力措施,如逮捕政治上的反对派、建立集中营,但是,这些措施却被解释为新鲜的,却远在地平线上的东西。那些日记和信件一般没有描述极其恐怖的形势。它们没有留下关于一个深受恐怖政策困扰的社会的痕迹。虽然这些日记提到了希特勒,说到了4月20日他的生日,往往称他为“元首”,但是对于生活在元首领导下的德国人,希特勒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中心人物。大多数日记记述的政治事件是当地国家社会主义者以及他们的附属组织的活动,如冲锋队(SA)、党卫军(SS)、各种女性组织、希特勒青年团(Hitler Youth)、帝国劳工服务局(Reich Labor Service)。这些日记注重的是纳粹的项目,而不是希特勒的领袖魅力;是纳粹的理念,而不是希特勒的所谓指导方针。
还有一件事令人印象深刻:当时无线电广播一直不间断播放。民族革命的壮观景象和声音扫荡了民族政策的怀疑者和犹太人的同情者。媒体精心设计了德国民众迫切想要得到的东西——民族政治复兴的证据。根据那个时代人们的记录,德国民众大都认为他们的邻居已经将自己动员起来,在思考并向纳粹立场靠拢,也有个别人,比如伊姆加德·科伊恩(Irmgard Keun)一本小说里的一个容易生气的人物,一听到戈林(Gring)讲话就关掉收音机,因为“我总是有一种被训斥的感觉”。日记不仅描述了社会压力的影响——纳粹、犹太人,并且战争是谈话的常见主题——还描述了国家社会主义及其社会能动论的诱人之处。很多人在日记中远离公共生活的条条框框,进入一种“内心移民”状态,但是他们也添加了一些有关1918年以来德国遭遇的苦难的描绘。这些自传式文字再加上其他支持性材料,可以进一步证明不管是第三帝国,还是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民众对自己所处的形势都很了解,行事都很谨慎。国家社会主义并不是通过引诱、麻痹或催眠取得成功的。对于数百万德国民众来说,国家社会主义让他们先是犹豫不定,后来感觉很有道理。实际上,“大多数人愿意……讨论政治经历”,这让身在第三帝国的很多外国人印象深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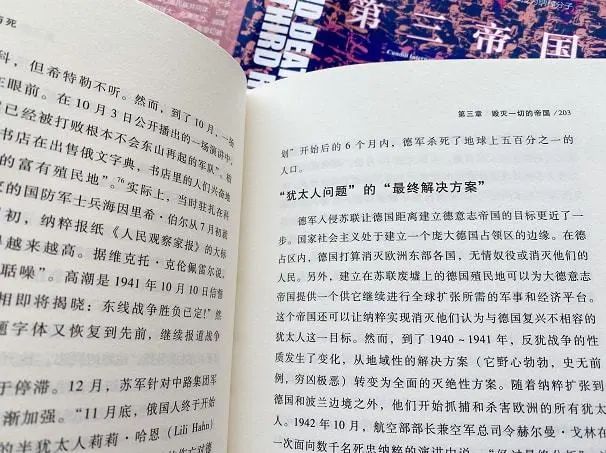
德国犹太人最终成了外部的旁观者,在很多方面,他们的目光要犀利、敏锐得多。他们也试图弄清楚纳粹的本质,以及它对其他德国人的吸引力所在。上文提到的写日记的维克托·克伦佩雷尔是一个年轻时皈依新教的德国犹太人,他一直在德累斯顿工业大学(Technical University in Dresden)教授法国文学,直到1935年,也就是他54岁那年,纳粹强迫他提前退休。他详细记述了他对纳粹看法的转变。虽然克伦佩雷尔越来越认为纳粹有广泛的民众支持作基础,但相较于大多数非犹太人,他在日记中更为警惕地记录下德国民众不完全拥护纳粹的细微表现和措辞。如果要给他的日记找一个前后一贯的主题,那就是克伦佩雷尔一直努力让自己与纳粹倒台之后的德国实现和解。他认识到了纳粹思想对人们的吸引力,但他也强调了恐惧、因循守旧和怀疑等元素的影响。
战争期间,克伦佩雷尔意识到纳粹德国会被打败,不过和欧洲其他地区的犹太人一样,他在日记中不确定犹太人是否能活到被解放的那一天。犹太人掌握的有关纳粹战争目标、种族屠杀的消息肯定要比大多数德国人更为全面。然而,战争将大多数欧洲犹太人与外界隔离了。他们在战争期间记录的许多日记戛然而止,无声地证明了驱逐和屠杀的发生。德国非犹太人的选择就多一些。他们甚至可以从容地做好战争结束、纳粹垮台的心理准备。想到1943年的汉堡大轰炸——在那场大轰炸中,他失去了所有的家当——作家汉斯·埃里希·诺萨克(Hans Erich Nossack)顾不上为自己难过。“那些真正可怜的人”,他解释说,是“那些站在深渊边缘,不知道能否跨过这一深渊的人,因为他们现在仍然局限于之前在深渊另一边时的思维方式,深陷在昨天与明天之间无法自拔”。如果其他德国人仍旧和第三帝国的未来绑在一起,那么诺萨克就拥有了另一个“当下”,或者已经完全摆脱了“时间的范围”(the precincts of time)。然而,在战争最后一年的某个时间点,数百万德国人确实跨过了诺萨克所说的那个深渊,终止了他们对纳粹政权、民族共同体、德国胜利的情感投入。这种转变往往伴随着耻辱,因为这意味着要彻底放弃他们持续多年在纳粹事业上的努力和投入。1945年之后,耻辱与愤世嫉俗相结合,使得最初促使德国人发动那场灾难性战争的政治转变的战后记忆重塑之路前进得极为困难。
诺萨克用的“深渊”一词形象地说明了有多少德国人用其他字眼替换了有关那场战争和种族屠杀的信息。当用词谨慎的克伦佩雷尔了解关键信息的时候,诺萨克将前者看到的一切描述成无法抵御的自然灾害,最终让克伦佩雷尔空手而回。他承认,他的选择是“要么忏悔,要么遗忘,没有第三个选择”。依托这些日记和信件,我可以实现写作《第三帝国的生与死》的最终目标——深入分析德国民众对于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的了解情况,深入分析德国民众和犹太人对我们现在视之为反犹大屠杀的那些事件的了解情况,以及他们怎样看待这些种族屠杀。那场战争日渐接近尾声的过程中,德国民众产生了一种徒劳无功、大势已去的感觉,甚至觉得德国是受害者。德国民众经常将1945年的战败说成一种国家事务的“大崩溃”。直到数十年后,人们才开始从“深渊”思维中走出来,更为深入地理解纳粹关于种族国家、反犹屠杀的表述,理解民众个体为什么要积极参与国家社会主义。在很多方面,从诺曼底到柏林,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枯拉朽般的终结方式让人们很少关注反犹屠杀的研究。即使如此,“深渊”之说另一边的、特立独行的诺萨克与德温格尔的受害者思维完全不同,因为诺萨克不再像德温格尔那样仍旧借助德国历史来淡化那些灾难。这种视角让关于德国历史进程的批判性评价的出现变得更为可能。
“深渊”“崩溃”这种说法具有迷惑性。这两个词旨在说明论述和理解种族屠杀,解释导致大规模杀戮的个体行为的总和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国家社会主义给西方思想一个巨大打击,像弗里德里希·尼采这样激进的思想者都想象不到这种种族屠杀。人们了解和掌握了有关纳粹针对犹太人战争的消息,但将这些消息变成有关15反犹屠杀的真实历史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实际上,纳粹主义这一现象很难解释,因为常规的社会和政治范畴似乎很难解释清楚这件事。分析阶级关系、社会出身、物资匮乏也无法解释清楚。独裁和恐怖不能解释公众的狂热或个体的思想转变。卡尔·马克思认为,存在(Sein)决定意识(Bewusstsein),而纳粹认为这一观点反过来也成立,即,意识决定存在。换句话说,对世界的认知方式决定了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因为纳粹重新描绘了这个世界,并且让德国民众在这条路上走了一段,所以学者们必须深入分析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关于社会群体、国家、种族的观点。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当时的德国人是怎样彷徨,怎样费劲地理解这些新词语的。要理解国家社会主义,就必须结合理解国家社会主义思想(这是一种令人不安的思想)的政治前提和语言范畴。纳粹之所以令人恐怖,是因为他们在现代社会里将那些政治和道德观念延伸到了极致。
我的观点建立在先前的一个观点上,即,国家社会主义脱胎于1914年开始存在于德国政治中的一场社会风潮(dynamic)。在那场风潮中,战争与革命动员德国民众参与德国复兴的国家项目。18魏玛共和国成立之初,这些项目增加了社会民主党和其他共和力量获胜的财富,但是,这些项目也持续引发了一场民族极端主义者的暴乱,暴乱针对的对象既有在一战中战胜德国的国家,也有没能取得最终胜利的旧君主主义精英。对新秩序的渴望主导了魏玛共和国的未来短期的政治生活,最终为国家社会主义者做了好事。16他们用年轻人朝气蓬勃的方式将平民主义、种族主义、国家主义结合在一起。魏玛共和国后期政治和经济危机强化了这一看法:只有改弦易辙,才能复兴德国。
从大萧条开始的1930年至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Workers’ Party)开始执政的1933年,大多数改变立场的选民不是转向纳粹党(该党在1932年7月的选举中获得37%的峰值选票),就是转向共产党(在1932年11月最后的自由选举中,共产党获得17%的选票,几乎超过了社会民主党)。两党并列就是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之后,纳粹对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主义政党成员进行残酷迫害的背景。这种迫切的危机感还意味着纳粹必须兑现在选举时提出的“工作与面包”的承诺。纳粹解决德国严峻的政治、经济问题所采取的第一批措施是就是动用暴力攻击政敌。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纳粹还积累了相当多的政治资本。纳粹党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选举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它能够赢得所有社会团体的选票,包括天主教徒和产业工人。数百万德国民众将1933年纳粹上台看作一场标志着德国历史发生根本变化的“民族革命”(national revolution)。这场革命给同情纳粹的人壮胆,让反对纳粹的人感到无力。随着1933年、1934年劳动力市场的持续发展,国家社会主义者关于民族共同体理想的描述逐渐获得了广泛的合法性。
1933年之后,越来越多的德国人参与了纳粹国家复兴的种族项目。国家社会主义者高效地将魏玛时期个体的不幸与国家的不幸(他们认为德国的不幸是因为内部和外部敌人——犹太人、共产主义者、盟军——对德国的无情打击)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有力地让人们17将国家视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如果身处险境,该统一体的复兴就有利于社会各个阶层个体生活的改善。越来越多的德国人逐渐相信,只有民族统一(national unity)才能保证社会和平和经济稳定。因此,人们越来越开始用“共同体”这一棱镜,而不是“阶层”这一棱镜来解读社会和政治形势。在民族共同体这一憧憬的影响下,纳粹的宣传和社会能动论从法律上打破了社会地位和出身赋予人的自负,让民众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平等感。社会平等仍旧不完全,但是,社会福利和其他重建工作的强大力度加深了人们的这一认识,即国家生活可以被重塑,也应该被重塑。
然而,紧迫的形势定义了社会修复过程的每个步骤。纳粹从来不相信它可以将德国带往一个安全的庇护所。在其看来,民众仍然面临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危险。这种面临危险的感觉起到了加快不安定的社会动员的作用。这有助于解释纳粹德国残酷的、有破坏性的,并最终毁灭自己的这场风潮。实际上,借助种族概念,国家社会主义夸大了国家复兴这个等式中的每个要素。一旦被赋予种族因素,那些危险因素就显得更为可怕,而解决方案就变得更为激进,他们要求的动员工作就更彻底,更可能诉诸战争。对于纳粹党来说,种族问题是一个功能强大的催化剂。
THE END
原标题:《普通德国民众如何一步步成为纳粹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