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谈|郭玉洁&王小平:写作的任务是什么?
近年来,年轻一代的中国台湾作家黄国峻、童伟格,在台湾的马华作家黄锦树、张贵兴等人的作品逐渐进入大陆读者的视野,同时著名左翼作家陈映真的小说全集也在理想国出版。
6月24日,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副教授王小平和作家郭玉洁来到“跳岛FM”第13期,一起讨论台湾当代文学的发展现状和脉络,以及大陆文学与台湾文学之间的映照关系。
“一开始,我把台湾文学当作一个 ‘冲击’。”郭玉洁回忆,大学刚毕业时她在北京三联书店看到了一批台湾文集,包括朱天文的《花忆前身》《世纪末的华丽》,朱天心的《想我眷村的弟兄们》等等,感觉打开了新的世界。

“我成长的年代,文学还是在一种现实主义的写作脉络里,读到的很多书都是很写实、很乡土的,然后突然看到了非常不一样的写作。这种冲击感有点像中学时第一次读到张爱玲的小说。”郭玉洁说,那种“不一样”有两个层面,一是那种现代派的优美雅致的文字,一是有关城市的感受与描述。
“我记得《世纪末的华丽》写一个女子在台北的一个顶楼里,不跟别人接触,每天做手工。那种一个人的孤独状态,和我们以前在乡村、家族里的感受非常不一样。再后来看《荒人手记》,又是一系列冲击。这是我对台湾文学的最早印象。”
而王小平在2003年前后去台湾做博士论文,论文有关台湾与大陆的文学交流,主要谈的是台静农这一代作家在1945年到1949年之间如何在台湾传承从大陆起源的“五四”新文化精神。

因为搜集资料的需要,王小平在台湾住了两个月,一开始从知识分子研究的角度进入台湾文学,后来也慢慢对台湾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兴趣。2016年她去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访学,刚好遇到了白先勇,也向他请教了关于台湾文学的一些问题,包括白先勇自己的创作经历和心得。“因为有这样一些接触,我对台湾文学的历史细节有了更多了解,对台湾文学的感性认识也慢慢多了起来。”
文学的钟摆:直面现实还是凝视自我?
在郭玉洁看来,现代派在台湾文学中完全占了上风,也就是从朱天文、朱天心、张大春那一代之后,台湾作家对现代写作技巧的实验和实践紧跟欧美潮流。
“有一次我采访骆以军,他就讲袁哲生、黄国峻、邱妙津这一代小说家写的都是密室里的自我,很受困,也很自我折磨。精神上的触角一定非常细,然后就不停地练那个东西。因为精神上的折磨,很多人都自杀了,还有人患有抑郁症。我到台湾读书的时候,创意写作班上都是很年轻的同学,我就发现抑郁症比例的确很高。因为他们都那么年轻,就只能写自己,一直在观察自己的内心和自己的行为,困在这里出不去。一方面他们写作的题材会很窄;另外一方面,每一篇都挺神经质的。”
而当郭玉洁回望台湾文学的脉络,她发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写实主义是那么好,有非常沉重的现实感,和底层站在一起。“所以我这几年又回到了现实主义这个脉络,包括在看大陆小说家的时候。我觉得以前我没有很公平地看待它(现实主义),因为它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一个文学潮流——我们总渴望没有的东西——可是它原来是非常成功的。”
王小平认为,台湾年轻一代的写作历程发展到后来就像一个钟摆,总是在两个极端之间不停摆动。“当现代主义向内转发展到一定程度,新的出路似乎就很难找到,那么这个时候再回过头来,向另外一个方向去汲取一些文学资源和文学经验,比如说现实主义,比如说台湾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乡土文学,比如对很广阔的社会的关注,比如像陈映真、黄春明这些人,从他们那儿是不是又可以找到一种新的写作可能性,从而打开更大的写作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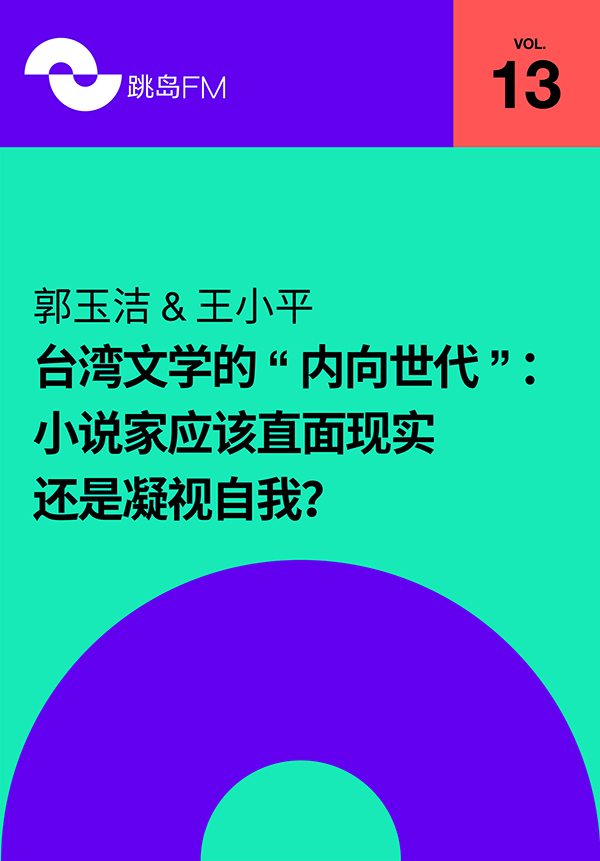
台湾小说家和大陆小说家的任务是一样的
王安忆曾说,1970年代发生在台湾的乡土文学之争,对于大陆文学来说像是一次提前的预演。
“其实我们今天谈台湾文学,也可以为我们讨论大陆文学提供很多借鉴。”王小平说,早年台湾文学整体上受大陆文学的影响很大,比如上海对台北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有很清晰的线索可以追溯。而台湾的当代文学对大陆文学也有一个反作用——1949年之后,张爱玲这条线索,这种世情小说的传统在大陆断掉了,但是在台湾接续下来。“有意思的是,在台湾接续下来之后,大陆的年轻人又受到影响,把这个带回来。这种文学之间的关系确实非常复杂。”
“我觉得每个地方的文学发展都有自己的轨道。台北和上海可能会有相似的地方,因为都是在大都市的生活环境里,然后也受西方影响。我从台湾回到上海之后觉得我们挺多元的。这么多年不同阶段的历史就在一个城市里完全并存。”郭玉洁说,中国大陆幅员辽阔,每个人背后都带着很宽广的地域和很重的家庭故事。“我一个台湾朋友来上海玩,后来又去了杭州,他就觉得来这边之后身体立刻变得非常解放,因为不像在台湾,有那么强的距离感。”
“每个年代的写作者都有自己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只能硬碰硬地去解决,是绕不过去的。我自己的感觉是,在之前的很长时间里,我们这边的文学写作者,尤其年轻写作者是不如台湾写作者的,理念和技巧都不如。可是这几年我有点觉得双方处在竞争状态了,这是挺好的一个事情。”
最终,郭玉洁给出了自己的判断,其实也提出了自己的期待:“我们这一代或者更年轻的写作者,我们写作的任务是什么?我们该怎么去把握现实,怎么从看起来好像彼此一样的生活里找到内核?这点对于台湾小说家和大陆小说家,任务是一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