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结束后你最想去吃什么——关于食物的记忆与欲望
年前疫情还没爆发时,我跟两位年纪稍长的朋友一起吃饭,饭桌上聊到的话题大多关于吃。比如他讲读书时伙食很差,想吃肉,食堂仅有的又是大片肥肉,只好忍着恶心吞咽。他讲带大自己的奶奶去世多年,自己偶尔从表姐家吃到一碗揪面片,第一口眼泪差点掉下,因为味道跟奶奶做得相差无几。
宅家期间,我时常回想起往日跟朋友家人吃饭的情景。一个人做饭固然有很多好处,省钱、健康,每天弄点新花样还能维持日常的新鲜感。可往往两三四个碟碗端上桌,没吃几口就觉得寡淡,胡乱扒拉几口便起身收拾碗筷。这个时候,聚在一起吃饭的念头会更强烈,想念经常去吃的苏州菜、铜鼓涮肉,年前一家很好吃的火锅。更久远的,还有外婆早年自制的油茶和腌菜,大姨家的臊子面,配一碟白萝卜丝就很好吃。
自然也会惊讶,困在家里,精神和物质都大打折扣时,居然能凭食物勾连起如此多的记忆和欲望。也似乎能理解疫情期间,那位从医院逃回家只为吃口汤面的老人,驻院医生得知能吃到辣椒炒肉时的兴奋,凡此种种,都远超口舌之欲,内里有对熟悉日常的渴望,也有对眼下恐慌和未知的回避。
文学与电影里,以食物表现记忆和欲望的作品不在少数,最有名的恐怕是普鲁斯特笔下的玛德琳蛋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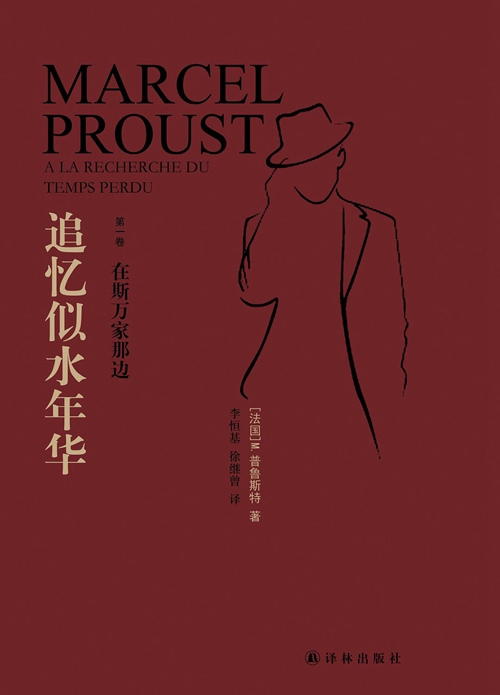
随后他用蛋糕泡着茶水,送进嘴里时:“我立刻浑身一震,发觉我身上产生非同寻常的感觉。”食物先是引发主人公近乎顿悟的情感体验,使他对人世的沧桑感到淡漠,对人生的挫折泰然自若。紧接着,在对这种味道的追溯中,往事浮现在眼前,他想起自己曾在姑妈家里吃过这种蛋糕。在物是人非,过去荡然无存时再次吃到它,记忆得以凭靠这个微弱的细节重新显形。他进而回想起姑妈那栋临街的灰屋,想起各种天气下的城市景观,自己曾奔走的街道和广场,直到整座名叫贡布雷德小镇逼真地展现出来。
“好好看,世界的全部秘密都藏在这些简单的形式下面了。”普鲁斯特这样说。
在这部书写时间和记忆的小说里,玛德琳蛋糕便是这种简单的构成,在那些我们以为永远不会忘记的、庞大又深刻的形式坍塌后继续长存,也不枉普鲁斯特赋予它堪比灵魂的高度:虽然比较脆弱,却更有活力,更加虚幻,更能持久,更为忠实,它们在回忆、等待、期望,在其他一切事物的废墟上,在它们几乎不可触知的小水珠上,不屈不挠地负载着记忆的宏伟大厦。”

料理中有母亲化矛盾为和睦的生活智慧。吃到第二道味噌汤时,喜欢白味噌的姐姐想起曾跟喜欢红味噌的哥哥斗气,直到母亲端上了混合味噌,这场红白之争才平息。秋刀鱼则使姐姐想起对母亲态度的转变,那句母亲教会的咒语“跡见苏婆诃”,让她极少被鱼刺卡住,鱼刺的消失是母女关系的缓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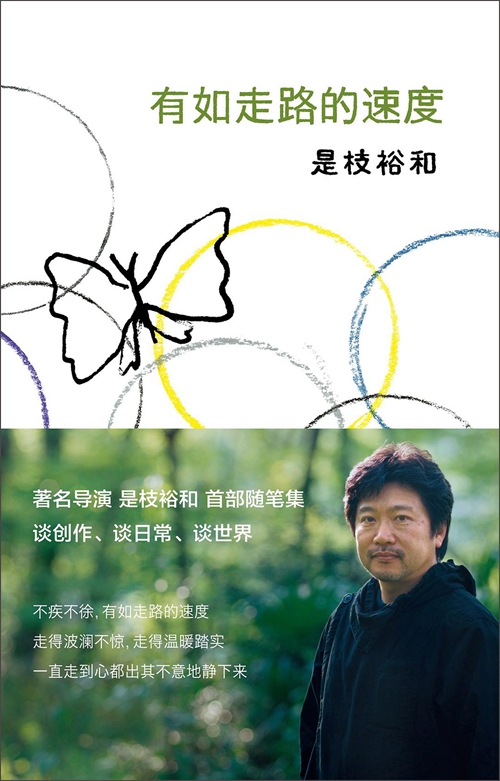

家庭的团聚只能在长子的忌日里实现,这种方式与《最初的晚餐》不谋而合。电影里,母亲炸玉米天妇罗时会想起长子,把一只睡前闯进屋的黄蝴蝶当作长子。《最初的晚餐》也好,《步履不停》也好,仅仅为了纪念死者坐在一桌,咀嚼着满是哀思的食物未免太过尴尬,甚至可怜。过去与眼下生活拧成的结,恐怕需要从“忌日中团聚”走出来,由日常多多关照彼此才能化解。
勾连记忆的食物,许多时候也关联着欲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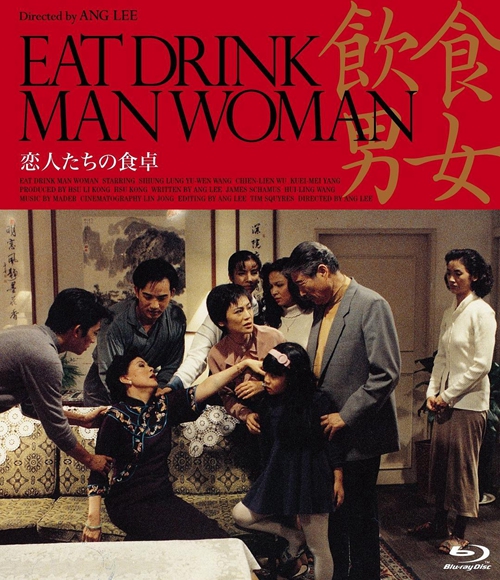
复工后,我每天骑车上下班。三月底在季节划分上当然属于春天,也许是疫情期间见多了空旷的街道,如今渐多的人和车让我感觉仿佛到了夏天。这样想,其实是对世界复苏的愿望吧,渴望夏天的汗流浃背、人声鼎沸,想要不再依靠食物的记忆度日,放肆满足口腹之欲。大概还得再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