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视野:创造新的普遍性想象
文 / 孙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尽管“亚洲”在国际关系格局中早已经被认知为一个相对自足的政治地理概念,但是人们远未形成把它作为独立概念加以使用的共识。即使是在现实中被使用的情况下,它也经常是一个边界含混轮廓模糊的所指。在人们的意识中,亚洲并不需要进行严格的界定,地理学所划定的亚洲区域就等于“亚洲”;但是,即使是在现实的国际关系层面,亚洲作为概念使用的时候,也从来未与地理学意义上的“亚洲版图”在覆盖面上完全对等。
我们常见的说法,基本上是在论述亚洲地区某一部分的时候,把它的问题作为“亚洲问题”加以定性,其中最为典型的,恐怕要数东亚了。早年东北亚(其实基本上只是中日韩,朝鲜基本不进入这个地域论述)笼统地把自己称为“东亚”,近年来随着东盟的日益发展和影响力的扩大,人们才开始在意识里和表述上把东亚理解为东北亚与东南亚的组合体;与此类似,“东亚”这一地域概念曾经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与“亚洲”互换使用,直到近年,伊斯兰世界与印度的崛起才使得东亚逐渐地告别了“代表亚洲”的含糊感觉,使东亚开始成为亚洲的一个区域,而不是可以与亚洲互换的同义语。
事实上,在认识的起点上,亚洲这一范畴本来就是欧洲为了自我认同而命名的“他者”,并不是亚洲自我建构的认知概念;而且,在亚洲被确定为政治地理范畴这一历史沿革的过程中,它的边界不断地发生变化,从地中海东部的“小亚细亚”发展为包括东亚、南亚在内的广大区域,同时也经历着亚欧、亚非边界的不断重新界定;但是,对于亚洲范畴的界定与使用,在漫长的历史中一直是欧洲人的“专利”。即使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奥斯曼帝国崛起之后,这种认知格局也并未改变,随着历史的变化,随着传教士对东方的深入,前近代时期东方社会逐渐接受了亚洲与五大洲观念,虽然接受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这为亚洲范畴在观念世界的翻转提供了基础;进入19世纪后期,特别是经历了以两次世界大战为顶点的殖民与反殖民的战争过程,亚洲真正开始了“觉醒”的历程,在这个过程里,几乎大部分受到西方列强宰割与掠夺的亚洲国家都获得了关于“亚洲认同”的自觉。亚洲概念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从为了证明欧洲的先进而被迫成为他者的被动状态,转化为在争取独立自主和民族尊严的斗争中自我确认的主体性符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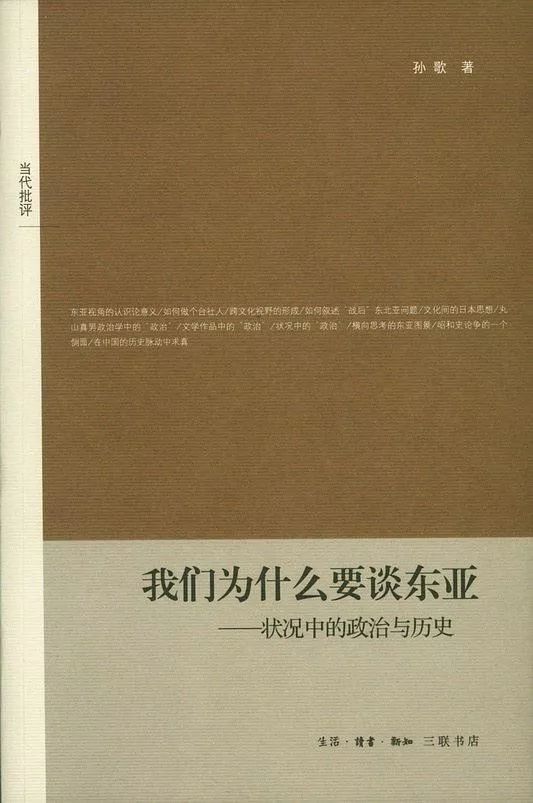
孙歌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12月
与此相应,现实中东亚乃至亚洲的一体化迅速推进,也要求认识上与知识上的迅速更新。亚洲这个范畴,在今天拥有了越来越重要的“问题性”,它能够催生的思考,或许比它本身的含义更为重要。通过亚洲这个范畴,我们可以进入我们的历史,重新审视那些被既定的视角所忽略的问题,把握那些难以被既定的知识框架所诠释的结构关系。正是在此意义上,亚洲不是一个已经“在那里”的实体,而是一个需要寻找、探索与建构的原理。
亚洲论述遇到的最大困境,在于它构成的多样性。它无法被整合为一个单一整体,很多反对亚洲作为范畴可以成立的观点认为,假如一个范畴并不能独立于其他范畴,那么它就无法成立;而不能独立的原因,则在于它既不自足,又不能被抽象为一体。
假如亚洲并不是一个历史范畴,并不伴随着如此复杂的沿革过程,那么,仅仅从逻辑学出发,我们可以同意上述否认亚洲范畴的看法。然而棘手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亚洲这个无法整合的范畴,在今天越来越多地作为一个论述单位在国际舞台上亮相,另一个是,否认亚洲范畴存在理由的人,却往往承认欧洲范畴有理由存在。尽管他们的欧洲想象多半是西欧,也并不覆盖整个欧洲。
如果说,第一个棘手的问题显示了认识与现实之间的错位,那么,第二个棘手的问题则暗示了存在着一个既定的认识论标准。由于后者的干扰,使得我们对于前者,即亚洲范畴的现实功能熟视无睹。因此,稍微对认识论的原理问题做些检讨,对于推进亚洲原理的思考或许不无裨益。
简要地说,思考亚洲原理面对的是这样一个理论困境:既定的认为亚洲无法成为论述单位的理由,在于它无法整合为一个自足整体;这个理由基于近代以来西欧自然科学逻辑的扩大化,也基于近代以来西欧向世界的扩张所造成的以西欧为世界模板的集体无意识。亚洲原理的创造,需要对这个认识论前提进行正面挑战,建立一种真正的多样化认识习惯:它不依靠整合造成单一求同的结果,而依赖于多元的特殊存在相互之间发生关联,建立起真正多样的世界想象模式。

酒井直树、孙歌 著,董子云、杜可珂 译
华人作家协会出版社,2018年6月
让我们还是先回到政治历史地理学。在这个领域里,对于特殊性的关注是推动研究者进行考察的动力。研究人与地理空间的关系,目的在于对那些特定的问题有所理解,而不是以此论证可以反复呈现的规律。地理因素的千差万别,致使研究者的关注重点自然而然地从共同性转向特殊性,政治历史地理的问题多数涉及共时性中的特殊状态,这种视角上的特点显然与其研究对象的特质有关。然而历史地理学的探讨并没有对普遍与特殊的关系格局提出挑战,更没有被其他知识领域共享。迄今为止,我们大家最常用的一个词就是普遍性。作为一个预设,普遍性不但经常被学院里的年轻学生们使用,而且它被转化成了一个评价标准。比如说,好的论文要有普遍性,不具备普遍性的特殊性讨论,就没有价值,因为它将是一次性的。这样一种对普遍性的理解从来没有被真正地追问过。没有人认真想过,那个所谓的普遍性,它到底是什么?
多样化的欧洲在经历了宗教、思想、现实社会发展等各个层面的抽象之后,被成功地整合为一个整体;而亚洲史的写作,无论如何都只能是一个拼盘。假如亚洲被作为一个单位讨论的话,它必须跨越“无法整合”的鸿沟,这就意味着世界史的认识论原理不得不经受挑战:无论是地区的历史还是人类的历史,迄今为止都墨守着一个潜在的约定俗成,这就是向着同一个方向发展的多样化历史,可以抽象为一元前提下的多元化图景。在这样一种认识论的前提下,知识人共享了关于普遍性的理解方式:从多种具体的个别性中抽象出来的同一性,具有高于个别性的价值,因此,普遍性高于个别性,而拒绝被抽象的特殊性,由于不能整合进普遍性,则在价值天平上贬值。
那么,我们如何利用亚洲的历史资源建立另外一种关于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的理论想象?
(原载于《信睿周报》第三期,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