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邪恶……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关于“邪恶”的思考与研究,似乎在今天比在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迫切性和现实意义。英国左翼思想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论邪恶:恐怖行为忧思录》(原书名:On Evil: Reflections on Terrorist Acts;林雅华译,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一书中从探讨恐怖行为的根源进入论述,其研究视角分别属于文学、哲学和神学三种论域,把邪恶区分为根本性邪恶和平庸的邪恶,分别与齐泽克和阿伦特的相关论述相关。伊格尔顿认为不能把恐怖主义简单地定义为邪恶,然而究竟应如何定义邪恶,他其实也无法给出唯一的答案,只能强调不要停止反思邪恶。但是作为左翼思想家,伊格尔顿在邪恶论题上当然不会放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他认为没有任何制度、体系能够像资本主义这样堕落和邪恶;在人类历史上,资本主义是语言动物所建造的最能恶化社会矛盾和最具有邪恶特点的制度。像他这样把邪恶与某种社会体制力量结合起来批判的声音,在当今全球范围的社会抗议运动中也早已成为越来越强烈的声浪。对于我们来说,需要重新反思何谓邪恶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恐怖主义行为在世界范围中从未停息,而是由于伊格尔顿所说的那种在他看来非资本主义莫属的体制性根本邪恶与在这个体制下绝大多数人的平庸的邪恶在当今生活结合得如此紧密、如此不可分离。在他看来,如果不紧紧扣住像资本主义这样的邪恶体制,谈论什么人或那个群体是邪恶的都是不准确和不够深刻的。在我看来,伊格尔顿对邪恶的论述其实很难说在哲学上或神学上会对我们有多么重要的影响,但是他把邪恶与体制以及体制中的个人紧密联系起来并予以无情揭露和批判的锐利目光,确实有重要的警醒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反过来再思考伊格尔顿在书中对邪恶在本质上如何作为一种形而上的无目的、无指向、无意义的无限意志,其目的是要彻底消除人的有限性、最终消灭人类自身的存在等等哲学论述,或许又会感到他的批判性过于形而上,如果用来分析现实中的邪恶力量会显得空泛而苍白。该书译者在序言中说伊格尔顿的目的“其实是要重新提倡人的主体性,人的道德自觉,以消解后现代本质主义的匮乏。……人需要在这个世界中有意义的活着”。这当然是对的,问题是如果仅仅是这样,则与思考和批判以体制之名施行的邪恶仍然有一种漫长的距离。我们需要再三思考的是,我们可以同意伊格尔顿说的,不能简单地将恐怖主义贴上“邪恶”的标签;但是这不等于说我们不能把那些早已被历史和现实证实为邪恶的主义或体系称之为“邪恶”。在他看来,简单地贴标签是一种放弃自身道德责任的行为;我们更应该说,一律反对所有的“标签”(在这里指的是给具有某种性质的事物命名)更是一种严重地放弃自身道德责任的行为。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哲学教授亚当·莫顿(Adam Morton)的《论邪恶》(原书名: On Evil;文静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提醒我们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要提高警惕,任何对邪恶的解释必须要帮助我们理解三件事:邪恶缘何而生;为何邪恶经常在平凡事件和日常情况下发生;我们如何被视为邪恶。……亚当·莫顿引用多种绝佳例证,提出观点:邪恶发生在与邪恶对抗的内部心理障碍崩塌时。他也向我们介绍了噩梦般的人,例如阿道夫·艾希曼和汉尼拔·莱克特,并提示我们虽然这些人的行为惨无人道,但只有将其视为人类行为的一部分才能使我们更进一步正确理解邪恶。”(弗雷德·阿尔福德(Fred Alford)《邪恶对我们意味着什么》,见莫顿该书中译本封底)在我看来,“邪恶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是一个更深刻和更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是从伊格尔顿到亚当·莫顿关于邪恶的思考和论述中应该突出和强调的问题。
亚当·莫顿和伊格尔顿一样反对简单地贴上“邪恶”的标签,而必须揭开邪恶的面纱,既为了防止暴行,也是为了更充分地理解人性。因此莫顿坚持必须了解暴行实施者的内心世界与思考模式,从动机的角度区分错误和邪恶的决策。但是,莫顿也没有把邪恶仅仅看作是个人行为,他把引自C.S.李维斯《地狱来鸿》前言(1961)的这段话放在该书扉页就说明了他对邪恶集团的批判与愤怒之情:“如今,最为严重的邪恶事件并不是发生在狄更斯笔下的那些肮脏的‘犯罪窝点’。更不是发生在集中营或劳改营。但在以下这些地方我们能看到这些行为所导致的致命后果。通常由那些看似安静、穿戴整齐、精心修剪指甲和胡须、不会大声讲话的人,在干净、铺着地毯、温暖、明亮的办公室进行谋划和实施的(他们甚至把移动和搬运的时间精确计算到每分每秒)。”因此,在该书中有一节专门论述“国家暴行”。他指出,“在20世纪,两件事带来了可怕的后果:现代化国家的建立以及伪科学伪宗教式意识形态的建立。以这些意识形态的名义,在纳粹德国希特勒统治的地盘以及……,数以百万的人被杀害。……大屠杀往往受意识形态的驱使,如果我们把宗教预言与宗教狂热都算在内的话”。(95页)他接着指出国家的性质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在那些重大的生死大权掌握在少数非选举产生的首领的手里的国家中,这些首领并不对他们所掌控命运的人做出任何解释,所谓的对错也是根据一系列由这些首领确立的不容置疑的信仰所界定的,这样的国家必定拥有巨大的罪恶之源。(96页)这与伊格尔顿对资本主义体制的邪恶本质的批判是不同的思考路径,但是在体制与邪恶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是一致的。
那么,“邪恶对我们意味着什么”的问题应该理解为:邪恶意味着人们必须抵制和消除身处的社会体制中可能具有或已经具有的邪恶本质,邪恶还意味着在体制之恶的阴影下无人可以独善其身,邪恶虽然最终无法在人类社会的所有成员的个体行为中消失,但是必须从国家体制和意识形态中驱除。亚当·莫顿指出,产生暴行的必要特征是个人良知对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屈从,而所谓的个人良知在经过训练和强大意志力的作用下会受到扭曲,最后虽然有过内心挣扎,但是最终还是会成为实施邪恶的力量中的一分子。(99页)他还特别警告我们:“不要因为自己的价值观坚定不移或者来自本质良好的社会,就过于自信地认为自己不可能在重大邪恶事件中扮演某种角色。”(160页)这是关于“邪恶对我们意味着什么”的最深刻的教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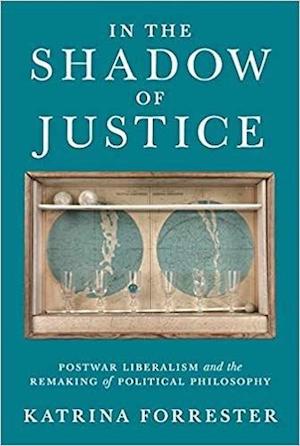
In the Shadow of Justice: Postwar Liberalism and the Remaking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
与关于邪恶的论述相对应的、而且关系最密切的论述自然是对正义的思考与论述,而正义论述无疑又是政治哲学的核心论域。近日一位青年学子向我推荐哈佛教授Katrina Forrester的最近出版的《正义的阴影下:战后自由主义与政治哲学的重塑》(In the Shadow of Justice: Postwar Liberalism and the Remaking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随后当我们在加州几处国家森林公园之间自驾漫游的时候,时而讨论着战后自由主义发展的思想谱系与罗尔斯的影响之间的关系。毫无疑问,约翰·罗尔斯是二十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无论是他对分配正义之于政治哲学核心性的重新强调,通过“原初状态”与“无知之幕”等思想实验对康德和黑格尔的重新解释与发展,还是他提出的差异原则对不平等同时进行的批判与维护,都可以说,罗尔斯不但提出了一套建基于公平正义理念之上的完整、全面的政治哲学学说,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英美分析政治哲学乃至政治哲学整体的问题意识与研究路径。然而,正因为罗尔斯的影响力与争议,加上当代英美分析主义哲学主要关注哲学问题而忽视其自身哲学思想史的倾向,罗尔斯的政治哲学乃至整个的战后英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往往都笼罩在一种众说纷纭而又似是而非的面纱当中。在此背景之下,Katrina Forrester的这本著作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因为她在书中所讲述的正是在罗尔斯正义论述影子之下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史。通过在英美当代哲学圈内较为罕见的第一手文献研究(包括此前未公开出版的哈佛大学档案馆藏罗尔斯早期在校资料)与思想史式的研究视角,Forrester提出罗尔斯那一代的政治哲学家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正是在二战后对大政府的不信任与恐惧以及风起云涌的民权和反战运动之间中产生的,而罗尔斯正是在经历了一定程度的思想转变之后把国家支持之下的分配的正当与正义性重新抬上台面的关键人物。在Forrester看来,这种在左右之间反复斟酌与拷问的思想发展并不仅是简单的学理纷争,而是塑造了70年代以后整个政治思想思考氛围的重要力量。然而吊诡的是,自80年代里根与撒切尔时代以后,其整体意识形态被归为右派的新自由主义似乎大获全胜,由贸易、金融而至资本整体全面自由化,国家提供公共服务与介入分配过程的权力受到诸多挑战而一再萎缩,以至于即使在后金融危机与民粹主义幽灵萦绕不散的今天,罗尔斯本质上属于温和派的公平正义与分配观念居然会被认为是激进极端的。
因此,重访罗尔斯与当代英美政治哲学的诞生就不仅仅是纯粹的思想考古,而是变成了对现实具有启示意义、揭示自由主义的野心与局限的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