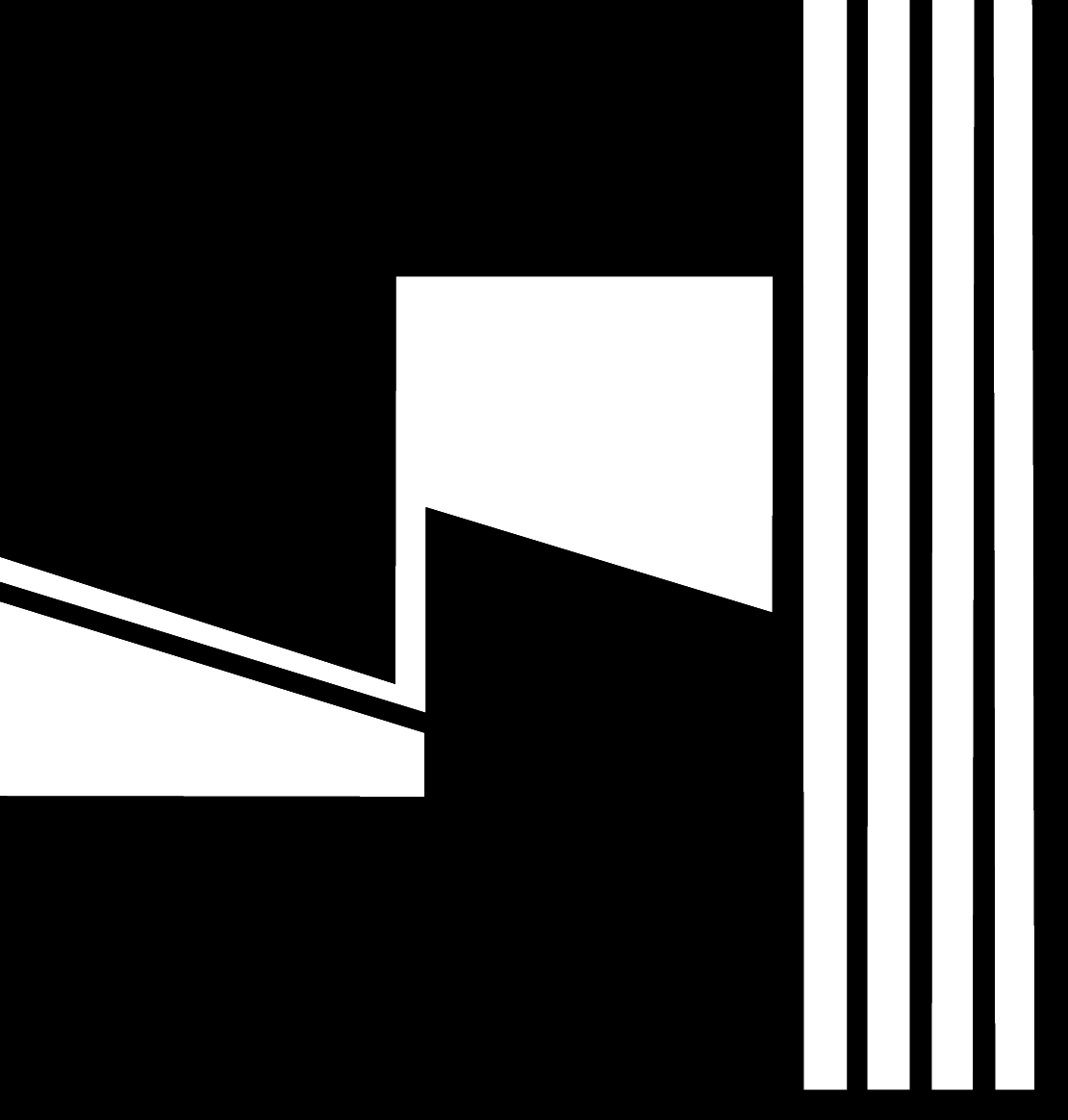恋曲1980:恋爱的纯真年代
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大龄青年的恋爱问题成了一个爆炸性的社会问题,一方面是因为50年代出生的人口到了婚嫁的高峰期,另一方面,大批知青返城时已成了大龄青年。当年在上海,为青年人找对象可谓是社会总动员,各单位工会、共青团和妇联纷纷开展各种活动,千方百计给他们牵线搭桥,原上海电气公司合金材料总厂的工会副主席谢菊仙、飞跃电器厂的工人彭珠凤以及轻工政治轮训学校的老师范本良都成了活跃一时的热心红娘。在那个纯真的年代,青年人的择偶标准最注重的是人的品行。
被耽误的青春
彭珠凤原本是上海市飞跃电器厂的一名普通工人,后来却戏剧性地被调到当时的南市区妇联做起了专职红娘,她的人生轨迹之所以发生如此大的改变,源自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突如其来的一个巨大的社会难题。
当时,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也就是“光荣妈妈”们的孩子,陆续都到了婚育的年龄。于是,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单身男女青年,当时称为“大龄青年”。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本来人口基数就比较大,他们大多经历过上山下乡运动,返城时已经耽误了青春,有的在十年动乱后,为改变命运忙于高考,把个人问题抛在了脑后,进入80年代后许多人都成了大龄青年。
原上海合金材料总厂工会副主席谢菊仙回忆说,当时厂里一千五六百人,有三百多个大龄青年。而据上海市地方志记载,新中国成立后,上海青年主要的择偶方式是由亲朋好友介绍,接触面相当小,同事、邻居在男女青年的牵线搭桥上起了不小的作用。
1982年7月29日,对于在上海南市区副食品公司卖猪肉的小伙子金圣轲来说,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在之前的两天,他一直彻夜难眠,原来,他的邻居彭珠凤为27岁的他介绍了一个女朋友小杜,29日那天他们就要见面了。在经历过很多次不成功的相亲之后,金圣轲有些忐忑不安,
其实他身高一米七八,浓眉大眼,挺好的一个小伙子,可就是找不到另一半。
金圣轲出生于1955年,那时候新中国成立不久,人口开始大幅度增长,当时社会上流行一个词叫“光荣妈妈”,以多生多育为荣。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像金圣轲这样的多子女家庭,由于生活拮据,住房紧张,结婚成了“老大难”问题。金圣轲回忆当时家里住房的窘迫:“我们家当时是九个小孩,九个小孩(和父母)就住在一间,十六个平方米的一间房间。当时家里面还有一个阁楼,六个男的睡在阁楼上面,四五个女的睡在下面,爸爸跟妈妈是分开睡的,没有办法,当时子女多嘛。”
当时金圣轲穷得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他该怎么去见人家姑娘呢?幸好他有位同班同学,由于是家里独子,条件比较好,于是金圣轲向他借了一件当时很时髦和神气的涤卡外衣,来到人民公园,开始了他和小杜的第一次约会。
人民公园是上海著名的“相亲角”,从2004年开始,每周六这里就会出现庞大的“大龄未婚青年”家长团,心急如焚的他们亲自代替子女征婚。人民公园之所以成为“相亲圣地”,是有其历史渊源的,拍摄于80年代的影视资料显示,当时这里已经是沪上赫赫有名的“恋爱角”,每周六的晚上,有几百个未婚青年男女,在亲朋好友陪同下来这里相亲。
人民公园关门后,两人又转战来到外滩的“情人墙”,第一次见面,两人对对方感觉甚为满意,可谓一见钟情。金圣轲回忆:“在外滩从(晚上)八点不到一直谈到夜里十二点钟。”杜桂英觉得:“谈谈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一会儿怎么这么晚了。”

外滩情人墙
从70年代末开始,一百多万上山下乡的上海知青陆续返沪,他们中的很多人因为怕失去回城机会而不愿在农村结婚,于是都成了大龄未婚青年。上海市浦东新区“党员红娘工作室”的负责人范本良阿姨当年也是其中的一位,她记得自己回到上海的时候已经29岁,却还没有谈恋爱,就是怕在农村谈了恋爱后,双方无法都回城而造成两地分居甚至婚姻破裂。
从18岁到28岁,上海姑娘周菊萍最美好的青春岁月,全都奉献给了黑龙江农场。受家庭环境熏陶,她从小就热爱文艺,能歌善舞,在黑龙江插队落户的时候,被安排到农场当小学老师。这样才貌双全的姑娘,当时不知道拒绝了多少追求者。当地极端寒冷的气候,让她坚定了一定要回上海的决心,她回忆道:“自己心里想,还是回到上海来,那边实在太冷了,最冷的时候呢,是零下二十五度到零下四十度左右,地里面都穿这么高的靴子,真的是叫‘水跟泥’,我们叫‘水泥’。因为自己想回来,所以就不谈朋友。”
1980年,在知青返城的大潮中,周菊萍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被安排在闸北青云街道里弄加工组,当时已经28岁的“大姑娘”成了父母的一块心病。
红娘: 甜蜜的事业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熟人社会”逐步向“陌生人社会”过渡,陆续回沪的百万知青也加剧了婚姻的“老大难”问题,当时上海的各级共青团组织、工会、妇联等社会团体对这个社会问题极为重视,想方设法举办活动,为大龄青年的婚恋创造条件。
原上海合金材料总厂工会副主席谢菊仙回忆,1978年厂里就成立了“联姻之家”,1984年四五月份,她还曾到北京参加全国红娘工作经验交谈会,商讨为大龄青年解决婚姻难的问题。彭珠凤记得当时的报纸上刊登中央领导如陈云等也很关心这个问题,希望各级组织都能关心大龄青年。
1984年7月,上海市工青妇等组织联合举办了大龄青年联谊会,在彭珠凤的印象中,类似的纳凉晚会、浦江夜游、联谊舞会等等,当年每个月都会举办三五次。大龄青年的社会交际面广了,择偶半径也不断扩大。当时各企业对本厂职工的婚姻问题也很关心,彭珠凤记得当时南市区妇联成立了一个婚姻咨询服务站,由她负责,于是她们就发动区内区外的企业,上钢三厂的工会主席送来1 200个小伙子,国棉厂的工会主席不甘示弱,也送来了约1 000名纺织女工。接着,他们就组织集体的联谊舞会给青年人提供交往的平台,而在跳集体舞或交谊舞的过程中,彭珠凤等红娘们也发现,由于当时社会风气并不是那么开放,青年男女跳舞时都比较害羞和矜持,不是很放得开。谢菊仙回忆道:“他们就头低下来这样跳,怕难为情,不好意思,没有见过这个世面。手是牵着的,男同志一只手搭在她腰上,不碰面的,离得很开,尽量不靠近,怕难为情。”
而在舞会后,红娘们对后续工作也相当尽心尽力,彭珠凤回忆,她会询问跳过舞的青年男女对彼此的印象,印象不错的就鼓励他们积极交往,并对双方的恋爱进展予以关注。“我看到是20号姑娘,我就把她喊过来对她说,刚刚跟你跳舞的这个小伙子你看怎么样?她说蛮好,那么我就说,既然你们蛮好的,那么你们出去以后就去谈。然后我就把他们两个人的表格拉出来,用别针别在一起摆开,我们也好去跟踪,他们到底谈得怎么样了,谈到什么程度。”

1984年7月上海市工青妇联合举办的大龄青年交谊晚会
1984年,曾在云南插队落户的知青王国生回上海已经有五年时间了,年过三十的他仍然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单身汉。王国生回忆,傣族人十七八岁就要讨老婆了,但是上海知青在那里不敢结婚,因为当时害怕回不了上海。
王国生没有想到,这年夏天,他所在的上海消防水带厂也加入了为大龄青年举办交友舞会的热潮,在舞会上,他遇到了令自己的心动女生,她就是从黑龙江回来的周菊萍。王国生的婚恋究竟是如何发生转机的呢?原来当时王国生并不太会跳舞,而周菊萍本来就能歌善舞,就主动跑过去教王国生跳舞,这让王国生一下子对周菊萍产生了好感。王国生和周菊萍没有想到,跳舞让他们俩在茫茫人海中相识、相知并最终结婚,跳舞又成了他们日后谋生的饭碗。1998年以后,王国生和周菊萍开始参加上海市的各种交谊舞大赛,没想到竟然一举夺魁,之后两个人成了交谊舞的专职教练。不过,现在来学跳舞的都是以健身和娱乐为目的的中老年人,而在20世纪80年代,彭珠凤利用跳舞这种形式,把几百对青年男女送进了婚姻的殿堂。她的体会是,这是一种高效的方式,“跳舞时人与人之间比较近,容易产生亲近的感觉,所以这样容易成双成对,又能解决得多。这样的一大批人跳舞,比如300个人跳舞,一晚上总归有十几对、近二十对就能够谈(恋爱),所以快呀”。
彭珠凤做红娘做得小有名气,在1984年,上海电视台专门拍摄了《她乐于做红娘》的纪录片。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彭珠凤这根红娘的线一直牵在手中。她记得80年代时,曾为一米八○的黄伟荣和一米六九的张莲娟牵线,两人最终喜结连理。纪录片中记录了她去三口之家探望的情景,当时黄伟荣和张莲娟的儿子黄安毅还只有两岁,而如今,黄安毅已经从医科大学毕业,在瑞金医院实习,有趣的是,黄伟荣和张莲娟又找到了彭珠凤,请求两人当年的月老再为自己的儿子物色个媳妇。
彭珠凤回想自己当红娘的经历,“自己开始做做也没有什么想法,后来越做越顺,越做越好。到最后他们讲,彭师傅,你很有技巧的,都成功,所以后来人家都认得我了,我又上了电视嘛,来找我的人人山人海,最多一晚上是介绍了12对、24个,少一点总归也有三五对”。

彭珠凤(右)安排男女青年见面相亲
求助红娘彭珠凤的信件像雪片一样飞来,工作之余,她发动全家甚至六岁的儿子一起上阵。每天她要约定五六对男女青年会面,所用的信封、
信纸和邮票,都是她用自己的钱买来的,她给有诚意的未婚青年写信,为求偶者巧点鸳鸯谱。那时候没有手机,因为联络不便还闹过不少笑话。彭珠凤记得她曾为一位患了小儿麻痹症而腿脚残疾的男青年和一位高度近视的大龄姑娘牵线。第二天,彭珠凤就约两个人见面,没想到约会现场竟然出现了两个腿脚残疾的男青年,这该如何相认呢?她灵机一动,把自己岁的儿子叫了过来,她让儿子分别走到这两位男青年身旁,慢慢地说“妈妈,你的名字我知道的,叫彭珠凤”,果然其中的一位马上跳起来问她:“你就是彭珠凤啊?”她通过这个办法认出了那位男青年。
恋爱的纯真年代
20世纪80年代,上海人的婚恋观仍相对保守、单纯,既不像五六十年代那样看重出身身份,也不像90年代后那样将物质条件放在一个更高的地位,但同时人们对婚恋的看法也慢慢产生了变化,婚姻恋爱不再是一个禁忌的话题,变得可以公开讨论,一些新鲜事物出现了,比如征婚广告。新中国第一个登征婚广告的人是谁?媒体的普遍说法是四川教师丁乃钧,1981年他刚摘去“右派”帽子不久,就大胆求助《人民日报》下属的《市场报》征婚,举国轰动,可是谁能想到,上海有一位姑娘的征婚启事,早在1980年8月就已经发表在《青年一代》杂志上,比丁乃钧早了五个月。
在征婚启事上,这位姑娘写道:“编辑同志: 我已经是二十七岁的大姑娘了,还未曾尝过恋爱的滋味,我期望能找到一个感情丰富、有事业心的青年,可是,在我周围很少有我心目中的对象,也没有什么社交活动可以参加,请人介绍吧,也是很别扭的,我该怎么办呢?”
原《青年一代》主编夏画回忆道:“1980年,我们《青年一代》提出这样子一个‘大姑娘的苦恼’以后,就收到600多封来信,全部都要向她来求婚。我们编辑部呢,找了其中十个男青年到编辑部来,一个个过堂,一个个相面,就是问他,你怎么样想这个姑娘。”

1980年8月《青年一代》杂志上刊登的“大姑娘的烦恼”
《青年一代》创刊于1979年,当时它提出关注年轻人的婚姻、恋爱、家庭,在社会上引发强烈反响。夏画回忆,那个时候社会氛围是不允许你
谈恋爱、婚姻、家庭问题的。所以1979年9月,《青年一代》的这篇《甜蜜的爱情,幸福的生活》一刊登以后,《中国青年报》全文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报,外国通讯社如法新社马上增发了一条新闻,称中国开始打破了恋爱、婚姻的禁区。
在解决了“大姑娘的苦恼”之后,编辑部又从应征的600多个小伙子里精心筛选出7个,倒过来面向全国为小伙子“征友”,整个过程历时半年之久。夏画还记得那时的情况:“为七个大小伙子征友,那个时候还不讲征婚,陆陆续续来了2 300多封信,每个人(小伙子)都抽了五个人(姑娘),你可以谈一到五个,第五个是最后一个,你再谈不成功我们也不介绍了。”由此也可见当时人们对于征婚征友的郑重其事。
1980年热映的电影《甜蜜的事业》曾荣获第三届电影“百花奖”最佳导演奖,这部影片最牛的地方是它让中国的观众首次在银幕上看到了女跑男追的慢镜头。上海向来是中国开风气之先的城市,街头上也出现了以“大三角”和“小三角”姿态兜马路的情侣。所谓“小三角”就是男女双方手臂互相勾着;而“大三角”就是男青年抄着女青年的腰,或是双方搭了肩膀抄着腰行走。陈德容老人回忆,当时“小三角”蛮多,而“大三角”还相对少见。
当年的恋爱青年,在牵手时和结婚后,对于物质条件看得并没有那么重,即便你一无所有,我依然爱你,这是那个年代渴望爱情的年轻人的心声。因此当摇滚歌手崔健跳上北京工人体育场的舞台,嘶哑着嗓子吼出“这是你的手在颤抖,这是你的泪在流,莫非你是正在告诉我,你爱我一无所有”的时候,台下是雷鸣般的掌声和泪流满面的观众。
谢菊仙的丈夫杨锐思回忆起两人结婚之初的情形:“当初结婚的时候,像现在所说的叫‘裸婚’,家里没房子、没车子,条件相当差,借了6平方米的房间就作为婚房,什么办喜酒都没的,就发点喜糖这样简单。”虽然条件艰苦,但是人们坚信,劳动可以创造一切。金圣轲和杜桂英结婚的时候,也是一穷二白,夫妻俩住在哥哥的房子里,金圣轲每天凌晨2点起床卖猪肉,菜场下班以后还要骑上黄鱼车送货,以赚钱补贴家用。
赚了钱后,他花了2300元钱买了一间私房改善居住条件,而当时他的月工资才40多元,可见他当时赚钱的拼命劲头。
光阴荏苒,大龄青年换了一茬又一茬,似曾相识的场景仍在上演,虽然20世纪80年代距离我们已经越来越遥远了,但是那个时代男女青年纯真的恋爱方式和观念,至今让我们怀念。
日本姑娘嫁入石库门
8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对外开放,人们的思想也开始活跃起来,随着与国外联系的增多,再加上拜金主义思想的影响,当时“嫁到国外去”成为很多上海姑娘的目标,在当时拍摄的纪录片里,我们能看到一幕幕上海姑娘与外国男性登记结婚的场景。
据上海市人民政府婚姻登记处统计,1977年至1979年上海市涉外婚姻共有446对,而从1986年到1990年则猛增到5 502对。当时社会上还出现了很多担忧的声音,说姑娘都嫁出去了怎么办呢?其实,有嫁出去的,自然也有嫁进来的,来自日本东京的村上牧子姑娘就是其中的一位。
1989年12月25日,牧子跟随一个日本文化旅游团来到上海,在华东师范大学进行短期的汉语培训,牧子没有想到,她即将在这里邂逅一段浪漫的师生恋。王幼敏是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的副教授,也是当时牧子的老师,课间休息,牧子都会把黑板擦得很干净,时间长了,引起了王幼敏的注意,他觉得这位日本学生很懂得尊重老师。王幼敏当时已经36岁了,大龄未婚,除了因为考大学、读研究生耽误了终身大事之外,当时上海姑娘的择偶标准发生重大改变,也是他被“剩下”的重要原因。
上海姑娘的择偶标准在不同时代有很多版本,比如“五十年代找工人,六十年代选农民,七十年代解放军,八十年代嫁文凭”,还有一种说法是要符合“五大员”,即“长相像演员,工资像海员,身体像运动员,政治上是党员,态度像服务员”。另外,姑娘们还普遍追求“三高”,一是个子高,二是学历高,三是工资高,后两项,王幼敏基本满足,但是在一条上,只有一米六五的王幼敏打了个大折扣,而日本姑娘却没有把身高这一条作为一个硬性条件。
牧子热爱中国文化,在华师大留学的几个月时间里,她走遍了上海的名人故居,而导游正是汉语老师王幼敏,不知不觉中,两个年轻人的心中
迸发出爱的火花。1991年1月,在上海姑娘的出国大潮中,日本姑娘牧子勇敢地嫁入了石库门。
牧子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走进石库门弄堂的情景: 王幼敏让她不要说话,不要暴露自己是外国人,她是怀着紧张的心情走进石库门的。当时王幼敏觉得,一个外国人走进弄堂,还是件新鲜事,很容易引起围观。
淳朴的牧子嫁到石库门后,她的婚姻生活遭遇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首先是住房的局促,王幼敏描述当时的情景:“同一间房间里面分成两间,隔板隔一隔,上面天花板都是通的,那你说夫妻生活怎么过?你要想表示亲密一下都不可以,声音前后都通,我的父母就在后面。”
一间房间里面住两对夫妻,这让来自日本的牧子感到不可思议。可是,还有让牧子更加难以忍受的事情,那就是不能洗澡。有学者戏称日本是“洗澡的民族”,对于日本人来说,不能每天洗澡是个很大的痛苦。牧子好干净,于是只能因陋就简,拉起窗帘,在一个红漆大木盆里放一点热水擦洗身体。

王幼敏和村上牧子夫妇结婚登记照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牧子不仅适应了石库门,还学会了说上海话,她快乐地“在中国做老百姓,生活在上海平民中”。牧子说:“这哪能行呢?这哪能办呢?我不晓得。这三句(上海话)经常说。上海话在上海生活、工作是必须要学习的,能听懂和听不懂完全是两个世界的。比如说,买菜时,我问他‘这几钿(多少钱)’?回答可能是八角一斤。我问‘多少钱啊?’的话,可能回答是一块钱一斤。那个时候我说上海话和不说上海话,他的价钱和态度都不一样的。”
摘自上海音像资料馆编:《上海故事:走近远去的城市记忆》,上海大学出版社2019年8月版。所收录的文章改编自上海电视台同名纪录片栏目《上海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