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毅超评《思想产业》︱美国思想产业的观察日记
对于思想领袖来说,这是最好的时代。对于公共知识分子来说,这是最坏的时代。而对于其他人来说,它是最易迷失方向的时代。
在德雷兹内看来,无论承认与否,象牙塔的时代已经逝去。知识分子将不可避免地被抛入整个思想市场。拥有大学教授、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三重身份的德雷兹内无疑是这一游戏的个中好手,《思想产业》则是其在2017年出版的最新作品。
德雷兹内意图通过自己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素养描绘当代美国思想产业的情况,以期找出可能的更好出路。他将他的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着重介绍美国现代思想产业的三个关键力量,即既定权威公信力的削弱、受众的政治极化,以及经济不平等的加剧;第二部分主要考察这一产业对主要供应者,尤其是学术研究机构的影响;第三部分关注思想产业的运作情况,以及市场是否存在改善的可能性。
美利坚思想产业观察日记
德雷兹内认为,现代美国思想产业有三支根本力量:即权威匮乏、政治极化、不平等加剧。在这三者中,经济不平等的加剧是“思想产业转变背后最重要的推动力”:它在削弱美国梦的同时,使得财阀捐助人占据更为强势的地位。讽刺的是,同样是这三个因素推动了整个思想市场的扩大。由于每一个阵营都需要自己的公共知识分子和思想领袖,从而显著增加了对这两者——特别是后者的需求。
借助以赛亚·伯林关于狐狸与刺猬的比喻,德雷兹内表示现代思想产业对思想领袖这样的刺猬更为有利。刺猬是真信徒与创造者。他们很少怀疑自己的信条,坚定不移地向他人强调自身思想的正确性。这使得他们更可能对党派保持高度的忠诚,他们的心理防御机制也更容易抵御外界批评。
严格来说,德雷兹内的三个因素并无新意。这三支力量不仅改变了美国思想产业,甚至改变了整个美国政治。它们早已充斥在党派领袖、新闻记者、专栏作家的口中,成为一种陈词滥调。德雷兹内自己也承认,“如果孤立地看,这些趋势当中没有哪一个是新出现的。……新奇的是,在这个媒体平台不断激增的世界里,这三种驱动力结合在了一起”(81页)。
现代社交媒体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一般人摄取信息的方式。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新闻的报道者和经历者。这天然削弱了由记者和学者所建立起来的专业壁垒。由遥远距离所导致的信息不足,已经被社交媒体的信息过载所替代。面对信息过剩的局面,一般人倾向于选择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世界。这一被强化的社群区分则直接加剧了媒体世界的巴尔干化。每个人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意识形态偏好,“在没有反对观点的信息生态系统里繁荣发展”(14页)。在左派的眼里,FOX是谎言的制造机;在右派的眼里,CNN则是假新闻的代言人。令人遗憾的是,媒体的党派倾向确实导致它们在节目的制作中存在系统性偏见,连《明镜周刊》这样一贯标榜自己客观中立专业的媒体也在去年年底陷入严重的记者造假丑闻之中。
这些新兴社交媒体进一步放大了跨国科技巨头的发言权。在经济不平等加剧的情况下,“大量的财富集中在少数富人手里,这一现象催生出了为新思想的产生和推广提供资金的新的捐赠人阶层”(75页)。被捐助的基金会必须体现出与捐助者相一致的理念。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就是这一思路的老牌推手。硅谷的财阀更加激进,他们将一切问题都视为工程问题,奉行技术至上论,迷恋于各种颠覆性的想法,德雷兹内形象地描绘道,“大多数硅谷精英不会把政治冲突看作是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而把它看成一段需要删除的错误代码”(79页)。这些新兴捐助人对全球性问题的关注远比具体事务来的更多。对政治学人而言,这既是机遇,亦是隐患。
德雷兹内的这一观察是准确的,然而他的结论却畏缩不前。跨国科技巨头的威胁性远不如他所描绘的如此温和。同时掌握了资本和流量的数据巨头,更有意愿重新塑造一般人的想法。通过针对性的信息推送和有效的信息筛选,他们已经掌握了引导舆论的钥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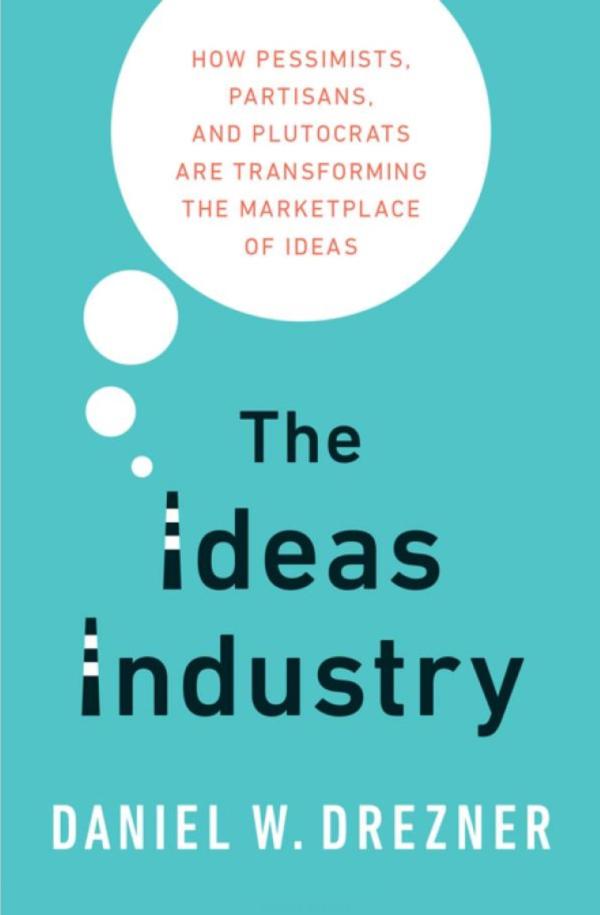
生存还是死亡——公共知识分子的至暗时刻
公共知识分子已经跌下神坛。即使是最顽固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几乎在所有的主要国家,公共知识分子的地位都大不如前。这一点在中国尤为明显。曾经盛行一时的“公知”,早已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从专家到“砖家”,从教授到“叫兽”,公共知识分子的污名化不断加剧。这固然与部分成员不检点的行为有关,但更与现代思想产业的范式转换密切相关。今日的公共知识分子和学术研究机构,同时承担了来自一般群众、政策制定者和财阀捐助者的共同压力。几乎所有人都对公共知识分子不满意。德雷兹内将这种不满意主要归纳为两个方向:与现实脱节和忽视个人能动性。
指责公共知识分子与现实脱节,不是什么新颖的说法。学术圈内外早就对这一问题做出过无数的讨论,“很多政治学家都会在文章里像小驴屹耳一样哀叹自己的无能”(126页)。德雷兹内尝试从两个层面回答这一问题。
在个人层面上,德勒兹内指出,与公众的刻板印象不同,“学者们热情地接受了新兴的网络平台,也乐于看到自己的舞台不再局限于同行评审出版物,可以向一般公众推销自己的观点”(102页)。桑德尔和齐泽克这样的学术明星就是典型的成功范例。德勒兹内批评学术界部分人士对新兴事物的过度恐惧和对年轻学者的压制,他们需要接受“思想产业中的声望等级制度与学界内部独有的等级制度并不完全匹配”(106页)。
在机构层面上,情况则要严重得多。一方面,学术研究机构已经形成一整套自我封闭的评价系统,“学术研究机构的专业化使同行评审类出版物的重要性被排在其他形式作品之前”(99页)。对学术机构的内部成员而言,他们不得不接受这套系统的规训,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如何将论文发表在由同行评议把持的高等级期刊上。学术出版机构通过严格的付费门槛,将一般群众隔离在整个生态系统之外。
另一方面,当代的政治学家集体性地倾向与政治现实保持距离,“专业人士的工作建立在他们所受的训练的基础上,而他们受到的训练是由所在专业的规范和标准决定的。这一思想从马克斯·韦伯的时代起就被学者接受了”(113页)。政治学家和政治家之间的韦伯式二分,使得政治学家心安理得地接受与政治现实的疏离。学术研究机构这种“何不食肉糜”的姿态自然引发一般公众的强烈反感。政治理论与现实的脱节,也使得公众愈发蔑视学术研究机构的存在。学术机构晦涩难懂的文风和行话进一步加剧了学术圈内外的隔阂。
轻视个人作用则是当代公共知识分子衰落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当今的政治学界展现出强烈的结构性偏好,“国际关系研究很少关注个体层面的变量,比如领导力,对领导人个体的关注则更少”(142页)。人的主动性被视为影响甚微和无关紧要的因素。简单来说,今日的政治圈相信制度,相信制度比人重要。这理所当然地激起了财阀捐助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反对。他们相信自己的成功是自己努力的成果,相信自己的能动性,相信是他们改变了世界。换而言之,他们相信人定胜天。
这种激烈的冲突背后,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在现代思想产业中,公共知识分子的特点决定了他们将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面对财阀捐助人的压力,他们要么选择屈服,要么选择退缩。
与此相反,思想领袖的地位得到了抬升。思想领袖的具体主张千差万别,但他们都对自己的主张怀有强烈的信念。德雷兹内表示,今日的经济学家比政治学家更加成功的原因就是强烈的共同信念,“经济学家之所以能够处于社科金字塔的顶端,是因为他们不会在公众面前表现得像公共知识分子,而是像思想领袖。经济学家们都坚信自由市场、自由贸易、最近流动和企业家精神能带来很多好处”(137页)。政治学家虽然有普遍的自由国际主义偏好,但是与经济学家相比,他们缺乏这样强有力的统一内核。德雷兹内的这一观察是否正确暂且不论,不过这倒是可以用来解释今日哲学界为什么如此衰落。毕竟,没有任何学科像哲学一样,如此缺少统一的范式。
难以令人满意的改善方案
到现在为止,德雷兹内是成功的。他成功地描绘出今日思想产业的现状,成功地分析了思想产业的缺陷,也成功地展示了公共知识分子当下的普遍困境。现在,他要杀出重围,为当今的思想产业开出自己的药方。在笔者看来,他的药方却沦为本书的败笔。
德雷兹内认为,当今思想产业受到权威瓦解、政治极化和经济不平等加剧的影响。那么,解决的方案也无外乎如何处理这三个因素。
德雷兹内开出的第一张药方,是承认往事不可追:现代思想产业的格局业已形成,所以怀旧派需要放弃幻想,接受这一新现象。
第二张药方就可能显得不那么靠谱。德雷兹内乐观地表示,“塑造现代思想产业的种种力量中,有一些很可能在未来十年里自行反弹。政治权威的公信度几年前跌入低谷,但是如今已有所回升,也开始有证据显示政治两极化趋势有所缓解”(291页)。然而,2019年的德雷兹内可能会后悔自己在2017年的幻想了。事实证明,美国政治的极化不但没有在这两年缓解,反而进一步加剧,甚至在世界范围内,政治的极化也在不断加剧。被他寄予厚望的前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更是带头跑路。
第三张药方更是一张空头支票。德雷兹内寄希望于高校和智库这样传统的非营利部门,认为它们需要“使出浑身解数,吸引更多的捐赠”(292页)。这无疑是美好的设想,但问题在于,德雷兹内压根儿没有指出高校和智库怎样才能吸收更多的捐助。这颇有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风范。
第四张药方亦值得商榷。为了解决政治学界高度趋同化的问题,德雷兹内建议通过“内部种族和性别的多元化”来增加多样性。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政治学界的趋同化指的是学者观点的趋同化。丰富多元化的方式是引入更多不同的意见,而不是强调种族和性别。
最后一条药方连德雷兹内自己都觉得有些天真,即知识分子的自我监督。“物质回报会使一般的知识分子堕落,但是愧疚和恐惧能够对抗经济诱惑。伴随成功而来的愧疚可以被利用,转化为自我约束。”(293-294页)这可能是一个方法,但这是一个纯然没有客观性保障的方法。一位信赖制度强于人的政治学家,最后的方案却寄希望在个人的自觉之上,不得不说充满了一种魔幻现实主义的味道。
不过,我们也不该苛责德雷兹内,他已经做到了自己的极致,做到了政治学界自由国际主义的极致。作者承认,“美国的学者远比这个国家的其他人更加信奉自由主义”(113页);作者也承认,“虽然财阀阶层的崛起为知识分子提供了良机,但这个良机向着更加自由主义的方向倾斜了”(78页);作者更加承认,“尽管专业性能够确保左倾的学者也能做好研究工作,但政治异质性的匮乏导致了更深层次的问题。……研究者可能会重点关注那些对自由派观点有力的话题,而避开对其不利的话题”(114页)。问题的关键是,作者将自己圈在自由主义的藩篱之中,不去思考几十年来政治学界的基本框架是否存在致命缺陷。
德雷兹内自缚手脚的做法,加上他圈内人的身份,使得他可能不愿处理这些尖锐的问题。他甚至没有指出,传统学术机构和新兴公共舆论市场背后是两套相互竞争的产业系统。如果我们承认由新兴社交媒体、科技财阀所构建的现代思想市场是产业,那么以学术等级制为主导、囊括了学术出版商的传统学术市场更是一种产业。这绝非简单的封闭与开放之争,它是两套产业对主导地位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德雷兹内指望传统学术机构向现代思想产业靠拢,意味着传统学术机构主动放弃自己的主导地位,成为现代思想产业的附属物。
与此同时,德雷兹内总是倾向于淡化问题的尖锐性。他写道,“学术研究机构这种左倾的趋势未必会导致学术研究也带有政治偏见,至多也就是像武装部队军官的右倾倾向损害到军民关系那样”(113页)。这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加以辩驳。一方面,如果事情真如德雷兹内所轻描淡写的那样,那么历史上那么多的军事政变可能也只是调皮的游戏。直至今日,军事政变都是政治现实中无法忽视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政治学家不可能在整个过程中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切割出去,这是对人性和逻辑的严重挑战。政治学家在面对不利于自身意识形态的数据时可以保持诚实,但他们的偏好将严重影响他们的焦点和路径偏好,从而动摇政治中立的根基。
德雷兹内没有注意到,导致今日美国政治极化和权威瓦解的主要因素,绝不是美国人周期性的反智主义。这种情况几乎出现在世界上所有主要国家的身上。这不是统计学上的波动曲线。自由霸权的衰弱才是真正的原因。自由国际主义与政治现实的愈发脱节,导致政治学界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这不断削弱了公众对学界的信心。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是这样,2008年的金融危机亦是这样,2016年的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更是这样。正如伯克在两百多年前所揭示的那样,政治是实践性的,理论的正确与否并不重要,“我们很高兴看到这样的情况: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在实践上是正确的”(Edmund Burke: 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dmund Burke Vol.1, General Ed. Paul Langfor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228)。
总而言之,德雷兹内的《思想产业》是一本很好的观察日记。他充分利用自己的经验和专业素养揭示出当代美利坚思想产业的现状和困境。然而,这也只是一本观察日记。德雷兹内并未成功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而是将自己局限在政治学界的同温层中。他不得不寄希望于盲目乐观主义的心态,展现了当代美国政治学界的自我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