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比较方法,研究好当前中国转型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本文系作者在第七届汇智公共经济学论坛及”新发展译丛"新书发布研讨会上的总结发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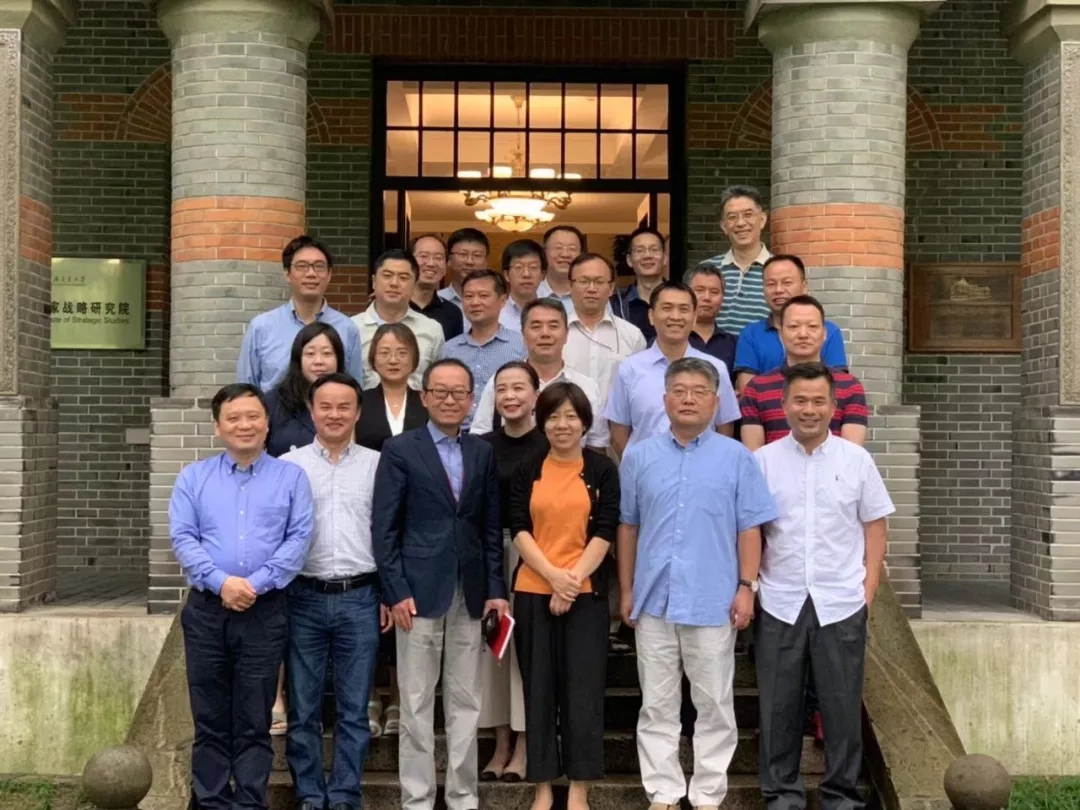
今天会议的内容很丰富。虽然分成两个阶段,两个阶段的内容有所差别,但主线梳理下来,就是要理解发展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上午我们聚焦在中国问题上,下午的讨论主要围绕《产权的政治学》和《掉队的拉美》这两本新译著,涉及拉丁美洲国家的一些经验与教训,每位专家的发言时间比较短,大家谈得相对散一点,但总体而言,还是在更宽泛的视角下讨论发展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今天会议的内容,我们会后会做整理。我的总结打算跳开这些具体内容,谈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我们做研究——包括讨论中国问题,讨论发展的政治经济学——我个人一直强调,比较的方法很重要,比较研究值得我们继续坚持下去。
了解国内经济学学术脉络的学者可能会知道,吴敬琏老师在中国社科院带博士生,一直带的是比较经济学的方向。他当年去耶鲁大学访学一年,研究的方向也是比较经济学,只不过现在这个方向的名字略有点改变,叫“比较制度分析”,其实还是比较研究。如果说过去的“比较研究”侧重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比较,包括比较经济学本身学科的内涵是做两个大体制的比较。那么,到了1990年代以后,随着计划经济国家纷纷转型,比较似乎变成了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不同市场经济国家之间,具体的、多样性制度安排的比较。
为什么经济学会有比较研究?理论上说,比较研究的方法在经济学里是非主流的。经济学试图把自己变成科学,科学追求对一般性规律的认识,所以似乎没有什么好比较的,因为要追求一般性认识是要理解不同国家的共性,要理解经济发展普通的规律。因此,我们看经济学的教科书,其实是不太在意制度的比较分析的,即便有也是放在最后几章去了。
那么,比较研究为什么重要?我自己本科是学习政治学的,南开政治学系那会儿很多老师的学术背景是学哲学出身,导致我多多少少也受到了哲学方面的熏陶。比如说,我们知道,中国哲学会讲到理学的一些概念,像“理”这个概念,说的是“自然、社会的基本规律”,这个基本规律可能只有一个,但是,在现实世界的表现形式可以是多样化的,朱熹将它比喻为“月印千湖”,也就是“理一分殊”。
即便经济学理论是探讨普遍规律的,这些规律反映在不同国家现实的国情当中,所表现的形式——无论是经济发展模式,制度以及文化,还是国家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即组成整个国家大的建构的一整套软件和硬件——可能都不一样。但不一样背后,仍然能够反映道理和规律的一般性。这也符合马克思的哲学观点,即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
当我们从经济学一般规律回到理解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的时候,比较分析的框架就有意义了。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在不同的条件之下,不同国家发展道路何以会出现差异性。就像今天上午张军教授讲的,为什么中国和俄罗斯转型的路径和绩效会存在明显差异,因为两国转型之初,包括制度、发展水平、分工程度等初始条件是不一样的。初始条件的差异使得各国即便受到同样经济规律的支配,也会走上不同的发展路径。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需要运用比较的分析框架,去理解不同国家能够演化出多样化制度背后的合理性,理解不同国家之间多样化制度甚至长期存在的原因。青木昌彦教授在《比较制度分析》里最后有一章,特别强调的一个基本观点正是:不同国家之间多样性的制度安排会长期存在下去。我们不见得会终结到某一个制度类型上,因为不同国家之间初始条件的差异,以及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路径依赖,会使得多样性制度安排具有内在的经济理性。
中国发展道路的经济理性在哪里?这种理性可能蕴含在中国制度演变的过程里面。我们不能说中国的发展和制度演变是缺乏理性的,只要承认人的行为是理性的,由人的行为选择所形成的策略均衡或者说制度——哪怕是暂时的——本身都有经济理性在当中。不管是拉丁美洲也好、美国也好还是中国也好,如果我们从多样性制度安排视角出发,去理解和发现不同发展道路的经济理性,就可以产生相互借鉴的作用。当然,要注意的是,发展道路选择背后具有经济理性,本身并不意味着,当下的制度选择或安排就是完全合理的,不需要改革或改进。理性和合理是两个概念,理性强调的是行为人在约束条件下个人收益最优的策略选择,而合理更多地要从全社会角度去看个体选择是否实现了社会最优。
总之,不管是政治学、经济学,甚至是人类学的研究中,比较研究方法值得我们长期坚持,新发展译丛出版的这两本书应该说也运用到了这一研究方法。
第二个方面,这两本书以及今天上午报告的三篇论文,提醒我们,要重视国家的治理架构和经济发展的双向互动研究。
学术研究,尤其是经济学研究,很重视识别因果关系,重视把因果关系的方向找出来,是A影响了B,还是B影响了A?有时候,之所以因果关系的识别很困难,就是因为A影响B的时候,B也会影响A,即现实世界中两个因素是相互影响的。当我们想把A影响B的程度有多大给识别出来,就不得不要把反向的作用力控制住。如果两个因素存在相互影响,正如国家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那么,要从长期理解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与发展绩效,就需要关注两者的双向互动。
当我们讨论中国问题、中国发展时,如今天上午张军教授讲的地方分权、还有所谓财政联邦主义带来的地区竞争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更多强调的是治理架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但我们也需要反过来问,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中国的治理架构没有发生变化?难道今天中国的治理机制和30年前是一样的吗?即便有的制度表面上看是一样的,内部的更具体的机制是不是已经发生了变化?
经济发展是否会影响一国的治理架构,就像政治学家利普塞特提出的假说那样,即一国的经济发展会导致民主体制的出现。姑且不讨论这个假说在经验意义上是否得到了检验,我们都要思考: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在何种程度上重塑了中国的治理架构?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又会受到今天这一被重塑过的治理架构多大的影响,以及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影响?这些问题都是我们需要研究、讨论清楚的。
无论拉丁美洲国家、美国、还是中国,当前都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发展问题。美国今天的问题也相当严重。美国国父们建国之初给美国建立的治理架构,两百多年来并不是完全没有变化。过去半个世纪的经济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革命以来的经济发展,已经给美国现有的制度架构提出了严重挑战,这一挑战必然会对其未来制度的演化产生冲击。冲击之下美国制度的调整又会反过来影响到美国未来的经济走向。它会继续保持经济强国的地位,还是会衰败?目前都未可知。尽管福山二十多年前提出了“历史的终结”这样的政治命题,但应该说,并不存在历史终结的问题。
这并不是说美国的现有的制度架构不值得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去借鉴。我这里想强调的是,要理解各个国家的治理架构和经济发展之间的长期双向互动,是一个宏大的问题,需要我们开展细致的研究,写出一篇一篇基于细致研究的论文,帮助我们揭示出其中的规律性,以及不同国家所体现出来的具体的相互影响机制。
第三个方面,如何回答一个我们都关心的问题:回到中国本身,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图景?
今天很多讨论和发言表明,在座的诸位学者都是有情怀的。理论本身是冷冰冰的解剖刀,但学者个人是心怀情感的。我们今天谈的许多问题,包括李寿初教授刚才问的问题,都是充满情感的问题。寿初的问题带有理想主义,尽管从比较的角度,从所谓制度多样性角度,也许并不见得有某个预设的结果在等着中国去实现。因为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未来是由今天的行动和选择所决定,而今天的行动本身就具有各种偶然性和多样性在其中。
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增长速度下调,从过去的快速发展——2007年曾经高达14%的年增长率,到今天只有6%多一点的年增长率。也许大家都想追问,中国经济当前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到底是什么?
上午郑新业院长讲到,中国经济只要继续维持快速发展,很多问题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都会解决。或者说,我们认为反映中国问题的各种指标,随着中国进一步的发展都会下降。所以他认为,坚持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对中国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观点我想在座的各位都不会反对。
然而,当前中国的一个客观现象是,经济增长速度在快速下滑。这就需要我们去追问,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了减速现象?以及,这个下滑会不会持续下去,甚至变得更加严重?
宏观经济学学者很容易对此给出分析,比如说对经济增长做一个分解,即进行增长核算。通过增长核算法,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增长下滑最核心的两个原因,恰恰是过去中国快速发展的两个驱动力正在丧失它们的动能。一个是投资率在下降。随着中国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当供养比越来越高以后,中国的储蓄率会下来,而投资率是取决于储蓄率的,所以投资率下降的趋势恐怕在短时间之内不会发生改变。只要人口结构不发生根本性转变——我相信这样的转变即便有也是慢转变,不可能很快完成,因此,投资率在未来长时段内都是要下来的,这一点我们想改变恐怕也改变不了。
另一个因素是,中国的生产率(TFP)出现了非常大的下调。从1978年到2007年,中国经济每年平均的生产率改进速度并不慢,无论是乐观的估计如3.7,还是悲观点的2点多,在全世界来讲已经是相当高的。可是,现在不同的研究都发现,中国的生产率增长速度已经掉到只有1点几不到2了,几乎砍掉了一半。而且生产率的下降还会阻止外部投资进入。
政策建议由此似乎不难得到:要继续维持中国经济较快的增长速度,就要提高生产率!刚才已经有人批评了这种过于直观的政策建议。因为问题在于,为什么生产率会发生这样的不利变化?决定生产率改进的一个因素是技术进步,另外,资源误配也会严重影响一个经济体的总体生产率。根据谢长泰等人的研究,中国经济中存在严重资源误配,并且这也的确拉低了中国经济的效率。但是,资源误配是我们认识上的错误导致发生错误投资,还是说,这种误配的结构本身是中国已有的治理架构、已有的经济政治架构所内生出来的呢?
譬如说,中国现有的某些治理架构,其存在的目的就是创造租金,并且把这个租金授予给社会中掌握力量的人,让他们不要滥用暴力,从而不要回到丛林社会——因为相比让某些人得到更多好处的体制,丛林社会更加糟糕。就像《产权的政治学》一书中所描绘的迪亚斯时代的墨西哥的体制一样,它通过构建所谓的垂直政治联盟这种分租体制,让某些社会的强势力量不捣乱不滥用暴力,让大家有更稳定的预期,由此就可以实现持续的经济发展。
大量研究表明,中国的国有企业生产效率更低,过多的国有企业恶化了中国的生产率,拉低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那么,为什么国有企业没有退出?尽管我们一直在强调低效率的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僵尸企业——要退出。按照前面的分租理论,它们没有退出这一现象就是内生的,内生于某种有利于分租的治理架构。为什么当前中国很多改革举步维艰?恐怕这也是内生于既有治理架构和利益结构的。
地方分权体制之下,中国改革前30年取得了非常好的发展,而今天,为什么这一治理架构开始不利于提高生产率和经济发展?这是当前需要我们展开深入研究的问题。不破解这一问题,我们就无法从根本上找到改进中国经济生产率的有效办法。
我个人对此的观点是,前30年前的发展模式,是一种从中央的政治领导人,到地方官员,再到企业家等各方能够实现利益兼容的发展模式,即包容性发展模式。邓小平提出来发展是主旋律,中国要以经济建设替代过去阶级斗争的路线,这是中央定下的基调。但是,中国是一个大国,即便在计划体制下,也是分权式计划体制,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是比较弱的。要实现经济建设这个目标,最高领导人必须依赖于中国各个层次大大小小的地方官僚去落实。
那么,为什么各个层次的地方官员愿意落实经济发展的目标?原因在于,不管官员从自身晋升的角度来说需要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还是从个人利益的角度出发试图实现最大化的私人收益,在改革之初,他的最优选择策略都是:把最优秀的企业家挑选出来,并且将有限的公共资源服务于这些被选中的企业家。因为只有这样,地方官员才能够利用既有的资源创造出价值最大的企业家租金。也只有如此,无论中央税收还是地方税收,还是地方官员的货币利益,还是企业家自身能够留下来的租金,才能得到最大可能的保障。这就是许成钢教授所定义的这种“政治集权、经济分权”的分权式威权体制,在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所带来的一个奇妙的结果。
在“新发展译丛”的序言中,我们把这种情况称为是一个巧合:中央、地方和企业家追求的目标居然是一致的。所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既有的治理架构和经济发展之间一度形成了良性循环的关系。
这种通过分配企业家租金进行激励的治理架构,今天正在受到极大挑战。一方面,因为供给短缺而形成的套利租金,在随着市场本身的发展而逐渐枯竭,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更多创新的因素加入进来。这个局面对于企业家、地方官员和中央政府都提出了不同于过往的要求:企业家需要发挥熊彼特意义的创新才能,而地方和中央政府需要构建更有利于技术创新的政策环境,而不仅是帮助企业家进行物质资本投资。
另一方面,过去的治理架构所形成的政商关系又会产生路径依赖效应:第一个发展阶段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已经和地方官员结成了政治关联,必然影响政府的下一步政策,譬如是不是要进一步开放市场?因为进一步开放意味着允许潜在的市场进入者挑战在位企业家。这种潜在的挑战会不会被允许?或者说,在潜在更有效率的企业家和在位企业家之间,地方官员会如何进行权衡取舍?如果权衡区舍的结果是保护在位企业家,那么,这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会带来何种影响?中央政府应采取何种改革措施来改变治理架构,以便在中国更好地促进创新?
中国现有的治理架构对下一步经济发展的各种要求——无论对创新还是更大程度的市场开放——显示出严重不适应性。治理架构转型的诉求已经提上议事日程,而转型的方向、路径及未来可能的选择却充满着巨大不确定性。就像《产权的政治学》一书里面所讲到的,迪亚斯时代的墨西哥所形成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治理架构作为一种策略均衡,并未根本上形成对权力的制约,也没有带来经济发展成果的普惠性分享,最终扼杀了墨西哥长期的经济增长。中国今天也面临着类似情形。因此,能否主动及时地进行治理架构的转型,这是决定中国能否避免陷入发展陷阱的关键因素。
下一步,中国的治理架构会朝着哪个方向转变?是转向强化中央权威的威权体制——目前似乎有此迹象、还是转到可问责的有限政府模式?还是说能够找到约束权力的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同样可以解决政府承诺的可信问题,从而中国的企业家和个人在稳定的预期下,愿意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技术研发,产品创新以换取未来的回报。如果治理转型不成功又将如何?一旦社会达不成可以获得创新收益的稳定预期,那么,我们所想象的那些改善中国经济生产率的行动就难以发生,中国经济当前所面对的巨大困难也就无法消解,经济增长速度就必然会进一步下滑。
从长远计,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学界进行深入而有成效的研究,从而得到更有价值的政策考量。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天开了一个非常好的会议。再次感谢在座的诸位专家和朋友来参加会议,感谢大家对汇智基金会所给予的支持,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