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而知新——周伟洲《汉赵国史》评介
一
周伟洲先生是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资深教授,同时兼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顾问、名誉会长,中国民族史学会顾问、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顾问等诸多重要学术职务。作为知名历史学家,周伟洲先生在中国西北地区历史,尤其是中国西北地区非汉民族史上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此外,以本书《汉赵国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为代表,周伟洲先生就五胡十六国时代的历史也有相当丰富的研究。《汉赵国史》初版于1986年(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作为“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丛书”的一种再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此次的第三次出版,则是作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策划的“十六国新编”书系中的一册隆重推出。
本书由正文八章、附录四章及前言、后记、索引构成。第一章至第六章,作者以汉末至前赵灭亡的时代顺序,讨论了汉赵国(刘渊所建汉国、刘曜所建赵国的统称)及相关诸问题。第七章、第八章则分别讨论了汉赵国的政治制度与社会形态。附录为三张表格、一篇论文,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书中内容。相比旧版,此次新版增加了《附录四:十六国官制研究》与索引。在此兹录目次如下,以便读者概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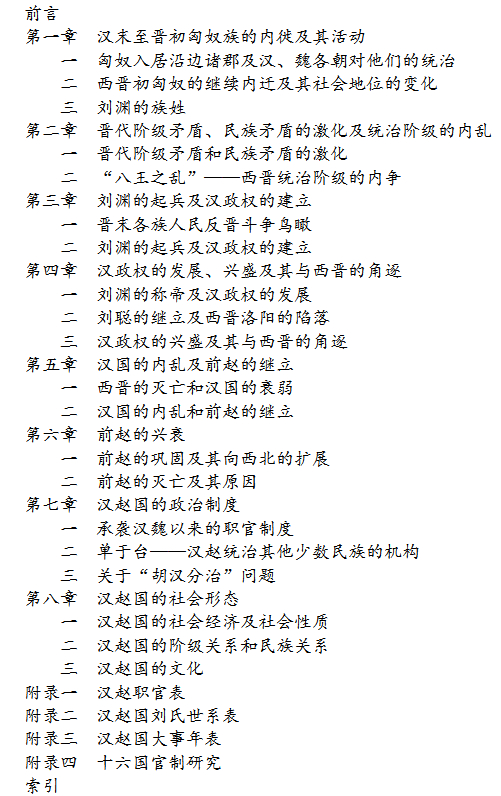
日本方面五胡十六国研究的学术史,三崎良章先生在其《五胡十六国の基礎的研究·序论》(汲古书院,2006)已有详细总结,在此略作概述。日本的五胡十六国研究,以志田不动麿先生1931年发表《五胡十六国史概説》(《史学雑誌》第42卷第7号,1931)为开端。此后,内田吟风的《後漢末期より五胡乱勃発に至る匈奴五部の情勢に就いて》(《史林》第19卷第2号,1934)及《五胡乱及び北魏に於ける匈奴》(《史林》第20卷第3号,1935)、宫川尚志的《晋の太山竺僧朗の事跡——五胡仏教に関する省察》(《东洋史研究》第3卷第3号,1938)、池内宏的《晋代の遼東》(《帝国学士院紀事》,第1卷第1号,1942)等成果相继问世,展开了一系列五胡十六国时期的相关研究,但五胡十六国只是其中涉及的研究对象之一,这一时代本身并没有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目标。
1950年以后,田村实造、谷川道雄分别以《中国史上の民族移動期——五胡・北魏時代の政治と社会》(创文社,1985)和《隋唐帝国形成史論》(筑摩书房,1971)为代表作,不断展开以五胡十六国作为对象的研究。接着,饭塚胜重、大泽阳典等学者针对五胡十六国中的某一国家历史继续推进研究,代表作如饭塚胜重《慕容部の漢人政策についての一考察》(《白山史学》第9号,1963)、大泽阳典《李農と石閔》(《立命館文学》第386-390合并号,1977)。另一方面,同时期还有前田正名的五胡十六国历史地理研究,1979年,其《平城の歴史地理学的研究》由东京风间书房刊行。总之,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日本的五胡十六国史研究逐渐深入、精细。无法一一列举的研究还有很多,相关研究史的梳理,可以参考前述三崎良章的著作,以及关尾史郎的《日本的五胡十六国时代史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回顾与探索——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九届年会论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9)。
1986年《汉赵国史》一书的出版,使得中国的五胡十六国史研究与日本一样,在同一时期进入了以某一国家为对象的精细化研究。事实上,本书也引用了谷川道雄先生的研究成果,由此亦可见中、日学界五胡十六国史一同深入、发展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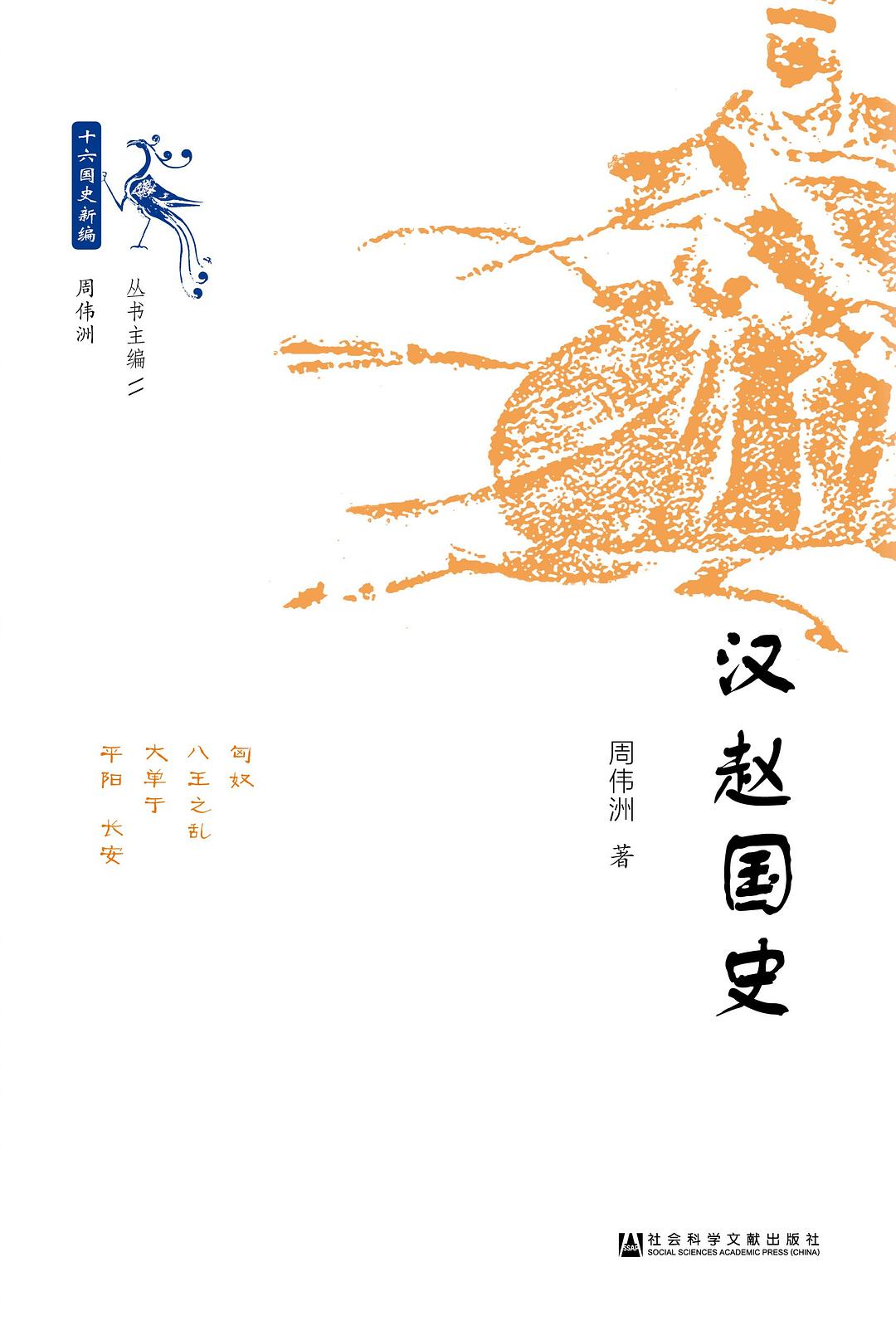
三
自1986年出版以来,《汉赵国史》作为五胡十六国研究的经典著作,为学界所广泛参考。由于史料的缺乏,五胡十六国的研究存在相当的困难。事实上,本书中也存有不少“资料缺乏,不可详考”的叙述。然后,即便在这样的状况下,作者依然通过各种方式来综合联系史料,以展开论证研究。
例如,《晋书》卷一〇三《刘曜载记》中有“休屠王石武”。关于该人物,作者利用《王真保墓志》,得出了与此前理解的“休屠王”名“石武”所不同的结论,认为应当理解为“休屠”的“王石武”。此外,关于前赵政权的游子远,文献中并没有类似列传的集中记载,考述其事迹相当不易。作者则充分勾稽各种文献记载,指出他是前赵政权中的重要人物。
尽管以《汉赵国史》为书名,但作者的考察对象触及汉代以来的匈奴人群与魏晋社会,以多角度的视野对汉赵国史展开研究。在这里,笔者想要特别加以关注的,是作者对支撑汉赵政权的诸种人群的相关见解。
作者认为,早先归降汉朝的匈奴人逐步汉化,从畜牧经济转为农耕经济。进入魏晋时代,部分汉化的匈奴人,以及部分乌丸、鲜卑等非汉族群成为了编户民,缴纳赋税。同时,汉赵国设置的单于台负责管理以部落组织为基本单位的非汉族群,即管理尚未汉化的非汉族群。
如此一来,汉赵政权治下的民众大体分为两类。一类为编户体制下的汉人与汉化的非汉族群,这些人群的经济生产方式主要是农耕。另一类则是以游牧、畜牧为经济生产方式的非汉族群,他们由单于台负责管理。在这里,不同的经济生产方式受到了作者的重视。例如书中指出,即便同为匈奴人,由于经济生产方式的不同,有一些并不在单于台的管辖范围内。
作者还指出,同样的状况也存在于军事方面。毫无疑问,由单于台管理的非汉族群所构成的军队,是汉赵政权的主力部队。但另一方面,汉人、编户、坞壁居民,都有被动员为士兵的情况,他们也是汉赵政权的重要军力。这一点,汉赵与同为五胡政权的南凉(鲜卑秃发部所建)存在很大不同(作者关于南凉政权的整体见解,另可参见《南涼与西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言,南凉政权由鲜卑秃发部负责军事,汉人及其他非汉族群负责为国家提供财政支持。在这里,作者注意到了南凉政权中鲜卑秃发部的族群自觉意识以及他们与其他族群之间存在的明确界限。而在汉赵政权中,虽然也通过单于台区分汉人与“六夷”,同样展开“胡汉分治”,但本质与南凉政权明显存在极大差异。笔者认为,这是本书作者一个极为重要的见解与视角。
包括五胡十六国在内的魏晋南北朝时代,非汉族群的活跃是学界聚焦的重要历史面相。本书作者不仅仅以族群为单位,更着眼于经济生产方式,对当时非汉诸族群的实际状态展开考察。当然,族群问题自不应轻视。但如果过分强调族群的作用,就可能会不慎得出与史实相乖离的结论。就这一点而言,本书作者关注非汉族群的经济生产方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如上所述,本书通过有效的研究方法得出了诸多结论,并为学界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视角。其所具有的重要学术价值,不言自明。实际上,该书反复再版的事实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当然,全无疑问的研究是不存在的。同样作为五胡十六国史的研究者,笔者对书中内容也存有若干疑问之处,在此试加列举,作为书评的最后一部分。
四
首先是一个小问题——关于“陕东伯”一词的解释。在第七章中,作者列举汉赵政权的爵位,将石勒就任“陕东伯”作为伯爵的相关事例。不过,笔者认为,陕东伯的“伯”,并非伯爵之意。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当时石勒还持有上党郡公的爵位。据《晋书》卷一〇四《石勒载记·上》等文献,石勒于公元312年7月被刘聪封为上党郡公,公元315年9月封为陕东伯。此外,公元318年7月,刘聪下诏擢升石勒官职时,诏书中有“公如故”一句,说明石勒一直持有公爵爵位,即上党郡公。则石勒被封陕东伯时,同时兼有上党郡公之位。如果“陕东伯”是伯爵,那么石勒就同时拥有公爵、伯爵两种爵位,这显然很奇怪。举例而言,据《宋书》卷九七《高句丽国传》,高句丽的长寿王在被刘宋政权册封时,“以琏为使持节、都督营州诸军事、征东将军、高句骊王、乐浪公。”可知高句丽王同时兼有乐浪公之位。尽管历代的高句丽王同时被中原王朝授予乐浪郡公的名号。但正如笔者曾经指出的那样,高句丽王是为支配高句丽地区而自称的名号,郡公则是中原王朝序列的爵位,两者共存,但分属不同系统。如果高句丽王本人被纳入中原王朝的爵位体系中,就相应地被授予郡公之爵。说到底,“高句丽王”并非中原王朝爵位序列中的王爵。因此,同一王朝的同一人物,无法同时持有两种不同等级的爵位。
王安泰先生曾指出,“陕东伯”并非五等爵中的伯爵。(《再造封建:魏晋南北朝的爵制与政治秩序》,台大出版中心,2013)笔者亦曾将“陕东伯”理解为类似于“霸者”的特殊称号(《後趙建国前夜——匈奴漢国家体制試論》,《立命館東洋史学》第41号,2018)。总之,将“陕东伯”视为伯爵,可能存在一些问题。
另一个疑问点是作者对靳凖之乱时北宫纯等晋人动向的解释。作者将晋人与靳凖的相互对立理解为胡汉间尖锐矛盾的体现。关于此事,《晋书》卷一〇二《刘聪载记》记载如下:
(靳)凖自号大将军、汉大王,置百官,遣使称藩于晋。左光禄刘雅出奔西平。尚书北宫纯、胡崧等招集晋人,保于东宫,靳康攻灭之。凖将以王延为左光禄,延骂曰:“屠各逆奴,何不速杀我,以吾左目置西阳门,观相国之入也,右目置建春门,观大将军之入也。”凖怒,杀之。
这条材料叙述了靳凖政变后各方的反映。又关于此事,《资治通鉴》卷九〇“晋元帝大兴元年(318)八月”条记载得更为详细:
(靳)凖将作乱,谋于王延。延弗从,驰,将告之;遇靳康,劫延以归。凖遂勒兵升光极殿,使甲士执粲,数而杀之,谥曰隐帝。刘氏男女,无少长皆斩东市。发永光、宣光二陵,斩聪尸,焚其宗庙。凖自号大将军、汉天王,称制,置百官。谓安定胡嵩曰:“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今以传国玺付汝,还如晋家。”嵩不敢受,凖怒,杀之。遣使告司州刺史李矩曰:“刘渊,屠各小丑,因晋之乱,矫称天命,使二帝幽没。辄率众扶侍梓宫,请以上闻。”矩驰表于帝,帝遣太常韩胤等奉迎梓宫。汉尚书北宫纯等招集晋人,堡于东宫,靳康攻灭之。凖欲以王延为左光禄大夫,延骂曰:“屠各逆奴,何不速杀我,以吾左目置西阳门,观相国之人也;右目置建春门,观大将军之入也!”凖杀之。
笔者认为,将上述史实视为由汉人对抗胡人所呈现出胡汉矛盾,似乎不太合理。上引史料记载了靳準政变及此后的政治情势。如史料所见,汉人大臣都站在了靳準的对立面上。特别是出身豪族安定胡氏的胡嵩拒绝靳準将传国玺归还东晋政权的提议,这点尤为重要。这说明,当时汉赵政权内部存在反对靳準归顺东晋的汉人。对于篡夺匈奴刘氏政权的靳準,他们也持对抗的态度。此后,居住首都平阳之外的刘曜、石勒起兵讨伐,靳準政权很快便土崩瓦解。在汉赵政权内部,靳準得不到胡(如刘曜、石勒等)、汉(如胡嵩等)两方面大臣的支持,失败也就在所难免了。
基于此,再次观察上引史料,如果北宫纯的行动理念是“汉人对抗胡人”的话,那么前后相关的史料记载与他们的行为准则似乎存在较大差异。并且在北宫纯起兵之前,靳準已经提出了要归顺东晋政权。当然,无论如何,北宫纯等晋人针对靳準起兵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
基于上述史实,作为靳準政变后的系列事件之一,仅仅基于“胡汉对立”的角度来理解北宫纯等人的动向似有不妥。再联系到胡嵩、石勒等人的行为,毋宁说当时胡人、汉人中都有针对叛乱者靳準的反抗,这应当是北宫纯起兵的背景所在。至于北宫纯“招集晋人”一事。考虑到他作为西晋降将的身份,以其自身的影响力所能够动员的大概也只有“晋人”。因此,将北宫纯的行为与胡、汉间的对立联系在一起,或许并不合适。
更进一步而言,还可注意到,北宫纯等人来历不明,不排除是非汉族群的可能。据《晋书》卷八六《张轨传》,北宫纯原属西晋凉州刺史张轨,是张轨派出增援西晋王朝部队的将帅。不过,汉赵政权在西晋与汉赵的对抗中获得胜利,于是北宫纯最终投降了汉赵政权。据《元和姓纂》卷一〇“北宫”条,北宫是春秋时代就存在的汉姓,北宫纯有可能是汉族。另据《后汉书》卷八《灵帝纪》等材料,东汉时代也有名为北宫伯玉的“义从胡”。换言之,仅仅从姓氏上很难确定北宫纯的种族。就史料记载而言,北宫纯出身不明,具体族属也因此难以确定。
以上,笔者对本书内容加以梳理,并提出了若干感受与意见。由于学力浅薄,其中不免有许多误解、误读之处,恳请作者一定海涵。《汉赵国史》一书,不仅仅是汉赵国史研究,也是五胡十六国史研究、乃至于魏晋南北朝非汉族群问题研究不可或缺的先行成果,重要性不言而喻。此次重新出版,也必将获得更多读者,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笔者也衷心期待五胡十六国史的研究不断发展,日趋兴旺。
附记:本书评原系日文撰写,由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的陆帅老师译为中文,在此谨致谢忱。当然,书评中存在的错误完全由笔者个人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