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该如何理解经典作品中那些“三观不正”?
什么是经典?刘知几说:“自圣贤述作,是曰经典。”这里经典代表着权威性和典范性。美国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认为经典作品应该具有“陌生性”,即杰出的创造性,这种创造性“要么不可能完全被我们同化,要么有可能成为一种既定的习性而使我们熟视无睹”。他更强调经典无与伦比的审美价值。
两种表述或许并不冲突,后世的典范往往来自于前代杰出的创造。关于“经典”,我们也许给不出一个准确的普适的定义,但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能被称作“经典”是一部文学作品无上的荣耀。那么,“经典”是否象征着最高的正确?经典中是否有一些令人难以接受的段落,或许在今天会被看做“三观不正”呢?
莎士比亚、《驯悍记》与《李尔王》
莎士比亚在西方文学史上的地位自不待言,“没有莎士比亚就没有经典……没有莎士比亚,我们就无法认知自我”,哈罗德·布鲁姆以此论证莎士比亚在西方经典文学中的地位。《哈姆雷特》、《麦克白》等悲剧作品,对心灵的恢弘与深邃的挖掘上罕有其匹。然而也并不是每一部莎剧都在这样探索语言与思想的极限,甚至有时会让人有些迷惑,你几乎分不清是讽刺,还是仅仅充满欢欣地拥抱庸俗。

《驯悍记》就是这样一部作品。故事开篇营造了两个截然相反的女性,一个是符合那个时代审美的温柔贤惠的贝恩卡,一个是贝恩卡的姐姐凯瑟琳娜,性格与妹妹相反,是“恶鬼一样的脾气暴躁的贱人”。想要向贝恩卡求婚的男子自然很多,然而姐妹俩的父亲巴普提斯塔先生要求必须等到姐姐出嫁,才会考虑那些妹妹的求婚者。几个求婚者一筹莫展,谁也不想向彪悍的姐姐求婚。
粗鲁又势利的“绅士”彼特鲁乔看中了姐姐的财产,欣然接受了求婚的任务。他为了“改造”凯瑟琳娜彪悍的性格,表现得比凯瑟琳娜更加粗鲁,更加暴躁,他强迫凯瑟琳娜在寒冷的天气和他一起骑马回家,凯瑟琳娜中途落马,又湿又冷,也不予以同情;不让她闭眼睡觉,每当她昏昏欲睡,就大声把她吵醒;在她面前摆上一道道美味菜肴,却又故意不让她吃。这些暴力最终使得凯瑟琳娜变得十分温顺,在结尾长篇大论,宣誓般地说:“只要我的丈夫吩咐我,我就可以向他下跪,让他因此而心中快慰。”

《驯悍记》创作的时代,女性的地位比今天低得多,完全是男性的附庸。莎士比亚的这部剧反映了那一时代男性对于女性的压迫。然而,似乎看不出这部剧中有什么严厉的批判或深刻的反思,甚至原本应有的思考也在闹剧一般的嬉笑怒骂中消解了。作者对于“驯悍”这一社会现象态度是暧昧的,仿佛仅仅将“驯悍”看做一件好笑的事儿。作者的态度尚且模糊暧昧,就更不能指望那个时代的观众们有什么超越性的思考了。这部剧似乎仅仅是为了博人一笑而存在的——它“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怪不得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会认为这部剧的最后一幕是“对女性和男性的彻头彻尾的恶劣冒犯”。
如果说《驯悍记》尚属莎士比亚早期不太成熟的剧作,因而道德上的“瑕疵”似乎可以理解的话,另一部剧作《李尔王》似乎很难逃脱这样的指责。《李尔王》是莎士比亚后期悲剧的代表作之一,艺术成就和思想深度都代表着莎剧的高峰。但即便是《李尔王》,在道德上也难逃被诟病的命运。

在那些诟病之中,最出名的当属另一位文豪托尔斯泰在他的《何为艺术?》中对于《李尔王》道德性不足的批判。他认为《李尔王》的故事缺乏道德和宗教力量的支撑,价值上不够崇高。
托尔斯泰做出这样的评价,似乎完全是合情合理的,他一生无论思想还是作品,都在锲而不舍地追求那样一种宗教和道德上的崇高,自然会对缺乏这些要素的作品嗤之以鼻。
但另一方面,《李尔王》的故事也确实让人在道德上感到沉重。《李尔王》是一个宫廷悲剧,英王李尔由于听信了口头的花言巧语,将原本打算分给三个女儿的土地分给了两个善于阿谀奉承的女儿,冷落了沉默但忠诚的三女儿。两个女儿拿到土地后很快露出了绝情的真面目,将老父放逐。
另一条线是葛罗斯特的家庭悲剧。庶子爱德蒙是典型的利己主义者,为了父亲的爵位先后陷害了哥哥和父亲。
故事的结局十分悲惨,出场的人物几乎无一幸免。尤其是象征纯善的三女儿考狄莉亚突兀的死,让很多读者无法接受。有论者曾经评价道:“我在多年前即对考狄莉娅的死深感震惊,后来直到我作为一名编辑去修订剧本时,我还不知是否能忍受再次阅读剧本最后几场的痛苦。”莎士比亚在这部剧中将爱德蒙的恶纤毫毕露地展现了出来,然而却并没有给人以希望,三女儿考狄莉亚的死亡让人深感故事中隐含的虚无与绝望,善在这部剧中,并没有被赋予哪怕一丝高于恶的地位,死亡面前,它们一律平等。
而这也正是托尔斯泰们无法接受的一点,善怎么能与恶平等呢?
该如何理解这种“三观不正”?
这种经典作品中的“三观不正”,也不仅存在于莎剧中。《包法利夫人》中,包法利夫人屡次背叛婚姻,《红与黑》中于连的爱情故事的开始是一次通奸,“垮掉的一代”的小说中充满了吸毒、滥交与灵魂堕落,日本文学中不乏挑战伦理的禁忌爱情,这些在卫道士们看来,似乎都是不能忍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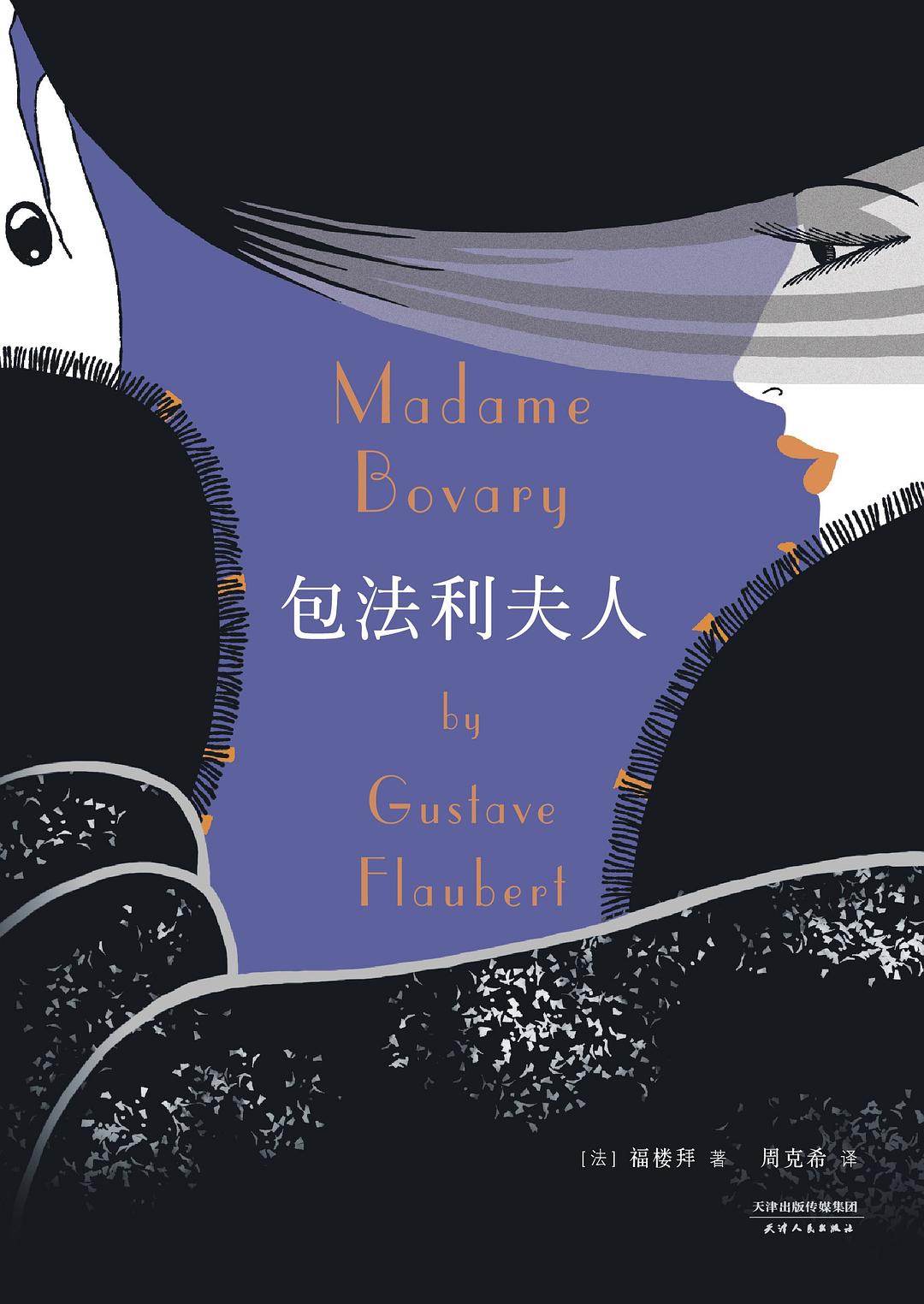
我们该如何理解经典作品中的这些“三观不正”呢?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经典并非从天而降的,很多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地位的确立都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莎士比亚在世时的名声并没有高出同时代的剧作家马洛很多,但现在谁还知道马洛?如今我们听到经典二字,就会联想到高不可攀的东西,但经典作品最初往往也只是流行文学。比如莎士比亚创作戏剧是为了演出,自然要考虑观众的感受,如《驯悍记》这样的作品,何尝不是为了取悦观众而产生的呢?我们无需过度拔高这些娱乐之作的地位,莎剧固然有超越时代的永恒价值,但也并不是脱离时代的美丽空中楼阁。
有时“三观不正”的确会严重破坏作品的价值,诸如我国古代白话小说中那些对于“齐人之福”的欣羡。然而有的“三观不正”却恰好反映了时代的病征,甚至促进了风俗的进步。《包法利夫人》在出版之初曾被指为淫秽之作,甚至被告上法庭。如今我们发现,包法利夫人的悲剧,恰恰反映出那个时代流血的资本和陈腐的偏见对于女性的压迫。包法利夫人的爱情越来越不被视为是背德的,反而越来越多地被看做对自由爱情的纯真向往。

此外,道德评判也不必成为评价文学作品的核心标准。在道德上完美无瑕的作品,并不会因为其“正确”而获得崇高的赞誉,相反,往往是“错误”的作品能够击中读者的灵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作《罪与罚》中,信仰的崇高一点也不比罪恶的合理更具说服力,我们真切感到灵魂的震颤,正是因为体会到了深藏自身灵魂之中的罪恶。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因为他最终倒向信仰的崇高而变得伟大,使他变得伟大的是他在强大的恶与崇高的善之间的挣扎。托尔斯泰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终选择信仰与莎士比亚在善与恶面前的模糊立场同样伟大,因为他们并没有为了追求一种“正确”而掩盖恶的合理,而这正是文学作品最高的真实。

正如哈罗德·布鲁姆所言,“西方最伟大的作家们颠覆一切价值观,无论是我们的还是他们的”,我们不应奢求从经典作品中获得什么道德警训或是人生指导,也因此不必让道德绑架文学。文学首先应该是基于文本的审美活动,随后才可以被附加多元的内涵。
【参考书目】
1.《西方正典》,【美】哈罗德·布鲁姆/著 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6月版
2.《莎士比亚全集》,朱生豪 等/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4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