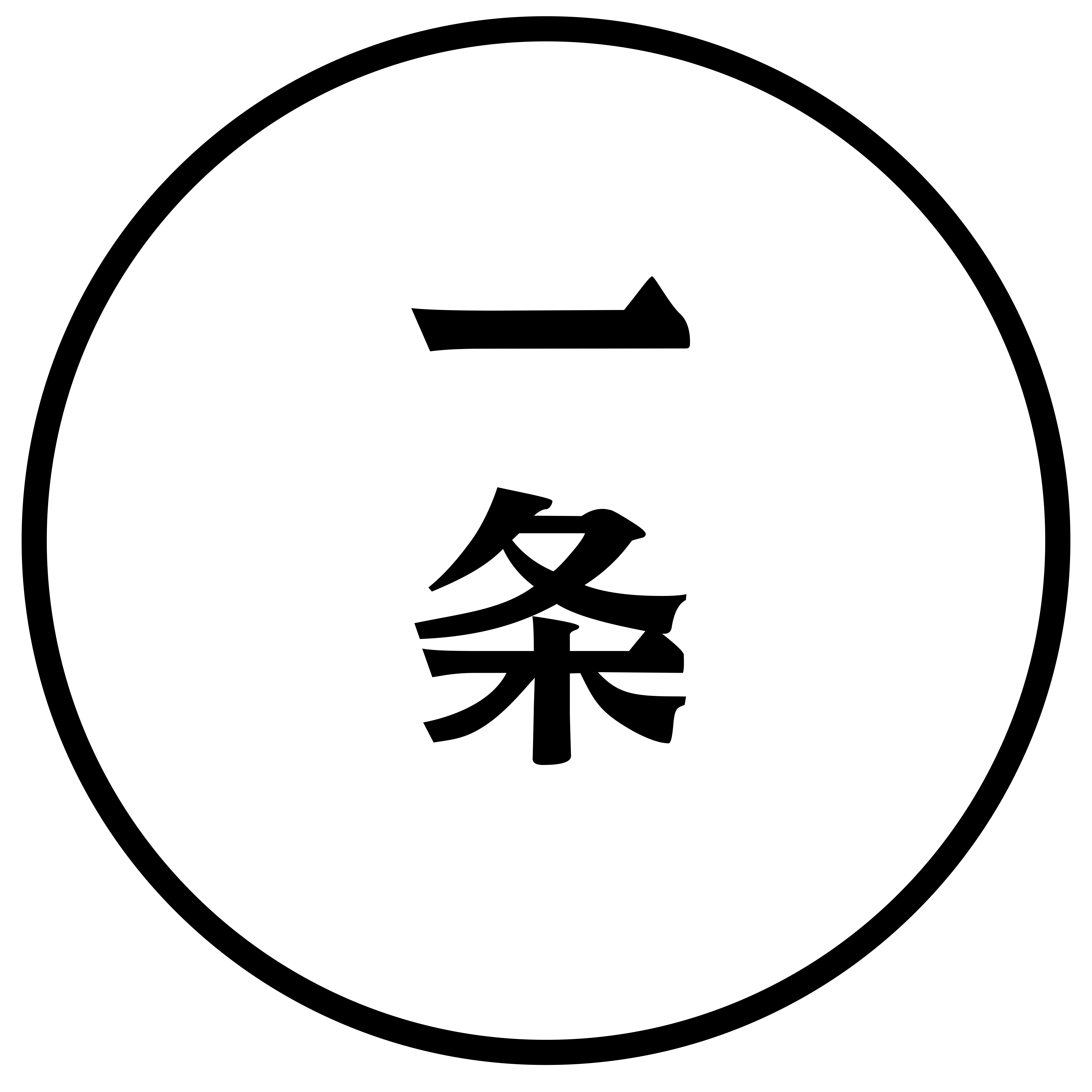中国的这些年轻人们,是如何理解“性”与“爱”的关系的?

要么被“婚姻”安排,要么被“爱情”支配。
但随着性革命的发生,
中国人的性开始变得越来越独立了。
性社会学家潘绥铭教授的学生,
社会学博士王文卿
从2006年开始研究“性爱分离”问题,
今年4月,他推出新书《性·爱·情》
对50位知识青年进行了深度访谈。

都受过或者正在接受高等教育。
他觉得这些中国知识青年
对性和爱情之间的断裂更加敏感,
他们是如何理解“性”与“爱”的关系的?
他们又是如何实践的……
自述 王文卿 编辑 倪楚娇


春泥说她是“一种比较分裂的状态”,一半很传统,一半非常叛逆。我的印象中她个子不高,不爱打扮,长得挺秀气的女孩。她特别爱看恐怖片,也常看A片。从外表上看,反差挺大的。
春泥谈了好几个男朋友,基本都发生过性行为,有些是被强迫的。她和男性交往的时候不会特别强调性别的界线,经常和异性有一些亲密的接触,其中一个前男友就非常生气,所以就分手了。
春泥小的时候,遭受过她爸爸朋友的性侵,也见过路上有一些露阴癖。但是这和她分裂的状态有什么关系,我觉得也很难看清楚。
在访问春泥的时候,她正和一位50多岁的研究生导师保持一种秘密的关系。
“这种关系补偿了父爱,这种跨越年龄段的……你说恋情,也勉强可以,是我以前很鄙视的一种感情。”

“我们俩已经心照不宣地定下游戏规则,就是相互不牵绊。任何一方想退出,随时可以退出,绝不纠缠。”
春泥说她终究要结婚的。在结婚之前,要痛快地玩几年。
她把自己定位为一个男性,要追求事业的成功,家只是一个休息的港湾,丈夫是要给她服务的。“性”对她来说,似乎也变得像对男性来说一样。有过第一次之后,后面的就变得无所谓了。她觉得,这种男女角色的颠倒“挺委屈将来和我结婚的人的”。
她对于“性别权力”挺关注的,虽然觉得自己很难真的抗拒它,但至少还不想这么快去顺从现有的性别体制。

晴雪是个大城市的女孩儿,家庭环境不错,爸妈是开放的教育方式,不怎么去管她。父母之间也相互不干涉对方,都给对方充分的自由。
她和一个外地的男生建立了开放式的关系。当时男生在国外留学,在国外和国内各有一个女朋友,而晴雪也有男朋友。两个人都很清楚这些情况,不需要遮掩。“只要我俩在一块儿高兴,只要他能陪着我,我管谁给他打电话,谁给他发短信呢。”
没想到的是,这种相互约束更少的关系反而是最稳定的。“后来我也分手了,他也分手了。但是,我们俩还是没在一起,我也找了个新的,他也找了个新的。反而发现我们俩好像在一起时间比较长,而且也不用换或者不换,最多可能他不想联系我了就不联系我了,我不想联系他了就不联系他了。反正就是不可能在一起。因为知道不可能,所以不难过,也不伤心,也不会做出努力非要跟他在一块儿。”

如果投入到一段感情当中,她认为会更容易受到伤害。她就在那儿想:“他怎么还不给我打电话呀?他现在怎么样呀?”她觉得自己被别人控制了,而别人又不受她控制,所以她就进入了一种无力的状态,她不希望这样。
她有很多能够发展为恋爱关系或开放式关系的潜在交往对象,也就是“备胎”。“我觉得备胎多一点儿,不管有什么事,自己也好受一点。……我觉得,我分手之后,肯定也不会太难受啊,反正后备力量那么大。”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是,你会觉得晴雪已经很开放了,但是反而在“性”方面,她还是被动的。只要男性提出要求,她不反感,稍微有点儿感觉,她就能接受。但她从来没有主动去提出过要求。
“工作比婚姻靠谱,但婚姻比工作重要。”她觉得婚姻是“女人第一大事业”。她倾向于把婚姻和爱情理解为一种位置,这个位置很重要,至于谁来占据这个位置则不那么重要。

思瑗是绝对爱情至上的那类姑娘。“人脑子里不能完全想性,那就成了纯动物了。人和动物唯一的区别就是,人有情感,动物没有。人是性爱加爱情,才是情爱。动物是纯粹的性爱。”
思瑗有一个比她大14岁的男朋友。男友有家室,很富有,而且性经历非常丰富。这给了她前所未有的性快感,是她之前的初恋男友所不能比的。思瑗无法让自己不去喜欢他。
但是理性又告诉她,她不能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他老婆是癌症,没有那种生活,子宫什么的都切除了,随时会有癌细胞转移。我不能天天盼人死啊,这个太坏了,我不能这样做。等个3、4年吧。如果没有结果,我就随便找个人结婚。”
思瑗是被“爱情”拽入这段情感的,她很无奈,能做的只有等待。


我今年39岁,出生在河南的农村。小时候为了减轻家庭的压力,被迫去了中等师范专科学校。但我还是铆足了劲学习,一心想通过保送生考试上大学,最后终于得偿所愿。后来,我报考中国人民大学的社会学硕士和博士,跟着潘绥铭教授研究“性”。这才是我自己的选择。
潘老师认为,在中国社会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性和爱情的关系。他在很多研究中都考察过这个问题,包括几次具有全国代表性的问卷调查。但他认为还不够。问卷调查尽管重要,但是它不能说明所有问题。我们必须要去倾听“过日子”的普通人发出的声音。
所以我这个研究,是基于50多个普通人的深度访谈,被访者的年龄在19到41岁之间,都受过或者正在接受高等教育。这类“知识青年”对性和爱情之间的断裂更加敏感。
我想看看,普通人是如何理解“性”与“爱”的关系的,他们又是如何实践的。

“性、爱、婚”这三者的统一是非常主流的看法,但在中国的历史其实并不长。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整体上看的话,“浪漫爱情”并不存在。潘绥铭老师提出,那时夫妻之间更多的是“夫妻恩爱”,“恩”还排在“爱”的前面,和现在所说的“爱情”是很不一样的。性是默认会发生在婚姻之中的。婚外性并不罕见,也没有被看成是一个问题。
五四之后,这三者的关系就变了。随着西方浪漫爱情观念的传入,自由恋爱成了婚姻的基础。这三者的顺序变为,有了爱情才有婚姻,然后才有性。
性,一直处于附属的地位,人们倾向于寻找一个更高位置的原则,并根据它来安排“性”。

最先打破的是婚姻与性的关系。
根据潘绥铭老师的四次全国调查结果,就男人而言,婚前守贞的比例从2000年的57.2%降到2010年的46.0%,再降到2015年的约1/4;就女人而言,婚前守贞的比例从2000年的70.1%降到2010年的57.3%,再降到2015年的约1/3(数据综合了《性之变: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和潘老师博客中的相关数据)。


就像潘绥铭老师说的,其实在目前,抑制着“性自由”的思想力量,既不是孔孟之道,也不是精神文明,而是爱情,是从五四以来就一直深深植入中国人心中的浪漫情爱。
自从1991年开始,潘老师做了6次中国大学生的性关系与性行为的调查。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提问就是:“在性方面,无论你现在做到了哪一步,你为什么没有继续做下去?究竟是什么阻止了你?”答案最主要的就是一个:“双方的感情还没到那一步”;也就是说,爱情还不足够。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21世纪,虽然有所减少,但是仍然占据主流。
像我这本书中的案例,对思瑗而言,指导她们行为的,并不是所谓的“正当”关系,她们更加看重“有没有爱情”。

在我的书中,有一个叫筱清的女孩。她的初恋男友出于所谓的江湖哥们儿义气,把她让给了所谓的“大哥”,并且彻底斩断了和她的联络。在等了几年之后,因为感到复合无望,筱清与一个刚刚认识一周并且只见过两面的男孩发生了性行为。
事后,她一度想得很开,觉得性和吃饭没有区别。但之后,她又回到了保守状态,觉得性不仅应该发生在爱情之内,而且只有在碰到让她“特别心动”的人之后才可以。
晴雪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她之所以围绕“感觉”来安排自己的性生活,实在是因为爱情的幻灭,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而这样一来,关系和性就失去了排他性,从而导致开放式关系的诞生。
2006年,我在博客上搜索以“性与爱”或者“爱与性”为昵称的博主,发现只有18个。而这个数字在2018年,变为了861个。由此可见,性与爱的关系已经成了大家日常思考的问题,也是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的选择。

“守旧者”的自我辩护:
“传统的不是我,是男性”
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守旧者”也开始有压力了。
冬葑和檀香就是两个典型。她们拒绝婚前性行为,但又担心被人看成“守旧”和“老套”。
冬葑一直在强调,她是一个特别特别理性的人。“处女情结”那一套传统的观念在她看来已经过时。她花了40分钟跟我讲,性可能带来的疾病风险和怀孕的风险。
檀香是基于一种理性的计算。她说并不是自己老土,而是这个社会上大部分男性还都这样想。如果她不是处女了,她将来能找到如意郎君的概率就小了。她怕的是吃亏,“第一次”性经历被视为一种重要的性资本。
但是冬葑和檀香都没有思考的是,她们为什么要去屈就于男生的处女情节,为什么要去配合男生。
还有一类女性说这是一种个人偏好,就像“我喜欢蓝色”一样,她就是喜欢在婚后发生性行为,但她不是理性派,没有一二三四这些理由。
对于接受了一些现代意识的人而言,面对着将性束缚在婚姻之内的“传统”,好像不能直接说“我拥护它”“我接受它”,而是需要包装一下,需要再找一些合理性。

在做访谈的时候,我一直在努力达成性别均衡。50多个访谈对象,男性只比女性少了几个而已。但是成书后我发现,女性的故事非常凸显,男性只是寥寥数语。我也在思考,为什么男性的资料没有引起我的关注?
在“性的快乐”一章中,其实提到了“蔚沅”这个男性个案,他具有非常丰富的性经验,不仅有很多的性伴侣,而且性伴侣的类型很多,既有具有一定情感基础的“婚外情”对象,也有“小姐”,还有网友这种“一夜情”对象。
女性在脱离爱情发生性行为时,自己是非常矛盾的。但是在蔚沅身上看不到这种矛盾。他分享起性经验时,侃侃而谈、兴致勃勃、充满自信甚至自豪,流露出一种“舒适自在”。
这种对比颇有深意。这本书之所以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女性身上,恰恰是因为女性在性革命进程中受到的牵绊和限制更多。哪怕是追求开放式关系的晴雪,也未曾明确主动地要求欲望的满足,而是被动地等待男性的邀约和提议。
相对而言,男性的性革命进行得更彻底。
男性能够接受自己的性探险,但却难以接受伴侣的性探险。

他们用更直接的方式去追求性快乐。不仅是男性,女性也可以在爱情、婚姻、商业性交易之外,获得性的满足。
性变得越来越独立,甚至可以去左右或安排其他的东西。比如,“无性婚姻”开始拿出来讨论了。人们对“性福”越发强调了,性生活质量成为婚姻质量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在私人生活之外,性还在渗透并塑造整个社会的经济体系,比如性治疗、性玩具的发展等。
潘绥铭老师曾在课堂上预言过爱情信仰的崩塌,情感在性的社会关系中依旧扮演重要角色,但当代青年已不再遵循以婚姻为中心的传统性秩序,开始积极地追求性的快乐。
部分图片来源网络,均已购买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