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背影 ——对话台湾眷村老兵

本文系大赛50强入围作品
作者 | 曾腾腾 邹婧子
前言:
十年前的八德金城街,是热闹的眷村,荣民爷爷们天南地北,齐聚一堂,侃侃而谈;
如今的他们已经步入耄耋之年,生命在逐渐凋零,垂垂老矣之时,乏人问津,终归于沉默。
这是一场跨越时间的对话,对话四位老兵,李永来爷爷、秦正全爷爷、汤学勤爷爷和芮海保爷爷。
走进他们独一无二的生命故事和人生经历。
对话李永来爷爷
李永来爷爷和他的老伴住在金城街六巷四号,他来自山东,今年已经八十八岁了。我们路过六巷街道时,爷爷家的小狗来福正在对我们一行陌生人大叫,爷爷推开家门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他穿着条纹衬衣,虽头发花白,但依然精神矍铄。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李爷爷。
我们同他打招呼,他热情地邀请我们到家里坐坐,他的家里不大,三层楼高,干净整洁,装潢简约明亮,和之前采访过的荣民爷爷拥挤简陋的平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告诉我们这个房子不是他们原来住的。他们原来的房子在爷爷退休回大陆后卖掉了,而在金城街的这套房子是曾经一位上校留下的,李爷爷指着房子结实的骨架对我们赞叹:“盖得很好啊,大小适宜,太大了反而不喜欢”。说完他笑着解释说因为年纪大了不方便打理。
李爷爷一边说一边按着室内的铃声,让此刻正在三楼养花种菜的奶奶下来,奶奶戴着黑色的绒帽,穿着橘色的大衣从楼梯上缓缓下来,淡定从容,爷爷喜笑颜开说:“让这位山东老太太陪你们聊天好不好”?后来我们才知奶奶并不是山东人,她是台湾新竹人,曾随爷爷在大陆的故乡山东待过五年,就被爷爷戏称是山东老太太,她也欣然应允,大概是源于一种对于丈夫故乡的亲切认同感。
“像我们这一代人,没有了”。——漂泊的苦难
当我们问起了爷爷何时来的台湾,他的思绪似乎被拉到了遥远的民国三十八年。
“我来的时候很小的,十几岁来的,跟着别人逃难过来的”。爷爷说她出生在日据时代,东北那时已经沦陷,到了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他们留在东北的眷属还没来得及撤离。

很多中国人打算把住在东北的日本眷属打死,“因为曾经他们对我们很坏嘛,让我们做了亡国奴”。后来蒋介石以德报怨,把他们都送回日本去了,当时爷爷的一位日本同学准备回去,爷爷怕他在路上遭遇不测,于是跟他一起去了日本大阪。回忆起从前那段异国之旅,爷爷只说:“啊呀,到日本去,破破烂烂的,日本工厂统统都炸完了,没有男人,遍地都是女孩子。到什么程度?给她一个馒头就跟你过了,没得吃的,穷得要死”。沉默片刻又说:“那时可穷了”!贫穷困苦的记忆在时过境迁之后笼上一层灰蒙蒙的浓雾,时代、历史、政治变得日渐模糊,只有满目疮痍的战后之景还历历在目。
后来爷爷漂洋过海逃难到了台湾,至于他当年是如何上的船?漂泊了多久最终抵达台湾?又是如何当兵入伍的?他都用一句“像我们这一代人,没有了。”来带过。人生万事,总是一言难尽,又一言尽。好像一切都是阴差阳错的巧合,又有点稀里糊涂的荒诞。
“当年追随蒋介石过来的人,还有多少呢?像我们小孩子来的,才活到现在”。一种反刍昔日的辛酸,慢慢地细嚼出几分活下来的骄傲和叹息,用奶奶的话说:“我们活了太久,看到了太多。”一次对话,如何能道尽爷爷奶奶动荡艰难的岁月?
“我非要当这官不可”。——风雨军校路
刚开始聊天时,奶奶就对我们说:“爷爷以前在部队里是军官,很会聊天,你们找对人了”!爷爷听后眼睛笑成一条缝,和我们说起了当年从一个小兵如何自学考上军校的故事。爷爷成功的故事颇为励志,但是当年支撑他考上军校的动力却特别简单。就是为了能吃饱饭。爷爷说当兵的时候一餐只能吃一碗饭,他说:“那时年轻,吃不饱饭,还要打战,还要训练,走路都打晃”。这段带着东北口音还有些押韵的吐槽让人忍俊不禁,却也能从中体会当时飢饿的窘迫和无奈。
“走不动啊”!末了又说:“真的有点惨”。
回忆起当时飢饿的军旅生活,爷爷印象极其深刻,“苦啊,我都苦了几年了,苦到二十几岁,受不了啊,吃不饱饭,整天想着吃饭吃饭,每次大家都抢着吃,装饭的时候盛得满满的”。爷爷边说还边比划着盛饭的动作,“因为第二碗没有了,七八个人围着一圈在地上,一小盆盐巴水,往肚里倒米,那个饭都是谷子,硌嗓子啊”。
奶奶这时来了一句:“难怪你会胃溃疡”!
我们听后笑作一团,爷爷望着我们笑得更开心了。飢饿的往事,因奶奶一句调侃的玩笑话有了一点苦中作乐的意味。
爷爷说:“那个时候当兵是真的苦啊,我没办法呀,被逼得没办法,当兵吃不饱饭决定去考军校,当军官,每天就找书看,当时考军官要高中毕业,我就自己看书自己读,自己动脑筋,不懂就问问学生,慢慢学。第一次考没考上。他们高中毕业的学生一考就考上了,我们考不上”。
“再考第二年,知道了要考什么,考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考法律这些东西,我没有书,就去图书馆找这些资料去看。考数学考英文我也不懂啊,考代数,我不懂,那是大学的事,第二次又没考上”。
“回来又继续读书,搞了几年,终于考上去了,考上去受训,完了以后,就当官,当了官能吃饱饭,因为军官吃饭一桌,吃不完,当兵一碗饭就没有了,当兵不是人啊,气得没办法,当官了。但是可费劲了,那时下苦工了,整天脑筋都在那书里面,连背带哭,我非要当这官不可”。
爷爷后来官至连长,退伍时正准备升少校。
爷爷的风雨军校路让我想到了很多年前看过的一部电影,影片中的女孩也是凭着自己的坚持和努力圆梦哈佛。人生其实真的可以改变,只要愿意努力,愿意付出。爷爷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一个平凡的士兵用执着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改变了自己,后来爷爷十年期满顺利退伍并转战商场,至此,爷爷的人生发展方向开始悄然发生改变。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商海创业之路
“那个时候我在制衣厂,他去开车”。
奶奶谈起爷爷刚刚退伍时四处找工作谋生,吃尽了苦头。
“当时开车才三四千块一个月,但在部队当官只有六十块。退伍下来的时候,国家辅导我,去学校当老师,教小孩,但要受训半年,学注音符号,而且不给薪水,怎么活?我不干。决定还是自己干,干到什么样也不埋怨别人,我们有一句口号叫什么,好汉不拿有数的钱,什么叫有数的钱,一个月规定拿多少钱,比如一个月给我十万块,我自己去做一万块,我就这个本事嘛,但我还有进步啊,等我拿到五十万的时候,你还是十万块,我自己闯,闯不出来是我自己没本事,没这个命,但是胆子要大,要聪明敢干”。

于是一九八八年,爷爷奶奶去了大陆,一呆就是二十年,在山东的五年,爷爷送走了自己的父母亲,尽完孝道。就去了东北鞍山十五年,在那里投资建厂。
由于以前大陆穷,爷爷当时拿了两万块美金去投资,市长、副市长都亲自到机场接机,可以想象那样的场面是何等的气派和风光。爷爷坦言当时回大陆的时候,台湾的钱很好用,台湾一个月的钱能在大陆用上一年,卖的东西都很便宜。当时的万元户还很少,爷爷就将美元换人民币,给他的两个弟弟、四个妹妹每人一万块,他们争前恐后地抢着要,迅速跻身万元大户的行列之中。在爷爷的心中,故乡是他永远的根,兄弟姊妹是最深的牵挂。少时离家,经年累月的苦难皆化为了对故乡亲人深深的眷恋与感恩。于是,家乡建设和经济的支助,便成为了不遗余力的奉献和最后的救赎。
爷爷奶奶刚回去的时候是打算做台湾贡丸的生意,爷爷买了四台当时非常高科技的机器,全自动化,但是做出来没人吃,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没吃过。送到饭店里,厨师也不知道怎么做,客人不知道怎么点,于是摆了一个月还在冰箱里。谈起第一次的投资创业,爷爷直言:“垮了。太早了”!的确太早了,那时候大陆的物价,一瓶酒才几毛钱,爷爷的一袋台湾贡丸就卖到了两块钱。远远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消费水平。后来万般心疼,千般不愿,爷爷也只能把那四台机器当废铁给卖了。
汲取了第一次投资失利的教训,爷爷在鞍山做起了石化工业,将炼油厂提炼过来的石油,卖到远航的船上,从中获得了很大的收益,生意逐渐走上正轨,通过十余年的积累,成为了一名成功的商人。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国营企业的改革,开始清查落后的工厂和小工厂,油价变得便宜了,很多台商都走了,爷爷奶奶的工厂也跟着倒闭。在讲述这段故事时,爷爷最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世事无常,总是超出我们所能预料的范围,当时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的爷爷奶奶又怎能料到如今年过八旬的自己又回到了台湾,安享晚年。
“我们现在就在这里吃饭等死,老了没有什么了,你们这一代太幸福了,赶上好时代了”。爷爷感慨时还不忘自嘲每天的晚年生活是在吃饭等死,他仿佛有一种天生的幽默感,像在说段子一样,一个接着一个,常常逗得我们哈哈大笑,他也望着我们每个人笑,就像在和自己的孙女一起聊天,说起爷爷的那些年。
“缘分让我们认识”——幸福美满的家庭
爷爷奶奶在和我们聊天时平和从容,在对事情对人生的体悟上保持着高度的默契,我们好奇地询问爷爷奶奶是怎么认识的?
他们又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是缘分。这样的默契令我们更加动容。仿佛彼此不说就已懂得。
爷爷笑着说:“那个时候我当兵,很穷啊,当军官很穷啊,也是没有钱啊,奶奶家有地,可以有粮食,吃得饱饭,就到她家吃饭”。并戏称他们是吃饭认识的。似乎是在告诉我们平淡才是真。奶奶听爷爷的故事时真的很认真,还会时不时向爷爷提问,并亲切地唤他“哥哥”,比如她会问:“那孔子怎么学习的”?爷爷就会笑瞇瞇的回答说:“请个先生来家里教喽”!奶奶听完便恍然大悟地点点头表示懂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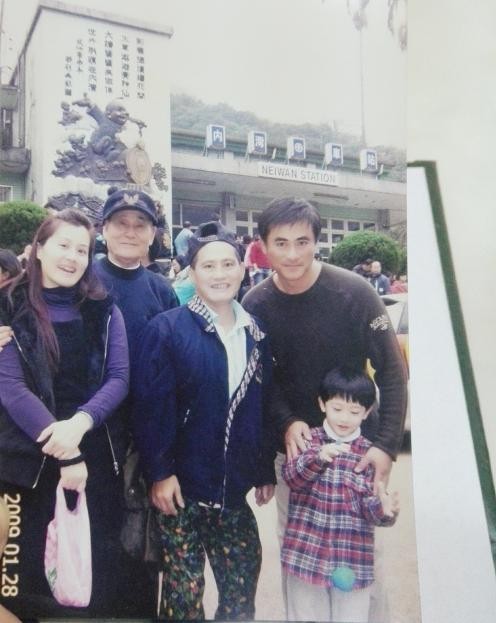
他们的家庭生活十分幸福。爷爷奶奶有三个孩子,两儿一女,如今都已经五十多岁了,早已成家立业,不用他们担心。他们谈起自己孩子时说得最多的还是女儿,大概是最疼爱的小女儿。他们的孩子们如今都在台北,经营着自己的小家,有空才会过来看望二老,但他们似乎特别知足,谈起孩子们时,特别骄傲,眼睛里闪着光。
在聊天的过程中,奶奶坐在爷爷旁边,大部分时候都是安静地听着爷爷说话,温柔地注视,偶尔补充一两句,或是怕爷爷冷,上楼给爷爷拿件外套披上。或许生命的意义并不在于人健壮时有多么地辉煌,而是在它逐渐凋落时,是否有明白他的人在一旁静静地听他说起多年前的往事,在屏息之间交换着生命的本真。任凭世界变化不停。陪着他,静静地。
结束访谈我们起身告辞时,爷爷奶奶一直挽留我们同他们一起吃晚饭,我们不愿打扰和麻烦,爷爷便邀我们下次有空再来,知道我们是交换生,便问我们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充满了关怀的亲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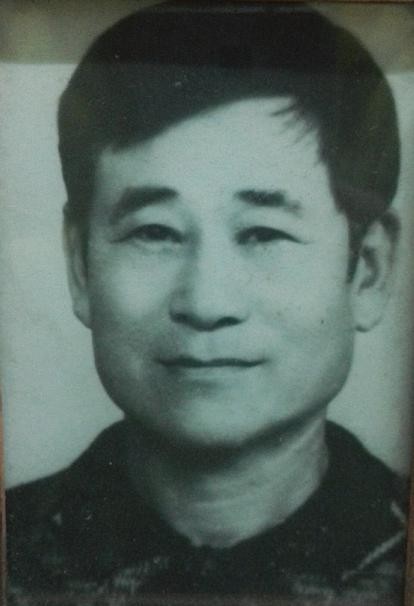

从军官到商人,爷爷身上却没有烟火气,更没有狂躁像,有的只是一副清癯的面容,一脸淡然的神情。送我们离开时还不忘叮嘱我们要好好读书,他说:“你们这个年龄都有发展,好好学习外语,很有用,多走走其它国家,体会不同的生活”。爷爷生在一个波折的时代,却勇气依旧,回望已走过的大半辈子人生路,有奋斗,更有取舍,丰富精彩的故事背后是智慧,又何尝不是一场人生的修为?
对话秦正全爷爷
秦正全爷爷今年已经九十岁了,住在金城街一号。他和李永来爷爷一样,祖籍山东。但他的个子小小的,眼睛小小的,他的双手更是小小的,看上去十分粗糙,那是日复一日劳作累积的老茧,后来秦爷爷告诉我们,他当年退伍之后为了生计去了工厂做纸箱,那时,把他们当成是廉价劳动力,对他们很苛刻,每天起早贪黑,也只能赚个六十块钱。超负荷的工作量让爷爷衰老得很快,如今老来一身的毛病,但是秦爷爷的生活节俭,不乱花钱,攒下钱来买了这样一套房子,上下两层,不大,但收拾得干干净净,井井有条。从采访过程中可以看到,秦爷爷是个极其厚道的人,不喜欢打麻将,也不爱打牌,生活简单规律。秦爷爷代表的是另一种老兵的生活状态,克制,节俭,认真。

“一个一个都不在了,没有了”。——时过境迁的感慨
秦爷爷说:“原来我们这个地方一百多户都是退伍的,都是老荣民,一个一个都不在了,没有了。现在这些都是外来的,以前的时候我们都在那边那个棚子那里聊天玩,很热闹的,现在不行了,我们这些老家伙,都不在了。”
秦爷爷和我们说起这些时,总是有着无尽的感慨。当年八德金城街天南地北,谈天说地的荣民爷爷们如今时过境迁人不在,终归于沉默。“我们都不在了”,是一种生命逐渐凋零的状态,让我想起了英语表达里的死亡进行时“is dying”,如今,步履蹒跚的他们行动不便,每天只能在家中,盯着电视里循环播报的新闻事件,就成了他们与外部世界保持联系最为重要的途径。
秦爷爷的身体也不好,由于心脏有毛病,常常要到医院去。他笑着说自己:“今天上医院,明天上医院,快了!”虽然是笑着,但我们当然知道他那句“快了”背后隐藏的意涵,有一点难过,却无可奈何。问起爷爷怎么去医院,他说:“打计程车,来回就是五百块。过去两百五,回来两百五。”听得出来爷爷对于这笔额外花费十分心疼。他本想告诉我们他常去的那家医院的公交站台,突然间就停顿了,想了好久也没能想起来,不好意思地冲着我们笑笑,指了指脑袋,说:“反应不过来了”。
爷爷告诉我们说他以前去看病的时候,还有精力跑到台北的荣总医院。但是更加辛苦,早上三四点钟就要起床,从士校坐车,从挂号看病到取药回来,一去就是一天,他说:“在台北北投那个地方,不方便”。
看病对于老兵来说是一件困难的事,其中有很多生活的窘态,却也展现了他们人生的真实状态。
“一出这个家门就没回过家了”。——工兵生涯
爷爷是民国三十七年当的兵,三十八年来到台湾,他从山东青岛出发,坐船到了基隆,仅在基隆街住了一个多礼拜,又上船,跟随部队前往海南岛作战,在岛上待了将近半年。十二月份又回到台湾,在高雄下船。
到了民国三十九年,又到彰化,四十二年以后,就到新竹。四十三年,到关渡,住到四十五年,又去金门,在金门三年,八二三炮战那段时间,爷爷就去小金门了,后来炮战不打了,民国四十八年回来,又遇到了八七水灾,来势凶猛,很多道路都毁坏了,爷爷去新竹,苗栗这些地方抢险救灾。由于工程兵的工作原因,爷爷的工作地点就在不停地流动,跟着部队,哪里需要就去哪里。
“反正就在台湾这个地方转来转去,转了一圈,五十四年,又到南部去,到了屏东那一边,到六十一年回的嘉义,一直到六十二年,到妈祖。在妈祖住了两年,六十四年,退伍回来了。那个时间我快五十岁了,每月退休俸还少,百八十块钱,但是现在不错了,一个月有两万块钱,就在这混混生活,能怎么办,什么事也不能做,不能干啦。”秦爷爷继续说着,他走了很多地方,走了很多年,始终一个人。
始终没有一个属于自己安定的家,这是一种舍小家为大家的牺牲,为台湾的建设奉献了自己全部的力量。爷爷说:“我当了兵就跟和尚出家一样,再也没有回过家,我们家就三个人,现在就我自己,那两个都不在了。哎呀,不提了,以前那个。”
我们听到这里,连那句“你后悔吗?”都不舍得问。怕撕开爷爷还没愈合的伤口,生生作痛,老年僵硬的膝盖已经无法跪拜,父母的坟头长满青草,乡里,已无故人。
“啊呀,太苦了,没有办法”!——无人理解的辛酸
退伍以后的爷爷也做了好几年的苦工,在工厂里面做纸箱,一做就是好几年,每天起早贪黑,没有办法,后来又在水厂干了几年,做临时工。
“工资一天六十块,还要扣八块钱的伙食钱嘞”!爷爷说到这里时总是愤愤不平,的确那时一个月还不到两千块钱的工资,一天有时却需要做十四个小时。
所以爷爷一直语重心长地叮嘱我们:“千万千万要读书,把书读好了”。爷爷认为自己一生吃了很多苦与时代相关,与学历也相关,也许有知识之后就不会过得那么苦了。

但是在采访中,爷爷好怕我们不能理解他,他总是说:“现在这个时代不同了,我们那个时代是和你们不一样。我现在讲你们没经历过不晓得的事,你会说我乱讲话”。尽管我们连忙否认,但他还是半信半疑,这是一种无人理解的辛酸,他那么希望我们能够听进他的叮咛,理解他生活的种种不易和属于他的时代,却又好怕我们不懂得,害怕我们不感兴趣,害怕我们会觉得烦。
爷爷膝下无一儿一女,大半辈子始终孑然一人,他也不是一个健谈的人,因而很多事情,他都放在了心里而非挂在嘴边。他一生都在舍小家为大家,对于社会始终有着很深的情感和责任在,他每每打开电视,看到酒驾车祸、吸毒诈骗的新闻滚动播放时,就会很难过。他和我们谈起这些时,有着一种痛心疾首的愤慨,他担心法律无法保护每一位好人,让有些坏人趁机钻了空子。爷爷总是不停地摇头,很多的失望,到了他这个年纪,除了摇头,还能如何呢?
“我太太是菩萨心肠”——晚年的家庭生活
爷爷快七十多岁才经人介绍结婚,当时在采访时,他的太太正好上班去了。秦爷爷向我们介绍说:“我和太太认识十几年了。她是湖南长沙人,长沙是个大都市”!
秦爷爷说这些时眼睛里有笑意,闪着光。看得出来,爷爷很爱奶奶,他现在很知足。他悄悄说自己很羡慕奶奶,因为奶奶家里的兄弟姊妹很团结,很和睦,这是他漂泊这么多年都未曾见过的,也是他一直渴望却缺失的那一部分。——其乐融融的家庭氛围和互帮互助的兄弟姊妹。奶奶自己有一个儿子,如今已经成家立业,在长沙做着自己的生意,也添了两个可爱的孙子。这让秦爷爷有了一点远方的念想,有了享受儿孙满堂的喜悦,爷爷因此去了好几次长沙,去年就呆了半年,他说起这些的时候很开心,他很喜欢长沙,很喜欢他的太太,他告诉我们,他们两人都信佛。但当我们环顾房间四周的时候,却又看不见与佛有关的任何物品,爷爷便说:“佛在心中”,的确,心诚则灵。
后来我们圣诞节和工作站的孩子们一起为金城街居民派送礼物的时候,见到了秦爷爷的太太,因为是同乡人的缘故,我们和她聊了一会儿天,她告诉了我们很多的故事,当时她经历了第一次婚姻的失败,只想走远一点,于是考虑到秦爷爷无儿无女,没有负担,退休金不少,才决定嫁给他,现在自己就在这边上班,吃与用都来自秦爷爷每月的退休俸,她上班的钱就能存下来,她说到这一切的时候,精细地计算和考量,完全是我们意料之外的,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世间万事都是表象的平静,现实面前,不得不为将来精打细算。
采访的时候,我们说有点冷,爷爷就很担心我们穿少了衣服,说:“多穿衣服,你看我!”,然后就给我们看他穿了几件毛衣,然后说:“这样就不冷了”。
秦爷爷的身上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感。从前坐在金城街大树下,或门口板凳上,说起“蒋公”、“夫人”、“学良”,像说自己很小时候就认得的朋友,有着很深的缘故。如今,坐在家里,看着电视,对于新闻事件失望难过,带着无人理解的辛酸,和我们絮絮叨叨地说着人生大半辈子的故事。
他说着说着就哭了,说着说着就老了,说着说着就快了。走时我们说爷爷身体健康,答曰,马马虎虎。转而望着我们笑,曾经沧海,也不过弹指一挥间。
对话张伦华阿姨
张伦华阿姨和汤学勤爷爷住在金城街四巷十号,汤爷爷是退伍的老兵,今年九十二岁。但和其他采访过的荣民爷爷情况不同的是,爷爷已经卧病在床,因为服用安眠药的缘故,进入了深度睡眠之中,加之已经完全听不见声音,无法和我们聊天,因此,他的妻子张阿姨是我们的采访对象,提前一个星期我们就已约好了聊天时间。张阿姨十分热情,欣然应允。还说到时候可以介绍他的大儿子和我们认识。
汤爷爷和张阿姨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也在中原大学念书,二儿子则在念永丰高中。由于高中的课业压力,他每天清晨上学,到了晚上才能回家,我们拜访那天,刚好看见阿姨的大儿子,他火急火燎地准备出发,据说是有一门考试,他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说着:“死了,死了,还没复习”,让人忍俊不禁。还没有和我们认识就已经骑着机车扬长而去,只留给我们一个潇洒的背影。阿姨笑着招呼我们进来坐,和我们娓娓道来了他们的故事。
“我们家乡的雪下很厚的。”——温柔的江南女子
阿姨是江苏苏北人,即靠近洪泽湖附近。原来是在家乡那边当小学老师,由于当时学校的老师比较少,阿姨什么都教,但是主要还是教国文。记得父母曾和我们说过的,老师是当时最热门的专业,需要考师专。竞争非常激烈,预考第一刷只有百分之十的上线率,然后再复试,再面试。最后能选上的都是十分优秀的学生。阿姨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夸赞阿姨很厉害欸,她好像有点不好意思,连忙说没有没有。

她告诉我们:“那个时候重男轻女,虽然允许我出来读书,但是还是重男轻女,我们五姊妹,我是老大,我读书在我们家姊妹中还不错,会努力。那个时候还没有电灯,回到家里还要挑煤油灯,挑灯夜读。上中学的时候,上学校都靠走的。我儿子都不相信,说我是编的。”她说这些的时候,非常温柔,始终微笑。一点都不像是在说一段艰苦的求学经历。这是阿姨的性格,带着江南女子如水的温柔,向我们娓娓道来,说起两个儿子,老大老二相差四岁,都在念书,书费负担重,好在政策福利好,考量到家中没有劳动力并且有一位病人,因此大儿子大学里的学费是全免的。她每每说到这里,总是很放心,很踏实。这是福利社保给她带来的便利,减轻了家庭的负担。她说:“我有一个朋友的女儿在屏东念大学,一年几乎要花到三十万台币,妈妈辛辛苦苦做护工才能勉强供她上学,爸爸走了。”阿姨喜欢和我们聊起身边朋友的故事,好像每一个朋友都在奋斗和挣扎,周旋于冰冷的现实之中,依然看得见生活的希望。
“我跟他们很有缘”。——在荣民之家
汤爷爷年轻时家境殷实,表哥表叔在部队里当官。爷爷当年二十几岁就跟随他们一起来到台湾,在部队里长期担任士官长,管理全营的伙食和钱财。
据阿姨说:“他很有福报,在部队,他自己有单独的房间,和别人吃的不一样,当了二十一年的士官长,一直到六十岁退休,人生都比较顺利,没有受过什么苦。”


说起和爷爷的相识,也是经人介绍,爷爷在大陆的亲戚是阿姨的朋友,也是老师,先是认识认识,过了好几年之后,再见面,汤爷爷就开玩笑说:“这是我女朋友欸。”当时就有人风言风语说,阿姨这么年轻,家境这么好,怎么会嫁给他。但当时阿姨刚刚和她对象分手,是个中学老师,因此心情很不好,加上这么一说,就一下子有了逆反心理,才和爷爷正式谈这个问题,阿姨就很认真地说:“你差我年龄这么多,虽然你很有钱,但是婚后过日子,两个人要谈得来,我们这边人会说闲话,不知道你们那边的人会不会讲?”阿姨说出了她心中的顾虑,一是年龄,二是共同语言,三是他人的眼光。但爷爷当时特别肯定地对阿姨说:“不会讲。我们慢慢谈。”正是这样几句话,开始了一段故事,三年之后,他们走入婚姻,阿姨也跟着来到台湾,有了两个可爱的儿子。

汤爷爷是个很不错的人,对阿姨很好,只是如今身体每况愈下,已经到了完全听不见的地步,平时交流只能靠打手势,因为时间长,家里人之间已经有了一定的默契。爷爷还患上了躁郁症,每天靠吃安眠药才能入睡,一睡就要睡到第二天中午十二点了。
但是治疗躁郁症的药物有很大的副作用,吃多了会精神紊乱,但又没有办法,“我现在不上班,全心全意照顾他。”
阿姨说的上班,是去荣家,她之前在荣民之家照顾老兵,遇见了很多和爷爷一样的情况,很多老兵,都处于失智状态。变成像小孩子一样,他们很多人都没有太太,独居一生。当年随蒋公过来,这么多年过去了,在台湾人眼中,他们始终是外省人。
唯一庆幸的是,晚年可以在荣家养老,只要交生活费,不要出照顾费。荣家里分三班照顾,早班,中班,夜班。为老人量体温,给予关怀和问候。一个荣家里面配有医疗单位,药局,医生和护士。还有专门的救护车随时防止突发情况,在荣家一个护工照顾八位老人,还有社工,照顾得非常棒。用阿姨的话说就是:“可以看电影,院子里有摇摇椅,还有打麻将的,下象棋的,下午还能唱歌,老年生活很OK。而且都是同时代的人,大家有话说。”
阿姨在去照顾之前还经过了专业的培训。要考核合格之后才能去。照顾这些老人给阿姨最大的感受就是:“人一老就会依赖。有的老人会一直很吵,想要人陪。”还告诉我们:“有的也会乱说话,那些以前干情报工作的,老了就会很惨,那种警觉性,因为很多年一直保持着,一离开那种工作环境很快就会崩溃。房间不给人进,是秘密,害怕大家来搜他情报,听到脚步声,就会大叫:要来杀我了!快转移!到最后都是精神失常了,照顾的时候太惨了,我们照顾很多这样的爷爷,很辛酸。”这样的故事听得我这样的外人都快要断肠。那一瞬间我突然想起了之前在很多老兵家的采访,那挥之不去的呢喃和绵长的怨叹,究竟有多少是病痛的折磨,多少是生活的艰辛,多少又是时代的远去,生命的逐渐凋零,分辨本身没有意义,物是人非里裹挟了太多的严酷。
“学佛,修道,修自己生死大事”。——佛经与信仰
阿姨说,自从爷爷卧病在床后,就没有再去上班了,每天都是围绕爷爷转,一晃就是六年的时间,除此之外,平日里最多的就是去佛堂上课,因为读佛经,可以清静自己的心。里面讲了很深的道理。
而所谓很深的道理就是:“我们每个人有八颗心,但我们有一颗真心,这颗真心是不生不死的,我们有意识,意识就会了之,有生有灭,睡觉的时候就不见了,死了也会不见,真心就会从此脱离,灵魂就会去投胎。父母生了你但是没有造你。”原因是:“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小孩。怎么制造是根据你前世做的业来造。现实生活中不顺和不如意都是因为前世大家的渊源。佛法是生命的真相。佛法道理很深,但很实用。”阿姨对佛法有着很深的执念,这是她的信仰,她和我们介绍这些时,像是在传法,特别激动,滔滔不绝,她告诉我们有很多人信的,她的师父是很厉害的,七十几岁了。可以看到自己前世,就连两千五百年前都可以看到。“我们都是她前世的弟子,是前世修来的缘。”

学佛讲因果,讲善根福报,讲前世和今生,阿姨给我们举例,比如,年轻人出来创业失败是由于前世欠了老板的钱,因此必须要逆来顺受,老老实实在老板手下干,不要有其他想法。她鼓励我们一起来学,“因为很多年轻大学生都在学,学完人生都变得好顺利啊!”
我只听到那句“人生都变得好顺利啊”,其实我也想。
看着阿姨眉飞色舞的样子,正是她从之前说话细声细语到侃侃而谈的转变,说实话我还不太能适应,中途,她在讲她的师父并努力劝说我们的时候,我已然神游到了很远的地方,但我努力告诉自己,阿姨还是她,只是有了信仰。
想起之前阿姨和我们聊起过的那些苦苦挣扎在生活边缘的朋友们和在荣家照顾过的那些失智老兵,他们的命运大都不好,因而听阿姨说那些佛法道理时,我没有任何反感,甚至看到在床上躺着的汤爷爷,略微有一点心痛,好像可以理解那些佛法对于身处困顿中的人是一种多么大的精神力量。
回去的路上,耳畔响起阿姨那句:“我听师父说我前一世也在江苏,我以后还要回去传法。”愿阿姨能收获属于自己的福报,回到家乡。
对话芮海保爷爷
沿着金城街往里走,第十七号就是芮海保爷爷和宫本珍奶奶的家。
在我们敲了很久很久的门以后,芮爷爷才拄着助行器步履蹒跚地走来为我们开门。一脸疑惑地看着我们突然地造访。
我们同他热情地打招呼,他却只是看着我们,一句话也不说。接着宫奶奶从厨房里走出来看我们,我们和她说明身份和来意后,她才邀请我们进屋坐一坐。奶奶后来解释说,芮爷爷已经听不大见了,需要很大很大的声音才能听得见,而金城街最近常常有诈骗集团出没,因此他们对每一位造访者都多留了一个心。我们听完有点心惊胆战,尤其是听到“诈骗集团”的字眼时,但宫奶奶却是一副轻描淡写的样子,好像这类事情早已司空见惯,象是久经沙场的士兵。
但宫奶奶不是士兵,她年轻时毕业于沈阳医科大学,后在南京药厂上班。她出生在大连,却在南京工作了很多年,因此她常说自己是南京人。但听得出来,她的口音里有明显的东北味儿,她笑着说自己是“五湖四海人”,其实掺杂了各地的方言。芮海保爷爷是少校退伍,江苏溧阳人,今年已经八十八岁。在宫奶奶第一任丈夫去世后,两人通过领导的介绍认识,现已经结婚二十五年。

冲上云霄——空降特种兵
爷爷出生在大户人家,可怜父亲在他九岁时就已去世了,但作为长孙的他在家里也是备受宠爱。
“我爷爷当时可喜欢我了”!
爷爷总是这样对奶奶说。后来他的爷爷抽鸦片,败光了家产被赶到庙里居住,大家就分了家。他与母亲相依为命到了十六七岁时,被抓去部队当兵。由于爷爷少时离家,幼年的记忆变得遥远又模糊,于是很少提及。
“我们每次吵架的时候,想起他以前那么惨,有时候也不忍心了”,奶奶对我们这样说到。
当兵之后,爷爷先到了苏州,后来随部队去了上海,最后几经辗转来到台湾。那一年他十八岁。他被派去了空降部队,成为一名特种兵。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由于出色的表现,使他成为了带兵的队长。长期在空中的训练和作战也为他留下了许多隐疾。奶奶说,爷爷如今坐骨神经、心脏的病痛都是当年经常性的跳伞活动留下的后遗症。“我现在从后面叫他,他都会吓一跳,魂都没了”,三言两语中尽是心疼,再后来,爷爷考上官校,一路晋升成为了少校。
奶奶说:“当时本应该到了晋升中校的时候,他就掀桌子打板凳地和当官的吵架,一直嚷嚷着自己没有学识,做不好这份工作。给他聘请文书他也不干,说是别人写的不好,给人家桌子都掀翻了。”最后本可以晋升的官位也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据奶奶描述,爷爷当年在部队可是一个暴脾气。像火药桶一样,犟得很,不好相处。
但在采访过程中的爷爷却十分安静,不吵不闹。只是安静地就坐在一旁的椅子上。好像静静地在听,可他早已经听不大见了,偶尔回答我们一两个问题,也需要奶奶在旁边为我们高声转述,他后来累了,瞇起眼睛在沙发上打盹,这与奶奶口中当年那个与长官掀桌子吵架的空军少校仿佛距离已经很远很远了。
安身立命——退伍之后
退伍以后,爷爷就在这金城街一隅安身立命。
刚刚退伍的时候,突如其来的自由让爷爷有些空虚和不知所措,少校的退伍俸足够他不为生计忧愁。为了填补这种空虚,爷爷过上了洒脱不羁的生活,每日在麻将和吃喝玩乐中消遣度日,今朝有酒今朝醉,钱也从来不懂得攒下来。用爷爷自己的话说就是“我自己饱了,全家就饱了”、“我开门也是一个人,进门也是一个人,没人管”。
但是很快就有人管了,在领导的介绍下爷爷遇见了奶奶。
两人刚认识的时候,由于爷爷的暴脾气和倔强的性格,又独身许久,和奶奶的相处处处充满了分歧。
奶奶说,他们刚认识时,爷爷去她家里,意见不合就敢直接摔她家的遥控器。奶奶当然也不让分毫,直接把爷爷从家里赶出去。带着东北女性的豪爽和直率。
婚后,两人有时吵架,爷爷就一言不合地把碗盘摔碎,还扬言要把奶奶赶回南京。奶奶和我们说起这些事情的时候仍然情绪激动,仿佛那些无法排解的委屈,突然有了倾述的对象,奶奶说,“我才不怕他呢!他要赶我走,我就让他直接买机票!”每次吵架吵到这个份上,爷爷也只能作罢。
就这样争啊吵啊,爷爷和奶奶就这么一起走过了二十多年。
奶奶回忆时说道,“但他从来不打人,我们俩吵架之后他看我不理他,他就看着我,看得我心软了就和他和好了。”
“现在呢,我要出去买个菜,他就跟丢了魂似的,在家里摸摸这里又摸摸那里。”
二十几年的磨合与朝夕相处,爷爷对奶奶早已有了深深的依赖,嘴上再固执却也离不开了。

其实爷爷虽然脾气犟但心肠却是很善良的。
刚刚退伍时,爷爷看中了金城街的这套房子,准备用退伍俸买下来。而此时另一个相识的爷爷跑来求他,想要和他合买上下两层的房子,但是暂时没有办法支付他自己那层房子的钱。
爷爷爽快地答应,自己出钱把两层都买了下来和他合住。之后也没再催他还过钱。
民国六十六年,爷爷返乡探亲,给他的父母修了两次坟,给他的七八个外甥出资,开了一个工厂,加工稻米送到上海去卖,后来等他再一次回去的时候,加工厂已经被变卖,他的外甥至始至终都没有告诉过爷爷,也没有给过他一分钱。
每次只是需要钱的时候,爷爷的外甥们才会和他通电话,由于爷爷没有孩子,他们还惦记着爷爷在金城街唯一的房产。宫奶奶看不下去,大骂了他们一通后,就再也没打过电话来了。
所有所有的这些事情,爷爷都没有再去计较,也没有再去提及。
只有当奶奶问起爷爷百年之后想要葬在哪里时。爷爷才连连摇头说:“我没有家人了,我不想回老家去,到时他们不知道还会把我怎么样。”像是看透了人情冷暖,世道人心。有着无尽的难言之苦。
“明年开春我带你回去看看”。——落叶归根的祈愿
爷爷是从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走来的人,心里藏着的是对党国不变的忠心和赤诚。从他的身上看到更多的是军人的信仰和使命。奶奶说,前些年爷爷生病住院,正值大选,他在病床上仍不忘喊奶奶花五百元打计程车去帮他为马英九投上一票。当时连医生都在笑他:“连老命都快没有了,还选举嘞!”,结果选上总统之后,就把爷爷他们这些老兵一个半月的慰问金给砍掉了。爷爷气到不行,在家里大骂马英九,凸显绚烂的口才,倒与学养无关。骂完之后仿佛意识到了什么,于是痛下决心:“以后谁都不选了!”
事与愿违的寂寥让爷爷隆重的使命感变成了螳臂当车的既视感。他们想发声,却最终随着时代的前进,不被听见,终归于沉默。此时我的耳边又响起奶奶向我们介绍当年八德金城街老兵们都在的情形:“有139户啊!当年!就是像他一样的人。现在,有些返乡了;有些去世了;还有些因为没有结婚,上了年纪没人照顾,死在家里了。都有,唉……”
说起爷爷最近几年的身体状况,奶奶又叹了口气。
“自从他半年前从轮椅上跌下来,半年内都在医院里进进出出,冬天穿衣服就像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地裹,就怕他感冒啊!上次生病时他都不能走路,在床上哭,攒着劲哭,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样哭过,第一次哭,我问他哭什么啊。”他就说,“我想回去,不想就在这里死了。”
奶奶就说:“那我们回大陆好不好?”
爷爷说:“大陆看病太贵了!”
听到这里我们和奶奶一样眼眶都湿润了,奶奶哽咽地说,我当时就跟他说:“你好好养病,明年开春我带你回去,看看我们百年以后的房子” 。她已经在南京的公墓给爷爷和她自己买好了墓地,她说她会一直照顾他到生命的尽头。带着一种生死与共的庄重,令人动容。

芮爷爷是幸运的,宫奶奶是个能干智慧的女人。她比爷爷小了二十几岁,不仅是当年少有的大学生,又是家里宠爱的独女。这些年,爷爷身体状况不好。当与爷爷谈及身后事时,她都对爷爷说,“你以后的事情我来安排,你就不要烦心了。”
芮爷爷的一生,少时离家,沙场点兵;潇洒半生,纨绔不羁;老来布衣蔬食,未至断炊;回首八十年,恍如隔世。
老兵的故事我们一直在讲,背后的深意到底是什么?无论曾经多么的光辉传奇,回归至生活,最后剩下的恐怕只有捉襟见肘的侷促和种种不如意的细碎。生活原相中的侷促和失意,或许才是历史本来的面貌。我们能做的,只有追寻他们的记忆,体会他们的情感。活着的意义就是活着本身的勇气。
从一个热血沸腾的军人,到一个飘零落寞的老兵。俯仰之间,已为陈迹。
▍大赛组委会
主办方:澎湃新闻
联合主办: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今日头条
指导单位:上海市作家协会
学术支持单位: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
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播学院
上海大学文学院
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