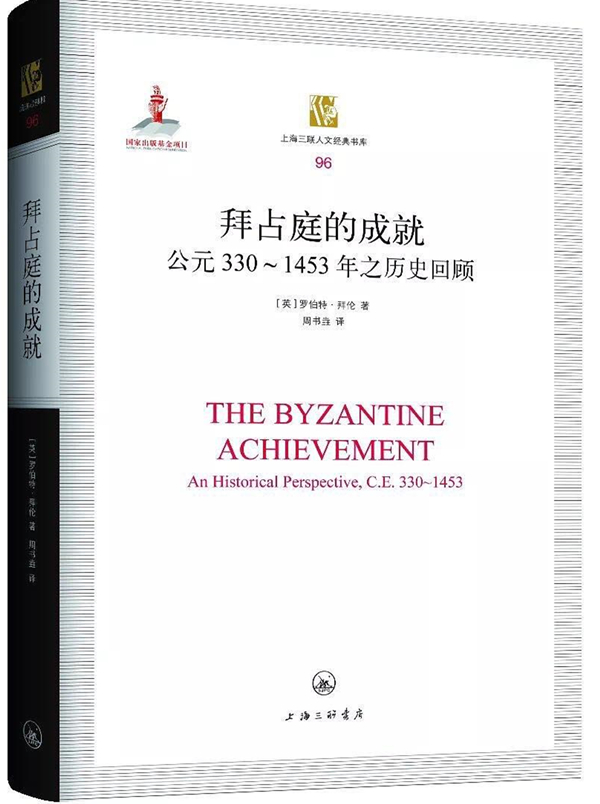千年拜占庭:古典与现代、希腊与拉丁在这里交织
人们一般把帝国的历史分成八个时期,其中第一段时期始于330年终于518年,从君士坦丁大帝建城至阿纳斯塔修斯驾崩。
作为帝国之梦,这座新都城遭到了考验。在黑海的掩护下,它仿佛藏匿于一把巨伞之下,躲过了亚洲民族向西南方向迁徙的大洪流。而这一祸水之所以能够被西引,是因为阿拉里克、阿提拉和狄奥多里克等伟大首领无法抗拒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诱惑。378年,哥特人在阿德里安堡大败东罗马军队;直到476年西罗马灭亡10年后,这一隐患才被消除。不过,仅过了一个世纪,君士坦丁堡就因人口增长而向外扩建了1英里。439年,狄奥多西二世任命的城市长官塞勒斯(Cyrus)建造了巨大了三层城墙,它全长5英里,建于三面环海的海角之上,为扩建的郊区提供了防御,至今依然屹立于此。
与此同时,对耶稣基督位格的界定正反映着这个国家的政治变迁。在对东方精神上的偏爱以及希腊对作为天国中心的上帝的哲学价值的关注面前,西方则坚持认为马利亚只是生育耶稣肉体。把精神期望与民族期望混为一谈使得这一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在431年的以弗所会议上,经由亚历山大里亚神秘主义者的提议,聂斯脱利派对耶稣位格的分析遭到了谴责,这就造成了一个独立的聂斯脱利教派与一个独特的叙利亚民族。20年后,在卡尔西顿会议上对这批神秘主义者的谴责又使得基督一性论教派、科普特(Coptic)教派和阿比西尼亚(Abyssinian)教派分裂了出去,北非教区的世俗野心也随之灰飞烟灭。多亏了罗马的帮助,君士坦丁堡教会终于在东方占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然而,在482年至518年间,教宗列奥一世已经把罗马教会提升至西方教会最高的地位,而君士坦丁堡教会却接受了强调基督神性而牺牲人性的观点,因此双方关系就此告一段落。帝国的实力在于黎凡特地区,而国家利益则需要政府安抚其狂热的民众。
拜占庭帝国就是这样在这场精神与物质的骚动中诞生并成型的。尽管欧洲已经被蛮族所淹没,但是它却完好无损。在其支持下,正统基督教的精髓得到发扬光大,这不愧是希腊思想的一座不朽丰碑。

第二段时期为518年至610年,从查士丁尼一世到福卡斯(Phocas)。
在这段时期里,查士丁尼打下的江山并未被保住。这位皇帝沉醉在一种虽可以实现但又野心勃勃的帝国统治的观念中,这使他不由得心系西方,并且对罗马所代表的昔日辉煌心怀向往。他逆转了宗教政策,与西部教会言归于好;对非洲和亚洲的一性论教徒进行了迫害。东正教教义的无上地位得到了确保,并于此根深蒂固了13个世纪,为希腊民族意识奠定了基础。不过,查士丁尼与西方如此心有灵犀,殊不知却在光复整个地中海版图的雄心壮志中出卖了其首都的资源和地位。在从533年至554年的20多年里,北非、意大利、西班牙南部,以及西西里、科西嘉、撒丁、巴利阿里等岛屿,纷纷归入了拜占庭的版图之内。狄奥多拉皇后(查士丁尼大帝的妻子,有塞浦路斯血统,与其丈夫一样都被东正教封为圣人)或许可以通过宽容的宗教政策得到叙利亚和埃及的支持,而在波斯人不断入侵小亚细亚,斯拉夫人和匈奴人已经渗透到摩里亚地区,且意大利伦巴第人尚未被征服的情况下,帝国由于战事连连而于565年查士丁尼去世时已经暂时性地被削弱了。他的继承者们把位于非洲(包括西班牙)和拉韦纳等偏远地区的总督区(Exarchate),以自备武装力量的附属国形式让他们自力更生,而专心处理巴尔干和亚美尼亚边境的蛮族与波斯军队的入侵问题。602年宫廷叛乱中止了这项工作。8年之后希拉克略的到来,才把帝国从无政府状态下解救出来。
虽说查士丁尼重建罗马帝国的努力只是昙花一现,但他的统治对拜占庭和欧洲文明发展的重要性是不可轻视的。尽管财富从陆路和海陆源源不断地涌入君士坦丁堡,但是皇帝心中却十分清楚,改革各个行政部门势在必行。对官员贪污受贿、横征暴敛的普遍不满最终导致了532年的尼卡暴动。暴动最后被平息了,但旧城有一半面积被烧毁,还有4万暴动者在大竞技场被杀死。在狄奥多拉皇后的鼓舞下才没有仓皇而逃的查士丁尼,提出加强中央集权,禁止买卖官职,并在各个省份推行军政权力合二为一的政策。不过,他最伟大的工作,早在其执政之初就已开始,那就是修订罗马法和以便于查阅的形式编纂罗马法律文献。在其筹划并下令编纂的法典里,根据基督教道德重新制定的社会生活主要规则,永远地造福了拜占庭、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子子孙孙。那时,从贝鲁特到罗马到处可见其缩略本,它为帝国的所有官员和子民开启了司法知识之门。
在尼卡暴动之后,城市四分之一的部分有待重建。查士丁尼对圣索菲亚大教堂的最终设想,以及罗马、塞萨洛尼基和拉韦纳现存的所有教堂和镶嵌画,统统要比文献来得更加直观,这些都展现出拜占庭鼎盛时期的创造力。一种世界性的、神秘的情感表现,吸收了对称、工艺和民族意识等艺术元素,它是如此完美协调,以至于几乎让观看者热泪盈眶。
这些就是这个海纳百川的文明的第一批产物。不论在文化意义还是社会意义上,其成就都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查士丁尼的计划被证实在政治上是一个极大的负担。他一生都在为构建一个西方堡垒而操劳,但是此时东方正在蠢蠢欲动。
第三段时期自610年希拉克略统治开始至717年狄奥多西三世被推翻。
自602年起,福卡斯篡位之后,拜占庭皇位的归属就充满了混乱斗争。其前任莫里斯,曾帮助过波斯王霍斯劳二世(Khosrau II)重新取得王位,他的遇刺成为了波斯入侵的借口,而这次危机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整个帝国都危在旦夕。安条克、大马士革、耶路撒冷、卡尔西顿,乃至埃及都屈服了,希拉克略就是在这一刻从其父的迦太基总督区起航,来夺取帝国领导权的,而此刻就连首都也已岌岌可危。尽管有阿瓦尔人在西部进攻,伦巴第人入侵意大利,以及帝国在西班牙的失势,皇帝依然将注意力集中在反击波斯人上。628年,他凯旋进入泰西封(Ctesiphon),从那里取回了13年前从耶路撒冷被夺走的“真十字架”。但是这一胜利产生两大非常严重的问题。战争导致的军费,虽有教会捐赠一部分,还是使得拜占庭帝国的非希腊臣民对高昂的税款怨声载道。而且统一被一性论迫害而疏远的埃及和叙利亚也是当务之急。正如伊丽莎白时期的英格兰那样,政治统一就暗示着宗教统一。东正教在君士坦丁堡根深蒂固;但是给在埃及和叙利亚盛行的基督只具有神性的信仰让步并不是皇帝个人意志能够决定的,况且这个神在传统意义的双重位格的原理下还能够化身成人。基督一志论(Monothelitism)这一权宜之计果然名副其实,虽然其目的是为了把矛盾双方团结在一个共同的政治框架之下,但是却发现两边都对其不以为然。在西方,它使得一位教宗在希拉克略死后8年遭到绑架。而在埃及,凭借牧首权力的利剑才使得它得以贯彻落实。因神学和财政上的困境而处境艰难的皇帝正深化着这个他本以为能够修复两者关系的讨论,而此时一个新兴的民族也通过宗教形成了自己的民族意识,而这种宗教对真主安拉的定义又有着无可匹及的执着。634年,穆罕默德死后三年里,麦地那的阿拉伯穆斯林首次战胜了巴勒斯坦的拜占庭驻防部队。
在闪米特人中,伊斯兰教最初的宿主是叙利亚人和埃及人,他们对宗教有宽容的态度,而且,也没有贪婪的官吏欺压,因此就从拜占庭人在物质与精神的压迫下以救赎者的身份登上了舞台。由于没有当地居民的支持,希腊军队被迫撤退。到640年,巴勒斯坦地区已经脱离了拜占庭的控制,埃及也遭到了入侵。次年,希拉克略驾崩,致使军民纷纷逃离亚历山大里亚。波斯和亚美尼亚也遭侵占。终于,冲突蔓延至了海上。塞浦路斯陷落;而655年,皇帝君士坦斯二世率领的希腊舰队在吕基亚(Lycia)海岸被击溃。但是由于君士坦丁四世继位以及希腊火的发明,情况发生了逆转。随着历时5年的对君士坦丁堡的海上袭击被击退,而后在678年,阿拉伯人在路上和海上的进攻势头停滞了下来,他们也终于愿意接受和谈了。3年后,由于埃及和叙利亚地区已惨遭蹂躏,一志论也失去了存在的理由,终于在681年君士坦丁堡举行的第六次普教会议上被判为异端。
天下终于太平了。在萨拉森人发动最后也是最强烈的一次冲破把他们限制于亚洲的赫勒斯滂海峡的攻击前,帝国获得了一个喘息的机会。不幸的是,从695年至717年,国内的混乱局面,使得这段时间所取得的优势未能全部发挥出来,也加快了北非的陷落。就在一时期,在西北边境,建国不久的保加利亚人的进犯也为帝国敲响了警钟。

7世纪以来,拜占庭的主要历史潮流就可追本溯源了。巴尔干和伊斯兰教问题具体来说就是保加利亚人和阿拉伯人。在行政方面,这段时期中的危机事件明确了行省的民事与军事组织转化为军区制的必要。在宗教方面,穆斯林占领了安条克、耶路撒冷和亚历山大里亚教区,这大大增加了君士坦丁堡作为宗教中心的威望。如今帝国主要部分几乎都在希腊沿海地区了。至此,拉丁人的最后一丝痕迹,即便是作为古风残留附属品的宫廷礼仪,都退出了历史舞台。
第四段时期,从717年开始至867年结束。
716年,阿拉伯人进犯小亚细亚直逼首都,而安纳托利亚军区将军伊苏利亚人利奥三世的胜利,使他被牧首和人民拥立为皇。就在他取得皇帝之位后没几个月,阿拉伯人的扩张行动就进入了高潮阶段,穆斯林的舰队和军队包围了首都整整一年。不过希腊人正躲在城墙之内享受着相对舒适的生活,而围城的军队却在饥荒和严寒的恶劣条件下损失了15万人,而这一数字还是他们自己估计的。这次失败给穆斯林世界将了一军,不过同15年后使查理·马特名垂青史的南征北战相比,这次胜利不过是一步险棋。拜占庭军队的威望被君士坦丁五世带入了亚美尼亚和幼发拉底河。由于阿拔斯王朝将国都迁至了遥远的巴格达,同时西方的保加利亚人在755年和780年间的一系列战役中蒙受了重大损失,因此伊苏利亚王朝的皇帝们开启了一个安定的新时代。在内政方面,他们能够审时度势并且行事果断。他们将军区管理制度化,并重新整顿了军纪。他们还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来制止日益不受约束的大地产贵族对小土地持有者的兼并,因为就是这些自耕农保卫了基督教世界。一部名为“埃克洛加”(Ecloga)的查士丁尼法典的修订版,引入了一个更加有基督教倾向的家庭生活观念。它在大多数情况下以断肢取代了极刑,而且法律中明文规定的阶级差异也被废除了。
不过,这段时期的真正重要性,在于一样类似于之后为人所知的新教的东西的出现,以及对捍卫超验价值的全新认识的首次尝试之中,这一源自东方之物对抗着南方之金牛。圣像破坏者对宗教艺术品的厌恶,随着新王朝一道从小亚细亚而来,而这里几乎就是当年的先知追随者们互相攻击的地方。726年,利奥下令全国捣毁圣像。巨大反应接踵而至:首都的暴动得到了伯罗奔尼撒的起义者的响应;而在意大利,拜占庭势力是如此之弱,以至于不到30年,拉韦纳总督区就落入了伦巴第人之手,而且罗马教皇也与帝国撇清了关系,转而向法兰克国王丕平寻求保护。这几个南方的希腊省份被报复性地安排在了牧首的教权管辖之下。与此同时,随着君士坦丁五世的继位,民众宗教信仰的结构在法律对圣徒遗物、圣母崇拜和圣徒代祷的进攻下危在旦夕。皇帝坚定不移的信仰制造了一起起针对偶像崇拜的修道士的迫害。但是在787年,伊琳娜女皇为了夺取皇位转而恢复圣像崇拜。
然而,东方狂热者的失利只是暂时的。815年,随着亚美尼亚人皇帝利奥五世的登基,圣像再度遭到禁止,而修道士们决不妥协的态度,再加上他们不断积累的国民财富和人力,也又一次导致他们遭受迫害和遣散。但是帝国的宗教生活还是发生了变革:斯图迪奥的狄奥多(Theodore of Studium)修士的修道院改革预示了克吕尼改革的到来,它注定会对整个欧洲产生深远的影响。这场改革不仅形成了一种相比从前更加有序积极的苦行生活,而且为教会灌输了一种从国家权威那里完全解放的思想。受此启发,修道士们转而求助于罗马教廷,因为在那里,神学问题的至高无上性还未被动摇。可是,这反而使得针对他们的毁坏圣像的暴力行径愈演愈烈。不过在843年,人们还是获准“敬重”偶像了。最终,这一由对偶像崇拜的争辩所引起,并由800年教皇加冕查理曼大帝为西罗马帝国皇帝而加剧的与罗马的不和,在867年达到了顶峰,形成了一场正式但又暂时的教会分裂。
因此,从形式上而言,保护基督教精神传统不受地中海地区唯物主义诱惑的第一次斗争以失败而告终。所幸的是,拜占庭艺术和欧洲绘画的萌芽被保存了下来。此外,毁坏圣像运动净化并唤醒了希腊人的智慧。若是没有这次运动,世界可能永远无法见证拜占庭艺术所成就的绘画表现与形式主义的完美结合。从当时来说,斯拉夫人在塞萨洛尼基传教士的影响下皈依基督教并且传承了其文化,而凯撒巴尔达斯(Bardas)又建立了君士坦丁堡大学,这些已经为富有品味和知识的文艺复兴埋下了伏笔,而这也为帝国盛世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第五段时期为867年至1057年,这段时期只有一个朝代,它的建立者是米海尔三世的亲信马其顿人巴西尔一世,他杀害了米海尔三世夺取了皇位。
在欧洲历史上,除了瑞典的瓦萨王朝,或许就没有一个朝代能像这一系世袭统治者和他们的军事将领们那样,统治时期长达两个世纪之久。这段时期的帝国疆域最为完整;而且在长达百年的时间里,这支受到基督教及其文明所鼓舞的战无不胜的君士坦丁堡军队,将穆斯林军队赶回了库尔德斯坦的要塞。四个亚洲军区被收复;而在北方,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被迫放弃穆斯林宗主权而听命于拜占庭,前者最终还在11世纪初被完全并入了拜占庭的版图——不过这种失掉前线缓冲地带的行为马上就被证明是极为不明智的。在9世纪70年代,巴西尔一世收复了西里西亚和卡帕多西亚。在10世纪,帝国的疆域又拓展至了两河流域。从此以后,战斗的中心就转移到了塞浦路斯北方的直角形海岸附近了。在尼基弗鲁斯二世·福卡斯(Nicephorus II Phocas)和约翰一世·齐米斯西斯(John I Tzimisces)的率领之下,阿勒颇、安条克、伊德萨、大马士革和贝鲁特被攻占了。961年,克里特岛的收复使得希腊人再度获得了爱琴海的控制权。拜占庭军队眼看就要解放耶路撒冷。
在西线,胜利的欢呼声同样响亮。从889年至924年,保加利亚沙皇西美昂一世试图称霸巴尔干半岛,他已将战争带到了君士坦丁堡城下。在他死于927年之后,斯拉夫人一直按兵不动,直到基辅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Sviatoslav)的出现才打破了这一局面。这股势力在970年被约翰一世所击败,整个国家直到多瑙河都被帝国所吞并;直到下一个十年才被撒母耳沙皇夺回。因此,“保加利亚人屠夫”巴西尔二世才开展了一系列著名战役,使得保加利亚人一败涂地,并在1014年灭绝了这一民族的所有男性成员。如今,整个巴尔干半岛都臣服于帝国的统治之下;而这位皇帝最终在雅典那已改为基督教教堂的破败残缺的帕台农神庙的金色石柱下举行了凯旋仪式。同样在意大利,阿拉伯人的入侵为拜占庭的干预提供了借口。从915年至1025年,从半岛南部,至教皇国边界,全都承认了帝国的宗主权。
东正教与天主教之间的关系最初并不尽人如意。由于米海尔三世的摄政王凯撒巴尔达斯品行不端,使他招致了伊格纳修斯牧首(Ignatius)的责备,后者因此而被免职。代替他的是博学的佛条斯(Photius),此人因其在古典哲学以及从医学到农学等所有的现存文献上渊博的学识。在他保存下来的图书馆中,人们发现了其许多重要作品,但都难以辨认,而使他在首都上流社会颇有影响力,这也解释了他何以在神职上平步青云。罗马教皇拒绝承认他的地位,再加上一系列争取保加利亚人的秘密阴谋,导致了教会的分裂。佛条斯挑起争执的神学,依据就是谴责罗马教会把“和子说”(即表示:“圣灵是由圣父和圣子而出”)(Filioque)加入教条,称此为异端,因为它意味着圣灵不仅出自圣父也出自圣子,这恰恰与希腊人对个人抽象交感的纯洁性的情结相悖。巴西尔一世登基后,罢免了佛条斯,不过5年后他又被召回了。直到898年,东西教会才得以和解,互相真正认可则是920年的事了。这一状态一直持续到了王朝末年。
在国内,商店、贫民窟、澡堂、宫殿、花园、教堂和修道院鳞次栉比,上帝保佑的君士坦丁之城,臻于繁荣盛世,军人皇帝在国外的武功相映生辉。三大洲的财富,从古罗斯的滚滚江河,从印度和中国途经特拉比仲德,沿着商道涌入了黎凡特和黑海地区,汇聚到这块当时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城市的财富又成就了一种建筑和艺术上的壮丽辉煌,拜占庭人心中神秘主义的悸动——这份对神圣之物的执著——又使其变得更加高情远致。在国外,罗斯人皈依了基督教;而在基辅,在第聂伯河这条商贸干线河畔,对拜占庭文明的有意接受使得一个全新的民族得以形成,这也使其形成了一个带有自身特色的文明。
在帝国内部正孕育着各派新势力,某些牧首和封臣的独立已让帝国颜面尽失。在帝国之外,塞尔柱突厥人正在东北方集结。而在意大利中部,代表着贪婪掠夺的诺曼人则将要效仿他们的同胞在黑斯廷斯的胜利。
1053年,狄奥多拉女皇这位巴西尔一世最后一位后裔的逝世,标志着帝国历史上第六段也是最错综复杂的一段时期的开始,而十字军在1204年占领君士坦丁堡和尼西亚流亡政府的建立标志着这一时期的结束。
拜占庭国家的基本实力已经产生了动摇。马其顿王朝的皇帝们遵循着伊苏利亚王朝的方针,企图继续削弱亚洲权贵的力量,因此而造成了大规模的起义事件,直到“保加利亚人屠夫”巴西尔二世才将其平息。马其顿王朝终结之后,封建家族争夺皇位的斗争就接踵而至。直到30年之后,在1081年,阿历克塞一世·科穆宁登基,以及其子及其孙的接续统治,才为这个依然是欧洲最强且唯一拥有文明生活,但却为强弩之末的国家,注入了新的活力。与此同时,官僚组织,在封建内战和源远流长的外部入侵的双重夹击下,几乎摇摇欲坠。一种古典文化的复兴也体现在了某种不切实际的政治风云中。一场针对半独立的小亚细亚兵团首领的反军阀运动,致使边防要塞遭到忽视,并且形成了一种青睐使用外国雇佣军而削减当地人部队的倾向,而这些雇佣军本身就善于见风使舵。在海上,通过出卖贸易优惠权而换取军事保护的灾难性政策,破坏了帝国的贸易,而且运送十字军战士来攻打拜占庭帝国的就是这些商船。早在这一时代之初,封建斗争,再加上柏拉图主义者普赛罗斯(Psellos)领导的知识分子派系所引起的恶政,就成为了1071年曼奇刻尔特(Manzikert)之战毁灭性失利的原因。这场战役之后,帝国失去了几乎整个小亚细亚,爱琴海沿岸第一次出现了突厥人的踪影。
随着11世纪历史进程的发展,穆斯林的团结力量,在什叶派异端的侵扰和巴格达哈里发无能统治的破坏下,走向了分裂的边缘。不过穆圣的传人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1055年,奥克苏斯河(Oxus)之外一支新兴民族的首领突格里勒贝格(Toghril Beg)被哈里发立为苏丹。从1063年至1091年,塞尔柱突厥人在不断地扩张。亚美尼亚首府阿尼城(Ani)连同南方的科尼亚(Konia)都落入了突厥人之手。前往御敌的拜占庭军队在位于埃尔祖鲁姆(Erzerum)和凡湖(Lake Van)之间的曼奇刻尔特被打得溃不成军,皇帝罗曼努斯四世·戴奥吉尼斯(Romanus IV Diogenes)也沦为敌人的阶下囚。10年之后,希腊人对小亚细亚的控制仅仅限制在了黑海和爱琴海狭长的沿海地区。帝国最富饶的省份变得荒无人烟,城镇被毁灭,农田也无人照看。最糟糕的是,帝国就这样永远失去了其最主要的兵员补充地。

在曼奇刻尔特之战同年,突厥人占领了耶路撒冷。这样一来,迄今一直被阿拉伯人和平对待的基督教朝圣者如今也无安宁之日了。于是,西方那诡秘莫测的骑士精神以及对土地的迫切渴望便找到了一条新的发泄渠道。皇帝阿历克塞一世·科穆宁在十字军的帮助下,成功地收复了尼西亚、士麦那和远至安条克的安纳托利亚西岸和南岸全部地区。在对抗如今已分崩离析的塞尔柱帝国时,阿历克塞之子约翰二世·科穆宁继续将拜占庭边界向东推进。但是其继位者曼努埃尔一世虽然在其在位早期小有成功,可最终却于1176年在密列奥塞法隆(Myriocephalon)大败于突厥人。而随着萨拉丁在叙利亚建立政权和耶路撒冷王国在11年后的覆灭,穆斯林之潮也卷土重来。
这不过是一股势将毁灭半个欧洲文明并将推进到维也纳城下的力量最初的小试牛刀。与此同时,一只更加迫在眉睫的命运之轮正从西方向君士坦丁堡疾驰而来。
在整个马其顿王朝时期,拜占庭在物质上取得的骄人成果也反映在教会的精神领域。牧首的权力相应地有所增加,而罗马教皇的力量却大不如前;若不是克吕尼改革唤醒了教皇的自我独断意识,东正教会实际上独立自主的现状很可能在理论上也能得到承认——只要他们愿意。然而在1049年,改革者利奥九世被选上圣座时,正值米海尔一世(Michael I Cerularius)任牧首一职,后者违背了外号“单打独斗者”(Monomach)的君士坦丁九世的意愿,故意挑起了关于意大利南部主教区归属的争端。使节被派去东部首都,将一张充满恶言詈词的诏谕放在了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圣坛之上。牧首则受到群众狂热拥护的鼓舞,而经过全面商讨批准了这场由他一手策划的分裂——而且经证明这是一场永恒的分裂。这是历史上一场意义无法估量的事件。从此以后,在天主教教义中,希腊人就再也不是基督徒也非教友了。而在那个年代,天主教和日益西进的封建主义基本上是如影随形的。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发起于1095年的克莱芒会议(the Council of Clermont)。次年夏天,“隐士”彼得抵达君士坦丁堡。在这一世纪中期,拜占庭人就已经与意大利南方的诺曼人发生接触,而后者通过在1071年占领巴里(Bari)将他们从这里驱逐了出去。10年之后,罗伯特·吉斯卡尔(Robert Guiscard)就已越过亚得里亚海来到伊庇鲁斯,深入到了马其顿和色萨利等内陆地区。因此,阿历克塞一世·科穆宁及其臣民理所当然地会认为,这群举止粗鲁、目不识丁,成天吹嘘着自己那暴发户血统的诺曼人所秉承的神秘的宗教理想,以及这群士兵对圣物匣的这份献身精神,根本无法补偿他们在行军途中以掠夺村庄为生所造成的损失;更何况第一次以及接下来的数次十字军东征的初衷,在这场势将——最终也确实做到了——给爱琴海地区输入一种外来封建主义的政治运动之下,也早已变得暧昧不清了。帝国将仅存的兵力调离了东方。帝国重心首次被西方吸引过来,另半边的欧洲注定会用这数百万条张牙舞爪的触角将世界团团围住,“东方问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
皇帝阿历克塞一世眼见无法躲避这些入侵者,便决定利用他们。作为对金钱和补给品的回报,十字军国家的首领们答应把从穆斯林手中夺取的之前属于帝国版图内的城市归还给帝国。但是在归还了尼西亚之后,这些诺曼国王们却扣留了安条克、耶路撒冷以及许多小城镇。作为对皇帝反对这项破坏协议行为的报复,安条克的博希蒙德(Bohemond of Antioch)组织了一支针对希腊首都的“十字军”。但他最终还是不敌阿历克塞,只得羞愧求和,隐退于意大利。
1147年的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由霍亨施陶芬家族的康拉德三世和法国国王路易七世领导。他们各自的追随者们在希腊领土上一路奸淫掳掠,最终却在突厥人面前一败涂地,还被他们的领导者抛弃在小亚细亚南岸自生自灭。两者都曾计划在途经君士坦丁堡时对其发动进攻,但最后都不了了之。
几年之后,皇帝曼努埃尔一世·科穆宁收复意大利南部部分地区,他受此鼓舞而制定了恢复查士丁尼时期帝国版图的计划。东方的几个拉丁公国被迫承认其宗主权。只有他才有足够财力支付外交贿赂,这使得欧洲半数国家被牢牢地捏在了君士坦丁堡的手中。1182年,诺曼人摄政女王安条克的玛丽(Mary of Antioch)不得民心,导致了一场针对君士坦丁堡外国居民的大屠杀。7年后,腓特烈·巴巴罗萨皇帝所领导的第三次十字军东征部队遭到了拜占庭人的公开攻击。与此同时,一支诺曼—西西里人舰队以残暴的方式洗劫了萨洛尼卡。而在1197年,亨利六世皇帝差点就在临死前对拜占庭宣战。西方的全部力量正熊熊燃烧着那些敢于抵抗其入侵和否认其教皇的人们。而这时出现了一位流亡的皇位觊觎者,他四处为其被废黜皇位和沦为阶下囚的父亲寻求帮助,这就足以将原本计划进攻埃及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目标引向君士坦丁堡了。
这次东侵的两位鼓吹者,蒙特菲拉特公爵伯尼法斯和威尼斯总督瞎子恩里科·丹多洛,两者都没有能够活着回到故土。威尼斯为此次东征提供运兵船只。1203年7月,远征军和平地入驻君士坦丁堡,可是当他们帮阿历克塞四世恢复皇位之后就露出了真面目。这群十字军战士一旦立稳脚跟,就开始为他们从未履行过的职责漫天要价。1204年,市民们为统治者屈从于拉丁人而愤怒,将其推翻,取而代之的是“忧郁者”(Mourtzouphlos)阿历克塞五世。拉丁人下定决心要发起第二次进攻。4月12日,这座城市首次被攻破;将近9个世纪的财富,再加上君士坦丁大帝从世界各地收集的艺术品,毁于一旦。土耳其人1453年攻陷此城不过是这次灾难的必然后果。对全人类而言,历史上没有比这次灾难更加不幸的事。一代欧洲文明就这样奄奄一息了。其12世纪的继承者在贵族、民族和崇古的偏见面前束手无策。受其恩泽的民族和土地如今即将步入长达7个世纪之久的贫穷、无知和奴役。
……

土耳其人由于一直受到1242年以来由成吉思汗领导的蒙古人大迁徙的影响,长期以游牧民族的形式分散在小亚细亚各处。在奥斯曼的领导下,土耳其人国家得以形成,并于之后以他的名字命名。在奥斯曼之孙穆拉德(Murad)统治时期,土耳其人受到一种宗教狂热的影响,使他们充满了一种远远大于世俗野心的激情,而这种激情也将体现在其随后的做所作为中。1306年,他们穿越了欧洲,渐渐蚕食了整个巴尔干半岛。1385年,索非亚放弃了抵抗。两年之后,塞尔维亚人在科索沃战役中一败涂地。这时,西方才顿感大事不妙。教皇伯尼法斯九世发起了一场新的东征计划,却使得一支泛欧洲军队在多瑙河畔的尼科波利斯被彻底击败。1399年,皇帝曼努埃尔二世·巴列奥略出访西欧各国,甚至去到伦敦,以寻求援助。就在其外出期间,君士坦丁堡已被团团包围。末日似乎已经迫在眉睫,但是帖木儿的鞑靼大军突然在安卡拉击溃了土耳其人,这让拜占庭人获得了一个喘息的机会。

双方相安无事了20年。而在穆拉德二世的领导下,土耳其人再度向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和伯罗奔尼撒推进。1430年,萨洛尼卡失陷。皇帝约翰八世·巴列奥略毅然决定为获取西方同情而做最后一次努力。在皇帝、教皇和一些东正教会与拉丁教会主要神学家经过冗长的讨论之后,东西教会于1439年在佛罗伦萨又再度牵手。不过这一努力还是无济于事。君士坦丁堡的人民再次表达了拒绝接受的意思。1444年,因这次牵手而组建的援助部队也在黑海西岸城市瓦尔纳(Varna)遭遇不测。而在1448年,另一支西方援军在第二次科索沃战役中几乎全军覆没。幸而,当欧洲劳师无功时,希腊人却总能一如既往地凭借其城墙坚守阵地。1451年,穆罕默德二世成为了奥斯曼帝国的君主。他立即着手准备对这座让他如坐针毡的城市发动总攻。他请人制造了一门巨炮。人们从奥斯曼帝国的四面八方被调集参战。在城内,君士坦丁十一世召集了8000人从海上和陆上防守14英里长的城墙。攻城战整整持续了53天。1453年5月29日清晨,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的末代皇帝为自己及其臣民的名誉而战死沙场。
不过,在黑海边的特拉比仲德帝国和位于伯罗奔尼撒的米斯特拉专制君主国中,希腊人依然在负隅顽抗。前者在1461年被征服。而在后者的教堂壁画上,在埃尔·格列柯笔下趋于成熟的绘画艺术的复兴,业已依稀可辨。但是这个希腊文明的前哨战在1460年屈服了。中世纪到此结束,连接现代与古代的拜占庭时代也终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