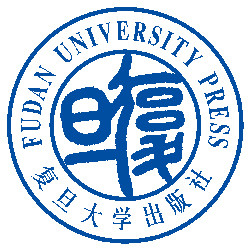炎黄时期的女性形象
炎黄之前的女性故事,主要是母系社会的生殖崇拜神话,如抟土作人的女娲,生育了伏羲的华胥氏女,生下了炎黄二兄弟的女蟜氏等。至炎黄与颛顼时期,从各位“天下共主”都为男性来看,当时已进入完全的父系社会。再从颛顼氏立法,妇女当避让男子于道路,黄帝“别男女”等记载看,男尊女卑的观念也被认为萌生于这一时期。然而作为阴阳之一方,女子半边天的社会作用仍没有消失。所谓“男耕女织”,“农”与“桑”并称为“农桑”,即是妇女作用依然被认可的反映。
先蚕氏嫘祖、帝女桑与嫫母

黄帝元妃西陵氏曰嫘祖,以其始蚕,故又祀先蚕。(《路史·后纪五》)
黄帝正妃嫘祖开创蚕业,故后世祀为先蚕氏。
不过所谓嫘祖始作蚕,见于《山海经·中次十一经》:视水之上——
有桑焉,大五十尺,其枝四衢,其叶大尺余,赤理,黄华青柎(跗),名曰帝女之桑。
帝女桑的传说又与炎帝女有关,《搜神记》《广异记》等都载有相关故事,综合起来,大致为炎帝长女仰慕仙人赤松子,随之风雨上下,至昆仑,后亦得仙,居于南阳愕山桑树上。正月一日,衔柴作巢,至十五日成。或化作白鹊,或显身为女人,炎帝见状悲恸,劝诱她回来而不得。于是就焚烧这株桑树,帝女就升天了。因此后世称这株桑树为“帝女桑”,民人每至正月十五日,就焚鹊巢作灰汁,“浴蚕子招丝”,就是纪念这位帝女的。
这一系列神话,已将桑蚕的发明推前到炎帝时代了,而其来源,又当与一种更古老的蚕丝记载相关联。《山海经·大荒北经》记:
欧(呕)丝之野在大踵东,一女子跪据树欧丝。三桑无枝,在欧丝东,其木长百仞。
这则故事可注意的是所谓“呕丝之野”“三桑”,都应是野生的成片的桑树,而呕丝之女当为野蚕。这说明在家蚕养饲之前,先民已注意到野蚕吐丝了,也因此我们认为不必因嫘祖为先蚕氏而否认伏羲或神农作瑟琴的可能性。伏羲时既能师蜘蛛作网罟,那么取野蚕丝为弦就在情理之中。
呕丝者为女,恐不仅为男耕女织所致,《搜神记》有“太古蚕马记”的故事,大意为:
太古之世,有一位姑娘,父亲出征在外,陪伴他的唯有一匹雄骏的公马。姑娘担心父亲,对马儿戏说,你如能迎回我的父亲,我就嫁给你。马儿听了,就挣脱缰绳而去,果然找到了那位父亲,父亲骑上马,马儿却回望来处,不断悲鸣。父亲担心家中有事,便策马回家了。因此马有非常之情义,所以“厚加刍养”,谁知这马儿从此不肯吃草料,每见姑娘出入,就“喜悲奋出”,十分兴奋。父亲感到奇怪,就问女儿,女儿就一五一十告诉父亲前因后果。父亲大怒,恐羞辱家门,就射杀了这匹马,将马皮晾晒在庭院中。一日,姑娘于马皮下嬉戏,对马皮说:“你是畜牲,而想娶人妇,所以遭到屠宰剥皮,又何苦来呢?”言犹未尽,马皮跃然而起,卷起姑娘就出门而去。几天后,父亲寻至一棵大树下,发现女儿与马皮已经化为蚕,在树上吐丝。所结出的蚕茧尤其厚大,不同一般,异乎寻常。邻妇取而养之,其收获数倍于常,因此名这棵树为“桑”。桑,就是丧(丧女)的意思。“如此,斯(那里)百姓竞相种之,今世所养是也。”
这个故事可注意的有两点。一是所记“桑”的得名与由“种”到“养”的过程。此前的蚕茧很小,当为野蚕,养蚕业则经由“种”桑养野蚕到家养的过程,而蚕丝的利用当在“养”蚕业兴起之前。其二,故事的时间为“太古”,地点则未明言。《搜神记》稍后的《中华古今注》(多取晋崔豹《古今注》)略同,至唐代的《墉城集仙录》等始具体化而称“当高辛氏时”,此时蜀地未立君长,蜀山氏独王一方,蚕女旧迹,“今在广汉(今属四川)”。这里所述时间是矛盾的。高辛氏即帝喾,在周人所造,汉人所传的帝系里是黄帝曾孙,五帝其三。然而这与当时蜀地未立君长不合,巴蜀最早的君长为传说中由洞穴走出来的廪君,其时代绝不可能晚于人文初肇的黄帝。蚕女传说由“太古”转为“高辛氏时”,应当由于帝喾传说与商人的天帝“俊”传说混杂而所致。最明显的是《世本》所记帝喾四妃,前三位为周弃之母姜嫄,商契之母有娀氏女简狄,唐尧之母陈锋氏女;而最后一位生挚(少昊名)的常仪,就是帝俊的那位生了十二个月亮的常仪(羲)。神话学家为帝俊、帝喾甚至还有更后的舜的关系常争讼不休,其实是商人奉帝喾为先祖,遂把原是天帝俊的神话加在了喾的身上,也因此会有畲族神话中置换了女娲来补天的高辛氏。至周代造作黄帝一系的五帝世系,又把显赫而本非周族的颛顼、帝喾也拉了进来,问题便更形复杂而几乎无解了。要之,唐人以“高辛氏时”代替晋人的“太古”,是把帝俊与帝喾混杂所致,所谓“高辛氏时”,当为“帝俊时”,也就是晋人所说太古之时了。不过唐人所指“蜀地”颇可注意,这反映了古巴蜀为蚕桑业兴起的重要地区。我们指嫘祖之西陵氏地或为西陵峡的推想,这也是依据之一(又《世本》记颛顼为蜀山氏女之子,亦可作为上述推想之参证)。
神话悠谬,所推测也仅是尽可能合理的想象,然而悠谬之中仍透露了蚕桑业形成的历史轨迹,这就是:
野蚕吐丝结茧,似蜘蛛吐丝结网一样,是多地初民早就注意到的自然现象。野蚕有生于其他树木,如柞树上的(柞蚕),有生于后来名为“桑”的树木上的。因某种机缘(如马头娘故事所述),发现食此“木”叶之蚕所结茧远大于食柞者,于是种此树而放养蚕儿于此木间;并因某女因此事而丧,故命此木为“桑”,并进一步摘桑叶而家养之,放养时代称“种蚕”,而家养之时称“养蚕”。又因养蚕,桑树多种于宅边,另一种宅边树为梓,故桑梓又成为故乡之代称。种、养以逐步驯化蚕的时间,从“帝女桑”与嫘祖故事看,当在炎黄之际,而黄帝娶嫘祖,或以有“织维之动”(《黄帝内经》),即于丝纺有重大贡献,故后来居上成为先蚕氏。嫘,女、累为字,累即积丝成线之意,这个名字可为上说参证。
嫘祖另有一个尊号为“祖神”,祖为路祭,相传嫘祖从黄帝巡游四方而死于道,黄帝祭之为“祖神”,也就是佑护行路之人的神道(《云笈七签》引《轩辕本纪》)。这故事的寓意应同于周弃死于行道之中,是为民劳瘁而死的。
黄帝之妃据说有四位(古书多有四妃、四子、四女等称,这应与四方观念有关),其中有一位次妃也很有名,叫嫫母。综合《轩辕本纪》《帝王世纪》等记载:嫫母极丑,额头似锤,鼻梁似蹙,形粗色黑,像驱鬼时所用面具,然而貌丑德高,黄帝娶了她,让她训导后宫。后来亦随黄帝巡游,嫘祖死,为祖神,帝又令嫫母监护于道,岁时祭之,后人因此以嫫母为方相氏。
嫫母为方相氏的说法出于《云笈七签》,显为后世道士的附会。方相氏是见于《周礼·夏官》的驱疫之神,“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明显是位威武的男性神。后世驱疫戴面具扮方相氏,这面具叫魌,或魌头,形丑,故附会丑而贤德的嫫母为方相氏。她死后也要服侍正妃嫘祖。虽然如此,嫫母与嫘祖为黄帝四妃中有事迹可传的二位,却反映了古代所谓妇德的观念,在“德、功、言、貌”四事中,以德、功为要,德为首,故嫫母以德而虽丑得传,嫘祖有德更有事功,故为正妃,而一应记载从未涉及嫘祖是否有言有貌,因为“女子无才便是德”,言,不是必须的;至于貌,则弄不好便成妲己、褒姒这样的“女祸”,所以不必为嫘祖所必备。当然,这都是汉人的观念,所以有关嫫母的记载都是汉以后的。
瑶姬与巫山神女——帝女灵

(鼓钟三山)又东二百里,叫作姑瑶之山,“帝女死焉”(天帝之女死于此),她的名字叫“女尸”,化为瑶草,叶片相重叠,它开黄花,果实像菟丝,“服之媚人”(吃了它会被人所爱)。
所谓“姑瑶”之山,其名当来自女尸所化瑶草,姑瑶即“瑶姑”,是瑶姬一名的源头。
姑瑶转变为瑶姬,天帝指实为黄帝,当始于战国楚辞作家宋玉的《高唐赋》,说是赤帝女巫山神女对楚襄王言:“我,帝之季女,名曰瑶姬,未行(出嫁)而亡,封于巫山之台,精魂为草,实曰‘灵芝’。”(参《襄阳耆旧传》)
宋玉赋所记于《山海经》有两点变化。一是地点,《中次七经》所记诸地大抵在今河南,姑瑶之山据前后各条推敲,当距少室山(嵩山)不远,而宋玉《神女》《高唐》二赋的背景是峡中巫山至湖北云梦二泽,云梦中有高唐之台。这应是炎帝族分为中原一支与西南一支的反映;二是由瑶草变为女人瑶姬,这变化的来由可从上述“姑瑶之山”的释义寻得;而所谓“服之媚人”更指示了女儿所化的媚人之草,又化为媚人的女人之演变的内在联系。由这二点我们可得出两点初步结论:
一是,瑶姬神话是上古原化(化生)神话的一种,其性质与为赤松子妻的炎帝女化鹊是一样的。
二是,宋玉赋虽为文人夸饰之作,但其脉理与《山海经·中次七经》一致。《山海经》尤其是最早的《山经》,性质是一种统合博物学与地理学的著作,所记必简,因此宋玉赋对于瑶姬身份的说法未必尽为文人好事,从战国之后此说广见于各书来看,瑶草、瑶姬很可能是神话原初状态时就有的成分。
据此两点,我们完全可以宋玉赋的描写来充实《山海经》所记。
宋玉笔下的瑶姬“未行而亡”(未及出嫁就夭亡)很重要,其深层意蕴且待下文介绍精卫鸟时再说,这里先说说这位“怨女”的形象:
帝女因未行而亡,帝哀之,封之于巫山。她身居“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云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虽然封了山神,但依然是这般的寂寞凄清。
楚襄王巡行至云梦之泽时,遥见一缕云气“崒兮直上”而变化无穷,宋玉告诉他,这就是传说中的神女之“朝云”,昔时楚先王曾游高唐观,“梦遇巫山神女自荐枕席”。次朝,遥望巫山,果然云雨迷蒙,于是为之建“朝云”庙。宋玉为之作《高唐赋》。后来神女又与襄王梦合,宋玉又作《神女赋》。后世称男女合欢为“云雨”,出典在此。
《高唐》《神女》二赋中的瑶姬是一位绝世美女,却又飘忽不定。“其始来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进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须臾之间,美貌横生:烨兮如华,温乎如莹,五色并驰,不可殚形……”总之是“茂矣美矣,诸好备矣,盛美丽矣,难测究矣;上古所无,世所未见”。这自然是辞赋家的渲染,但也见出神话对文学的影响。中国文学史上有三篇描写久旷女子的传世名赋,后来者无出其右。《高唐》《神女》即其二,第三篇是曹植的《洛神赋》,写的是伏羲氏女,她溺水而亡,化为洛神。由此足见古代神话对中国文学的启迪作用。
由瑶草(灵芝)至神女,由化生至爱情,是瑶姬神话的第一次转型,时间如前述在晚周;而至唐宋时期又完成了故事的第二次转型——神女成为助圣佑民的神祇,有两种类型,都由民间传说而来。
第一种为助大禹治水。其最终系统化为唐末文人道士杜光庭的《墉城集仙录》。杜记:瑶姬成为王母的二十三女,封为云华夫人。大禹治水时,至峡中,大风振崖陨谷。夫人因助之,召来狂章、虞余、黄魔、大翳、庚辰、童律等,助禹斫石疏波,决塞导厄,以循其流。大禹拜谢,只见,崇山峻岭间夫人化而为石,一会儿又倏然飞腾,化为轻云、夕雨,游龙、翔鹤——依然是那么飘忽不可踪迹。故事成型,虽在唐末,但其起源应当更早。证据是①:故事中所提到的庚辰、童律等诸神,同样见于大禹治淮水,降伏怪物“无支祁”的神话中,而无支祁故事据中唐人传奇称,得之于“文字奇古”,传为庚辰之后图形之的《古岳渎经》,也就是说为大禹治水的实录。②《全蜀艺文志》录有《神女庙碑》。碑记神女助禹凿三峡情状为:“百灵恐惧听指挥,巨凿震响轰雷车。回禄烈火山骨菹,垦辟顽狠如泥涂。”此碑作时虽未详,但神女庙即“朝云”宫,为宋玉时所建,且碑文古奥,因此可推想所据为三峡一带的民间传说,时代应在先唐。杜光庭应是将这一应有关传说作了道教化的改造而成为前述故事。
第二种是神女佑航传说。见于南宋陆游《入蜀记》、范成大《吴船录》等。说是神女庙有神鸦,客舟将来迎之于数里之外,船过亦送行数里。人以饼饵投之,神鸦仰首接衔,十不失一,因此名之曰“迎船鸦”。三峡激流险滩,历来视为畏途,神鸦迎送自然有导航越险之功。这类故事应起于三峡中的船工。
由瑶草至“未行之女”瑶姬,至助圣护船之神,瑶姬故事的本源与转型,其意蕴是相当丰富的。这里有对早夭的弱者的同情,有对于美的礼赞、爱的歌唱,有对于自然山川的敬畏,而这一切当然都与对于瑶姬之父——炎帝这位圣人的敬仰分不开的。
精卫与白额雁——帝女雀

(神囷之山)又北二百里,曰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漳水出焉,东流至于河。
发鸠山为太行山分支,在山西上党长子县西。精卫的“卫”字意同羽,箭羽称为“卫”,精卫也就是“精鸟”,即精诚之鸟。想来以卫代羽,或有以其心志如箭之直而无还的意思,所以《述异记》又记精卫曾自誓不饮其(所溺)水。“一名誓鸟,一名冤禽;又名悲鸟,俗呼帝女雀。”誓亦作“矢”,“誓言”多书作“矢言”,所以“誓鸟”之称是“卫”当释为矢羽的有力证据。
精卫填海故事的寓意,最通常也是最直接的意思是表现了先民与自然抗争,虽死而尤未悔的强毅精神。这自然是正确的,从精卫之名、之“誓”、之“志”便可看出。
然而如果更进一步探究还可以发现一些更深的内涵。
我们不妨由两个疑问来开始探讨。
一是女娃为什么游于东海而溺亡?二是精卫究竟是种什么鸟?这两个问题是相互关联的。我们先来看第二个问题。
从“发鸠之山”来看,精卫应当是鸠类之鸟。《左传·昭公十七年》述少昊氏鸟历,在历正凤与四司玄鸟、伯赵、青鸟、丹鸟后,更列有五鸠等不同职司鸟。鸠的意思是纠正以安民,所以五鸠都任高级的民事官。五鸠之一为鸤鸠氏,鸤鸠又作尸鸠,又有多种别名,其中有六个很可注意——鸣鸠、怨鸟、杜鹃、子规、阳雀、布谷。尸鸠合乎女娃溺海而化,鸣鸠合于《山海经》所记“其鸣自詨;怨乌合于”,《述异记》所称此鸟又名“冤禽”。可与此合参的是杜鹃、子规。子规即杜鹃,传为蜀帝望帝所化冤禽,夜啼至口血殷殷,尸鸠即大杜鹃。大杜鹃背羽黑色,与精卫“其形如乌”正相合。大杜鹃(尸鸠)是候鸟,随阳而飞,故又有“阳雀”之别称;大杜鹃,亦即布谷鸟,故又名布谷。以上尸鸠及其各种别称与精卫鸟太相似了,又,尸鸠在“鸟雀”系统中为“司空”,司空之职其初为主管工程,亦与精卫填海的“大工程”可相联系。所以,我们以为尸鸠(大杜鹃布谷)当为精卫原型的第一位候选“鸟”。
以精卫为尸鸠的唯一看似不周之处为精卫“其鸣自詨”,即自呼其名,布谷的鸣声似“布谷”,似与“精卫”之音不合,不过自呼其名,可以而且更合理的解释是自呼其原名“女娃”,这才合乎上古自招其魂的习俗。女娃之“女”指性别。女娃的名字其实只有一个“娃”,娃与谷古音均近于娲,因此精卫自呼其名的声音应近于古音娃(娲),这就可与“布谷”的鸣声对上号了。
那么,尸鸠又怎么与填海扯得上呢?《述异记》的有关记载可解答此一疑问。说是女娃溺死东海后,“化为精卫,其名自呼,每衔西山木石填东海。偶海燕而生子。生雌状如精卫,生雄如海燕。今东海精卫誓水处,曾溺于此川,誓不饮其水。一名鸟市(疑当为“沛”字去三点水),一名冤禽,一名志鸟,俗呼帝女雀”。
这就是说,精卫鸟与海燕交合而生有雌雄二鸟,其搏击海上者为雄鸟精卫,而居山自鸣“布谷”者或为雌鸟。这样精卫鸟就更为可敬了。它一方面自誓而填海不已,一方面又随阳而至帮助神农催促着人们不要忘了播种——这两种工作,又以尸鸠、海燕结合,子孙相传而子子孙孙永无穷尽。
《述异记》的记载有一定现实依据,因为我国的海燕均在东南沿海,毛羽灰黑,与精卫相近,故以海燕的特征赋予了精卫。虽然《述异记》为南朝梁任昉所作,为后出之书,但所记有如下启发。
一是精卫鸟的原型应以尸鸠(大杜鹃布谷)为主而参合了海燕的特征;
二是显示了中华民族改造自然,不畏艰险而世代相继的强毅精神。试想,一只娇小的鸟儿搏击于惊涛骇浪、万里无垠的大海之中,世世代代,不休不止,是何等地壮丽而可歌可泣。这一点正与愚公移山精神相通。
由似海燕的雄精卫填海,又可对精卫故事的又一疑问,女娃为何东游于海,作进一步的探究。
尹荣方先生的《神话求原·精卫填海与大雁衔枝》对精卫的原型提出了一种新见解——白额雁衔枝跨海。白额雁,身黑,嘴边头额处都有白色横纹,与精卫鸟如乌而文首、白喙相合。白额雁也是候鸟,在西伯利亚繁殖,迁我国长江下游一带越冬,中经山西与渤海碣石一带。雁儿跨海常衔尺许长树枝,疲倦时即将所衔树枝浮于海面,栖浮枝之上暂息。日本奥州边界,每年雁所衔来的树枝堆集,乡人集为燃料,以煮浴汤,谓为“雁浴”。又有传说,山西北边,每年鸿雁来时,常落下口衔的枯木细枝,土人集以为薪出售,年值达白银五万两之多。后一说又与“发鸠之山”在山西上党可相联系。由此尹先生推断精卫原型当是白额雁。它们从西伯利亚经山西与渤海湾(当时尚无渤海,概称东海)至今东海之滨长江下游,一路丢下所衔树枝,这就启发了精卫的传说。
尹先生的推断虽尚有些欠周之处,比如怎样解释“发鸠之山”,山西之雁是否为白额雁,“冤鸟”“志鸟”“帝女雀”诸说又如何安顿等等。但仍不失为一种富于启发性的解说。白额雁可视为精卫原型的又一候选“鸟”。
这样有关精卫原型已经有了三种鸟:尸鸠(布谷、大杜鹃)、海燕、白额雁。这看来矛盾,但恰恰是神话产生的固有特点,它往往是多种生活现象的综合。我们认为由“发鸠之山”来看,精卫鸟当以尸鸠为主(后世发鸠山下有女神庙,侍女手擎白鸠,鸠儿预报漳水之涨,可为参证),揉合海燕、跨海之雁等多种勇敢的鸟类的产物;而所以归之于炎帝女所化,当是炎帝确有一女溺海而死,人们痛惜怀念这位夭亡的圣王之女,便综合数鸟特征,让她原化为神奇的精卫鸟。
将精卫鸟三种主要原型布谷、海燕、白额雁联系起来看,这种鸟不仅由冤禽提升至强毅、勇敢、利民的高度,更使“衔枝”除“填海”的意蕴外,产生了一种新的意蕴——跨海。“女娃”游于东海的“游”,即使最初级的,如今天所说的旅游,也含有见识新世界,也就是探求未知的意味。联系东海为炎黄时代的东“至”以及《山海经》中众多海外奇观来看,说女娃游于东海,是想探知“海那边”,应不算牵强。
精卫故事还会引起一些联想。
早期神话中,炎帝女娃之前的伏羲女,之后的虞舜二妃,都传说溺水而亡,且都化为了神,伏羲女化为洛神,舜之二妃化为湘水之神,神话学界有所谓反映“水难”之说,然而水难为什么多记女性,甚至治理水灾的神在早期也是女神女娲?我们认为这首先与初民认为水性属阴而柔,滋润万物的宇宙意识有关;其次与溺水女神神话产生的时代有关。相比于母系时代女娲理水神话之壮丽,溺水神话多产生于母系向父系转化的时期,故又添上几层怨丽、哀丽的色调。这种色调与禀承女娲传说的女性的强毅精神糅合在一起,表现了中华民族女性的性格特征:她们是强毅的又是柔美的。她们参与了人类对天地造化的改造,同时也以其水一般的柔情,在孕育生命、延续世代的过程中使原始的性欲升华而催生了“爱情”的意识。
(本文选自《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考述》,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