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空间︱“活的景观”:滨江空间与日常生活
自2017年底45公里上海黄浦江滨江空间贯通以来,时间已过去一年。2018年相继公布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黄浦江、苏州河沿岸地区建设规划》《黄浦江两岸地区公共空间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8年-2020年)》等规划文件,层层深入、具体细化,描绘了功能复合、协调发展的蓝图,开启了滨江空间“后贯通”发展的新契机。
以此上溯到2002年,黄浦江两岸综合开发启动以来,以往集中于黄浦江两岸的重工业、高能耗等工厂企业相继关闭或撤离,推动了全市产业升级和城市转型。过去以交通运输、仓储码头、工厂企业为主的格局,开始逐步朝着以金融贸易、文化旅游、生态居住为主的方向转变,逐步由生产型向综合服务型的功能转换与定位升级。
自此,黄浦江作为上海通往“现代性”的门户作用逐渐消失,滨江空间进入了一种“后现代”的格局:事实上,如果我们把各种隔断视为空间结构化的方式,那么“贯通”实际上就是一场去结构化的“解构”行为。通过对空间要素的重新组织,解除其中出于生产的要求而建立起的种种屏障;在此意涵下,滨江作为“公共空间”的区域定位亦是水到渠成。
从空间的社会性到社会的空间性
包亚明曾在《现代性与都市文化理论》一书中认为,城市中的公共空间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对市民开放;二是要有公共活动,无论其参与者范围的大小。这二者不仅对公共空间而言是必要的,而且共同构成了公共空间的充分条件,并因此构成公共空间的一个定义。
从惯常的“空间本位”角度出发,将这一定义应用于黄浦江滨水空间的讨论,不难得出类似这样的结论:滨江空间的贯通标志着第一个条件的达成,因而当前所需要的是利用好空间,为之赋予合适的活动内容。
但与此同时,这一定义还只是描述性的和形式的。从文学文本到世界经验,向我们呈现的往往不是某种预先给定的空间,通过向市民的开放和容纳公共活动的发生而获得了某种作为偶然性的“公共空间”身份;毋宁说,在过往城市公共空间的建构中,总是那些首先作为活动地点的场所随着活动的日常开展而建构。
秦淮河的历史属性不是通过某种外显的文本介绍进入到人们的思绪之中,湘西的水与吊脚也并不诞生于景观的组织。桨声灯影、摇橹唱歌的日常使之具有了烟火的气息。但如果说它们只是某种前现代或“现代化”过程中特定族群通过他们的视角所看到的社会景观,那么像是2000年开始,以阿姆斯特丹、柏林为代表的一些城市鼓励民间手工业者和艺术家进入毗邻河岸的空地,则借公共艺术活动的活力带动公共空间的生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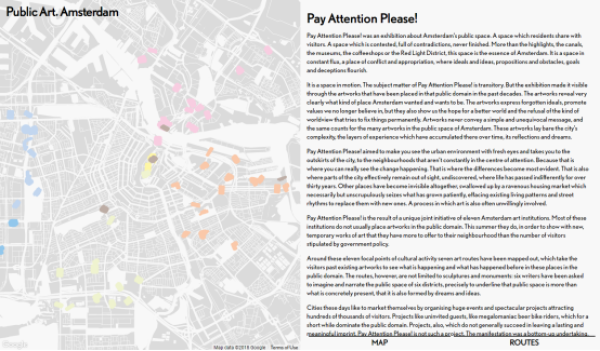
“请注意!”公共艺术活动地图 来源:https://publicart.amsterdam/en/pay-attention-please-2/
例如阿姆斯特丹,其主要滨江片段位于艾河(Ij River),靠近目前的市中心,公共资源集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港口的西迁,此片中心滨江带逐渐被占屋者及艺术家占领。此后,各种公共艺术在滨水区域遍地开花,使阿姆斯特丹的城市与艺术融合方面创立了一项传统。
值得注意的是,同今天遍地开花的“文创园区”和艺术“工场”主打各类“高大上”的设计理念和文化品牌不同,艺术家聚居区在其草创阶段往往同时也是“脏乱差”的代名词;由于当地政府和公众所给予的宽容,这些艺术家聚集区才得以通过一种表面的混乱塑造出鲜活的新秩序,从而带动了所在的滨水空间的更新。
诚然,人群的活动也可在规划的范畴之中,然而,正如教堂庙宇是出于宗教的目的建设,却也同时成为集会乃至交易的场所,并从而要求和带来专门的政治中心和交易市场;自上而下的规划与自下而上的聚集是公共空间的两种相互关联的生产方式,并不能以一者来取代另一者。
在描述的视角下,它们所带来的结果都可以满足上述的条件,但从空间中隐含的历史过程来看,往往是公开的活动生产出临时性的公共空间,而固定场所的建构与其说是公共空间生产过程本身,不如说公共空间再生产的条件的生产。
从列斐伏尔的观点中可以导出,对人来说有意义的空间,都同时是三重意义的复合:它既是物理的,也是精神的(即被感知和认识的),同时还是社会的。通过人在空间中的物质生产活动,物理空间得到了更新、维护,精神空间与之调适,而社会关系以此产生和维系。
通过将空间作为“社会关系存在模式”的基质(underpinning),未尝不可说列斐伏尔是将“空间的社会性”倒转为“社会的空间性”,明确了社会关系与社会存在所具有的空间性质。而“生产中的社会关系之所保有社会存在,以其保有空间性的存在为尺度;社会关系将自身投射到空间中,在其中得到铭写(inscribe),在此过程中产生出空间本身”,社会的空间依托和嵌合于物理空间之中,同精神的空间一样是对物理空间的逻辑和观念建构。

这样,包括滨水空间在内的城市空间,就不仅仅是一种通过组织社会活动来填充其内容的“空”容器,而本身应是一种积极构建的产物,也是对城市居民社会性存在的刻画。区域外的力量对滨水空间施加的规划与建造,其实质是对沿江一带展开的各种社会关系的重构,尤其是对沿江及周边市民生活状态的再组织。
“活的景观”及其三个尺度
已有的关于浦江两岸滨水空间的研究,主要关注三类景观:自然景观、历史景观和艺术景观。显然,这三种景观都是处在空间中、并以此标识特定区段的物。但从上述的理论视野出发,可以看到空间不仅是物的聚集(ensemble of things)。Potteiger等人注意到,调动激发在地人群的参与,才有可能建设起为民所用、为民所乐、为民所爱的滨水空间。他们将这种以人和活动(事件)发生为基本条件的空间设计组织形式总结为“景观叙事”,用以包含一系列积极寻求促进、激发各类活动和事件在公共区域的发生。
景观叙事将空间嵌入到人们的生活经验和地方记忆中,提升市民的获得感和游客的满意度。在实践上,它关注活动和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为其创造条件。但事实上,在所谓“活动”和“事件”的底层,还有一个行动的层面。这些行动之于空间就如同物质之于空间一样,是景观的构成部分。
仿照“活的空间”这一提法,我们应当说还存在一种建立在市民生活经验之上的“活的景观”(lived spectacular)。不同于主观的生活经验本身,它作为景观,处于他者凝视的目光之中;而它是“活的”,或更确切地说是生活方式的一个部分,在于成为这种景观同时也是一种有意的选择。
首先,“活的景观”体现在观景、跑步、玩耍等具体的行动上,而这些行动同时也是个体行为和集体活动的基质。而借助这一向“行动”的还原,我们也得以重新定位滨江公共空间的不足之处。

例如,从以往的“活动”视角看待滨江空间,就会诟病于目前滨江主要用作通道而服务于所谓“线性的活动”这一现实。但是合理安排的慢交通系统应当能够为自行车和行人创设和谐共行的条件,不同速度的运动,同静止闲坐的人一道构成活的景观,赋予原本匀质的空间以多重的节奏感。
公共空间用作通道未必不可,真正的问题在于,目前滨江空间设计中强调的“三道贯通”聚焦于基础设施之有无, “散步道”“跑步道”“骑行道”的引导标志虽然随处可见,三者间的相互关系却是模糊而混杂的,由而并不能有效地组织其好不同行进速度的人群,使之按设计者预想的情形构成节律。“活”态的要素得到真正的重视,恐怕还需假以时日。
而在此基础上,“活的景观”还意味着一种互为景观的状态。每个身在其中的人,既是这一景观的构成者,也受益或受限于这一景观。曾几何时,外滩有一道著名的“情人墙”。当时就有人将它看作是上海的一道“景观”,从而才为之命名;而还原到这一情境之中,每个人也自知是这一“景观”的一个部分,在一方面受限于旁人,在另一方面也得益于身处其中而获得的一定程度的匿名性,从中取得公众意见的允许。这种群体情境下个人行为的遵从与相合,正是前述自下而上的公共空间建构中秩序性的来源。
要让这种“活的景观”获得存在的可能从而真正带动黄浦江滨水公共空间的生成与活化,我们可以从如下三个不同的层面加以思考。

第一个也是最为直观的层面,也就是人身处滨水空间之中的层面。要使之成为可能,一方面它强调的是可达性,另一方面则是它的包容性。前者已通过公共交通与导向标志的逐渐完备而得到改善,而后者指的是让各年龄层次的市民游客和残障人士都可方便地享用这一滨水空间。但在根本上,其核心仍在于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空间在此展现出它的资源意义。
但随着空间物质设施的建成,并形成所谓的“存量空间”,目前我们所迎来的是第二个层面,也就是区域性的。它借助滨水空间的改造之机,改善市民生活环境,带动生活品质提升,促进城市产业结构调整,从而带动局部的城市更新。

在这一尺度下,滨江空间目前实质上的“通道”功能和它的“公共空间”愿景也不构成冲突,相反,正为愿景的实现提供了有利条件。“上海2035”提出,要“强化公共空间的贯通性,以慢行道、滨水空间、街巷与公共通道等为主,联系公共设施与文化遗产,构建公共空间网络”。
而2018年以来相继发布的两项规划也都提出黄浦江将更具引领性的复合功能,将滨江空间的纵深融合发展推上前台。以此观之,让公共空间向“阡陌纵横”中延伸,是符合现阶段实际情况,发展滨江空间乃至城市公共空间的有效途径,也是化解当前滨江空间较不充分的景观性,和功能性之间矛盾的可行方式。
最后,第三种层面是广域的,让滨水空间的景观成为城市的一个窗口,此时的景观已成为整个城市的象征。
人们或许会说,几乎自开埠之时起,浦江两岸就以当时极其有限的滨水空间而起到了城市名片的作用。但此时,外部的人们涌向城市时,所看到的“城市名片”还只是一种城市自身物质存在的标志物。要让逶迤流淌的黄浦江在整体上经由滨水空间的打造而成为一张名片,则意味着从“理想的城市”转向“理想的城市生活”。这就要求在黄浦江滨水空间在成为便捷可达的共享之地并区域性地产生影响的同时,还能够对整个城市的生活方式升级转型起到推动的作用,带出一种城市生活的典范形式。惟其如此,才可以称得上真正是“世界级”的滨水空间。
“活的景观”的实践塑造
滨江空间所取得的成就离不开对“景观”的高度重视,而其中目前暴露出的一些问题,也和对“景观”等同于“物的景观”这一片面理解分不开。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滨江空间的主要“症状”在于活力不足。2018年在徐汇滨江召开的人工智能大会,还有像上海马拉松赛这样大型的年度性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让人们发现滨江空间的潜能。然而仅仅依靠这些低频事件,对拉动长达45公里的滨江岸线空间的活跃程度而言是远远不够的。
这里的变化可以归结为“认识滨江”到“滨江与我有关”。这里的“我”既可以是“享受”公共空间的市民游客,也包括生活和工作在它周边的社群、机构雇员,乃至涉及到在整个城市中生活、暂留的人们。滨江空间应当邀请人们进入滨水空间、与滨水空间互动,并通过互为景观的状态参与到滨江公共空间的建构。

从媒体报道中可以看到,目前滨江空间中存在着许多负面的限制。《城市中国》曾在其公众号上刊发一则报道,汇集了滨江公共空间中的各种禁令标志。这样的禁令难免影响了市民游客利用滨江空间的兴致,也使市民难以自发地在此聚集和活动,削弱了长时间停留的可能性。
这里固然需要城市管理者发动智慧,实现从“堵”到“疏”在操作层面上的转变;但从原因上来说,造成这一局面的,短期来看是制止某些游人的不文明行为,而从长远来看,它体现的是公共活动设施的缺乏、休憩空间的供给不足,加上商业配套设施的不便利。这些负面因素在各种程度上削弱了滨江空间的吸引力,反过来又催生了一些不文明现象,或是产生出新的安全隐患。

滨江步道周边商业设施分类情况 朱恬骅 图
因此,目前滨江空间所暴露出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有效的公共空间供给不足,而市民游客对此的需求强烈。在单纯的空间建设之外,滨江空间还要产生出适合于它的“公共性”来。
考虑到目前滨江空间热点集中、冷热差异较大,距居民区仍有一定路程,而又不可能无限制扩张的现状,通过向既有的商业设施等延伸滨江的概念,提升空间的利用效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缩减和黄浦江的认知距离。例如,一些商业、办公建筑的底层可否开放通道作用?当消费性场所用高度换取滨江的感受,非消费性的公共场所是否也可以向纵深发展,运用好既有建筑的各类空间资源?

此外,增加公共空间供给不等于简单增加面积,让滨江空间成为某种新的“广场”。设计者在积极引入西方经验营造公共空间时,也应当对中国历史中的空间传统投以必要的重视,并使之现代化。
在中国古代,宽阔的空间场域大都作为皇权乃至自然神权的标志,是统治阶层进行祭祀、政治集会、阅兵的地点。《考工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这样的格局中,城市市民公共活动的中心和政治中心分离,其拥挤繁忙也和政治中心拥有的宽阔空间形成对比。
可以说,正是那种适宜于行人、适宜于停留的空间布局塑造了它的繁华,让它留得住“人间烟火”。相反,广场以其富于外来文化色彩的“纪念碑性”,对日常性产生了极大的压制,阻止了微观的日常生活。
现代意义上的“公共性”,在中国古典城市构造中发生的主要场域,存在于街道、集市,存在于“阡陌纵横”之中。因而中国人对公共空间的理解,与“广场”还是有所差异的。毕竟,只有当人们能够从滨水空间自如、自在地进入到城市的日常生活,真正共同享有了城市公共空间构筑的成果,和在此之上城市生活的经验,一种新型滨水公共空间的格局、一种城市中的生活方式才有可能得以完成。
参考文献
[1]包亚明:《现代性与都市文化理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
[2]王卓尔:《回到浦江——对滨江慢行系统及开放性的思考》,时代建筑,2017(4),第36–43页。
[3]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Donald Nicholson-Smith. Malden, Mass.: Wiley-Blackwell,1992.
[4]Potteiger M., Purinton J.: Landscape narratives: Design practices for telling stories. John Wiley & Sons, 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