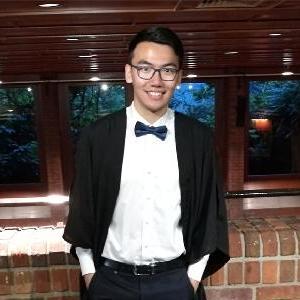当华裔、亚裔、中国人看《摘金奇缘》,他们看到了什么?
文|童辉
编辑|薛雍乐
“大家听好,”越南裔美国作家Monique Truong清了清嗓子,“我前段时间看到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新闻。我们的Crazy Rich Asians(直译为《疯狂的亚洲富豪》)将要在中国上映了,可他们竟把标题翻译成了什么什么‘摘金’?我们的女主角呀,摇身一变成了海外淘金女!”
台下的观众大概有两百人(大都是亚裔),大家发出哄堂大笑。
这一幕发生在10月底一场题为“《摘金奇缘》:种族、代表还是反抗?”的座谈会上。当今美国亚裔圈最成功的几位作家和编剧齐聚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对这部在美国引起了巨大轰动的电影进行了深入讨论。
我坐在哄笑的人群中,感到十分难堪。并不是因为我真的觉得“摘金奇缘”这个名字翻译的有多么不好、不准确——更何况, 纯粹从受众角度来说,这个译名直白道出这部电影有爱情、冒险成分,又是关于钱,每一条都足以戳到中国观众的关注点。
让我真正感到难堪的是,当《摘金奇缘》在美国被当作一场亚裔政治运动之时,当制片方把这部充满“东方色彩”的电影推向中国市场之时,仍有一堵巨大的壁垒,横亘在美国亚裔与中国大陆的文化认同之间。

切中热点的亚裔大片
《摘金奇缘》在北美上映前,我就被吊足了胃口。我们学校的书店把Kevin Kwan的原著三部曲摆到了最显眼的促销位上;我们学院的亚裔学生群里也有人发言,鼓励每一个亚裔学生去影院支持;打开推特,就能看到“全亚裔卡司”一类的标签被大量转发。毕竟,这可是继1993年上映的《喜福会》后,25年来好莱坞制作的第一部全亚裔演员阵容的电影。
于是,在院线上映的第二天上午,我就迫不及待地一个人跑去了时代广场旁的AMC影院。虽是工作日的十点场,但偌大的影院里仍有近三分之二的上座率。
这是一部纯好莱坞式的爱情喜剧电影。女主角瑞秋是纽约大学经济系的年轻教授,谈了个帅气的男朋友杨力。杨力带瑞秋回新加坡见自己的家人,蒙在鼓里的瑞秋却不知他的家族是新加坡第一富豪。在各种奢华欢乐的派对之间,瑞秋和对自己心存怀疑的豪门婆婆展开斗争,最终收获真爱。片中情节十分诙谐,令观众们笑声连连。
可走出影院的那一刻,我就对这电影丧失了额外的兴趣。除了几位主演偶尔冒出的蹩脚的中文、一些老生常谈的“中国传统”(如包饺子、打麻将)之外,这部电影似乎并没有与“亚裔”、“亚洲”产生什么联系。如果全换成白人演员阵容,故事似乎都行得通。
但关于它的讨论仍然主动找上门来。没过几天,一个韩裔同学和一个菲律宾裔同学就来问我对电影印象如何。“你们觉得呢?”我反问道。
“我感觉跟我们的生活也没什么联系呀,所以才来问你,”菲律宾裔同学面露好奇。
很遗憾,也许跟“华裔”身份更有关联的我让她失望了。“说白了,这仍然是一部美国人的电影罢了,”我叹了口气。

几天后,这电影又被提起了。“我特别好奇啊,”一个黑人同学试探地问道,一边用叉子努力插着我给他煮的速冻饺子,“你怎么看待《摘金奇缘》这部电影?”
我重复了之前给其他同学的答复。
但他仍然是感到不解:“说实话,我对亚洲人确实没有什么了解,我还真觉得这部电影描述的就是你们真实的生活状况呢。至少,包饺子那段很真实嘛!”
他回绝了我让他蘸口醋的邀请,吞下了一个牛肉馅饺子,竖起了大拇指。
而在与纽约许多年轻华裔、亚裔影视戏剧圈朋友交流之后,我才发现,不光是黑人群体给这部电影打上“亚裔”的标签,许多亚裔自己也把它视作一种“激励我们、令人振奋”的政治与文化运动。
他们确实有这样相信的理由。这部电影的美国国内票房超过1.7亿美元,全球票房累计超过2.35亿美元,进入了过去一年美国电影票房收入的前二十名。它的商业成功让更多亚裔制作得以成型。此前,有多部亚裔阵容、亚洲故事的好莱坞电影正处于筹备期,该片的成功推动它们直接进入了制作阶段,包括莉莉安·于编剧的《光棍节》,以及《摘金奇缘》续集。
真正的美国亚裔、华裔,究竟是如何解读这部电影所创造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影响?当我听说巴纳德学院邀请了凭《蝴蝶君》成为第一个拿到托尼奖的华裔编剧黄哲伦、著名越南裔小说家Monique Truong、亚裔主题专栏作家Jeff Yang、韩裔作家Marie Lee、曾与李安合作多次的制片人James Schamus等一起来讨论《摘金奇缘》的社会意义时,还是迫不及待地去礼堂占了个位子。

谁能代表亚裔发声?
奇怪的是,当近百分之九十都是亚裔的两百名观众济济一堂时,这部看似“为亚裔争气”的电影反而成了争吵的根源。
一个新加坡观众举手起身,用长篇大论表达自己的愤怒:这部设置在新加坡的作品,跟新加坡普通民众的实际生活毫无联系。片中突出的大多数角色都是华人,而新加坡其实拥有百分之三十的非华裔人口。于是许多新加坡人(尤其是非华裔)制作了各种讽刺视频来介绍真正的新加坡。
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所谓“亚洲人”也不开心。“疯狂有钱的亚洲人”似乎强调了其描绘的华人群体暴富、高调、挥金如土的负面形象,这既不是这些地区大多数人的文化背景,也和他们实际的经济状况相去甚远。甚至正是由于这部电影,华人在东南亚的经济优势,以及与社会大众发生分化的潜在矛盾被凸显了出来。
印度人也参与进来,表达对“亚裔代表”的不满。在场的一位观众高声质问:为什么这个富豪家族的两个门卫是“棕种人”,是不是华裔群体有意的刻板印象?为什么美国总是有意无意把“亚裔”等同于“东亚裔”?为什么这些在座的作家、编剧们,利用“亚裔”之名,行“东亚裔”之实?提问结束后,全场掌声雷动,台上嘉宾一脸尴尬。
而在所谓“东亚裔”内部,来自韩国、日本的人们似乎也被遗忘,本来已经很富有的他们根本没被纳入讨论的范围。
在这样的境况中,可能跟电影内容真正密切相关的华裔也感到深深的无力。华裔是美国亚裔群体中数量最庞大的一部分,本希望能通过努力为整个亚裔群体发声,但最终却受到了更多的质疑。
一位纽约当地的华裔动作演员Johnny Wong讲道,虽然他因为《摘金奇缘》感到非常振奋,但也深深体会到,不同亚裔群体的身份认同点完全不一样,这种疏离感让他无所适从。最终的结果是,他更愿意与白人群体接触,成了一个真正的“香蕉人”。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有些讽刺的现象: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亚裔内部的族群对这部电影内容本身感到满意。

在美国的舆论场上,“亚裔美国人”常常作为政治词语,用来“一致对外”、争取共同利益,但这种团结往往反而暴露出了分裂。最近就有两起热点新闻:一是大量亚裔认为哈佛大学在内的一系列美国精英大学在招生过程中涉嫌歧视亚裔学生,从而将哈佛告上了法庭;二是纽约市长白思豪决定取消纽约特殊高中入学考试,试图改善这些学校中亚裔比例过高(一些学校超过60%)的现象,亚裔群体则对这一决定强烈抗议。
但在这两次运动中,大多数抗议者其实都是东亚裔,尤其是华裔群体。《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用“平权运动下,亚裔美国人的挣扎和分裂”的标题来指出运动中掩盖的问题:东亚裔、华裔提出的“亚裔”群体的总体概念,忽略了大量的较贫困的东南亚裔人口,后者的诉求时常与黑人、拉美裔相似,恰恰与所谓的“亚裔共同利益”背道而驰。
我甚至不知道,《摘金奇缘》这部影片是使亚裔更加团结还是更加分裂了。
“当一个群体极其、极其缺乏他们在文化领域的声音时,只要有一部关于他们的作品出现,每一个人就都希望这部作品可以代表他们文化的每一个方面。”亚裔编剧黄哲伦讲道,“但我们要意识到,没有一个群体是同一的(monolithic)。”
面对新加坡和印度裔两位观众尖锐的提问,他摇了摇头,“我们并没有足够多元的作品去代表整个亚裔。这一部电影,它承载了太多不必要的负担。”
说完,他给坐在旁边的Monique Truong使了个眼色,希望她能帮自己圆个场。
Truong思考良久,慎重地答道:“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你,这么说吧,就让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发生在新加坡的美好幻想怎么样?它可以不实际代表任何人。”

当华裔遭遇中国
美国华裔面对的可能是真正的“内忧外患”:对内,他们的努力无法达成属于亚裔群体的共识,而对外,他们对庞大的中国市场、对理论上的“同胞”所产生的依赖和期待,却常常落空。
正如开头Monique Truong主动提起《摘金奇缘》的中文翻译那样,“中国”也是这次座谈会上讨论的中心议题。“《摘金奇缘》在中国市场的表现将扮演重要角色,决定未来好莱坞是否会拍摄更多亚洲题材、亚洲卡司的作品,”她说。
“中国现在正在大力宣传他们的文化与理念,试图在国际上变得更具吸引力和软实力,”黄哲伦略显激动,“与我们亚裔在美国逐渐在文化界站稳脚跟相对应的,是中国也需要文化软实力。”
从他的语气中不难听出,作为美国最著名的华裔编剧,他对于能够参与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有多么期待。
“我不懂中国,所以问问你啊,你觉得中国观众会对我的故事感兴趣吗?”在过去的一次采访中,话剧《公民王清福》的编剧张德胜也如此问我。《公民王清福》正在纽约进行制作,讲述了1870-80年代的华裔记者王清福为中国移民声张正义的故事。
我不知如何回答,也不想让他失望。我很少在国内看到关于早期美国移民的文化作品,毕竟在我们的思维里,“国籍”是一个很硬性的概念,几乎可以定义一个人身份的一切。早期移民?他们已经成为“美国人”一百多年了不是么?
于是我谨慎地回答:“我觉得国内观众可能会觉得这个故事比较新奇吧,可以尝试。”
“太好了太好了!”电话的那头,张德胜难掩自己的喜悦。

我的心里却闪现了许多画面——国内一些网民对个别留学生对华负面言论“辱华”的谩骂,对林书豪“怎么说也不是中国人”的谩骂,对明星“入了外国籍”的谩骂,不一而足。
而在大洋那头,有许多亚裔、华裔美国人却在翘首期待得到中国的认可。
大多数人也许永远不会把他们的作品带回中国,然而黄哲伦这样的大编剧的确得到过这样的机会。2016年,他和赖声川合作,创作了英文歌剧版的《红楼梦》,在旧金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我计划把这个歌剧版《红楼梦》带到中国,并且可以把全剧翻译、或者字幕翻译成中文给中国观众看,”在座谈会上,黄哲伦说道,“可是中国的制作方告诉我,不要翻译,我们就要英文的。”
他苦笑道:“我说,不翻译成中文怎么吸引大量中国观众呢?制作方告诉我,我的作品是‘国际作品’,是美国来的。那时候我才明白,原来在中国,‘国际’等于‘英语’,而我和《红楼梦》,都是‘国际’的。”
他也许遗憾自己作为“华人”的赤诚之心得到了冰冷的回应,但我心想,说他是“国际”的、让他的作品用纯英文演,制作方的本意可能只是使他看上去更“高级”、更值得尊敬。这种思维惯性,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化隔膜。
“华裔”仍在寻找自己的位置。在寻找的过程中,这些亚裔、华裔作品,夹在西方与东方之间,不远不近,不高不下。

走向共识的第一步
在座谈会现场,有一位华裔中年观众,讲一口标准的美式英语,可能是从小在美国长大的二代移民。在印度裔和新加坡裔观众提出质疑后,他显得十分激动,大声对他们喊道:“你们不懂,你们没有经历过这些!”
他显然对这部讲述亚裔故事的电影极为自豪,拿着相机,仔细地录下台上几位嘉宾说的每一句话。当Jeff Yang说到他很多年来第一次“对我们亚裔的文化群体感到十分乐观”时,他激动地一直点头。当黄哲伦分享他在中国碰壁的经历时,他也会愤怒而不解地摇摇头。
英语中有一个词语叫做“lived experience”。美国马萨诸塞州州立大学中国史教授叶维丽曾在《为中国寻找现代之路》一书中将其翻译为“活法”,用来描述20世纪早期中国留学生作为美国边缘群体,怎样互相分享个体遭受偏见、挑战的生活经历,从而形成了专属于“中国留学生”这个群体的独特“活法”。
换句话说,“活法”便是在极其多元的现代社会中,来自边缘群体的个体通过相似的生存环境和社会待遇,形成的个体与群体之间的身份连接和认同。

而座谈会上的这位华裔观众,显然并不以为自己所经历的那些华裔“活法”能被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新加坡裔、印度裔观众所分享。
而我们该怎么样扩大这种“活法”的边界,从而达到真正属于亚裔内部的共识呢?
我把这个问题抛给了来我们新闻学院做分享的著名韩裔作家Wesley Yang,并以《摘金奇缘》为例向他说明亚裔内部的分歧。Yang坚持为亚裔写作,刚刚出版了文集《黄种人的灵魂》。
“为什么我们要从分歧来思考问题,而不能寻找我们的共同经历呢?”他回答道。“最简单地来说,大批亚裔来到美国,基本上都是在1965年移民法废除了对移民来源国家的限制之后。我们当下亚裔的中坚力量大都是二代移民,有共同的成长环境。但是,不管是东亚、东南亚还是南亚,我们都很少作为一个整体发出政治文化上的声音,所以这部电影的意义在于,不管它的故事真正代表了谁,但它进入主流文化,为亚裔群体发出了声音。”
“而更有助于达成亚裔身份认同的方式是,我们要学会向外看:我无数次地说过,现在我们亚裔被夹在黑白二分的种族关系之间,被夹在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激进和保守两极分化之间。我们应该意识到自己作为亚裔的重要性,应该作为一个整体去平衡这些种族上、政治上的分化。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亚裔和亚洲人在世界范围内应该起到一些领导作用。”他说。
我想,中国与华裔之间的关系正具有这样跳出二元政治、放眼世界的潜力:还有哪两个群体,能够像中国人和美国华裔一样,分享相同的血脉,并沟通东西方文化呢?
“镜相”栏目首发独家稿件,任何媒体及个人不得未经授权转载。欢迎记录真实世界的个人命运、世情百态、时代群像。转载及投稿都请联系邮箱reflections@thepaper.cn。一经采用,稿费从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