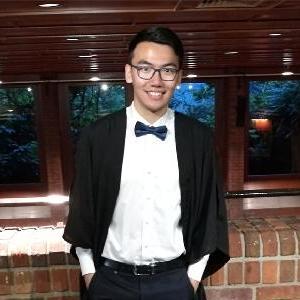到美国贫民区跟拍纪录片,我却为“政治正确”所困
文|童辉
编辑|薛雍乐
1
“利姿,你去卡姆登一定要小心啊,车要停好地方,注意安全!”
利姿的妈妈把车钥匙交给利姿,一字一顿地反复交待,终于挥挥手,上班去了。
利姿是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纪录片项目的同学,在下着大雨的美国中期选举日当天,我们从普林斯顿出发,驱车前往新泽西州臭名昭著的卡姆登(Camden)——全美最危险城市排行榜的榜首,拍摄利姿的纪录短片。
利姿的妈妈是普林斯顿医学中心的医生,爸爸是普林斯顿大学金融系的教授。她自己在普林斯顿出生、长大,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了本科——和她的两个哥哥姐姐一样。毕业后,她在哥大攻读数据科学硕士,之后作为数据科学家在咨询行业工作了三年。
三年后,她感到人生的意义需要重新寻找,果断决定要自己拍纪录片。她听说之前的同事把数据公司开到了伊拉克,于是毅然跑到了伊拉克,想要记录一名数据学家是怎样在当地战乱中努力通过知识改变当地人民的——只可惜,知识没改变当地受苦受难的人民,倒是改变了那数据学家自己——他成功地来到了美国工作。
“没关系,下次等他回伊拉克,我再跟着回去把纪录片拍完,”利姿握紧方向盘坚定地说。
在伊拉克短暂的拍摄经历让她意识到自己拍摄经验的匮乏。于是她来到了哥大开启了纪录片的学习。
也因此,我才会作为她的拍摄助手,在这个天地混沌、大雨磅礴的清晨,从静谧的普林斯顿小镇,前往别人口中凶险的卡姆登。

“你知道吗,黑人小孩子的夭折率是白人小孩子的八倍!”在雨刷器一来一回的声音中,利姿特意提高了嗓音。这已经是我过去一个多月大概第三、四次听到类似的话了。
哥大新闻学院是一个价值观十分强烈的地方,学院的宗旨是“关注社会不公、社会正义”,我想这宗旨本身是没错的。可是,学院的构成又是以白人(尤其是家境很不错的白人)为主,他们平常生活的范围和圈子有什么样的社会不公呢?于是乎,在我的报道课上、纪录片课上,一共也不到三十来名同学,竟有四个(全部是白人同学)表示自己要关注“黑人妇女怀孕问题和婴儿早夭问题”。
而问题的核心就是这“夭折率八倍”的数据,她们每一次都会提到。
“市中心这一片看上去还不错嘛!”利姿小心翼翼地把车停好,虽然她出生长大在普林斯顿,距离卡姆登只有不到一小时车程,但是这是她第一次来到这座小城。
我不觉得这城市“看上去不错”,也许是对传说中“最危险小城”的心理防御机制在起作用吧。雨下得更大了,城市被笼罩在阴云中。
2
“欢迎你们来!快请进!”丹娜是个瘦削但热情的白人女性,满面笑容地把我们迎进了办公室,“咱们在会议室里采访吧,你们去里面坐坐,我去叫主管来。”后来我才知道,丹娜是这家教育中心的对外媒体负责人,也是利姿唯一的联络人,今天我们所有的拍摄任务都是丹娜安排的。
一分钟后,另一个白人女性走了进来,微胖,脸上堆着笑,分别与利姿和我握了手。她是项目主管克里斯提娜,负责针对卡姆登当地生育十二个月内的新产妇进行的健康教育和咨询项目,每周会派固定的辅导员到当地新产妇的家中,了解她们的生理、心理健康状况,并对婴儿早期陪护进行辅导。
“你们住得离这里远吗?”利姿主动挑起话茬。
“我家离这儿二十分钟。” 克里斯提娜答道。
“我家也二十分钟。”丹娜插嘴道,“我们卡姆登的人最常说的就是,我家二十分钟远!”
二十分钟,不长不短。这些在当地工作的人自然不愿意住在这凶险的小城里,但他们同样无法逃离这里,于是住到了二十分钟以外。

采访很快开始了。克里斯提娜显得十分激动,我想可能是她们的项目很久没有见到有记者主动上门采访报道了。她说了许多“好话”,例如她们的项目如何建立并发展,如何和当地医院合作,如何覆盖当地众多居民。
“你们覆盖的居民,人种构成是?”利姿问道。
“就是当地的居民构成呀。我们这里产妇的话还是拉丁裔偏多,黑人比较少。”
“那你们没有专门针对黑人的服务吗?”
“我们的服务都是一样的,不会对黑人有特殊的服务。”
“那你们知道黑人婴儿夭折率是白人的八倍吗?”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我们只是做好本职工作罢了。”
利姿很失望地抿了抿嘴。就在克里斯提娜两眼放光的自我宣传、丹娜十分自得的旁观、利姿心不在焉的回应中,采访结束了。
“那我们现在跟着你们的辅导员去产妇家里拍摄吧。”利姿略显失望地收拾着器材,“这才是我们的重头戏。”
虽然据克里斯提娜所说,她们服务的当地产妇拉丁裔居多,但是利姿在来之前特意指定了黑人家庭进行拍摄。毕竟,“八倍”这个数据是有关黑人的,只有他们才在统计学意义上存在。
3
我们开车只走了三分钟,便出了所谓“市中心”的区域。紧挨着市中心的,便是满目荒芜的居民区。不知何用的铁丝网稀稀落落地瘫倒在路边。
房屋多是毫无特点的灰砖房,和美国郊区常见的一排排小洋楼、楼前带有小花园、楼旁配个车库的景象大大不同,这些房子每一个都独享几百平米的大草坪——但这些草坪没人修理、垃圾遍地,它们的存在只衬托出这些房屋有多么稀疏。偶见几个“政府房屋重建计划”的小牌子立在草坪上,牌子锈迹斑斑,大概已经立了几年。
一个中年黑人妇女给我们开了门,看到我和利姿背着大相机包和三脚架,她显然有些惊讶。我们一行人除了我们,还有进行家访的辅导员——一位年轻黑人女性,另外还有丹娜,她想旁观我们的拍摄。
丹娜主动向那位中年妇女说明了情况,表示我们两位是来拍摄她们的服务项目的。
客厅里的小沙发上,一个看上去只有19、20岁的黑人姑娘向我们投来好奇的目光。她的怀里抱着一个小孩子,大概七八个月大的样子。
“啊,好,好,好,”那中年妇女犹豫了一下,回答道。“那你们别拍我,哈,哈,哈。”她发出几声干笑,躲到了客厅另一边。

辅导员很快坐定,等着我们准备好器材。得到利姿的一声肯定,她才开始和新产妇的交流。
交流的过程只能用“非常平淡”来形容。辅导员手里拿着健康中心给的几张问卷,大多数问题都是“你最近晚上有失眠问题吗”、“你最近的心情有没有低落”、“你最近白天会感到没食欲吗”这样是与否的问题。
那位年轻姑娘,显然对问题并不感兴趣,大多数的问题都用简单的“没有”来回答。偶尔,她也附和着辅导员讲两句“对,我做妈妈很激动”、“我很珍惜我的宝贝”这样的话。
在一旁拍摄的利姿皱了皱眉头,显然是觉得这场景太平淡了。她给我使了使眼色,让我靠近那姑娘怀里的婴儿去拍些特写。
我并不很情愿——离小婴儿几十厘米左拍右拍也许不太合适。“没事儿,你看她多可爱呀!”利姿在我耳边轻声说。
我便大胆地拍摄了起来。那年轻姑娘倒是不在乎我的存在,就像她也不怎么在乎对面的辅导员一样。她真正在乎的,只是在她怀里熟睡的婴儿。
小孩子永远是世界上最可爱的生物,即使是睡眠状态下。她在妈妈怀里翻了几次身,时不时地张开小嘴打个呵欠。
我自然拍得很入迷,连续二十分钟,镜头都没有离开她。
辅导很快结束了,利姿却并不感到十分满意。“我觉得我需要自己采访一下这位新产妇。”她向丹娜看去。丹娜看了看辅导员,又给那年轻姑娘使了个眼色。
“好吧。”那姑娘依然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拍了拍她的孩子。
于是利姿凑到了那姑娘面前开始了采访。“你的宝贝太可爱啦!”利姿的声音高了八度,但马上又降了下来,“告诉我,你在怀孕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
“什么问题?”年轻姑娘有些不解。
“就是对你的健康状况的关怀,来自政府或医院那边的?”
“哦,我有一次,应该是快生了,肚子有点疼。”
利姿投去十分关怀的目光。
“然后我给医院打电话嘛。不过当时比较晚,他们没人接。”
“什么?这太不好了!”利姿的声音又高了八度,眼珠子都瞪圆了,“这个问题太严重了!”
“也还好,后来也不疼了其实。”年轻姑娘面不改色,亲了一口她的孩子。
“那,你在怀孕过程中还有遇到什么结构性问题(structural issues)吗?”
“没有吧。”年轻姑娘随意地回答,跟回答“你心情有没有不好”是同样的语气。
“你觉得当地政府对黑人社区的健康状况关怀是不是很不够?”利姿追问道。
“可,可能吧。”年轻姑娘嗫嚅着。
“这太不好了。”利姿遗憾地摇了摇头。
4
我和利姿所在的纪录片方向是我们新闻学院项目的一个分支,每年的学生们都会拍出七到八部半小时时长的纪录片作品。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确定选题的阶段,每个人有自己的选题,并互相帮助,拍摄一些短片来说明自己的选题。
而最初引导我们选题的时候,教授已经列好了话题的范围:“美国社会最关注的话题”,包括移民,司法公正,性别,医疗,教育这几项。还有一项是“文化艺术”,教授并不很推荐,因为文化艺术很难直接联系到“社会问题”。
教授比较推荐的几项其实都跟很具体的群体有直接挂钩:移民——中美洲,尤其是墨西哥非法移民,以及穆斯林;司法公正——黑人、犯罪和警察纠纷;性别——LGBTQ+大潮;医疗——贫困问题,尤其是黑人群体;教育——更多的是关注残障儿童。
很巧的是(也许也不是巧合),去年的学生拍出的作品,恰恰正和这几项一一对应:一部穆斯林,一部墨西哥移民,一部黑人出狱后的改造,一部LGBTQ+主题,一部残障儿童。
很“社会问题”,很“正确”。

可我想象中和实际看到的纪录片世界是极其多元的。在中国,我看到最早的吴文光拍摄的《流浪北京》,群像式地讲述身边艺术家们的故事;我看到张侨勇的《沿江而上》,记录三峡游船上两个年轻员工的喜怒哀乐;我看到王兵的《铁西区》,拍摄者静静地和工人们、拆迁户们生活在一起,历史的变迁是自然发生的;当然,还有我们《舌尖上的中国》,信息极其丰满。
即使在美国,我更喜欢的也是那些导演从自己亲身经历、沉浸的文化出发的,从真正了解的选题出发的片子。例如最近华裔导演刘冰拍摄的Minding the Gap(《滑板少年》),记录了来自暴力、离异家庭的他和他的朋友们玩滑板的故事,把家庭暴力等问题融入简单的叙事之中。我问他拍摄之初是不是想展现一个“家庭暴力”的社会问题,他说其实并不,他只是想记录自己经历的、了解的生活。
我喜欢这样的共情、这样的“兼济天下”:是你从泥土里爬出来而对泥土产生的共情,是你从乡村走出来而对乡村产生的共情,是你经历了体验了足够多的“天下”后而对“天下”产生的共情。
与之相反,如果只是说服自己“黑人产妇问题”很重要,居高临下地研究一番,然后拿着相机跑到一个贫困社区的黑人妇女家中,能产生多少真正的共情呢?如果自己都没有真诚地了解、建立共情,那我们又希望观众们感受到多少呢?
我自己喜欢戏剧,也是华人。这是为什么我想要拍一个唐人街的小学组织华裔小朋友演音乐剧、参加大多为白人孩子的戏剧节的故事。我不觉得这其中有什么“深刻的社会问题”,我只是喜欢他们,而且从那些孩子中看到自己了而已。
但是我仍需要小心翼翼地呈现出一个“亚裔被歧视”的社会问题框架来让教授们满意。
5
“我觉得今天我拍的东西可能不会用得上。”驱车回普林斯顿的路上,利姿嘟囔着。
“为什么啊?”此刻我的内心是极其崩溃的,跟她花了半天多的时间,从纽约辗转到两个多小时外的卡姆登,难道就是为了美国最危险城市一日游?
“太无聊了啊,”她搓了搓方向盘,“今天都没采访出什么问题的本质来。”

下午三点,我们回到普林斯顿。她把车开到医学中心门口,把车还给她妈妈。
“你们拍摄得怎么样?我跟他们说要出来见你们,就提前下班了。”利姿的妈妈很热情,“今天挺忙的,看了十几个病人。”
我想起很多朋友跟我吐槽过的美国医疗系统,看个门诊,医生跟你闲聊十分钟,开点药。拿到账单,几百刀。
而这其中的资本游戏也有不少。普林斯顿医学中心已经被置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中心”之下了。利姿的妈妈告诉我,宾大不久前买下了普林斯顿医学中心的很大一部分股份,医疗质量进一步提高,成本也提高了。当然,这医学中心服务的对象也大多是当地的富裕阶层。
利姿的妈妈开车送我们到普林斯顿火车站回纽约,几分钟的路程中,她作为美国医疗系统的“内部人士”,一直语重心长地告诉利姿,她听说系统里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尤其是对于黑人群体:“你一定要好好地调查其中的问题,这会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纪录片。”
不过利姿的妈妈自己没去过卡姆登,很难提出具体的建议。利姿也没敢在她妈妈面前直说今天的拍摄有些“无聊”。
我倒是感到很羡慕,原来利姿这个选题,她的妈妈似乎比她还要懂。
6
在我们新闻学院这个可以被称作美国自由主义大本营的地方,我已经看到太多同学对一个所谓“弱势群体”毫不了解,甚至不懂他们的语言,便随便研究一番,采访一趟。
有一次,报道课上一个美国同学十分同情地说,她决定报道法拉盛华人区妓女们的艾滋病现象,并略带迟疑地说:“我觉得中国人可能对艾滋病比较羞于启齿。”
许多同学们点了点头,但我很庆幸有个同学说了句:“所有群体都不会愿意说自己得艾滋病了吧。”
那个同学的报道想法大概是夭折了,因为她为零的中文水平大概无法支撑她对可怜的华人妓女们的关怀。
我甚至跟朋友开玩笑说,如果利姿拍摄的是一部“普林斯顿毕业生的空虚生活”,或许会更加真实,更加能吸引人。
不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我们都希望建立社会群体间的共情,这也是我们社会协同发展的最强大动力。但是,我深深地明白,哪怕对中国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我都远没有达到共情的能力,而在这之前,我希望能对他们进行足够的、平等的、真诚的了解。至少,在拿起相机拍摄一些人之前,我要知道这些人真正需要我,我也需要他们。在拍摄前和拍摄中,我希望所有的问题我都可以和他们共同经历。

在一个月前的华盛顿“双重曝光”纪录片电影节上,主展映影片是一部叫做The Ghost Fleet(《鬼魂舰队》)的影片。制片人和导演是两个美国白人,他们听说印度尼西亚有很多渔船非法雇用了很多来自泰国、老挝等国家的劳工,并囚禁他们做苦工十余年。
于是他们找到了当地的社会活动家,登上一艘条件不错的渔船,去解救那些被奴役的劳工们。他们不懂当地的任何语言,只是作为这艘船的“领导”,每到一座新的村庄,用自己的白人身份和它所代表的不可抗拒的权力,把相机对准了每一个当地人。
映后分享会上,导演笑着说,拍摄时有当地人很不愿意,也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但他们都听不懂,翻译也没敢当时告诉他们,直到剪辑时才说。
在场观众看上去都被他们寻找正义的努力所打动,直到一个来自印尼的姑娘问他们对当地的整体文化和政局有多少了解、有没有长期计划去解决问题。而他们能回答的,无非是“我们在和当地专家联系。”
我看到这个印尼姑娘以及寥寥几个亚裔观众投去了非常不屑的目光。
也许我们可以想想,如果有两个白人来到中国的农村说要“拍纪录片”,我们对他们会是什么态度?如果两个中国人到美国农村去呢?
在美国,以及世界范围内,有些权力关系还远没有破除。我想纪录片这个小小的侧面所展现的,是“政治正确”这个概念如何成为了权力关系的副产品,并进一步固化了这种权力关系。
19世纪末,National Geographic(《国家地理》)杂志在殖民主义最兴盛的年代诞生。无数欧美摄影师们拿起昂贵的相机,冲向了这星球上原始而新奇的“其他地方”去记录“其他人”的生活。一个多世纪后,《国家地理》最初的拍摄模式已经受到了许多批判。
但是这种权力关系究竟有了多大的改变?还是只是衍生出了另一种矫枉过正的叫做“政治正确”的东西?
优越阶层对弱势群体、社会不公的关注,当然值得鼓励。只是在实践的过程中,是否有太多优越阶层的自我感动?关注“弱者”的时候,在美国、甚至在中国的优越阶层们,关注的真正是什么?
7
关注的究竟是什么呢?
回到纽约的第二天,我们在纪录片课上分享自己之前拍摄的素材。利姿一脸愁容地告诉大家,自己拍的东西“非常无聊”。
她显然是没有看到我帮她拍的那一大段小婴儿的特写,因为两分钟后,当她把内存卡导出,看到了第一段小婴儿的画面,便用那高了八度的声音喊出,“他太可爱啦!”
班上的女生们都围住了利姿的电脑。大家津津有味地欣赏了半节课各种角度的小婴儿特写。
“利姿怎么会觉得她拍的东西无聊呢?”下课后,一个同学兴奋地对我说,“多可爱的小孩子呀,我觉得她做的片子哪怕只放这个小婴儿的特写都够我们看的了!”
利姿看上去很满足,她似乎决定继续探索这个选题,顺便可以拍摄更多可爱的小婴儿。
不过不会是同一个婴儿、同一个家庭、乃至卡姆登的当地居民了。我问她,还会不会回到卡姆登继续拍摄当地的医疗问题。
“卡姆登?我不会回去啦。”她简单地回应道。

镜相工作室独家稿件,任何媒体及个人不得未经授权转载。欢迎记录真实世界的个人命运、世情百态、时代群像。转载及投稿都请联系邮箱reflections@thepaper.cn。一经采用,稿费从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