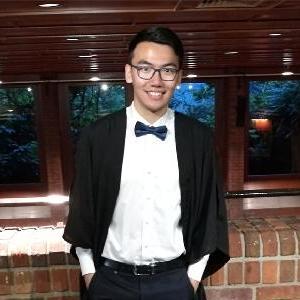行走海外,我开始思考“中国人”的身份意味着什么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作为“中国人”的意义在哪里,从我自己的身上,从接触到的人身上,我试图去理解这种强烈的“中国人”意识究竟意味着什么。我的毕业论文表面上写的是一百年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戏剧活动,实际上探讨的也是他们自我意识中的“中国”和“中国人”是怎样同时由环境内化和由舞台外露的——至少,这说明“中国人意识”至少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都存在,并且是一个重要议题。
我向来不是一个喜欢讲“主义”的人,所以,如果只是给这种意识加上一个“民族主义”的标签,那是最简单但也最大错特错的事情了。
我想在这里分享几个我经历过的小故事。
1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深圳。去年夏天,我在一个戏剧教育机构协办“莎士比亚戏剧夏令营”。两个比较知名的英国戏剧教育老师被请到营地里负责全程的教学和排练,最终由学生们上演莎士比亚剧作给家长和部分领导观看。作为戏剧助教,我要做的便是做好翻译工作,协助排练,和孩子们搞好关系,当然,还有其他和场地、人员之间的协调沟通。
就在这场地的协调沟通中,我遇到了大麻烦。
演出场地并非专业剧院,于是灯光、音效方面需要我帮助两个英国老师和当地场工进行协商。那场工是个典型的“剧场坏大叔”形象,个子不高,眼角的皱纹有些凶狠,在白天的大多数空闲时间里要么不见踪影、要么在操控室里睡着大觉。
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就不甚愉快。带着两个英国老师,我敲开操控室的门,想让他帮我们讲解一下舞台灯光的构造。操控室尘土飞杨,各种规格的连接线卷成一堆。他搁下手机,抬头看看两个老外,然后瞪了我一眼。
“你翻译啊?”
“嗯我翻译。”
“呵。”他不屑地回过头。“就这几个好的,左边仨右边俩。”
我给英国老师翻译并试图解释这个场地不够专业,那大叔特不耐烦地盯着我。
“那边上那两溜灯呢?”我问道。
“都跟跟你说了,都坏了!”
“能修吗?”
“来不及修,修个屁呀,外国人来了就要修啊?”
趁着我给英国老师解释的当口,大叔走了出去,甩下句“我还要忙别的”,不见了踪影。
从此大叔好像跟我结下了梁子,而且,只针对我一个。每一次关于舞台的交涉,他是不会正眼看那两个“外国人”一眼的,所有的怨气却全洒到了我一个人身上。我越是试图调节沟通中的种种矛盾,更长时间地用他听不懂的语言和英国老师交流,他便越用一种极其鄙夷的眼光看着我,仿佛我正背叛他,试图和两个外国人一起从他身上获利似的。
灯光坏的坏暗的暗,音效操控位置也不对,正在说不通的当口,他又瞪了我一眼走开了,甩下一句,“他妈的老外来我们中国不学中文算什么劲?还翻译,怎么不直接请中国人来?”
最终的演出完毕后,他终于找了个方式惩罚我这个“汉奸翻译”,非要说我弄坏了一个电脑接线的插头,在网上搜了个新的,告诉我,“三百多,你自己赔我。”而这个线原价也就不到一百。
英国老师帮我圆场,说根本不能证明是我弄坏的。
他一直逃避两个外国人的眼睛,只是瞪着我说,“我就要你赔。”
英国老师说他就是个纯粹的loser(失败者)。我笑笑没说话。我似乎不应该把他这个还算认真工作的中国人当作一个loser。因为中国有很多很多像他一样的人。
那么问题出在哪儿?
2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叫做“Arcade”的购物中心里,我正在ATM机取些现金——在这个实际上已经有些落后的国家里,我的中国和美国信用卡都根本找不到地方可以用。背后一只手突然拍拍我的肩。
“现代吧?”一个肥头大耳,头发油腻的白人男子一脸奸笑地看着我。见到我他竟用西班牙语说话,也不知是故意,还是真的连句英语也不会说。
好吧,反正我会说西班牙语。“你说什么现代?”我问。
“这里多现代呀。”
“呵,对,现代,很现代。”我很疑惑他到底是什么意思。而他也完全没因为我会说些西语而有任何的惊喜或热情。
“你们中国没有这么现代的地方吧?哈哈哈哈。”他上下打量着我。我不知道我哪里穿得“不现代”了,难道是长相?
“现代?那中国北京上海这样的地方多了去了。”我迅速地走开,大脑一片空白。我的西语水平,还不允许我在意识到他想表达的意思后向他提出什么铿锵有力的抗议。我很后悔没能学得更多更好。
在那整个晚上,我特别难堪,脸上一直热热的。不知道为什么——难道是因为连站在我身后的人都能一眼认出我是中国人?难道是他们对中国的“误解”触碰了我什么敏感的神经?
在购物中心点快餐的时候,厨师大叔问我是哪里人。我回“china”,但用了不同的方式。西班牙语里的“china”虽然拼写相同,但是发音偏向我们众所周知的侮辱性的“支那”。我跟那厨师大叔故意说,“拆那”,以为这可以帮我的脸上解一些燥热。可大叔没听懂,非要再问一遍。
“是‘支那’,但是我们都叫‘拆那’。”
厨师大叔显然是没听懂,一脸疑惑。
我脸上更热更红了。
你可以告诉我,购物中心里的那个人,不过是阿根廷的一个loser罢了。可是为什么我会为一个loser而如此难堪?“外国人”里,又有多少这样的loser?我们可以真的置之不理么?
3

同样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因为有了半天的闲暇时间,旅途又很漫长,所以决定在当地理个发。理发这件事儿,我像大多数在国外的朋友一样,一定是要找当地的“唐人街”的。于是我便摸到了布市的唐人街,找到一家小理发馆。
理发店小哥见到我进来很是激动,看上去很久没生意了。关掉正大声播着游戏配乐的手机,他给我熟练地洗头并剪起发来。“打薄推高斜刘海”,这些让我用西班牙语说,我可是不会。英语都够呛。还是中文说着亲切。
“哪里人啊?”
“我福建的,福清。”
我好像听过这个地方,什么“福清帮”。
“那你怎么会跑到阿根廷来啊?这国家有什么好的?”
“就是想出来呗。美国签证没给我过,我就看觉得阿根廷挺好,跑阿根廷来了。”
“那阿根廷签证就给你过啊?”
“嗨还不是蛇头给准备的,反正都是假的,阿根廷这边看不出来。“
“什么头?”
“蛇头啊。”连蛇头都没听说过,我在他眼里看来像是未经世事的小屁孩了。“蛇头就帮你把材料准备好,签证搞定,然后送你上飞机。到这边过关还有人接。”
“你给蛇头多少钱?”
“美国的话现在成了是三十万好像,阿根廷的话我给了十五万。”
“十五万?”
这“福清帮”花十五万就为了来阿根廷这地方?十五万,在中国开个小理发店不行吗?
“嗨反正就为了出来嘛,想换个环境。没想到来到这边发现真他妈无聊。我也一句西班牙语不会说,现在签证也过期了是违法拘留,天天也不敢出店门,就只能待在店里打游戏。”
“这边华人大多数都是非法的吧?”
“反正有做生意有钱的就娶了阿根廷老婆,混得非常可以呢。我不行,我一句西班牙语也不会说,就会‘噢啦’。我晚上敢上街了也不敢看当地人,都低着头。”
低着头,卑躬屈膝的中国人哟。我默想。可你又为什么偏要来这儿呢?
“不管怎么样,至少家里人可以跟别人说,我在国外啊。”他的眼里闪着光。
真给中国人丢脸。我又想。可这似乎也并不成立——对于他来说,他所做的一切,似乎都为了给自己和家人长脸。
事实证明他理发技术不高。我出了理发店没两分钟就意识到自己的鬓角剪的乱糟糟的,于是马上折回去找他。他已经又玩起了手机,百无聊赖的神情。
当晚,我看了许多阿根廷当地新闻。打击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已经成为当地警察的常规工作。那些简陋的小超市里,人们抱头鼠窜。
我脸又红了。关上了手机。
那个理发小哥,他是个loser吗?我以什么样的标准在判断着他并认为他是个loser?
4

由于我自己在外留学、也在很多不同的地方旅行的背景,可能对于“中国人”的身份有了极其特殊的敏感度。路上的小朋友对我做出一个眯眼的表情能让我难受上一天。但我想这绝不是个例。
近百年前,闻一多回忆道,在美国科罗拉多学院毕业典礼上,当他们一队中国学生走入会场时,来自美国学生的目光令人感到焦灼,他不由得脸红了,感到一种不知从何而来的羞耻感。有一期《锵锵三人行》上,梁文道和许子东也回忆起他们在海外旅行时出丑的经历,许老师因为不会用咖啡机,洒了一手,而感到特别特别地难堪,当时就感觉“旁人的阳光好像在嘲笑我们中国人。”梁文道做得决绝,他看到所谓“没素质”的国人只好采取“我跟他们不是一拨人(我比他们优越)”的心态来自我安慰。
但我觉得这并不真的有效。
所以,“中国人”究竟是什么?说着相同的语言?长着相似的脸?散发着相似的“气场”?我无法为这些表面现象下一个定义,因为如果屈服于这样的定义就好像种族意识的倒退。
“中国人”,总是对自己的中国身份充满满足又充满自卑。在这种内在紧张的矛盾心态下,“中国人”这一定义本身便不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一种变量,用来达到自己判断他人、定位自己的目的,这倒是和中国一直以来的实用主义传统吻合。
在我讲的几个故事里,什么是“中国人”,什么是“loser”的细小想法,也在我身上和我遇见的人身上发挥着相似的效用。
如果,非让我和这种内在紧张做什么和解的话,那么我想,这种作为“中国人”的内在紧张,似乎是我们中国人本身最大的特质。如果说我们作为“中国”的现代化叙事能够和其它国家有所不同的话,那便是我们的身份也许并不是民族国家下的那种同一的,线性的身份。我们有内部的贫富、城乡、阶级等等太多的差异,这些给“中国人”的身份添加了许许多多更深层次的注解;而对外,我们又不得不成为一个同一的整体,因此产生无数焦虑、自卑、甚至某些群体的自我剥离。
我深深地意识到这一点,而我想如果更多的人意识到这一点,也许我们会少很多“你国”开头的恶意嘲讽,和“我国”开头的自大吹嘘。也许我们的自卑会少一些,自信会多一些。“loser”会少一些,能懂得自己何以为“中国人”的人会多一些。
我没那么有理想主义,相信世界大同。但我相信,一个接受这种内在紧张的中国人,能够和他的同胞,以及这个世界和解。
作者简介:童辉,美国康奈尔大学本科历史系毕业,曾在英国剑桥大学交换一年,现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纪录片方向。关注全球视角下的华人历史,以及当下美国亚裔群体的戏剧、影视与各类文化议题。
(首发于微信公众号“童导”:traveldefinesli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