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强︱《近代中国的学术与藏书》中的李滂生平事迹略补
高田时雄先生《近代中国的学术与藏书》以书籍的聚散和再发现为基点,考察晚清以来的中日、中西学者交往,虽然所辑录二十篇前已陆续刊发,但其中亦有首次译成中文者,其范围之广、论述之严谨,足证作者对所关注领域如中外交通史、敦煌学、版本学史料的搜集穷幽极微、至纤无际,读毕让人不禁肃然起敬。
《李滂与白坚——李盛铎旧藏敦煌写本流入日本之背景》为本书开篇,高田时雄先生在正编写就后又接连三次予以补写,时间跨度自2008年起至2014年止,可见其用力之深。其中“再补”(以下简称李文,全书页码)一节以李滂生平为核心,以艾俊川先生所藏一手档案史料为基础,很多细节得以首次披露,但仍有值得进一步补述的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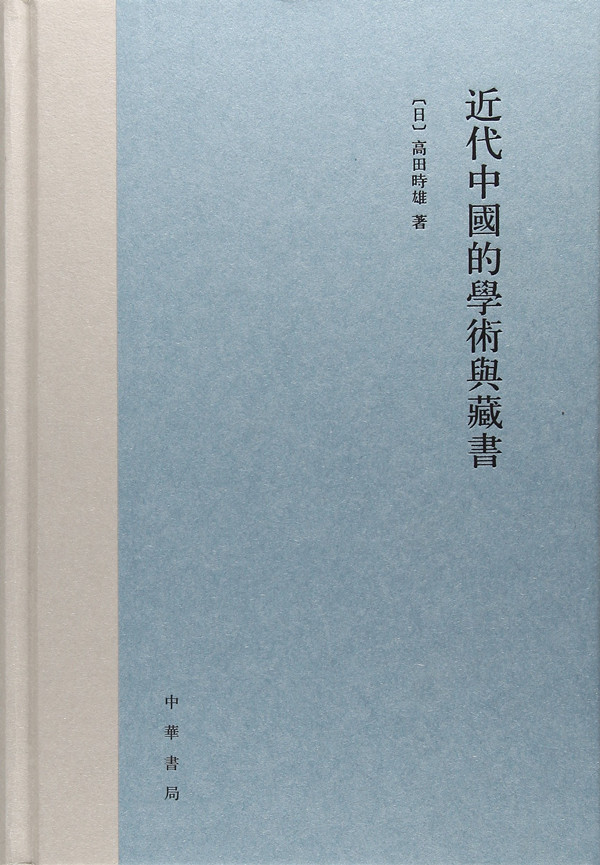
“近世藏书家概略”一文的再考察
是文为1933年李滂在省立河南大学的讲演,后刊于《进德月刊》第二卷第九、十两期(1937年5月、6月)。据原文可知本次讲演分作两日,均由汪志中记录。首日邵次公先致介绍辞,略述李滂继承家学,唯结语处言“此次来汴,闻亦欲办理中国古物保存会”,属于有用信息,查本年初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的确筹设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此次南下似于此事相关;李滂在开讲时亦略述来此缘由,云“滂因事有首都之行,便途莅汴,承关伯益、张中孚、邵次公诸位之邀请,作近世藏书家概略之讲演”,这一表述与李文(51页)表述略有出入,后者称“他是应当时国文系主任邵瑞彭(字次公,1887-1937)之聘”,此处“聘”字似为译者之误,因高田时雄先生抄录李滂自撰履历书(48页)时亦写道“民廿二河南大学作□月游”,并无聘用之说。
《张元济年谱长编》中有一处提及李滂,为“1909年9月上旬至中旬初”涵芬楼购入顾锡麒謏闻斋旧藏,编著者曾引用李滂记述:“顾氏收书始于明代,方涵芬楼往购其书时,滂亦随往,见其拭几待客,皆以宋刻书残叶,不胜悼惜”,出处标为郑伟章《文献家通考》第869页。笔者大骇,因据李滂履历书及《邺亭忆旧录》(47、49页)均可知李滂生于1907年,两岁孩童恐无陪同前辈访书、心感悼惜并记忆犹新之可能;另据“李母横溝宜人传略”可知,李滂随父母于宣统己酉年(1919)返国,有无可能于同年9月抵达上海,颇令人怀疑。
笔者查阅《文献家通考》,发现这一说法的原始出处即“近世藏书家概略”,为李滂第二日演讲中论及商务印书馆涵芬楼部分,且文词一致,并无错录。分析诸可能后,笔者认为孙毓修稿本《书目考》所记涵芬楼购书时间“宣统纪元八月”应为可靠时间,李滂所言虽有细节描述颇为生动,但应为托大妄言,想来应从其父亲或木师门人道听而来。
除此之外,该篇仍有两处细节值得瞩目。
一是首日李滂发言以杨氏海源阁为结语,言“旋有王子灵者,以为奇货可居……托言市诸国内某家,实则暗中卖于阴险卑鄙之侏儒岛夷也”。其中“王子灵”应为汪志中误记,实指琉璃厂藻玉堂书店老板王子霖,其日记残篇刊于《王子霖古籍版本学文集:日记、信札及其他》。李盛铎即最早购入海源阁旧藏者之一,王子霖日记中多次提到木老购书且皆为感佩之辞,未有李滂的只言片语,将两方之言对照颇值得玩味,而真伪之别,笔者不敢轻言。
二是李滂讲演中很客气地将“邵次公双玉蝉馆”列为藏书家之一,谓“本岁先生以讲学来汴”,这一说法稍有误,查《河南省立河南大学一览》1932年版,可知此时邵次公即为中国文学系主任兼教授。

《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中的李滂史料
2011年出版《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一辑)第一百三十六至一百四十二册(以下简称抄本)为李盛铎档,笔者仔细检视各卷目录后发现,除抄本第一百四十二册外,其他各册均有涉及李滂的史料文献,包括家书、友人往来书信、公函(片)、文章底稿、书目、遗著目录等。该史料似未被高田时雄先生所关注,故笔者在此将其中与学术史、书志版本学有关者以主题分述如下,其中字迹模糊或涂抹处以□标识:
(一)白坚致李滂书信。
抄本共辑三封书札,白坚皆用其谱名“劭暐(韋)”敬称李滂。
1
劭暐十哥左右:新秋伏惟,侍奉多福。仆昨还沪矣。尊臧被攘窃,近况若何?冀见告。
坚 顿首
八月廿日
按:此信见于抄本139册238页,具体年份不可考,似在某次为李滂卖书之后。
2
劭韋十哥足下:与均公一再相晤语,闻之喜不可言,今后马首何之。足下自昔有游峨眉汶岭之愿,今非其时耶。仆还乡以来,无恙时欲出游,则以道难而止,比无可乐,得作此书为乐。肃此,即希
德诲,并问眷爱咸安
坚 顿首
十月十九日
江陵张圣奘今在重庆大学教授,中秋顷曾相往还。此君有修正明史之壮志,而于蒙古元史尤用功,若承德诲,乞寄重庆化龙桥虎头岩王家花园白隆平。
按:此信见于抄本139册248-249页,写于何年亦不可考,但应不早于1934年,查1935年5月出版的《重庆大学一览》职员名单可知张圣奘于1934年秋到校任教。
3
久不获尊处消息,起居何如,伏惟侍奉安胜。坚自春初伤风,至今未愈。中间尝卧半月,小愈则东渡,归则游黄山,静养之日甚少,乃今医者谓肺病也。然而不咳嗽不吐痰,惟稍畏寒耳,一感寒则肺部立感不快,有喘息声,斯所谓肺病欤。近日中西医术并投,中药则服半夏露,若有神效;西法则受人工太阳灯兼注射Helpin海尔平。坚卧静养月余,期必全愈云。斯疾一日不愈,则活动殊难矣。弟所有石与书悉欲脱售,往尝一再劳神之毛钞书籍,欲乞为一问书估,彼欲此书之人究竟所欲何种?所欲之书确切不移出价若干?乞赐示及,即凭割让,何如?
弟坚 顿首
上劭暐十兄大人足下
十三日
按:此信见于抄本一百三十九册266-267页,具体年份不可考。

(二)假借两汉书、晋书影印事。
此事为上海涵芬楼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背后经过,主要推动者是傅增湘,虽然最终皆用其他底本,非木犀轩藏书,但李滂作为李盛铎的代表直接参与其中。《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以下简称尺牍)存札和抄本散见的书信恰巧可以较为完整地还原筹办过程。
1927年7月26日,傅增湘去信告知张元济:“今日李木老来此,谈及其世兄少微赴申,借印汉书事可与径商,渠仍住民厚西里。木老言(木老已告其世兄矣)其世兄住申约两月,不知此两月能照完否。请公速与接洽,毋失此机会也。”(尺牍167-168页)据张元济8月7号的复信可知,他打算拜访李滂,但结果如何并无明确记载。10月5日张元济去信傅增湘,坦言:“木老允借两汉晋书,索酬万元,公司中人认为过重。时局如此,即印出恐亦无甚销路,暂行缓议。”(尺牍175页)到此,假借木犀轩藏书之议搁置,而索价如此昂是李盛铎意抑或为李滂主张,不得而知。
1930年春此事忽有转机,傅增湘作为李盛铎的门人、商务印书馆的股东,在两边不断游说(尺牍228、229、230、234等页),双方争议已非酬金数额,而是影照地所在,李盛铎要求必须在天津而张元济则坚持运抵沪上,至于酬谢方法,则已改为赠送百纳本二十四史全书数套。抄本所辑信札多在1930年底至1931年3月,笔者根据其逻辑(时间)顺序整理如下:
1
少微十哥世大人赐鉴:前杉村兄自津回,恭审夫子大人福履绥和,精神弥健,游泳佛海,味道而腴。引詹函丈,慰兴忭会。尊藏宋本晋书,张菊生拟假印入全史中,沅叔先生曾在师座前言及,昨沅公来函重述此事,特将原函寄呈左右,祈加詧纳。宝本拟日内赴津面聆夫子训诲并与吾哥作半日清諙,腕疾增剧,西医诊断为神筋痛,故而终止,驰仰万千。近见海源阁旧藏荛跋书多种,索值奇昂,无法合议,惟据以订正楹书隅录之误数处耳。专此,敬颂
撰祺 上叩
夫子大人福安
世小弟徐鸿宝 再拜
十二月廿一日
按:此信见于抄本141册392-394页,应写于1930年12月21日,虽存信封但邮戳模糊无法辨认。“杉村兄”即日人杉村勇造。“荛跋”应指黄丕烈所撰题跋。此信所言“昨沅公来函”应为下函。
2
张菊生前日来函,决欲假李木师之宋本晋书影印,酬以衲本全史三部,此层前与木师言及。公近日赴津否?乞转达,能将全书交弟处即可。决保毫无损坏也。黄善夫本史记竟配全,至可喜。
曹理斋之律吕正义后编此二百元不能少
闵葆之之内钞明名臣奏议此三百元可略减大约二百五十元可办
二书能留否,此两公皆待款渡旧岁者也。乞酌示
森玉仁兄台鉴
增湘 拜启
按:此信见于抄本141册390-391页。曹理斋即曹秉章,曾参与编纂《清儒学案》;闵葆之即闵尔昌,晚清秀才,曾任袁世凯幕僚。
3
少微世兄大人阁下:前奉复函,敬悉一一。菊生来书仍欲奉借尊库晋书影印,曾属森玉代陈,未知夫子大人意旨云何?乞示知。百将传二书祈费神早为买定,若价值有差,可由兄酌为增加,祭书将举,欲得此以助雅兴。此候
台安
世愚弟增湘 拜启
按:此信见于抄本141册383-384页。原信未写日期,似为1931年2月初,首先信封邮戳(北平)虽然模糊,但仍可依稀看出是某年2月7日,其次由内容可知《晋书》尚未得允借出且此时临近春节,傅增湘藏园祭书约在农历腊月二十八日左右,可参见《许宝蘅日记》1932年2月4日祭书的记述,而1931年春节为2月16日。
4
少微世兄阁下,昨岁到津,未及承教为歉。弟订于廿八日南游三星期即北返。前次所谈菊生假印晋书事,究以此书是否运津?
夫子大人云须兄查悉,乞赐示。大概何时可交照?菊翁有函询及,便语之也。此候
台安
弟增湘 拜启
正月廿四日
按:此信见于抄本141册381-382页,应写于1931年3月12日。
5
沅叔先生世大人阁下:
手教敬悉,晋书存南中,俟滂赴沪方能□□□也。□□。敬请
著安
弟李滂 顿首
正月廿五日
按:此信见于抄本139册306页,应写于1931年3月13日。原文被涂抹,故无法辨识相应文字。
随后, 4月7日、5月7日张元济又去信催问,而傅增湘5月8日的覆信则告知“前日在津。亲往晋谒,适少微世兄自申取书回。当即将全书八函交来。近因朱君赴会之便。特托寄呈。”(尺牍264页)至此,木犀轩藏宋本《晋书》终于得借,其中“朱君”似指朱国桢,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的副经理。而在尺牍一书中亦多次提到白坚,如1930年10月8日、1931年1月27日、1931年3月6日诸信,足证傅增湘对其颇为信任,常常委托他携带函件、贵重书籍赴申拜谒张元济。
(三)捐赠古物与天津印心精舍事。
1937年2月4日晨,李盛铎病逝于秋山街私邸,非抄本第136册 “李盛铎简介”(约222页)所述之1934年。第139册第263至265页为1938年6月9日天津印心精舍申谢函。由此可知,李盛铎去世后,李滂将已分得之部分家产经洪得之、魏振生二位先生赠与该舍,所捐之物包括经卷、碑帖、字画、古玩,并有意待剩余家产分配后再行捐赠。印心精舍收到该批宝物后虽有点交,捐赠目录却无从核查,故难以判断其中有无重要古籍,但由此推知1940年李滂卖与伪北京大学之书已非“七七事变”后木犀轩的全部藏书。
(四)出任北平民国大学校目录学校勘学教员时间。第139册第205页为北平民国大学校公函一纸,请其出席9月16日(星期一)开学典礼,虽未标注年,但月日信息与1929年相符,可证其履历书所言不假。
(五)其他文稿。笔者拣其重要相关者,略述于此。
抄本139册收录“李母横溝宜人传略”底稿两份,与李文所录版本对照,并无太多差异,惟尾部处抄本稍有多出者。抄本137册23至26页收录“九江李少微先生遗著书目”,仔细研读后令人生疑。
首先此文似由他人抄写,非李滂亲笔;其次书目之中多常见著述如“水经注校录”、“文选校记”,少有能明辨确定者,其中《安愚室印谱》二卷,笔者查此书实际署名为“山阴金若琰辑”,李滂倘若托名亦无改变籍贯之理,故笔者认为此书目并不可靠。此外,抄本中有两封致李滂信函,分别由袁同礼、徐森玉两先生撰写。兹抄录如下:
少微先生大鉴:日昨晤教为快。承兄惠赐论文(关于大典校□者),极为感谢。倘承早日赐下,尤所期盼。奉上敝馆善本书目史、子、集三册,承希转呈尊大人是荷。第一册俟刷就再寄。此上,顺颂
道褀
弟袁同礼 顿首
八月廿三日
赵斐云兄定本星期日赴津会商印四库事
按:此信见于抄本141册379-380页,写于1935年8月23日。
少微十哥大人左右:久不承教,驰思无已。近维兴居安善,上侍康娱为祝无量。故宫更替,弟为环境牵帅,堕入樊中,苦痛万状,俟叔平兄北返后,决计摆脱,还我本来。吾哥卓识,当以为然也。上元郦君衡叔承铨,喜蓄书而能自勘读,曾得秦敦夫旧藏斠本宋六十一家词,乃毛氏刻成复经陆勅先诸人别据善本勘正者。郦君今由平来津,夙仰夫子大人为士林泰斗,又知吾哥善承家学,欲得奉手,藉罄仰止之忱,命致书为介,傥郦君晋谒时□祈陈明师座,赐予接见并加教诲,感不可言。匆此,敬请
揖安上叩
夫子大人福安
世小弟徐鸿宝 再拜
十月十七日
按:此信见于抄本141册385-386页,虽然信封邮戳过于模糊,但应写于1933年10月17日。1933年7月马衡出任故宫博物院代理院长,命徐森玉为秘书处秘书长,这一重担应为其“堕入樊中,苦痛万状”的根源。郦衡叔,江宁人,曾撰写“愿堂读书记——六十家词”,刊《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8卷第1期(1934年2月)。而徐森玉绍介之请确有下文,郦衡叔在“建康实录校记跋”中追述“去夏草此校记上卷竟,旋有燕都之行……徐森玉先生语及海源阁宋椠本今尚在琉璃厂估人手,虽未得寓目,但书能长留人间终当供学人雠勘未遭劫火亦自可庆也。又顷者李少微先生过访,蒙见告以吾乡孙先生文川藏彭文勤公钞本今在木犀轩中,且谓就愚所校勘之胜处亦略具焉……甲戌十年承铨校竟记。”
结语
在抄本之外,笔者在旁处亦见及有关李滂的史料,除去出任伪职之记录,其中有益学术史者大致有以下三点。1941年底,白坚、蒋尊袆、宋介、溥叔明、李滂发起成立敬天会,后白坚任中方副会长、李滂任顾问,此事记于1943年出版的《华北民众团体概况》;1942年王晋卿刊行《文禄堂访书记》,是年上元节(3月1日)李滂撰“跋文禄堂访书记后”,称赞王晋卿博于闻见、勤勉好学,略述其与李家二十余年的往来情谊,署“德化李劭暐邺亭”;1944年初,李滂撰“重修蓟县县志序”,收录于3月出版的《重修蓟县志》。
1950年1月25日,郑振铎去信夏鼐说:“兄信里提到的,李家敦煌卷子事,我们为什么不收买呢?这有原因。这批卷子是森老介绍的。我也和李氏主人见过面,国家不可能买他的,因为李某在敌伪时代做过重要的官儿,在解放前才被释放出来。……现此批卷子,已落在商人手中,不久即可由北京图书馆收得。”该信收录于《郑振铎全集》第十六册第229页,是笔者所见涉及李滂的最末史料记载,其后之遭遇实无从查阅。
数年以来,笔者辑录国立北平图书馆史料,曾于抄本等处见及李滂与平馆各位先贤的交往,且多次得高田时雄先生赐教,故拜读完《近代中国的学术与藏书》后,有意撰文尝试小补。为撰写此文,笔者曾求教于中华书局柴剑虹老师和上海博物馆柳向春老师,志此以表谢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