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强迫症那八年,我就像推石头的西西弗斯 | 三明治
原创 丹丹 三明治


意识到自己“不对劲”,是从一堂数学课开始的。那是2013年,我当时高三下学期,原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黑板上看公式演算过程,余光却总是瞟到站在黑板旁数学老师的脸。
我的数学成绩一直不太好,当时距离高考只剩下最后两个月,为了不耽误学习进度,我开始尝试控制自己的余光。控制并没有成效,我的余光还是会不断瞟到老师,甚至讲台上的黑板擦、粉笔盒。同时,我又因为控制注意力而丧失了注意力,错过了眼下正在进行的另一部分课程讲解。
自此以后,我发现自己在课堂上“不对劲”的次数越来越多。有时正在写作业,会瞟到旁边同桌的袖子;有时在听英语听力时,突然意识到周边有人咳嗽、头顶的风扇在转动……
而我越想不要关注到这些,我的注意就越被死死黏着在它们身上。注意力的失控,也让我的学习状态越来越差。我害怕因此在爸爸称作是“唯一出路”的高考中发挥失常,焦虑得整夜无法入睡,有时躲在被子里哭,睁眼到天明。
从小,我就处在严格的学习管制中。小学开始,每天的作业都要经过爸爸检查,即使家里停电了,也要被带到爸爸的工作单位把作业写完。高中妈妈陪读,如果月考没考好,她会有点冷落我,像是以此惩罚没有给到对等回报的自己。所以学习于我一直是天大的事情,每次成绩好坏都牵动着脆弱的神经。但这次的情况明显不太对劲。它不是一时的情绪低落,而是演变成了整天都存在的、想控制又控制不了的痛苦和焦虑。
当时爸妈听说我的困扰,以为我只是临近高考、压力太大了,后来感到情况确实有点严重,转而安慰我“没考上重点本科也没事”。我的心稍微放松下来,一边控制余光,一边忍着煎熬,告诉自己要先把高考考完,高考是眼前最重要的事。在当时的县级高中,升学率也是天大的,同学们忙着备考,老师忙着怎么达成指标,几乎没有人能发现我的异常,也没有人会真正关心一个学生如果出现心理问题,应该怎么办。
那会儿的我并不知道,命运之手已经将自己推入了一条幽暗漫长的隧道里,那是一条几乎听不到其他声音、背后只有一只叫“强迫症”的野兽追赶的路,我被巨大恐惧驱使着拼命往前跑,不知道自己能去向何方,也不知能否再重见光亮。

高考结束后,同学们都在为再也不用过以前的压抑生活而开心,而于我而言,一切才刚刚开始。进入大学,那种“不该瞟到旁边人/物体”的念头,每天会在我的脑海里出现成百上千次。刚开始,它们只在上课看书时出现,后来,慢慢变成了走路、和朋友聊天、去超市、吃饭时,我都很担心自己的余光飞到别处。
当生活被恐惧、焦虑、紧张挤到无限小,我对生活的热情和活力就开始迅速消失。每天早上起床成了我最难面对的事情,因为那意味着控制注意力的一天又要开始了。与此同时,我身边的同学都在“正常”轨道上过应有的校园生活,一想到他们能做到的事情我就是做不到,我可能永远跟“正常”无缘,这种悲观让自己几乎陷入了绝望的境地。
我过着两种生活,一种是看似与旁人无异的学生、朋友、女儿,另一种是只有我自己才知晓的:大脑中有一座随时随地都会喷发的活火山,闯入性想法每出现一次,就好像火山喷发一次,随之而来的恐慌和焦虑,以及想控制又控制不了的无力感就如同熔浆,烧得我痛苦、疲惫不已。
我跟父母聊过,他们表示无法理解——“不要钻牛角尖。”“想开点就好啦!”“不要那么在意,不用去管。”对当时的我而言,这就好比对断了腿的人说“你要试着去走路”一样荒诞,因为问题根本不在于我不想不想做到,而是我头脑里的“系统”彻底失灵了,我没办法做到。
我只能先自己试着重启“系统”,先在网上寻找大量跟强迫症相关的资料,去看其他病友的记录分享、专业的书籍,然后还约了学校的心理咨询。去之前,我犹豫了很久,感觉特别羞耻,害怕被认识的同学撞到,觉得我有心理问题。聊完一次后,对方似乎仍然只是把我当作一个学习压力有点重的学生,试图分析:你想的太严重了,不应该这么想,你那样想就会通了。在感受不到理解后,我便没有再去。
也许是我的自救意愿足够强烈,也许是已经快要达到承受极限了。一个晚上,我实在受不了了,除了跟强迫症相关的痛苦,我的生活几乎是空白,我哭着打电话给妈妈,强硬要求她周末来学校,陪我去医院做个心理检查,而这距离我第一次出现症状,已经快过去两年了。
那是我第一次走进医院的心理科室。候诊的人都异常安静地坐在椅子上,即便有家属陪同,也会压低声音交流,唯恐被别人听到些什么。一种无法言喻的羞耻感笼罩在候诊室上方,每个人垂着脑袋,维持一副拒绝和人交流的样子。陌生人名不断从候诊屏幕上浮现,快轮到我时,我唯一的祈求就是护士声音小一点,别叫第二次,我不想被别人知道自己的名字。进诊室之前,我甚至特意迅速扫了一遍候诊室里的面孔,确认这里没有自己熟悉的人。
这一切导致当我拿到“强迫症”的确诊结果时,反而松了一口气。所有之前的反常行为和感受,终于有了一个确定的医学解释,父母再也不能认为我只是在钻牛角尖了,他们必须承认我得了心理疾病这个事实,承认我的痛苦是真实存在的。
接下来,我开始定期来去医院做心理咨询。虽然这里的医生更专业,至少知道”强迫症“大概要怎么处理,但医院每天都要接收大量就诊患者,所有患者都像是流水线作业上的罐头,被标准化处理,在15-20分钟的聊天里,困扰我的事情还没说完,医生就得按流程接待下一位。几次下来,我强烈感觉到这种方式救不了自己,于是便去寻找更专业的咨询机构。2015年10月,我做出改变自己人生的第一个重要决定:去上海,找到那家我认为可以帮助自己的心理咨询中心。
对当时一个农村家庭来说,花将近三万去看心理咨询师,这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爸爸刚开始觉得有风险、不同意,妈妈听完只对我说了一句话:“不管有钱没钱,我一定得让女儿好起来。”
妈妈拿出她当年外出务工攒到的全部积蓄,义无反顾陪我踏上了去往上海的火车。和咨询师见面后,他建议我不用为此休学,保持正常的生活节奏、配合咨询,会更有利于病情的恢复。
于是,我正式开始了为期八个月的“强迫症”治疗疗程。

暴露、切断、脱敏、重塑,这是我接受治疗过程中的四个关键词。
我向咨询师吐露,自己看书瞟到旁边的人后,会产生焦虑、恐慌和自责的情绪,这些情绪驱动着我检查自己的余光,越是检查、不允许有余光,越容易出现余光。这种强迫和反强迫的挣扎感,加剧了我的痛苦,让我更迫切地想回到没出现强迫症状前的“正常”状态。
咨询师建议我,首先把自己“暴露”在引发强迫的场景中,把一连串的想法连锁反应记录下来,然后找到那个核心信念——“应该做到百分百完美,如果出现余光,就会影响完美,带来可怕后果”。也就是说,当“余光不能瞟到别人”的想法出现时,我应该第一时间觉察到它,给它贴上“强迫想法”的标签,完成一次“切断”,让自己不被这个错误的想法带跑。
这一步还算轻松,但接下来才是最难的地方。因为我不是不明白“余光不能瞟到别人”这个想法可能是错的,而是这个想法随时都有可能冒出,由此引发的恐惧和焦虑会持续引诱我,很难不去做检查和确认。咨询师告诉我,无论如何,必须面对这些情绪;即便非常抗拒,也一定要亲身体会恐惧和焦虑的感受达到顶点后、慢慢自然下降、直至消退的过程。
之后要做的,就是成百上千次地熬过出现“余光不能瞟到别人”这个想法带来恐惧、焦虑情绪的时刻,切身地体验到,原来我对“余光不可控”的恐惧只存在于想法中,它们在现实中伤害不到我。
除了余光问题,咨询师又让我列出了其他九个生活中让我难以接受、容易引发负面情绪的强迫场景,让我在逐级递增、循环往复的暴露练习中,慢慢提升耐受等级。这套方法是有效的,当咨询进行到第四次时,我开始感觉生活重新燃起了一丝希望和活力。
为了避免强迫症继续泛化,抢夺我的生活空间,咨询师提醒我:不能因为恐惧和焦虑,就上了“强迫症”的当,回避生活中任何引发症状的场景,这样只会被它吞噬掉生活的热情。所以解决症状只是现阶段紧迫的事,更长远的是要把注意力放在当下本应该去做的事情上,重新夺回自己对生活的控制权。
那会儿已经临近大三下学期,我也面临工作还是考研的选择。说实话,虽然我有过考研的念头,但因为强迫症的存在,我连自己能否顺利扛到考试那天都是极大的未知数,更别提最后结果是否能如愿了。但咨询师鼓励我:如果这是你想要做的事,那正常人可以完成的,为什么你不可以?
在纠结了好几周后,我逐渐想清楚了自己备战考研的动机:有想重新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专业、提升学历的目的;但更重要的是,我想重走一遍高三时自己没有走好的路,直面这个过程中所有可能出现的强迫症状和痛苦。那些曾经差点压垮我的东西,也许自己有能力处理好它们了。
这是我在这条路上做的第二个重要决定,但现实远比想象中艰难,接下来迎接我的,是比高三最后两个月强度更大、发作频率更密集、持续时间更长的强迫症状袭击。我感觉自己就是那个被诅咒惩罚的西西弗斯,好不容易把巨石推动上山,又眼看着它毫不留情地滚落下来。一切似乎重新回到了起点。

我考研考了两次,那两年可以被称为是高强度脱敏时期,几乎每天都是长时间跟强迫症状正面交锋。
2016年1月份备考开始,第一个挑战就来了:自习室一张桌子是四个位置,两两并排、相对而坐,无论坐哪个位置,我的余光都不仅能瞟到左右两边,还能看到前面和斜后方。没过多久,我明显感觉自己的余光问题变严重了,不仅担心瞟到旁边物体,身边人的复习专注度也让我压力倍增;身边每换一个新面孔,又会产生新的余光恐惧。
随着复习压力增大,强迫症继续显露出它狡猾、善变、贪婪的一面。有天,我突然怀疑自己看不懂书上的字,且每读一行字,心里就多一分“看不懂”的恐惧。我不得不经常性地在读到下一页的时,翻回上一页,以检查、确认刚才读过的内容。这导致复习的整个下午,我的时间几乎都花在这上面了,但还是无法分辨自己究竟看懂了还是没看懂。
后来,我又总是注意到自己正在眨眼睛、吞咽口水。每出现一个新的注意力问题,我就会恐惧它跟高考时我发现余光一样,肆无忌惮地入侵备考考研的生活。
恐慌和焦虑,也开始催生身体上的反应:全身发紧、侧脸烧灼感、尖锐偏头痛。大脑里似乎有一团粘稠、厚重的雾;它像个破旧已久的机器,因为锈迹斑斑,很难正常启动、整个人恍惚、昏沉。我的情绪也时常在“亢奋”和“低落”之间横跳,往往症状持续好几天后,随之而来的就是一段时间的抑郁情绪。
看到身边复习的同学都正常地看书、做题时,我几乎要到嫉妒的程度:我想不通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要如此惩罚我、让我承受这么大的痛苦。最严重的时候,我悲观地认为自己永远都无法过上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没办法上班、没办法谈恋爱、没办法有自己的小孩,连那些最普通的烦恼我都没有精力顾及,那这样活着有什么意义?
每当情绪风暴出现,我就尽力让自己动起来,去操场散步、跳绳,做正念练习、记录日记、听咨询师的课程录音、读灵修书……那段时间,爸妈跟我通电话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他们从之前的不能理解,慢慢地变为主动了解我的症状,我也能把一些心里话说给他们听了。他们特别焦急、心疼、不知道能为我做什么,我暗暗告诉自己:即便只是为了爸妈,也得扛过去。
慢慢地,高强度的暴露确实让我感觉到情况在发生变化了。有两种力量在我身体里对抗,一个是新生的细小的改变,另一个是顽固的强大的症状。
我尝试接受、尊重这两股力量的对抗,一点点安抚它们。在这种共处下,它们开始表现出愿意跟我合作的一面:有时候我能一整个上午都感觉状态不错,偶尔又可以连续一天都感觉不错,继续复习,保持相对正常的生活节奏。总体来说,我对于场景和情绪的接纳能力在一点点增强。
就在这样的波动和不稳定中,我来到了最关键的一段时间。初试分数不占优势的我,不愿意放弃复试翻盘的可能,早上6点起来复习、晚上12点才休息,吃完睡觉都感觉是在浪费时间。
但越想考上,强迫症状就越严重,几乎是每分每秒,像潮水一般向我席卷而来,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与此同时,我出现了更严重的躯体化症状:剧烈的上背部疼痛。几乎每隔1小时,我就得擦一遍止疼药或者用按摩器械做放松,不然根本无法复习下去。
2018年3月月份,离复试只剩十几天时间,想自杀的念头开始频繁出现。我后悔了。如果当初边服药边接受心理治疗,会不会要比现在好?我高估了自己承受的能力,考研对于正常人来说都已经够吃力,更别说我还要同时面对这么残暴的心魔。
所有的感受都在制止我:你应该停一停、休息一下。但我真的不甘心。这张弓,我用了整整两年才拉满;这根箭,我用了每一分每一秒与症状对抗的力量才得以削尖,而射中靶心对那会儿的我来说,可以暂时不用承受工作压力,有两年相对可以喘息的休息时间,慢慢从强迫症中恢复,再凭借更好的学历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一个强迫症患者,能有机会通过考研这种方式,奋力一搏,未来可以养活自己,也可以尽力去争取自己想要的人生,而不是只靠家里人。我怎么可以放弃?
爸妈看到我这么难受,一直劝说别再坚持了,接受调剂吧。但我就是犟,根本不听。因为不肯服用精神类药物,也不想让爸妈在支持我重考一年的同时,再为我多花咨询费用,我没有去找其他有效的支持手段,来让自己哪怕稍微轻松一点。
这是一段我觉得最对不起自己的经历,也是最想跟自己说抱歉的经历。
最后,箭还是偏差了,我以一分之差没被录取。看到结果的那天早上,我一直呆坐在房间里,眼泪不住往下流。我总觉得命运一直在跟我开玩笑,但这种玩笑对我来说却异常沉重。
来不及过多难过,我开始找工作。唯一让我觉得庆幸的是,这两年,强迫问题暴露的时间足够长,也足够彻底,似乎提前把我以后本可能会经历的症状,都提前透支完了。复试结束后,巨大的压力状态解除,我的状态开始持续好转。
慢慢地,我开始对考研结果形成另一种解读——如果说高考那会儿的我,是因为惧怕考试结果,诱发了强迫症,那考研的结果是好是坏,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这个过程,已经让我收获颇多,至少我强烈感受到,即便在最难的时候,自己仍然可以熬过去,甚至还能取得不错的表现。

找到第一份工作之后,我的生活开始恢复了七八成,但还是落下了上背部慢性疼痛的毛病。症状的复发会让我有点手足无措,不过它开始从一座大山缩小成一块大石头,绕个弯,或者费点力挪开它,总有回到正常轨道的那一刻。
参与生活的活力在被更多地捡回,我开始像这个年纪的女孩子一样:想穿好看的衣服、追追剧看看电影也挺好玩,对谈恋爱也有了冲动、还想攒钱去其他城市旅游。我太珍惜这些感觉了,在此之前,它们对我来说似乎都很费力——每天大脑中的战争,已经耗尽了大部分精力。
2021年,我参加了一个正念工作坊,它像是“手术”结束后的康复治疗,从此以后,症状已经很少再影响我了。但过往的创伤经历,还是把我困在一个叫做“病耻感”的牢笼里。它就像一个喃喃低语的背景音,当我开始想要尝试新工作或亲密关系时,总在潜意识里暗示自己“不值得”。
因为害怕压力事件会带来状态波动,我在一份不合适的工作里犹豫将近一年不敢跳出;前男友提分手时,我第一时间想确认的不是我们是否不合适,而是他有没有因为强迫症嫌弃过我……
有天晚上,我看到一篇关于强迫症的科普文章,刚想要转发到朋友圈,又犹豫起来。最后我还是转发了,还提心吊胆地附上了自己的强迫症经历。我爸第一时间发来微信让我删除,“你这个会被同事和其他朋友看到,肯定影响以后工作和找对象。”
在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如果一直沉默,那个伤口只是被暂时遮掩住,它仍然会发烂发臭,让我疼痛,让我自己都没办法喜欢自己。
我不想再背着那层沉重的壳往前走了,也不想还有人因为缺乏这方面的科普,无法提前预防或者错过治疗的黄金时间。我必须做点什么。
2022年6月18日,我做了在这条路上的第三个重要决定:参加一场公共演说,公开自己这段强迫症的经历。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个晚上,刚开始还有点紧张,等到真正上台时,看着专程过来支持我的同事和朋友,想到守在直播面前的家人,还有过去八年自己走过的路,却突然感觉异常踏实和坚定。讲完那一刻,我发现那些深深压制在自己身上的东西统统都被卸下了。
有人听完这场演讲后,曾在私底下好奇地问我:所以康复到底意味着什么?你是不是再也不会受到它的困扰了?
事实是,跟很多身体疾病一样,康复并不意味着彻底治愈。我知道身边有同样困扰的人,每个人情况又不太一样,有的人可能需要继续服药一段时间、有的人还可能会面临小范围的复发。而对我来说,强迫症也并没有彻底从生命中消失。我偶尔还是会出现某些强迫想法,也可能会短暂陷入情绪中,但它并不影响正常社会功能的发挥,也无法影响我去过一个普通人应该拥有的生活。
走到现在,大部分时间,我已经可以平静地讲述自己的故事。只是偶尔,翻开当年的日记和咨询录音,我还是忍不住会哭泣。我一直以为身后追赶自己的巨大恐惧,是会伤害自己的野兽,但终于停下来回头看时,才发现是那个被忽略的十几岁时的自己。而那些曾让我害怕的想法,是在用另一种方式告诉我:那会儿的她缺乏安全感,需要真正的拥抱和关爱。
那个十几岁的自己,我欠了她太多句“对不起”——
对不起,我对那会儿的你充满近乎野蛮的苛责;
对不起,我不应该让你一个人走完那么孤独漫长的一条路;
对不起,我把你逼得太狠了,明明身体那么难受还不肯放弃执念;
对不起,看到你说会想到自杀时,我没办法陪在你身边……
可是啊,日子永远无法再重来,我再也没办法回到那会儿的你身边。现在,我只有给你很多很多的爱、很多很多的支持、很多很多的肯定,才能让你淡忘掉以往的那些苦痛。
以后的每一次,我都会学习无条件地站在你这边,我发誓要成为你最好的朋友,相信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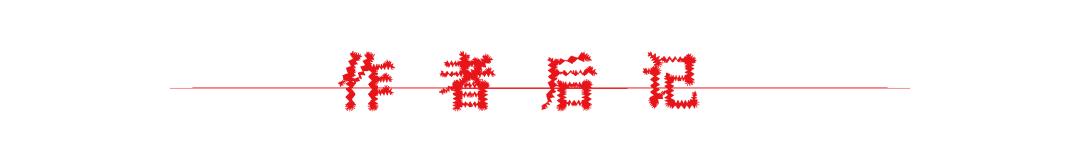
目前,国内对于强迫症的公共讨论还很少,而10年前我出现第一次症状时,完全不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有国外研究表明:强迫症从首次出现到接受药物治疗的平均时间为八年。诊断困难、难以治疗是强迫症患者面临的难题。
跟很多慢性身体疾病一样,心理疾病的康复也并不意味着彻底治愈,就像写这篇文章时,因为唤起了之前的创伤回忆,我还是会出现过往的强迫想法以及明显的情绪和身体不适反应;但好在,我会学着轻轻安抚它:没关系,现在的你是安全、被爱的,别害怕。
回看为什么强迫症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为什么自己会这么在意学习成绩、这么要求完美。除了家庭教育、个人特质和可能的遗传外,还有很重要的社会压力这个原因。
写这个故事,原本更多是想给自己做场清创手术,是为了自我救赎。但类似心理的痛苦还在很多青少年身上上演,甚至更严重。最近频繁上热搜的新闻,让我觉得这个故事会有更多的意义:当一个具体的人站在你面前诉说时,大家对于青少年可能经历的压力和痛苦的认识,就会具象、深刻很多。
理解是重要的第一步,而之后我们能做的也许是:在这个无常的宇宙里,别让年轻的孩子一个人,留在那个孤寂难过的世界里枯萎。
原标题:《治疗强迫症那八年,我就像推石头的西西弗斯 | 三明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