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田里的守望者
在安徽和县乌江镇村民眼里,叶连平是个“怪人”。
一个90岁的退休教师,每月领三四千,为了省块儿八毛,常常骑车7公里到镇上买菜,还要去捡菜贩丢弃的蔬菜带回家。出远门也不舍得坐车,到南京,到芜湖,到扬州,都骑自行车去,最远到过灌南,300公里。
住着三十年前的旧平房,穿着六十年前的破衣裳,这样节俭到常人无法理解的人,退休后,义务为学生辅导英语19年,分文不收,却总是几百、几千、几万地为学生花钱。
十几年前,县委组织部党员电教中心主任王小四在拍摄叶连平的纪录片时,颇受困惑,究竟是什么在支撑他这样做?他跟拍了三年,似乎找到了答案,又似乎还没有,事后他仍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面对不理解,叶连平在各种场合下解释了很多道理,最后只剩轻描淡写的一句:“我的情况跟人不一样,我的人生可以写一本书了。”

一幅盲人画
1984年6月的一天傍晚,天色有些暗了,15岁的常久明与父母在棉花田里劳作,远远看见叶老师一跌一撞地走过来,父母叫他赶紧躲起来,别让叶老师看见。
那天下午,他跟叶老师说不读书了,然后提前回了家。他家离学校五公里路,路很难走,要过河爬山,河在长江边上,正值汛期。他没想到叶老师会来。
叶老师是来劝他的。他成绩很好,非常想读,但家里太穷,三个妹妹都没读了,父母早给他找好了师傅学裁缝。“我们全家人都很尊敬叶老师,老师一说我们肯定是受不了的”,常久明一直躲到天黑,才敢回家。
那个年代不读书的人很多,少年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个老师会这么远跑过来劝?他步入社会摸爬滚打,走过许多坎坷之后,才体会到,“那是老人的一份舍不得啊。”
三十四年过去了,常久明依然深刻记得,那天傍晚叶老师蹒跚走来的画面。“每次想到这个事情都要淌下泪。”他回忆时泣不成声,用了几分钟才平复情绪。

常久明不知道,在很多年前,相似的一幕也曾发生在叶老师身上。
1928年,叶连平出生于山东青岛,上面两个异母姐姐,下面两个同胞妹妹,他是家中独子,从小养尊处优,备受宠爱。父亲给外国人做厨师,下班很晚,常常捎些茶食、水果回来,塞到他熟睡的被窝里。
父亲是河北沧州人,少时跟三哥学艺,弹腿不直,挨了一巴掌,赌气跑到天津。因为没有文化,只能给人听差,当苦力。父亲讲过一个真实故事:有个潍坊人满某在青岛给外国人干活,东家赖他偷了夫人的首饰,写了一纸诉状,还叫他自己送到警察局,满某不识字,当场就被关了起来。
父亲以上三代文盲,吃尽了苦,尽管吃穿都成问题,仍想方设法一定要他念书。
叶连平8岁那年,举家迁往天津,上过私塾,小学由日本老师教日语。12岁那年,母亲因病逝世,他跟随父亲和继母到上海,进光夏中学读初中,学英语。


他对英语一窍不通,也听不懂上海话,个矮坐前排,总听到身后传来嘲笑声,几个高个女生拦他路,用上海话骂他“十三点”。
他忍无可忍,跟父亲说不念书了。父亲气极,对着他胸口狠狠打了一拳。父亲一辈子就打了他这一次。打完又心疼,给他买膏药贴,软声劝导。
叶连平从此发奋苦读。他记性好,学东西快,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园序》十分钟就能背下来。初中毕业,考了全班第一名。第二名后来成了清华大学数学教授。
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雇主陆续离开,父亲因此失业,开始摆摊修自行车,也骑车往郊区贩运大米,经过日军哨卡时总是提心吊胆。有次鬼子一刺刀把麻袋戳破,大米撒了一地,不敢去收。
在这样艰难的岁月,父亲仍坚持供他读书。高中入读南苏中学,班主任林志纯老师知他处境艰难,多方给予帮助。但一个学期下来,生活已到了绝境。
林老师听说他要辍学,反复劝他,给他打气,可是没办法,“饿着肚子怎么念啊?”林老师实在舍不得,绘了一幅水彩画,临别递给他,眼里满是泪水。
画上是一个盲人,一手拄着一根棍,一手打着乐器,探路前行。这幅画在“文革”时被烧了。
没戴上的帽子
2018年5月5日清晨,叶连平在雨中张望,等最后一个迟到的女生。他本来担心下雨,有些孩子来不了,没想到48人全员到齐。
带学生到南京、合肥,参观科技馆、博物馆、烈士陵园等,是叶连平十几年的惯例,每年春秋各一次。安徽省科技馆有感于叶老师的行举,从三年前开始资助,欲包揽全部费用,叶连平不答应,坚持要出车费。这次去合肥两日游,他出了半个月工资。
在蒙蒙细雨中,大巴奔驰在高速路上,车里响起整齐的歌声:“XYZ,Now you see,I can say my ABC.”叶连平在过道上站着领唱,双手挥动,声音洪亮,中气十足,就像他每一次上课那样充满激情,好像永远不会疲倦。


去年到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参观,遇到三个外国人,孩子们跑去跟他们讲话,对方用法语说:“我不会讲英语,我们是法国人。”叶连平年轻时学过一点法语和俄语。但他最在行的还是英语,交流无障碍,曾接待过香港大学副校长何立仁(Ian Holliday)。

他17岁辍学那年,抗战胜利。次年随父亲到南京,进入美国大使馆工作,起初不谙英语,只能任勤杂。
父亲的东家大卫·白格担任一等秘书,会说中文。有次他把叶连平叫来,故意说英语:“George!A hammer,please?”叶连平一脸懵。亏他记性好,把这句话原封不动记下来,跑到楼下找接电话的李大爷,复述一遍,李大爷告诉他“hammer”就是榔头,他赶紧拿个榔头送去。白格摸摸他的头,称赞:“Good!Good!”
从大使馆开到闭,叶连平生活在外国人中间三年零六个月,一天到晚跟外国人打交道,“把嘴练出来了”。
勤杂什么人都能接待,叶连平认识司徒雷登、巴特沃斯,也见过宋子文、孙科、白崇禧、陈诚、翁同酥等众人物,还跟宋美龄握过手。

“就是因为大使馆,我吃了大亏。”老人话锋一转,眼眶湿了,两行浊泪溢出来,顺着沟壑纵横的皱纹缓缓流下。“请原谅。每每想到这个事情,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方素旧的手帕擦了擦眼角,“差点把老命送掉了。”
解放初期,很多劳动人民都是文盲。离开大使馆后,叶连平暂时失业,闲暇无聊,便与几位居民、同事携手,办起了识字夜校。津贴有限,但谁也不在乎。

1955年冬天,叶连平已是南京琅琊路小学群众夜校的总务主任。一天,户籍警突然来到学校,把叶连平抓走了,隔离审查9个多月,什么也没查出来。又对他管制一年,进行群众监督,警察经常上门让他写资料。审查两年半,帽子没戴上。但往后二十年,始终无法摆脱“特务”嫌疑。
“那时候怕戴,现在想想,我还想戴。反正已经受折磨了,如果戴上帽子,平反以后补发工资,那我赚到了!”叶连平在大使馆每月102美元,他本可以去领退休金,但他不敢拿了。
1960年,户籍警再次上门,叫他签志愿书,强令他离开南京。他下放到老家沧县,住在三大爷家,大队干部们议论,南方来了个“坏小子”。
时值三年自然灾害,叶连平不会干农活,挣不足工分,雪上加霜。刚开始有点行李物件,可以坐火车到山东换些地瓜干回来,让全家人多撑两天。几趟下来,连皮鞋毛巾都换掉了。饿得不行,什么野菜、树皮、生癞蛤蟆都吃,吃完就拉肚子。

这样度过了极其艰难的三年,到1963年,双腿已肿到膝盖,袜子都脱不下来,眼看不行了,终于咬着牙回了南京。
叶连平拿着迁移证去落户,派出所不肯接受。没有户口,便没有工资、没有粮票,依然吃不饱。1965年,经同事爱人张厂长介绍,迫不得已才来到石跋河。
救命之恩
石跋河与南京相去不远,位于安徽和县乌江镇,时属卜陈公社。叶连平在此遭受了最重的政治压抑,也收获了最多的善意。
开始寄宿在张厂长家。张厂长的侄子张广源当时在和县读高中,周末回家一看,“哟,我们家怎么来了个外国人?”因为叶连平身高体长,高鼻长脸,还讲国语。
家里宰了鸡,张广源喊他吃,他说他“平生不吃肉、不吃蛋、不吃鱼”,只吃素。家里韭菜多,他最喜欢吃韭菜。这种状态维持了几个月。
村民觉得“这人有点怪怪的”,不吭气,少言寡语。不管分内分外,什么事都干,“干了记不记工分,工分算多少,他从不计较”。
先到窑场干活,烧窑搬砖拉砖,勉强干了一年,场长看他干不来,就让他当炊事员,一天挑三十担水,累得要命。
这期间,把大队干部得罪了。大队部拿来几条黄鳝,让他烧好,供干部喝酒。叶连平不敢碰这酷似毒蛇的活物,有个干部说了两句横话,惹得他失控了:“我是为职工做饭的,不是服侍干部的!”
这名干部后来贴了张叶连平的大字报。公社通知大队三天内将叶调走,大队任书记劝他暂时规避,等风头过去,还可以回来。任书记蹲在板凳上,说:“你是个好人哪!”
2012年,叶连平被评为“中国好人”。他在合肥作报告,滔滔讲了45分钟。讲完后,一位离休干部上来,拉着他的手问:“你怎么成为中国好人的?”一下把他问住了,“僵得几乎下不来台”,台下六百多人还没散。为难之际,忽然一句话从他脑中飘出来:“因为我生活在好人中间。”
窑场同事给他吃山芋,村民收留他住。他干不了重活,大队安排他到生产队。他不善农活,生产队照顾他,让他种树养猪记工分。
叶连平再度回到石跋河,被赵兴柱接纳在家,那位大队干部曾威胁他赶走叶连平,赵秉性刚直,拍胸表态:“我赵家三代贫农,要是老叶犯法,由我代罪!”就这么把他护下来。
一天清晨,叶连平正把收割的油菜摊晒在门前,队长通知上午开会。排队去公社的路上,民兵营长陈朝余将他喊出队列,叮嘱他:“无论上面说什么,都不要吱声。”
那次大会批斗十个人,算命的、要饭的、换鸭毛的等等。有个人因不肯低头被民兵一把撂到墙头。轮到叶连平了,愤怒控诉充斥全程,他始终一声不吭。
“回到家气死了!”一进家门,痛哭失声。他缩在房里,越想越难受,萌生了死念。正当此时,对门的李银才推门进来,劝他好久,又帮他收油菜、打菜籽。
1970年,初冬乍寒,叶连平被押到历阳镇的“文攻武卫”指挥部,三教九流混在一起,关了7个多月。指挥长喝醉酒就打人,晚上常听到女孩的哭喊。叶连平在难闻的酒气中,也挨过两巴掌。
曾收留他的同队社员刘友良,叫他爱人赵桂珍炒了一袋小麦熟面,送到指挥部。叶连平看到她,惊诧不已,再看到那袋炒面,差点落下泪来。
那种环境下,没人敢和他沾边,唯恐避之不及。妻子离开他,亲戚疏远他。刘友良夫妇与他非亲非故,却冒着酷暑,往返五六十里,给他送一小袋炒面。
“不是这些好人我早死了。”叶连平嘴里念着一个又一个名字,动情地说:“这些人都是我永远忘不了的,永远忘不了。”
拨乱反正后,他曾有两次机会回南京落户,没回去。当教师后,两任教育局局长要调他到和县,也婉拒了。
“我在最困难的时候来到这里,这个地方救了我的命,这里的父老需要我,我不能离开。”
这位前半生颠沛流离、受尽苦难的老人,决定扎根异乡,把自己的一切拿出来,守望这片土地上奔跑的孩子们。
“不务正业”
叶连平教了四十年书,学生遍布四面八方,走到哪儿都能遇到。
5月11日早晨,他坐船过江去火车站看班次,三大爷的独孙过几天结婚,他要回沧州喝喜酒,十几个小时,不肯买卧铺票。
去的时候,一个面包车师傅喊他,是他以前的学生,叫他上车,他没上,大概不想耽误人家的时间。回来时,有个学生在码头卖鱼,帮他拎东西上船,下了船,又拎下来,还给了他两条鱼。
卜陈学校附近的村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他学生。退休教师老韩的儿子、女儿、女婿都被他教过,孙辈也在他那里补课,出了四个大学生。老韩说:“他培养了我家两代人。”

叶连平清楚记得他重新站上讲台的那个日子,1978年11月24日。这距离1955年他从夜校被拉下马,已过去整整二十三年。
这二十三年正是他年富力强的黄金时代。“怎么说呢,我再也回不来了……我玩了命地干,我也补不回来了。”
1978年,张广源考上大学。彼时,他已是卜陈中学初三毕业班的班主任,他一走,没人上语文课。他跟校领导说:“你们要思想解放,我给你们推荐一个人,叶连平。”
“别人认为我是这里最好的老师,但其实他可以做我的老师。”张广源说。
叶连平当了近十年猪倌,负责全队三十多个猪圈。那时候,大人们包括老头老太都出勤挣工分,家里只剩下娃娃。他整天在全队区域转来转去,顺带照顾那些年幼的孩子。读书的孩子放学了,经常跑来问作业,所以他对课本大概熟悉。
那天大队干部来猪圈喊他时,他正在勾猪屎,围着大围腰,穿着胶靴,手持钉耙。他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从猪圈里跳出来,就这样全副武装、浑身骚臭地赶到大队办公室。卜陈中学教导主任坐在桌后考他课本,当下拍板,让他第二天来学校上课。
从猪倌一夜之间变成教师,叶连平做梦也想不到。公社派人与校长一道去南京查他档案,带回来的结论只有三个字:可以用。
他接手的是初三甲班,48个学生,之前落下一个多月课,待改的作文本堆成小山,时间紧、任务重。学生居住分散,若留校开夜班,难保安全。于是他把全班分成5个组,将邻近村子的学生集中在一起,找个合适的人家上课,每周分别下乡到5个组。家长都很支持,点两盏灯照明。几个月下来,效果颇佳,中考考上11个,比乙班多9个。
下一届,叶连平从初一新生带起,除教语文外,搞了很多课外活动,用某些人的话说,开始“不务正业”了。
他组织学生勤工俭学,带他们漫山遍野去采草药、打树果,用板车拖到镇上去卖。他还让学生养兔子,养好了去卖,也卖过废铜烂铁。卖来的钱作为班费,买图书文具和运动器材。
“卖药材没多少钱,怎么能买那么多书呢?整个学校都没有我们班的书多。”常久明知道叶老师贴了钱。
他组织学生打扫厕所,要挑粪,又脏又累,他带头干,一干就是三年。还带学生去清扫大桥、慰问养老院、到部队营房参观,不一而足。
王小四也做过老师,但叶连平当年做过的事情,很多是他从来没有想到过的。“我觉得他很接近教育的真义。”
那时候,叶连平不赞成照本宣科上课,自创“四步教学法”,在省内外示范推广。在学生们看来,叶老师上课生动有趣,像讲故事,完全不拘泥于课本。
学生说,叶老师每年每个同学至少家访一次,不管多远都要去,提着马灯满村跑,有次还跌得满身泥水。了解情况后,尤其照顾那些家庭困难、住得远的同学,送钱送书送衣物,邀他们到自己家吃住。学生考上大学,他亲自送去报到。家长送两个鸡蛋,他都不要。
常久明几个同学上学要过河,河面20米宽。有次下大雨,水势湍急,他们找根绳子绑在腰上,坐着小盆冲过河。叶老师看到他们来了非常感动,抱着他们说:“孩子们,你们辛苦了。”类似的小事很多,让常久明觉得,“他跟其他任何一个老师都不一样”。
正直仁义
1985年,叶连平被评为“全省优秀教师”。随后,他从民办教师转正,乌江镇党委委员盛锦平动员他入党。

他在大使馆工作那三年半,整天跟美国人打交道,不关心也不懂政治,日子几乎是一帆风顺的,除了中共地下党员何馥麟一事。
何馥麟从上海总领事馆转移到南京,与叶连平成为同事。1948年冬天,何的身份暴露,国民党包围了大使馆。那天何上完夜班,去找了叶连平。
叶连平回忆,那时他住在使馆后院,看老何突然闪身进来,说要借宿一晚,且衣着单薄,并未生疑,赶紧添煤生火,给他炒了碗蛋炒饭,但看他只吃鸡蛋,咽不下饭,便知他有心事。何说是青帮找他麻烦,叶有意陪他回家,何拒绝了,并称已派侄子何耿芳穿着他的大氅和皮帽给妻子送信了。两人抵足而眠,何辗转反侧,天还未亮,就起身要走,迟疑片刻,问:“小叶,你有钱吗?”叶连平打开箱子,给了他一沓关金券,大约二十张,每张2万元。他数也没数就揣进口袋,朝外走。叶连平抽出一件长袍,喊他披上御寒,但人已不见踪影了。
何馥麟脱身后,妻儿被监控,家门口一天到晚有特务守着。何妻要回上海,叶连平亲自护送母子三人到火车站,后面一直有特务跟着。
解放后,何馥麟写信邀叶连平来上海。叶连平到他家(霞飞路北侧),何妻拉着两个儿子下跪,感谢他救命之恩。
“其实我也没有救他的意思,都不知道他是地下党,很偶然的。”叶连平落难时没有去找他。
张广源毕业后调回家乡工作,从副镇长一职退休,现是镇关工委主任,一直与叶连平有来往,有时也讶于其言行。在他看来,叶连平是个爱憎分明的人。
2012年夏天,朱鸿卿去世。叶连平被公社驱逐后,一度借居他家。张广源考虑到叶连平年纪大了,天热路远,就没有告诉他,独自奔丧去了。回来后,叶连平向他发火,然后带着两块烧饼一瓶水,骑车上扬州,近200公里路。到了朱家,车子一放,直奔坟地吊唁,一句话不讲。次日天不亮就往回赶,因为还要上课,朱家留不住他。
而在另一场葬礼上,叶连平的态度截然不同。
原村书记是叶连平的学生,因贪污拆迁款被撤职、开除党籍。半年后他的父亲去世,叶连平买了个花圈去奔丧,把他喊到跟前,当众训斥,大意是:你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你好好干,你老子去世,还有点光辉,就因为你这个不肖之子,贪了几个钱,你老子死不瞑目。一顿话,把他骂得哭笑不得。
学生出现品行不端者,叶连平认为自己也有责任,“说明教育不到位”。几个教育失败的案例,让他更加笃定,教师树德育人,任重道远,非一日之功。“一个教师如果言行不一致,更坏。”
老校长次子严政是叶连平的首届毕业生,后来也当了民办教师。一天偶然撞见严校长罚跪严政,原因是严政打麻将。叶连平从中调解,费了许多唇舌都无用,忍不住开炮:“你没有资格教育他,你不要孩子打麻将,你自己打不打?”老校长不吭声了。
因为订的辅导书有误,叶连平骂过教育局领导。因为纠了个错字,得罪了学校主任。他性格耿直,往往对事不对人。
1991年一天中午,两个老师家属在学校后院卖菜,发生争执,厮打了起来,场面很难看。叶连平赶过去把两人拉开,然后跑去找时任的校长解决,但四处不见人影,找到时,他正在一位老师家里吃饭喝酒。叶连平进门就发火:“外面都闹翻天了,你还在这儿喝酒!”
叶连平当时已超龄工作两年,那个学期一结束,就退休了。
闲不住的人
叶连平捧着教材、参考书,和两个省下的黑板擦,交到教导处,便没法走出来了,“趴在桌子上哭得不像样”。很多老师不理解,退休了有什么可哭的?
高中辍学离开学校,他也是这般不舍的心情。班主任林老师十分痛心,送画泪别,引发他对老师的眷恋。解放后,看到很多底层劳动者不识字,他们的孩子念不了书,推己及人,他自然投入扫盲工作,开办托儿所。后来,他真正从事教育事业,体会到教师育人的特殊职责,便已立志为之奉献余生。
叶连平是闲不住的人。在南京被管制期间,没有职业,没有收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是无聊而痛苦的,于是他给自己找事干,每天打扫街道,写黑板报,为学生补课。至今他还保持写黑板报的习惯。


退休28年,他几乎一天没歇。各个大队小学有老师请假,都找他代课,短则几天,长则三年,哪有需要,喊一声就去了。
代课金300块一个月,都还给了学校。他给5所小学买了6台二手风琴,给宋桥小学装电灯,给龙王小学栽了100棵水杉树,给黄坝小学种了220棵白杨树等等。

看到农村学校英语教学条件差,影响升学,叶连平很着急。以前被怀疑是美蒋特务,他从不敢说英语,这时,他决定“拿出来变废为宝了”。
2000年,他在自己家里开设英语课堂(后更名为“留守儿童之家”),义务辅导小学和初中生,所需的书本用具都是他掏钱买。那间三十平米的旧屋,每天一放学,就挤满了书桌和孩子。
这些孩子来自周边村,大多父母不在家,爷爷奶奶没文化,对功课帮不上忙。6年前,镇政府出钱把他家对门的学校仓库,改建成两间教室,一间供他上课,一间作为图书室,学生可以在这里做作业、看书、下棋、打球。


去年中考,卜陈学校考上重点高中8人,其中5人都在他这儿补课。“为什么孩子有这个积极性?我不承认是因为我不收费,关键有效果。”
有人骂他二百五,说他作秀,也有人嫉恨他,断人财路。“我们这里有个小学老师,是我学生,说出来打我自己的嘴巴,他给孩子们补数学,收费800块一个月。”
叶连平不太在乎外界的褒贬。他领过的奖都摆满橱窗了,这些表彰对他而言,“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只代表过去,不代表未来;不是光环,而是负担。
“如果我在言谈举止上有一点点不妥,甚至错误,那这个责任不都是我的,国家也要受损失,人家会怎么说?就你还中国好人呢。”
这次带学生到合肥,叶连平两天没睡好,等孩子们安全到家了,心才能放下来。“虽然是个好事,但出了事故,名声就不好了。”
老伴对他不理解,回来朝他发牢骚,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一块钱车舍不得坐,一去合肥花掉一两千。家里的煤炉漏气,封不紧,老伴去买了个新的,二十块钱不到,叶连平硬是叫她退了回去。他的原则是,该花的钱绝不小气,不该花的钱,一分都不会花。
别人说宽裕生活是“小康”,他自我感觉已是大康,不愁吃穿,可以在家上厕所,还有坐便器(注:几年前房子漏雨,政府帮他翻修,装了卫生间),“我跌跌爬爬能撑下来,已经很知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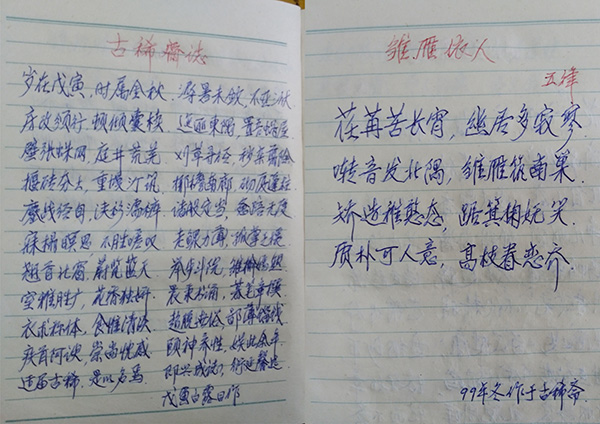
“死而不已”
最近,有几个“重点人物”老在叶连平脑子里转悠,忧虑他们的成绩、升学和经济状况,包括一个已读高二的孤儿。
他至今仍坚持家访,在他这里上课的孩子,除了新来的不了解,每一个的家庭情况、爱好、缺点,他肚子里都有本账。
“有人奇怪老头子还骑车满天飞,那我不飞,孩子交给你了,如果干不出成绩,怎么交代?”
5年前,叶连平在家访路上被电瓶车撞到了,从那以后,他就经常跌倒,越来越严重,有次半夜跌在地上,昏迷了。居校长送他到南京医院,查出是脑溢血加脑膜炎。
一开始医生说他年纪太大,没办法了。居校长求医生,说他是中国好人,现在还替孩子们免费上课,医生才愿意做手术。但风险很大,成功率只有5%,“可能下不了手术台”。
也许是福报,手术很成功。本来要住院一个月,但第四天叶连平就急着出院了。医生犟不过他,打印了一张自愿提前出院的证明让他签字,才肯放他走。
当时头上盖着纱布,线还没拆,根本走不了。他先打电话给居校长,问他能不能来接,居校长劝他好好休养。他又打给南京的学生,一个退休区级干部,来了两辆车,夫妻俩用担架把他抬上车,一直送到家。
过了一礼拜到南京拆线,医生说:“你这个老头,我们都没见过,这么大的手术你四天就往家跑,你回家能干什么啊?”
不光心疼住院费,叶连平也想早点回去守着留守儿童之家,虽然上不了课,但每天都有学生来借还书。他天天坐在那儿,一边借书,一边写回忆录。
以前没时间写,周末两天上课,周一周二改作业,周三印讲义、上书法课,周四周五备课、家访,一天忙到晚。
老韩劝他不能再这么劳累,身体吃不消,他说:“老韩啊,正因为我不行,我再不干我没时间了。”


当年,王小四问他为什么退休了不好好享福,他满脸笑容:“我已经在享福了,我非常幸福。这样的工作可比休息强多了!”一天到晚跟孩子们在一块,使他常常忘记自己已是耄耋之年了。
对他来说,老有所为才能老有所乐。他有个十六字心志:生命不息,战斗不止;鞠躬尽瘁,死而不已。“我活一天我蹦一天,走了就走了。”
他已安排好后事。如果走在老伴前面,除了留下一定的生活费,他会将全部积蓄捐给叶连平奖学金基金。这个基金成立七年,他陆陆续续投了5万。
其次是将遗体捐献给安徽医科大学。他有五个学生读安徽医科大学,过年来探望时,曾提到做解剖学实验没有人体标本。
叶连平没有后代。他的首任妻子曾怀过孕,因为他政治上受到怀疑,妻子将孩子打掉,与他离了婚,现在这个老伴是他71岁时收留的,那时她被儿子儿媳撵出家门,生境狼狈。

虽无儿无女,但学生满堂,桃李天下,也是另一番慰藉。眼下他最大的遗憾是找不到接班人,“我走了以后,这些孩子们谁管?”
目前寄宿在叶连平家的学生是特困户,家离学校很远,没有电,从初一开始住到现在,马上要中考了,她功课不太好,叶连平答应她无论考好考坏,不用担心经济问题,“只要爷爷有口气,不会让你念不起书。”她以后想当老师,改变农村教育现状,“希望像叶老师一样创造人才。”
春去秋来,日升月落,孩子们从各地汇聚于此,学习,嬉闹,奔跑,成长,又散落四海。叶连平像一个稻草人,风吹不倒,雷打不动,守着这片乡土,这间教室和这些孩子们,直到生命尽头。
“叶老师再见!”孩子们每次都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