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罗斯在拧紧
编者按:当地时间5月22日,美国著名作家菲利普·罗斯去世,享年85岁。本文原发表于《新知》,由作者授权澎湃新闻使用。
菲利普·罗斯的最后一部小说《报应》(Nemesis,2010)在成稿前共写了十三稿。这位文坛老兵并不认为这种写作匠人的艰辛值得自豪,因为不断的重写无非证明了他并未找到写作的感觉。为了写好这个以1944年新泽西纽瓦克脊髓灰质炎爆发为背景的寓言故事,他特意重读了加缪的《鼠疫》。罗斯一直羡慕厄普代克和贝娄,因为文字在他们笔下可以肆意奔涌而出,而自己却“不得不为每一段话、每一个句子而战斗”。前一年写就的《羞辱》(The Humbling,2009)虽然第三次荣膺了国际笔会奖,但他深知这些不过是对即将退场者的纪念勋章。书中主人公阿克斯勒(Axler)倏然消失的舞台灵感,正是罗斯感同身受的创作焦虑的投射。贝娄在八十五岁高龄还写出了《拉维尔斯坦》(Ravelstein,2000),罗斯却发现自己已身心俱疲,无力继续经营好长篇小说了(或者用他的话说,无法再“从无中抓出有来”)。


1.
青年时代的罗斯有过不可思议的文学起跳。那个27岁就凭着短篇小说集《再见,哥伦布》(Goodbye, Columbus, 1959)获“国家图书奖”的记录,怕是极难再被文坛新人超越了。那时,刚从康奈尔毕业的品钦还在酝酿着自己的小说处女作《V.》。在日后的回忆中,这个仅年长他四岁的罗斯如火箭般冉冉升起,曾让同样雄心勃勃的品钦颇受鞭策。
然而,罗斯最早的文学声名却并非完全因为评论家对其写作本身的赞美,而是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国犹太社群的抗议声潮。《再见,哥伦布》中最受争议的一篇是《信仰捍卫者》(“Defender of the Faith”),它最早单独发表在《纽约客》上,讲述了一个二战期间的美国犹太军官在新兵训练营里如何被同民族的年轻人激怒的故事,因为这些犹太士兵总以宗教信仰为由,讹诈军中的各种特权。
作为新泽西纽瓦克一个典型的美国犹太移民家庭的后裔,罗斯童年时接受了并不算少的犹太教育。在正常的学校学习之外,他每周有三个下午都要去当地犹太会堂,和其他孩子们一道接受正统的希伯来宗教教育。可是,当这样一个雅各布的后代在战后美国文坛初露头角时,却是以滑稽笔法刻画品德可疑、虚伪无趣的犹太人物为能事,这不得不让那些刚摆脱奥斯维辛噩梦的同胞感到震怒。在他们看来,去小众的犹太人杂志批评本民族的道德瑕疵是一回事,去《纽约客》这种针对美国上层白人读者的地方写这些无异于“告密”!甚至有个犹太教教士愤而投书该杂志,指责“正是这种关于犹太人的认识才在我们时代导致了六百万人被屠杀”。

《奥奇·马吉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Augie March, 1953)是罗斯人生中拥有的第三本精装书。主人公开篇的那句“我是一个美国人,生在芝加哥”给罗斯以极大震撼,它意味着一种新的犹太声音,并确凿无疑地成为罗斯想去模仿和再现的对象。对颠乱叛逆的1960年代而言,如何将犹太身份融入到当代美国的生活经验中,成为了困扰罗斯这代人的麻烦。《波特诺伊的怨诉》关于手淫的放肆描写,以及对犹太家庭喜剧的凶狠挪用,甚至让曾经肯定过他的欧文·豪都感到尴尬和羞怒。这已经不是将犹太民族从战后的道德神坛上拉下来的问题,而是罗斯对那些古板、滑稽、专制的犹太母亲(还记得《生活大爆炸》中霍华德母亲的尖叫吗?)夸张戏谑得是否用力过猛了?
可如果说罗斯对美国犹太人的讽刺太不留情,那恐怕也是因为他对任何人性之劣根都如此刻薄。犹太主题如此频繁地出现在他的早期作品中,这只是因为彼时的罗斯对这一群体最为了解罢了。北美犹太文化中对于金发碧眼的shiksa(意第绪语中的“非犹太裔女人”)的终极禁忌,其实在更深刻的层面上体现了犹太身份与美国身份的互斥性。于是,罗斯的小说会引领着读者发问:为什么我们不能同时成为犹太人和美国人呢?这样的诘问早已超出了犹太性的单纯范畴,它指向了所有族裔文学中身份政治的那个压迫性前设——“非此即彼”地成为某种人。

莱斯利·费德勒曾说,“成为美国人与成为英国人或法国人不同,它意味着去想象一种命运,而非继承什么;因为美国人总是栖居于神话而非历史之中。”罗斯想必非常赞同这一说法,至少他在1970年代之后写的小说,都是沿着这一想象的轨迹在运动。书写犹太民族在美国社会中的种种玩笑,似乎已被这个成熟后的作家所摒弃。他更为关注的,将是“美国梦”这个国家神话中的种种许诺、沉醉、谵妄和背弃。罗斯之所以要对这个动荡岁月的国家做愤世嫉俗的道德观察和政治讽刺,绝不是因为犹太性的烙印让他选择了自我边缘化,而是基于这个出生在1930年代、完整见证了美国二战英雄主义的新泽西男孩毫不动摇的爱国情感。当罗斯为尼克松的政治谎言而义愤时,就写了言辞激烈的社论投给《纽约时报》,在遭到拒稿后转而将之改成讽刺小说《我们这一帮》(Our Gang,1971)发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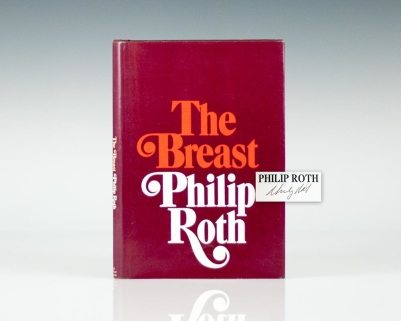


在1970年代中期的一次布拉格之旅中,罗斯引来了秘密警察的跟踪,甚至险些在大街上被捕。罗斯高举护照后大声求救,最后侥幸跳上一辆城市有轨电车才得以逃脱。这些独特经历让罗斯意识到,从自由民主社会里发轫的美国现实主义,其实是对该国作家的天然馈赠,他们往往很难意识到在欧洲的另一种文学传统下,写作是在消音下进行的,需要小心翼翼地逃避各种审查和禁忌。讲述现实已是一种奢侈,更遑论以文学为武器去对垒政治和传统?

自《波特诺伊的怨诉》后,罗斯小说创作真正意义上的突破,其实是1970年代末的《鬼作家》(The Ghost Writer, 1979)。这是一次久违的突破,它代表了罗斯与卡夫卡对位想象多年后的成果,也是上天为他送来了“奥菲莉娅”(这是克莱尔·布鲁姆17岁时在戏剧舞台上饰演过的角色)后,生命重新焕发的异彩。他说自己的灵感来自于一次对马拉穆德(Bernard Malamud)的拜访。在这个老作家的乡间别墅里,罗斯发现了一个据说是照顾他生活起居的年轻女学生。在暧昧的闪躲目光后,罗斯直觉地感到了某种怪异。这种神秘的直觉,并不只是引领着他发现了马拉穆德逝世前才公开承认的忘年恋,还让罗斯发现了重新讲述和诠释《安妮日记》的可能。
当然,更重要的一个文学衍生品,则是书中那个叫内森·祖克曼(Nathan Zuckerman)的小说家。他和《了不起的盖茨比》中那个尼克一样,既是推动情节发展的人物,同时又是游离在故事之外的叙事者。同时,祖克曼作为罗斯本人的分身,还不断自我暴露着文学虚构的本质。他构成了想象界与真实界的一道缓冲的滤网,甚至昭告天下:“如果我还想知道更多,我就得去编造。”这种叙述格局成了罗斯最重要的文学标签,他将以祖克曼贯穿后来的八部小说,尽管也会有人批评这种做法:“谁总那么关心作家是什么样子啊?”

毋庸讳言,罗斯对祖克曼的钟爱,某种程度上出于作家本人的精神自恋。在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钦点的四位最伟大的在世美国小说家(另外三个是德里罗、品钦和麦卡锡)中,罗斯的“自我”是最为外露和巨大的,他的私生活也常常成为公众谈论的话题。与英国妻子布鲁姆在1994年的离异,罗斯虽抱着几分怨恨,却觉得两人还算是朋友。但布鲁姆写的回忆录《离开玩偶之家》(Leaving a Doll’s House, 1996)令罗斯再次感到了来自女人的背叛,因为“奥菲莉娅”宣称自己其实是“娜拉”,这无疑让罗斯深深地蒙羞。于是,祖克曼这样的框架叙事就给了罗斯一种自我正名、自我解剖、自我变形的机会,他需要让世界知道艺术与生活的界线其实有多么暧昧,讲故事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

但无论这些作品如何揭露美国政治与历史的阴暗,罗斯始终不是一个反美主义者(正是在这一点上的分歧,彻底毁掉了他后来与哈罗德·品特的友谊),譬如《美国牧歌》的主题其实不是关乎政治的保守或激进,而是为了表现各种因为固执一念而导致的现代悲剧。换言之,罗斯在小说中精巧细密地进行文本运作,为的是放弃任何意识形态的立场,希望去诠释更为永恒的人性冲突,去刻画欲望与道德的交战。古典文学教授科尔曼之所以后半生要用犹太人的身份诓骗世界,与其说是出自对黑人族裔的耻感,不如说是向往白人肤色的透明与自由,向往赋予自我欲望更多实现的可能。罗斯在《人性的污秽》中体现的这层境界,自然是超越了时下那些纠缠于族裔、性别和文化关系的时髦文学小说。

可以说,暮年的罗斯具有了清晰的晚期风格。父母的辞世,友人的故去,疾病的侵袭,没有什么比这些更能真切地让作家感受到人的衰老和必死。他已在《退场的鬼魂》(Exit Ghost, 2007)中最后一次安排了老去的祖克曼目睹和冥想死亡,也在《垂死的肉身》和《萨巴斯的剧场》(Sabbath’s Theatre,1995)中操练了各种死亡的恐惧和挣扎。他对于犹太人的描写愈发充满温情和理解,在多本关于父母的半自传小说中,不断施展文学的终极法术,将坟墓中的家人和邻居召唤出来。此时的罗斯已经确信,那个曾让他一心想逃离的纽瓦克犹太家庭其实是童年的天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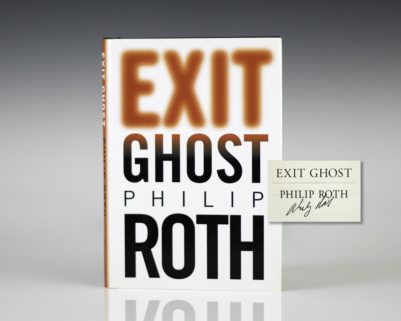
德里罗在《天秤星座》(Libra, 1988)中也会去写反历史,但那是后现代派的写法,最后要揭示的是某种元历史的神秘真相。罗斯虽然也喜用元叙事的技巧,虽然也乐意进入历史的幽暗处展开想象,却仍然在骨子里是个现实主义作家。他从卡夫卡那里学到的重要一课是,“小说的想象越是玄幻离奇,细节上的处理就越要现实主义。”罗斯在不同场合告诉那些试图将他归入后现代小说流派的采访者:“是的,约翰·巴斯很不错,但请给我约翰·厄普代克!”
不过,他对德里罗和麦卡锡还算欣赏,尤其是前者那种无所不包的小说风格,在罗斯看来与他的另一个文坛偶像汤姆·沃尔夫(Tom Wolfe)颇为相似。这恐怕也是为什么罗斯得到第一届“国际笔会/贝娄奖”后,在2008年和2009年以评委身份先后推荐了这两位作家。那个写过用动物内脏手淫的罗斯或许是评审时第一次读到《血色子午线》(Blood Meridian, 1985)和《大都市》(Cosmopolis, 2003)。他以古怪而哀伤的口吻说:“读他们,让我觉得自己很普通。”
当然,没有比这更伟大的自谦了。
【注】本文部分素材来自新书Roth Unbound: A Writer and His Books,作者是Claudia Roth Pierpont, Farrar Straus Giroux出版社2013年10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