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杨国强:追寻历史变迁中的因果与意义
【编者按】本文原载《学术月刊》2018年第2期。
杨国强,1948年生于浙江。1985年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师从陈旭麓先生,1988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9年进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学研究所工作,历任副研究员、研究员。2008年至今任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近代史的研究。著作有《百年嬗蜕:中国近代的士与社会》(1997年)、《晚清的士人与世相》(2008年、2007年)、《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徨》(2008年)、《历史意识与帝王意志》(2011年)、《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2014年)、《脉延的人文:历史中的问题和意义》(2017年)。
张洪彬,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讲师。

张洪彬:杨老师,您好。很高兴有机会采访您。《学术月刊》的学人访谈栏目主要采访学者的学思历程,尤其是问题意识、代表性论点、思想资源、方法论等,以帮助读者阅读学者的作品。首先,还是请您谈谈您是如何走上学术道路的吧。您的胞弟杨国荣教授是哲学学者,您是历史学者,你们中国思想的研究和方法有什么异同?请问是怎样的家世背景、人生道路和学习经历使您对史学研究发生了兴趣?
杨国强:我的父母都是工人,属于中国成千上万劳碌一生把子女养大的寻常老百姓。他们识一点字,能读报纸,但文化程度都不算高。因此,父母留给我的是养育之恩,但就学术而言,其实并没有家世背景。而说到学习经历,则记忆最深的是,小学读书因野气太重而不肯上心,弄得常常要补考。在长辈眼中,显然是被归入顽劣一类的。其间稍有一节可取,便是十岁前后起喜欢胡乱读课业之外的闲书。这种胡乱,既在于有什么书就读什么书,今天读《铁道游击队》,明天读《说唐》,后天再读《创造十年》和《吉珂德先生传》;又在于似懂非懂和了无章法,以读完《三国演义》的那点知识就敢懵懵然读《汉魏六朝诗赋选》、《世说新语》等等。但由此形成的心之所好,则留下了一种以文史为取向的精神惯性。所以中学时代开始野气收敛,有如脱胎换骨,但这种惯性却始终相伴,并演化为此后二十多年里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好读书不求甚解当然不能算是对待知识的正确态度,然而这个过程以其漫无边际造成了阅读的广度,也以其日积月累造成了阅读的总量,两者无疑都会成为影响思想和眼界的实际所得。所以,以后来反视当初,今日之所知,又正是由此胡乱读书和不求甚解为起点,一路七高八低地走过来的。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经历和个人经验,并不具有普遍性。但相比于眼下淹没在题海里的中小学生,则意中引为感激的,是我们这一代人所处的教育环境至少还宽留余地,在一生中最适合广泛阅读的年龄段给予了一种可以广泛阅读的机会和可能,而后由阅读获得的知识和感悟化为涵育,化为造就,遂使人面对古今之际能够想得更深一点。与这一面相比,后来以治史为业的“学术道路”则更曲折一些。1977年恢复高考,我选择的志愿都是历史专业,但没有一个大学的历史系愿意收我。于是移到政治教育,并在毕业之后教过三年党史。因此1985年考入陈旭麓先生门下已经37岁了。王安石说“命属天公不可猜”,所指大概正是这种人生自主的有限性。
至于你所说的“思想史研究”,可能归类过于简约,就我个人的本意而言,其实很少把思想自身当成认知对象,更关注的是人物、群体及其历史活动。因此下笔涉及的思想,大半是附着于历史过程和反照历史过程的。以此为比较,则哲学的本性决定了哲学家论思想不能不由概念起讲,并在概念的界定、演变和串连中形成分析和叙述。所以哲学更需要用过滤和抽象为功夫,以筑成思想的骨架和逻辑,而史学着眼于具体和个别,遂更多一点思想的血肉和情理。
张洪彬:请谈谈您的导师陈旭麓先生如何引导您的史学研究。换言之,您对陈先生的继承和发展主要是在那些方面?读陈先生的研究和您的研究,感觉有一个明显的共同取向,即都很注重通惯地理解较长时段的历史变动。如果这种观察正确的话,可否谈谈这种取向背后有怎样的缘由?
杨国强:陈旭麓先生晚年自编文集,以《近代史思辨录》为名,表达的正是一种自我归结的学术取向和学术特点。总体而论,与作史相比,陈先生后期尤用心于论史,因此,其治学固重历史知识,而更重历史思维。在八十年代自述读书心得的一篇短文里,他曾特别提到自己每年都要读一遍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用意里显然也在于此。这种把思辨引入史学的自觉在那个时候的中国是少见的,但又是从其数十年治史所得和反思所得中形成的。现在想来,当年我读《论中体西用》之日尚未入陈先生之门,而印象深刻的是经此发蒙,始知叙事的历史可以达到这样的说理深度。这是一种思想锲入了史实内里的深度,而思想之能够锲入史实内里,借助的便是思辨。历史是一个因果之中的过程,是一个矛盾之中的过程,是一个合多样性为一体而又常在分化组合之中的过程。这些都决定了历史过程里的人物、事件、思想,只有置于因果、矛盾、分化组合构成的前后联系、上下联系、左右联系之间才能显示其本来面目,从而认识其本来面目。因此,在横隔了时间和空间的当下与过去之间,要依靠不成片段的历史材料重现这种因果、矛盾和联系,历史叙述的困难便常在于脱不出单面立论、浮面立论、局部立论和静止地立论。陈先生于此尤有清醒的意识,所以论史之际能够更多地以全面性成就深刻性,更多地由历史的外观触及历史的本相和内里;更多地观照于前一段历史和后一段历史之间,沿此以审知历史的走向和脉络。在我学而后知的有限体验里,思辨虽是一种思想方式,但其实际结果却会最终形成别开一路的视角和视野,有此不同的视野和视角,而后是熟识的史实常常会在更广的时段,更远的因果,更复杂的联系中显示出原本不容易见到的意义。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曾长久地成为史学研究的对象,但以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为眼光,则比其自身的兴衰起落更深入地影响了后来历史的,其实是由此引发的十多年内战促成国家权力下移,使三十年以洋务为中心的漫长过程借助于地方权力而起于东南,同时是此前二百年久抑的绅权因筹饷募兵而重起于地方;疆吏的幕府因战争的集权而大幅度政府化;捐纳、保举冲击科举并导致吏治失范,以及用扩大学额奖励捐输所造成的士人在数量上的大规模增多,等等。这些变化因太平天国内战而来,却长久地留存于晚清最后四十多年之中,并衍生为后来的因果,以其造成的正面和反面的影响四面八方地牵动了后一段历史的曲折变迁。然则以此为实例,又说明思辨之能够形成视野和视角,对于主体来说,其论史的深度本是以读史的广度来成就的。由此而及你所说的“贯通”和“较长时段”,则因其“长”而后能有其“通”,对应的也正是这种关系。因此,思辨虽常常被看成是治史的悟性,而其背后却是无可取巧的层层积累,是日复一日与故纸青灯相伴的辛苦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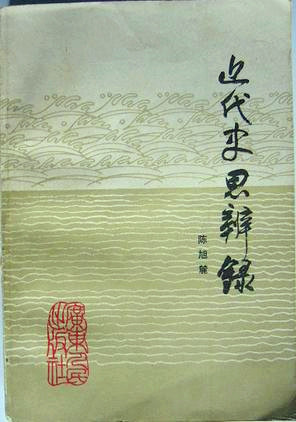
作为陈先生的学生,我视为不断努力而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不过是薪尽火传。三十年来虽以阅读、思考和写作、教书为人生之常态,并在这个过程里所涉论域后来广于从前,但一路走来,心中委实未曾想到过自己这一点出自陈先生所教的本事能够廓然张大,用来“发展”陈先生的学问。
张洪彬:陈旭麓先生讲近代历史的新陈代谢,一般认为包含较强的进步主义的价值取向;您则似乎更关注历史变动中失落的东西,比如秩序的崩坏、国家的分裂、民生的凋敝、德性的溃散。您曾经说过,“每一种进步都是以摧折为前提的,从而每一种进步都是以牺牲来成全的”。可否谈谈这种问题意识是如何产生的,这种视角对您为何重要,是否有意识地对陈先生或其他前辈史家的研究做一些补充或超越?
杨国强:陈旭麓先生论述中国近代历史具有明显的进步主义取向,因此我进入陈先生门下,一开始就在进步主义的影响之下。但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出自我笔下的历史叙述,似乎已更多地涉及历史变迁过程中与进化相伴而来的曲折、舛错、污秽、利欲,以及身在其中的有人欢喜有人愁。与进步主义相比,这是一种变化。但这种变化是在一个一个具体历史问题的论说中显现的,所以相当一段时间里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回想起来,最早对我进行教育的,是比我早入师门的茅海建教授,他说我们陈先生是进步主义者,你怎么变成文化保守主义了?有此棒喝而后有随之而来的自我审视,并因自我审视而更深地理解了陈先生。后来我对海建说:陈先生志在以史经世而溘逝于八十年代后期,因此,对他而言,在经历了文革之后,八十年代以理想主义、进步主义呼唤现代化,以及此中所内含的希望和憧憬,便都成了其意中经世的主题。之后是这个时代面临的问题和关注的问题由外而内,汇入这个时代历史学家的眼光和尺度,使之竖看历史之际,会非常自然地重心集中于近代中国艰难变迁中的开新与守旧,并着力于说明开新相比于守旧的必要性、必然性和不容怀疑的合理性。这种特定年代的重大问题与特定时代历史学家之间的关系是古今之通例,所以克罗齐所说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常常要被人引来作诠释。而作为一种事实,每个历史学家都是特定时代中的人和每本历史著作都产出于特定时代,又说明了历史为什么可能一遍一遍地写和历史为什么需要一遍一遍地写。

与陈先生相比,我们看到了八十年代犹被呼唤的现代化在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国节节铺展,看到了市场经济的活力,看到了财富和物力前所未有的大幅度增长。然而身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同时又直观地看到了日益切近的现代化本身所内含的复杂、矛盾和歧义;看到了市场法则的泛滥化以及由此导致的官场腐败、学界腐化、人际关系的商业化;看到了价值分化、贫富分化、社会群体分化;看到了社会随经济变迁而变,经济随技术变迁而变以及人在其中的被动应变与身不由己。这些都是八十年的理想和憧憬中所没有的东西,而在真实的现代化过程中却已是实际面对和必须应对的东西。面对和应对,既说明了现代化不会自然圆满,则同时又说明了现代化的本义仍然需要认知、并仍然犹在认知之中。两者都决定了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和关注的问题已不同于八十年代,而这种由直观催发的思考,最终不能不影响眼光和尺度,使我在读史之际不仅会看到历史进化过程中的一片光亮,也会看到同一个过程里的七颠八倒。我意在叙述历史本身的具体和复杂,其实与进步主义和保守主义都无关。但自外观而见,由此表现出来的,便是学生不同于老师。但作为学生,我非常相信的是,以陈先生之睿智,如果他能活到现在而目睹铺展中的现代化所显示的真实矛盾,则我所说的这些话,他大半都会说。因为他始终是一个追求真实和深刻的历史学家,一个以史经世的历史学家。我以这些自我审视之所得回答了海建,在我的印象中,似乎能够使进步主义的海建教授意有所动。所以,也希望这些自我审视之所得能够回答你的问题。
而你所提到的进步以摧折为前提,说得通俗一点,不过是20世纪初年以来国人熟知已久的破旧立新之相为依连。而其间之难于辨识,则在破与立的一时不同于一时之莫可名状。清末最后十年里时论推崇尚武而贬斥文治;朝廷为兴学而停废科举,都是以进步为理由而牺牲掉时人眼中的落后。然而曾不数年,民初的时论却已在力倡文治而痛詈武人当道的暗无天日;而同一个时间里,最先主张兴学以废科举的梁启超又最先转过身来悍然主张“复科举”。读史至一见再见这类同一个人以左手打右脸,之后又以右手打左脸,于是切知进步之为进步的容易论说而难于判定,相比于论说,真正的结果其实只有在长时段中才能看得明白。因此多年以来我下笔论史,对于一时一事的前后嬗递便不肯轻易用“进步”一词,而往往以变迁为陈述的止境。在这一点上,罗志田教授以“权势转移”说权势变迁极能表达其见理之深。而就我个人所得的经验来说,与此同来的一个附带结果,便是身在一个欢喜过度推断的时代里,这种自以为谨慎的不肯轻言进步,在后生辈者看来,便常常成了潮流之外的不可归类者。

张洪彬:您的不少文章表现出明显的人文关怀,您也强调史学研究不能脱离“人”来展开。请您谈谈,“人”为何是历史研究的核心对象,不考察具体人事的史学研究是否可能?您怎么看待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切入史学研究?史学研究是否需要跨学科?
杨国强:按照我的理解,本义的历史不过是人和人的活动,因此,历史的主体只能是人。古人说“诗亡而《春秋》作”,由此开始的数千年中国史学便始终以人事为中心,而中国人历史叙述的脉延与中国文化的脉延遂因此而得以连为一体。不能想象没有这种连续不断的以人事为中心的历史叙述,而会有今日五千年连续不断的中国文化;也不能想象抽掉了以其一路演化串结了一个时代和另一个时代的文化与人物,中国历史还会成为可以理解的中国历史。所以,后人读史所直接面对的中国历史,便是这种以人事为中心和以文化为重心的历史。
以人事为中心,遂不能不涉及影响了历史的个人,且尤多涉及帝王将相。但其指归则大半都在因人而见事,着眼点和用心处皆集注于世运盛衰、国计民生、是非善恶、天下治乱。这个过程中芸芸众生虽然很少一个一个出场,但世运盛衰、国计民生、是非善恶、天下治乱的映照之所及,归根结底都落脚于一世之苍生的苦乐。有此归根结底,而后以人事为中心的历史遂能够成为真实的历史。因此,喜欢极端立论的梁启超曾以开新对守旧为立场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这是一种以彼邦的史学为比较以否定中国的旧史。而史学造诣更深的章太炎回应之曰:“还有人说,中国的历史,只是家谱一样,没有精彩;又说,只载了许多战争的事,道理很不够。这种话真是可笑极了。中国并没有鬼话的宗教,历史自然依帝王的朝代排次,不用教主生年排次,就是看成了家谱,总要胜那鬼谱。以前最好的历史,学术、文章、风俗、政治都可考见,又岂是家谱呢?后来历史渐渐差了,但所载总不止战争一项,毕竟说政治的得失,论人物的高下,占了大半”。他也在比较彼邦的史学,但立场则是守护中国的旧史。若以梁启超言之滔滔的论说里广为引证的人物和史事,多半仍以“二十四姓之家谱”为来路相比较,则章太炎的话显然更有道理。因此,今日治中国史,依然不能不以这种以人事为中心的记述为起点。
而以人事为中心的历史又以文化为重心,则直接对应的,正是数千年历史变迁里中国之为中国的恆定性所在和统一性所在。与过去相比,今日的史学各立标帜而各有流派,由此形成的纷呈多态有如满天烟花。其间的各自努力当然都意在拓展历史的广度和思想的深度,但其间的各是其是又很容易化为墙界,既使这一边的人看不到那一边关注的东西;也使那一边的人看不到这一边关注的东西。对于我们这些门外的人来说,便但见各种术语之前所未有地增多和各类题目之前所未有地增多,而少见这些同属中国历史的术语和题目,互相之间的沟通与勾连。近年评阅博士论文,可以引为实例而用之以作比较的,是由社会史而区域史的一路深入形成多量产出,其中好一点的论文皆能态度认真而用力甚勤。然而认真和甚勤,都意在挖掘和展示作者所选定的有限区域同其他地方相比而见的差异和独特。这个过程提供了许多翔实而细密的地方性知识,使我们能更具体地知道贵州的一个地方不同于云南的一个地方;山西的一个地方不同于河北的一个地方。但这种各不相同的地方性知识因彼此之间的无意贯通而成了实际上的无从贯通,则其一片纷披绚丽的代价,便常常会是中国之为中国的恆定性和统一性脱出视野,在历史叙述中变得无足轻重和非常稀薄。而后是缺失了后者的前者,已不能不成了实际上的碎片。与之成为对比的,是以思想文化为对象的论文多以概念和观念为主体,其中的良莠之分,毛病常在史事悬隔之下的好以今人之观念推演古人的思想,遂使观念和思想的背后都缺乏真实的历史,其天马行空便往往言之侃侃而不能切中肯綮。然而作为一种显然可见的事实,则是其间真肯用功读书的人,大半都能对中国的恆定性和统一性具有更多自觉意识,并因此而与地方的社会史形成了明显的不同。但这种随区域地方史和思想文化史的各分流派而来的差异,在司马迁以来的二千多年历史叙述中并没有成为一个问题。其实以中国的广土众民而散处于道途崎岖的阻隔之间,其地域不同、物候不同、产出不同、语言不同、民族不同、习俗风尚不同,本属自古已然。但二千多年的中国同时又是一个以统一为恆定的中国。从秦代的书同文,到汉代的循吏以劝农桑、行教化治理内地和边地;再到隋唐之后一千三百年间的科举选官和科举取士,中国历史的演化始终与中国文化的深耕远播一路相伴,并且浸润于这种文化的深耕远播之中。这个漫长的过程以世局的变迁造就了今时不同往昔,而文化则在深耕远播的厚积中成为深入于人心内里的东西;成为千变万化中稳固不移的东西;成为各不相同的地方和人群共有的东西和共奉的东西。因此,文化的恆定性和统一性为每一个中国人提供了恆定而统一的归依和归属,从而中国之能够长久地凝聚和长久地统一,本源和本质都在于长久绵延的中国文化。然则二千多年的中国史学以人事为中心写照各相殊异的世情和世相,以文化为重心传承恆久同一的人情与物理,其间留下的事实为今日的地方区域史和思想文化史都提供了可以立说的理据。但古人手里延续了二千多年的整体性,则因之而在今天被分成了两路。所以,就史事之研究只能截取以分段,而历史的认识不能不重归于整体而言,我们在仰慕新理论和新方法的同时,是不是也应当想一想古人还有比我们见事更深的地方。对于你所提的问题来说,这些话似乎绕得太远,但就我的个人体验而言,自己的人文意识,以及人在历史中居于主体的意识,正是在读史过程中由这种以人事为中心和文化为重心中所获得的。

言及“跨学科”研究,其实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何炳棣曾自述说,《明清社会史论》是他“所有著作里,运用社会科学理论较多,也最为谨慎,曾引起不少学者仿效。但此书问世若干年后,蓦然回首,我对于某些社科观点、方法与理论逐渐感到失望与怀疑”。主要是“由于其中不少著作不能满足历史学家所坚持的必要数量和种型的坚实史料,以致理论华而不实,容易趋于空诞”。所以此后二十余年,“‘仅’求诸己,致力于考证学的更上一层楼,欣然颇有所获”。这种出入于跨学科之间的经验所留下的反思,可以引为启迪的,一是要想跨学科,则必须先有自己的学科和足够的学科素养。否则跨来跨去最终不过是游骑无归而没有一个学科可以接纳。二是从自己所属的学科跨到另外一个学科,则必须对两个学科之间所能交汇的程度和限度有切入的真知。否则跨来跨去很容易以牛头对马嘴而越出常理常识之外。因此,前一面和后一面都需要拥有累积的学科高度和思维能力。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里,能够使人心悦诚服的跨学科而有真知灼见的著作实在不能算多。因此,以我这点知识程度,便从来不敢轻易尝试跨学科论史。这里说的是作为研究过程的跨学科。但人在获取知识的学习过程之中,若能于专业之外旁涉其他性之所近的学科,则以我的经验而论,常常会获益匪浅。所以跨学科之说不是一个可以大而化之地作一概而论的题目。
张洪彬: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第一讲就是“论史学非求结论之学问”,很有意思,可惜只存一个目录而无内容,因此颇费思量。就我的阅读体会来猜测,您可能比较赞同这种看法,所以想请您谈谈对傅斯年这种看法的理解和体会。
杨国强:史学既面对着作为历史事实的人物、事件和过程,也面对着这些人物、事件和过程留给当时和后来的意义。就其作为历史事实的一面来说,则可以实证便可以确定,可以确定便可以获得结论。但就其作为历史意义的一面来说,则意义因解释而见,便不能不随解释而变。解释的不容易确定,一方面在于真实的事实本身是由多面构成的事实,又是处在多种因果交汇之下的事实;另一方面在于后人之解释前人,其个体性、具体性和主观性,都决定了这个过程会常在视野的局限之中,知识的局限之中,观念的局限之中,阅历的局限之中,因此很容易见其一而不见其二。是以论史之际,很少有人真敢把自己的评说当成最后的定论。然而解释和评说面对的都是真实的历史,与之相对应的,便是见其一不见其二虽然不足以穷尽道理,却仍然抉示了一面的道理。而后是出自不同人物和不同时代的论说不断地继起,各以其一面之理映照事实,又以其相互纠错和相互补正趋近历史的本相。一百多年来,作为人物的曾国藩和李鸿章,作为事件的戊戌变法和义和团,作为过程的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都曾在一遍一遍的解释和评说中获得过不同的意义。而后人对于历史的认知,也因之而在层积累进中得以越来越深和越来越广。解释历史是为了理解历史,司马迁称之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所说的“一家之言”,既是对自己认识程度的限定,也是为别人留下余地。由此构成的过程显然不是具有终极性的结论所能够一次完成的,因此这个过程既不会以一时的结论为止境,便不会以一时的结论为目的。以此引申,则大半历史都会有思想史的性质,而史学之所以有永久的魅力和“读史”之可以“使人明智”也正存乎其间。我不知道傅斯年这句话的本意所指,只能以自己读史的体验作一点推想。

张洪彬:无论是讨论近代绅权的扩张,还是科举废除的后果和近代舆论的发展和变异,您的研究一直聚焦于读书人。请您谈谈,理解近代史,读书人为何是一种重要的渠道和窗口?我们知道,社会史、新文化史等史学流派批评这是精英的历史,只有少数人的历史,您如何看待和回应这些批评?
杨国强:关注近代的读书人,其实是关注斯世斯时的士人群体。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常相交缠,又尤以外力西来所造成的冲击之大和祸患之烈为前所未有。而最先代表我们这个民族起而回应西人冲击的,正是身当其时的士人群体。作为历史结果,晚清七十年中国的历史变迁便与林则徐、魏源、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等以事功和思想深度影响了国运和世运的人物连在了一起。遂使后人要认识和理解这一段历史,则不能不认识和理解这一群人。像我这样更多地关注百年世事催嬗蜕的人尤其如此。
以历史而论历史,因为士大夫最先起而回应西人的冲击,所以本以二千年历史经验为依傍的士大夫,也最先由中西交冲而切知西方人的世界在中国人的历史经验之外。随后的中西之争演化为古今之争,直接促成了借西法以图自强的三十年洋务运动。作为一种历史因果,则借西法以图自强的移接,既使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过程借助于移入的西法而获得了一个实际的开端,也使这种以移接为开端的近代化过程生于外铄,在后来的岁月里便非常容易地化生为变形的近代化和夹生的近代化。等到戊戌变年间维新潮流继起,则古今之争已急急乎变为新旧之争,同时是借法一跃而成变法。与前一段历史以中体西用为界限相比,后一段历史则重在除旧布新。除旧布新也在回应外来的冲击,但由此造成的剧烈变革和剧烈动荡一路相伴,遂使中国历史的近代化变迁与中国社会在结构上的解体同时发生于一个过程之中。两者的矛盾促成了旧朝的崩塌,而其间的历史因果又在延伸中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民国。这些都是七十年之间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的基本事实,而造就并主导了这些事实的主体,则全都出自士人。但作为一个改变了中国的群体,深度卷入了这个过程的士人,其自身又在这个过程的牵拽之下一变再变,由各自分化走到自相撕裂,并最终以其首倡的废置科举而自己消灭了自己。因此七十年晚清中国的历史,同时又成了二千多年以来的士人群体所留下的最后一段历史。我想,自己之所以更多地由这一段历史中的读书人观察这一段历史,原因和理由大概都在于此。
至于新史学流派,以及他们用批评的方式所表达的多数人的历史比少数人的历史更重要之说,在三十多年来熟见潮来潮去之下的学界众生相之后,我想说的仅仅是:第一,一种理论和方法能够成为流派,一定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和真实性。但名目各异的新史学流派一时俱起和同时并存的事实,又以其彼此之间的各立界域和显分异同,说明了每一种理论和方法的合理性和真实性都是有限度的,从而每一种理论和方法都没有办法以一己之说笼罩天下而独步一时。第二,不同方法和理论之间的相互比较,以及因比较而批评是常有的事,因此是无须太过深作思虑的事。我想,把史学当成对象的方法和理论,其出发点和归宿,应当都在于更富深度和广度地接近真实的历史和认识真实的历史。所以,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则一种方法和理论的价值之所以能够成立,并不是全靠方法对方法的批评和理论对理论的批评来证明的,而只能靠借用这种方法和理论所获得的研究结果,及其所能达到的研究程度来证明。否则史学之为史学,将变成只有理论方法而没有历史东西了。因此我更期待的,是能够看到用多数人的历史为神技,来重新诠释实际构成了近代中国剧烈变迁,而又与多数人相隔既深且远的思想、潮流、变法、革命以及学堂、报馆和天演之公理等等,以信而有征地说明少数人的历史之不足取和这一段历史的别成一种因果。第三,由于每一种理论和方法都具有合理性,也都具有局限性,因此,我对每一种理论和方法都抱有足够的敬意,但从不曾在一种特定的理论和方法脚下作盘旋。当各不相同的理论和方法都在显示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且前潮犹未退落,后浪已经滚滚而来的时候,则面对历史本身的横不见边际竖不见尽头,你只能相信最好的方法是史无常法或史无定法。无常法和无定法,有时候正是一种可能容纳会融各种流派之合理和卓识的方法。

《衰世与变法》封面
张洪彬:请问您如何选择培养博士研究生?怎样的潜质和天赋是您特别看重的?有哪些基本的能力和素养是一定要习得的?
杨国强:在常见有人三字经还没有读完,已自以为能够评论二十四史之后,我所希望于学生的尤在于:一、对史学有真正的志趣和敬意。有此志趣和敬意,则不太会习为浅薄轻佻,把自己看得比古人和时贤都要高明;二、已有的史学阅读积累。有此积累,则更容易识得天高地厚,不太会以臆想独断作凿空立论;三、不拘于特定流派的理论思维能力。有此思维能力始能于满地碎片中以史识串成整体。这个过程中形成的独得之见,是作为个体的学者区别于他人的地方,也是个体学者治史的价值之所在和贡献之所在。三者之外,若既有悟性,又有定力则更好。否则,往往是十个聪明人,九个不成材。但师生相遇是一种偶遇,因此选择之外,其实还有缘分。
张洪彬:最后想请您谈谈您的研究计划,近期有何研究和写作计划?
杨国强:目前关注和思考的,主要是废除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