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指与余秀华的争执是诗人争吵时代的余音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中国新诗自百年前诞生以来,就从没有停止过争吵。
正如诗人姜涛所言,“诗人们先是要和传统争吵,以确立自己合法的立足点,既而又要和庸俗的大众争吵,和陈腐的文化官僚和学院派争吵;无人可吵的时候,诗人们就自我分裂成敌对的集团。”
食指和余秀华之争虽然是诗人之间的争吵,只能算是这个脉络的遗绪。食指虽然是在诗歌层面喊话,对诗歌现状充满忧虑,但是他走不出时代的桎梏,对当代诗歌发展和现状缺乏理解和同情,因此再怎么疾呼也是无效的。在这个意义上,食指的发言,与其说是诗人对诗人的喊话,不如说是诗人之外的声音。而余秀华的回应几乎不在诗歌的层面上,只是委屈、愤怒下的牢骚发泄,也不必当真。
但是无聊的争吵折射的文化生态并不一定是无聊的。所以抛开事件本身,仍有多个维度值得思考。

从与大众吵到诗人自己吵
诗人们先是和传统争吵,这是新文化运动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诗坛的主旋律,不与传统切割,就无法自立。但是传统的力量是强大的,钱锺书在《围城》中借用董斜川之口说,“只有做旧诗的人敢说不看新诗,做新诗的人从不肯说不懂旧诗的”“新诗跟旧诗不能比”,是当时极具代表性的声音。时至今日,古典诗歌的典范和高度仍然是大众常常诘难新诗的工具。
但是大众对新诗的诘难并不止于此。大众是一个虚无缥缈的词,不同程度的阅读层次和审美水平,使得这种诘难也呈现出不同的向度。“读不懂”是批评中的最大公约数。
与“读不懂”的大众争吵,在新诗史上也是由来已久,但实际上争吵最激烈的时候恰恰是新诗与大众结合最为紧密的1980年代。等到1990年代以后,诗歌迎来了个人化写作浪潮,与大众的短暂亲密关系也就结束,诗人们发现问题已经不是“读不懂”了,而是没人读,争吵的对象失去了还有什么争吵的必要,何况这注定是没有胜算的战斗。
于是诗人们分裂出各种流派、群体,自己和自己吵。标志性的事件就是著名的盘峰论争,这个口语派和学院派的论争从1998年一直持续到2002年,以于坚、韩东、杨克、侯马、沈浩波等秉持“民间立场”的口语诗人对秉持“知识分子”写作立场的西川、欧阳江河、陈东东、程光炜等为代表的学院派诗人发起猛烈地反动。
盘峰论争涉及人物众多,各种命名混杂,细分的立场不一,既有诗艺的分歧,也有话语权的问题,在极大丰富汉语诗歌写作路数的同时,也开启了网络论坛时代诗人混战的滥觞。但是网络论坛时代的诗人们吵得热闹,骂得激烈,却鲜有盘峰论争那种对汉语新诗写作思考深度的论争,大部分只是山头和圈子之争。余秀华在成名之前,就是一位活跃在各个论坛,战斗力极强的论坛诗人。

从羊羔体到乌青体
网络论坛时代来得快去得也快。随着新媒体的发展,论坛、博客被微博、微信取代,诗人们失去了最后的战场。像食指和余秀华隔空喊话这种事,其实已经多年不曾出现。
和大众吵吵不赢,自己吵又谁都说不服不了谁,诗人们累了也明白了,诗歌的可能性只能寄托在孜孜不倦的语言探索中。但也有不甘寂寞者,“利用时代提供的机遇,借助‘事件’的力量,依靠夸张的先锋表演,在激怒大众的同时,也尝试去娱乐大众,兼及娱乐自身并获取资本。(姜涛语)
个别媒介也乐于迎合这种表演,甚至制造事件,引起大众的注意。从梨花体、羊羔体到打工诗人、乌青体,再到各种诗歌行为艺术,乃至余秀华,都是个别媒介和部分诗人希旨大众趣味而共谋的产物。
赵丽华的《一个人来到田纳西》并不是绝无从艺术层面讨论的可能;车延高也不止写女明星;乌青的《对白云的赞美》虽然不过是反崇高写作的遗意,但不能说不是诗;某些诗歌行为艺术可以看到对传统认知的挑战;余秀华的残疾和农妇身份与她的诗歌关系也没有那么天然。但是,在一个固定化的装置里这些都无法被看见,只有最刺激最爆炸的才能唤起人们对诗歌的注意。但是这种注意并不是那么返回到语言内部的诗人所希望看到的。这是新时期诗人们所面临的新挑战。
在不断加固的印象里,当代诗人的不堪、当代诗歌的无效是不言自明的。所以尽管余秀华因标签而走红,但她的诗歌被大众认为是期盼已久的“清流”是她能持续引起关注的主要原因之一。所谓的清流,用诗人评论家陈超的话来说,大概就是“又懂点又不懂”,是平均数水准或者稍稍高那么一点的诗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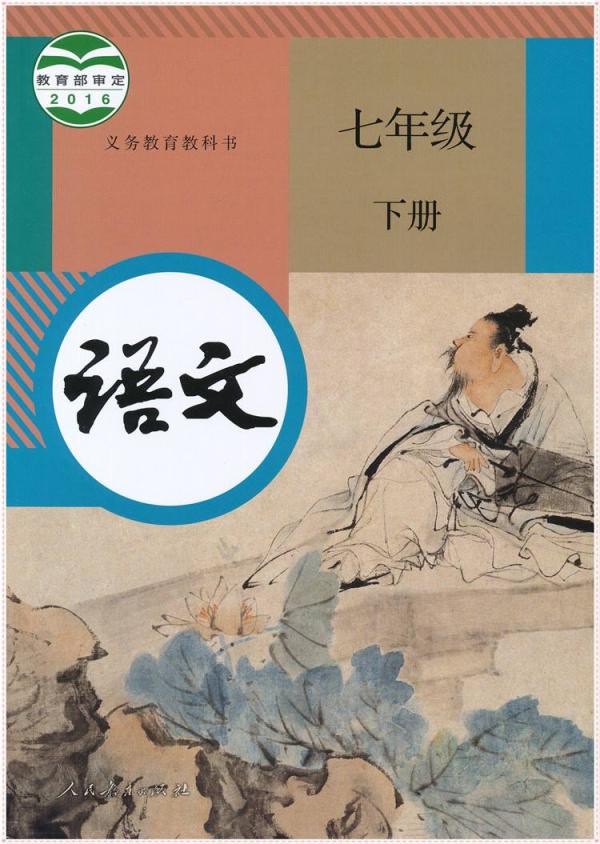
读不懂是诗人的责任吗?
我还是不死心想再谈点“读不懂”的问题。
当代诗歌越来越“读不懂”,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的。但是“读不懂”是诗人的责任吗?一部分是的。正如我在上一篇评论《食指与余秀华之争:两个时空的喊话》里说的,这是1990年代以来个人化写作的一个结果,别说有些诗一般读者读不懂,批评家读不懂,甚至就是诗人之间也读不懂,这是私人经验入诗带来的困境。
但是诗人应该为此负责吗?也不必。刨除那些故弄玄虚的作品,让更多人读懂并不是判断诗歌品质的核心要素,也不是诗人的使命。判断诗歌品质的要素很多,甚至莫衷一是,但大方向上是揭示生命体验和探索语言奥秘。值得信任的诗人,无不是在这个方向进行努力。
更何况当代诗歌的阅读难度也不是全由诗人带来的。
检索从小学到高中的语文课本,新诗少得可怜,和古典诗歌比例悬殊,而仅有的二十来首作品中大部分都是1980年代以前的。当然,新诗百年,积淀的经典作品和两千年的古典诗歌本来就不能对等。那国外部分呢?也是停留在十八、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以来大概只有弗罗斯特的《未选择的路》和狄金森的《篱笆那边》。
我说这个是想说明我们从小所受的现代诗阅读广度、审美训练相当少。诗歌是艺术,而理解一项艺术都是需要训练的。以古典诗歌为例,从《咏鹅》到杜甫,就是一个训练过程。没有人一上来就能读懂杜甫。
批评家的阅读深度和广度有了,对诗歌艺术的审美理解也有,为什么仍说“读不懂”呢?在于一首诗的背景和经验。如果不是对杜甫的经历和整体写作经验有深厚的认识,也很难进行文本批评吧,这就是为什么说做杜甫研究的不敢说懂苏轼的原因。所以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强调同代人做同代人批评,甚至是最好是与研究对象是熟人是朋友。
因此,对于读者来说,读不懂就不必读,或者去读那些读得懂的。毕竟,烂作品哪个艺术门类里都有,哪个时代都有,还是一大堆。但是决定一个时代文学或艺术高度的并不在于烂作品的多寡,而是好作品的多寡和高度。
而对于真正有抱负的诗人来说,也不必纠结于读不懂的评价,或是诗歌事件对诗歌形象的伤害,既然选择了以诗歌为志业,就必然是选择了一个人冒雨赶路,选择了与历史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