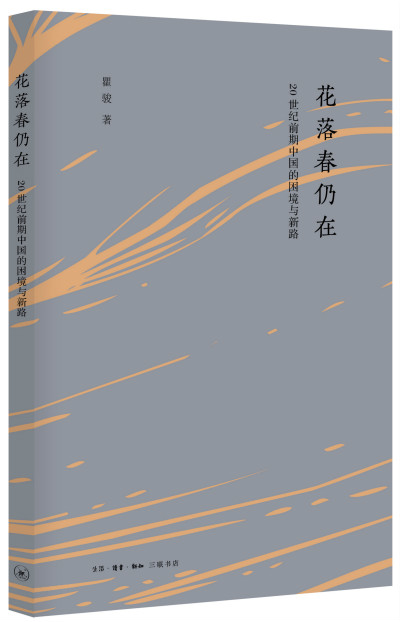瞿骏:现代中国是“旧有”与“新来”的共存
淡淡烟尽活,疏密雨俱香。
鹤避何嫌缓?鸠呼未觉忙。
峰鬟添隐约,水面总文章。
玉气浮时暖,珠痕滴处凉。
白描烦画手,红瘦助吟肠。
深护蔷薇架,斜侵薜荔墙。
此中涵帝泽,岂仅赋山庄。
据说此诗曾得到曾国藩激赏,此试自然也成了俞樾最刻骨铭心之科场一役,他凭此成了“殿元”,遂命名自家书斋为“春在堂”。而此句在今天看来正成为一个巨大的隐喻,提示我们如何来看现代中国的历史。

现代中国的历史以“变”著称,但如何“察变”却是个到今日仍颇费人思量的问题。在既有的历史叙述中我们多看到的是变化后了的模样(当然是否真是这等模样也依然可以存疑),而不太清楚变化的过程,更模糊的是变化之前的模样。马克思曾说:“人类创造着自己的历史, 但是他们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 他们自己不能选择创造的条件, 而是只能在直接面对的、已成事实的、从过去传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而我们恰恰对这些“直接面对的、已成事实的、从过去传承下来”的条件重视不够,以致常常只看到了落花飘零于泥尘的“近代中国屈辱史”,而看不到“春天”究竟是在还是不在。
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既有“春天”在与不在变得无关紧要(同时事实上依然还在),国人特别是读书人的心目中径自发展出了各自想象的“春天”与自以为的“春天”,并为了他们的想象和自以为而努力、奋斗,直到互博与厮杀。
于是,落花、新枝、仍在发展的却不被人重视的既有“春天”和想象与自以为的未来“春天”就这样在现代中国交织孱杂在了一起,这种因交织孱杂而互渗联动的状态既引发了现代中国历史的困境,也开拓了现代中国历史的新路。
从困境这一面来说,“落花飘零”即现代中国的“黑暗沉沦”确乎是每个中国人所经历的生存状态,但对于此种基本生存状态的回应方式,各人却有所不同,遂有中体西用、全盘西化、革命、改良、接续、调和等多种方案和主义。1935年陶希圣曾把中国之思想界分为三大阵营:“封建社会的回想的阵营,资本主义的模仿的壁垒和社会主义悬想的阵线”。陶氏的说法与前些年流行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的三分法有一些相似,但所见更深,且其立场不在任何一方,因此也就不能引起各家“教主”的注意。在这些阵营、壁垒和阵线之中有坚持中国既有“春天”仍在且相当重要的,亦有笃信“落花飘零”之后必定会有另一个不同“春天”的,所以看上去针锋相对,彼此对立,但其实它们大多都共享着同一个预设即张灏所说的“前瞻意识”。这种“前瞻意识”让人对现实有强烈的沉沦感和疏离感,同时对缥缈的未来有无与伦比的热切盼望。我将其称为“一种近于无可救药的未来乐观主义”。

而之所以为“共享”,是因为不仅我们常称之为“激进”的那些主义有这种“前瞻意识”。那些曾几何时遭无数人激赏追捧的改良主义等也一样有这样的意识。这从廖平、康有为、梁启超的著述中可以看得特别明白,其“革命”的目标之远、范围之广和着力之深常令人感叹和咂舌,让人不禁要问,真的有改良派吗?究竟谁是革命派?
现代中国的三重连续性困境困窘由此产生:第一,“新社会总是从旧社会脱胎而出的”,因此现代中国在如何“变”,总有事实上仍在的“春天”,同时又有读书人想象中的和自以为的未来“春天”,这常使时人产生一个基本的困惑即如果自己“既不赞成复古,又不愿意完全把西洋的整个搬过来”该怎么办?
第二,正因为有此困惑,从中体西用开始,到调和新旧与接续中西,再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之说,它们虽有各自立说的理据,但体现的都是一种以“新旧杂存”的方式来通向光明未来的尝试。张东荪对这种“新旧杂存”的思路做过有力的挑战,其挑战的意义并不仅止于指出所谓“新旧杂存”很多时候不过是新旧“共存”,更重要的是点明了无论是“杂存”还是“共存”大概都是长期性的,“新的增加一分,旧的便汰去一分”。这种对“时间”力量的期待会让“前瞻意识”强烈的国人急迫而躁切。他们一方面觉得这样的期待是一种惰性,是“人类本能上一种恶德,是人类文明进化上一种障碍”,另一方面则无奈地发现现实就是“新的不可以一天长大,旧的不可以立刻消灭”,走向光明未来的路漫漫又长远。
第三,光明未来的遥远而不可得,让现代转型中的部分读书人一边经历着“落花飘零”的苦痛现实,一边愈发觉得我们无法依靠“时间”的力量来再获春天。郭沫若就警醒众人说“不要以为春天去了,永远会要再来”!因此他们从盼望新的春天转换成了要主动创造新的春天,要一换而过的是种子,是土壤,甚至是气候。在这样的氛围里,人们对那些正在养花以收获春天之人的努力,常抱以有意忽视或无意忽略的态度,进而常常期盼调换一批更善于养花,乃至能呼风唤雨,创造春天之人。但历史常常是不如意的,调换了未必更好(但也不一定更坏)。可是这样一来,现代中国的历史叙述却演化成为一个循环路径:在北洋追慕晚清,在国民党统治下怀念北洋,时至今日则有晚清风度、北洋精神和民国范儿等林林总总的“旧日重现”,其实质都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借助谈历史而对现实形成一种批判。但这些批判常常忽视了一个基本逻辑:若对旧日的怀念成为了循环和常态,那么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
从新路这一面来说,尽管近代中国有如此多的“困境”,但一个主权完整,疆域范围基本保持,人口、民族依然众多,文化有“一线之续”且有进一步复苏迹象的中国仍在那里,这对一个经历过“民族帝国主义”时代的古老国家来说实在是一个奇迹。
从这个“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奇迹里显示出我们一定有新路可走。这条路不是简单的“脱亚入欧”或者是成为被东西洋列强标准所规定的“民族国家”,因为历史和现实已经说明“脱亚入欧”或是成为“民族国家”的短暂成功与长期虚妄,而且在追寻这虚妄的过程中,对自身和对它国都有无穷的流弊。中国的新路某种意义上正蕴藏在她的困境之中,即杨国强教授说的“中国人不能不背负着旧有的历史以因应新来的震荡”。
这句话洞穿了百多年的中国近代历史!“不能不”表明“旧有”与“新来”的共存很多时候不是能够人为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从世界上一切可能的事物中精心搜集起的一堆‘好的方面’,稍一碰撞就会化为灰烬”!这种共存是我们脱不开的“既存状态”,其有弊亦有利,有危亦有机。对历史长河来说,百年不过一瞬!仍在的“春天”一方面或许是造成我们无穷困惑的部分原因,另一方面却也是我们获得生机的源泉。中国“旧有的历史”在今日决不只是我们要卸之而后快的包袱。相反的,它能为我们已经贫乏至极的政治、社会想象提供鲜活的养分。康有为、钱穆、章太炎、陈嘉异、闻一多、陈寅恪等近代思想大家的论述尤能说明这一点。他们的价值既在今朝,更在未来。
1907年鲁迅曾说:“往者为本体自发之偏枯,今则获以交通传来之新疫,二患交伐,而中国之沉沦遂以益速矣。”放在清末的历史环境看,此说无疑比那些东京、上海之“仁人志士”跳踉轻发的高蹈言论深刻得多。但110年过去,中国似并未“沉沦”到底。在此前提下,我国本体自发究竟为何?中西交通传来的是否仅是“新疫”?特别是二者究竟如何“交伐”,“交伐”产出何物等都仍是一个个“进行中的问题”,值得治史者用心去追寻与讨论。这里我们不妨再读一读1919年时周作人写下的一段话:“为邻国人民的利益计,为本国人民的利益计,我都希望——而且相信日本的信任能够向和平正当的路走去。第三个师傅当能引导人类建造‘第三国土’——地上的天国,——实现人间的生活。”
这个寻找“和平正当”的路的过程是一场长程竞赛,且经常不以成败来论英雄!
(本文摘自《花落春仍在:近代中国的困窘和新路》自序,瞿骏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12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