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焄︱“不可卒读”的章太炎演讲记录稿

应江苏省教育会的邀请,章太炎于1922年4月1日至6月17日期间,在上海举行了十次公开演讲,并由《民国日报》派去的年轻记者曹聚仁记录整理。记录稿最初在《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上连载,修订结集后以“国学概论”的名义由泰东图书局于当年11月正式出版。尽管面对的听众并非专业人士,使得章太炎在演讲时只能点到即止,其博洽精深的程度远不及《国故论衡》《菿汉微言》等同样源自日常讲学的著作,然而却成为他毕生著述中流传最为广泛的一种。正如曹聚仁后来所说的那样,在近现代问世的大量国学入门读物中,“全国大中学采用最多的,还是章太炎师讲演,我所笔录的那部《国学概论》,上海泰东版,重庆文化服务版,香港创恳版,先后发行了三十二版,日本也有过两种译本”(《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第一部分《从一件小事谈起》,三联书店1986年)。迄至今日,各地仍有出版社在不断翻印,足见此书盛行不衰。

最先披露此次系列演讲具体内容的,除了曹聚仁的记录本,其实还另有其他记者笔录的《新闻报》本和《申报》本。《新闻报》有始无终,只报道了前五讲便戛然而止,可以暂置勿论。《申报》馆虽然从一开始就接受江苏省教育会的委托,负责宣传推广,并自诩道:“所讲述者,另有纪录员纪录,以便整理,送由章氏核阅,以便发布云。”(《章太炎讲学第一日纪》,载1922年4月2日《申报》)原本应该最具权威性和可信度,不过据其后续报道,在第一次正式开讲前,“报名者竟有六百余人之多,临时到会者又有一二百人”(《愿听章太炎先生讲学者注意》,载1922年4月4日《申报》);慕名前来的听众随后“争先前往索取听讲券,至昨日下午,已满足一千人,可谓盛矣”(《章太炎今日继续讲学》,载1922年4月8日《申报》);可是能够持之以恒听完全部演讲的并不多,最后数次竟然人数锐减,“到者不下七八十人”(《章太炎九次讲学纪》,载1922年6月11日《申报》)。章太炎亲眼目睹前后如此悬殊的景象,恐怕也免不了意兴阑珊,未必会仔细核查订正报社的记录稿。因此《申报》上每次刊登的演讲内容繁简不一,有时洋洋洒洒数千言,有时则寥寥数十语,显得敷衍潦草,彼此并不相称,当然也不便汇集成书。曹聚仁后来追忆说,《新闻报》和《申报》派去的记者根本听不懂演讲内容,“他们所笔录的大错特错,错的太可笑了。结果,几乎只能让我这个对考证学有兴趣的人,一直写下去。这便是我的《国学概论》记录本的来由”(《我与我的世界》四一《国学与国学概论》,三育图书公司1972年)。尽管略带几分同行相轻甚至自我标榜的意味,但这两家报社派去记录的人员未能恪尽职守,确实是不争的事实。

曹聚仁:《五版自序》
《国学概论》付梓仅半年,就连续印行了五版。曹聚仁对此相当得意,在《五版自序》(载曹聚仁编《国学概论》,泰东图书局1923年5月第五版)中故意调侃道:“我曾期待江苏省教育会底文言本出版,或者会使我明白自己有什么缺点而使我得以修正;但是这期待到现在还只是期待。”到晚年撰写回忆录时,他更是直言不讳:“省教育会所请的两位记录,虽是老年人,他们也不懂,所以记不下去。”(《我与我的世界》四一《国学与国学概论》)。然而就在1923年4月,一部题为“张冥飞、严柏梁笔录加注”的《章太炎国学讲演集》由中华国学研究会印行,内容正是此次系列演讲的文言记录稿。该书的版权页除了明确交代笔述者为长沙张冥飞、加注者为湖州严柏梁外,还列有嘉善鲍定一、青浦鲁承庄、德清虞悟旭等一众校阅者。其中仅身为南社成员的张冥飞略微知名,“一度任南方大学教授,为文主切实用,不主张浮夸虚饰及诡怪瑰奇以炫世俗”(郑逸梅《南社丛谈》九《南社社友事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其余诸人的生平行事则难以详考,但籍贯都属江浙一带,而江苏省教育会的成员主要就来自江浙地区的政、学、商各界。据此推测,此书应该就是曹聚仁所期待的由江苏省教育会主持整理的文言记录稿。

尽管《章太炎国学讲演集》的出版比《国学概论》迟了半年,可依然很受读者欢迎,平民印务局(1924年)、梁溪图书馆(1926)、新文化书社(1935年)、文海出版社(1973)等都先后多次翻印过此书。究其原委,其实也不难推知。虽然章太炎在演讲时已经力求浅近,可内容遍及经学、哲学和文学等多个门类,对绝大多数听众而言仍显得艰深费解。张、严两位对演讲内容详加注释和评议,全书虽以浅近文言撰就,但较诸曹聚仁仅录讲辞而毫无评注的白话本,似乎更容易满足普通读者的需求。但据章门弟子沈延国所述,章太炎晚年曾提到:“昔在江苏教育会演讲,曹聚仁所记录(即泰东书局出版的《国学概论》),错误较少;而另一本用文言文记录的,则不可卒读。”(《章太炎先生在苏州》,载《苏州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二辑,政协江苏省苏州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4年)尽管并未明言,可矛头所指显而易见正是张、严两位的评注本。章氏嫡孙章念驰在搜集其演讲稿时曾大费踌躇,因为“大多演讲是别人记录的,有的演说没有经他认定,记录者水平又有高下,文章的质量会受影响”(《章太炎全集·演讲集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有关这次在上海的系列演讲,他经过一番筛选别择,最终采纳了曹聚仁的整理本,并改题为《国学十讲》(收入《章太炎全集·演讲集》,按:章念驰谓此次演讲时间为4月1日至6月7日,又称《国学概论》出版于1929年,并误),而舍弃了张冥飞、严柏梁的评注本,毫无疑问和章氏本人的意见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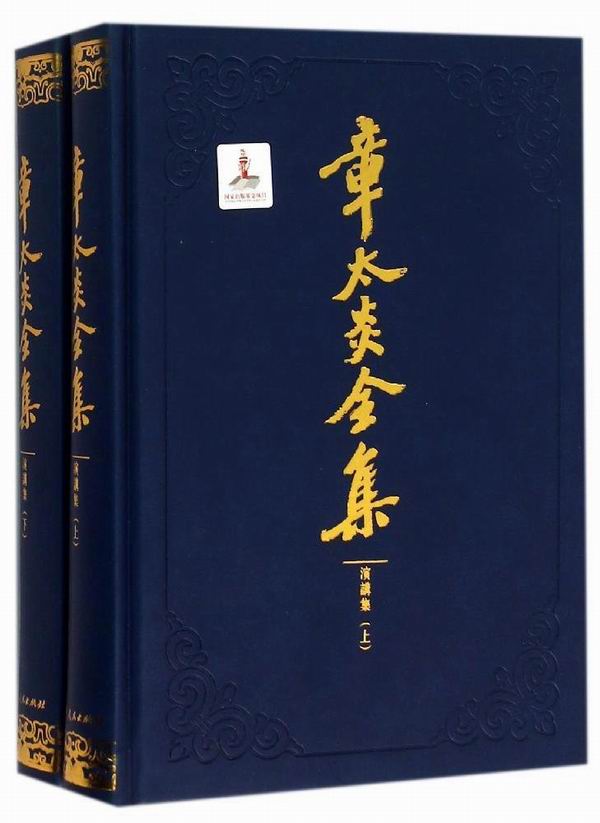
不过评注本究竟如何“不可卒读”,还是令人颇感好奇的。与曹聚仁的整理本相较,两者最大的差异即在于语体上的文白之别,而从中似乎又能折射出邀请方和演讲者之间的微妙分歧。在1922年3月29日《申报》上刊登的新闻《省教育会请章太炎先生讲国学》中,合盘道出了主办者筹划此次演讲的初衷,乃是痛感“自欧风东渐,兢尚西学,研究国学者日稀”的现状,认为“西方之新学说或已早见于我国古籍”,因此“同人深惧国学之衰微,又念国学之根柢最深者,无如章太炎先生。爰特敦请先生莅会,主讲国学”,显然是想倚重章太炎的威望,达到鼓吹旧学而贬抑新学的目的。这番宣传在学界迅速激起了很大的反响,章氏早年的弟子周作人在尚未知悉具体情况之下,于4月10日撰写《思想界的倾向》(载1922年4月23日《晨报副镌》,后收入《谈虎集》,北新书局1928年),一开篇就忧心忡忡地指出:“我看现在思想界的情形,推测将来的趋势,不禁使我深抱杞忧,因为据我看来,这是一个国粹主义勃兴的局面,他的必然的两种倾向是复古与排外。”随即深为惋叹地提到:“听说上海已经有这样的言论,说太炎先生讲演国学了,可见白话新文学都是毫无价值的东西了;由此可以知道我的杞忧不是完全无根的。”在最先刊布的演讲内容中,除了《民国日报》之外,《新闻报》和《申报》上的连载都使用文言,或许正是由此造成了周作人的误会,以为章氏在演讲中反对“白话新文学”。其实章太炎虽然对方兴未艾的白话新诗颇持异议,却并未一概否定白话的价值。根据曹聚仁的记录,他在演讲时还专门提到:“白话记述,古时素来有的,《尚书》的诏诰全是当时的白话,汉代的手诏,差不多亦是当时的白话,经史所载更多照实写出的。”(《国学概论》第一章《概论》)有意思的是,在张冥飞、严柏梁的文言评注本中,这段议论却荡然无存,表明记录者并不认可这番对白话的褒扬。曹聚仁后来撰有《文白论战史话》(收入《笔端》,天马书店1935年),其中有一节“上海的复古倾向”,顺带提到过此事,也可资参证:“民国十一年,江苏省教育会请章太炎先生演讲国学,本是沈信卿他们有计划的复古运动;太炎先生个性很强,他的讲演并不利于复古,社会的反应也很轻微,那回复古,可说是完全失败的。”更直截了当地指出章太炎演讲的旨趣不尽符合主办方的要求。评注本故意隐没这段针对白话的讲辞,无疑是事出有因的。

文言与白话虽然是语体的差异,可往往也关乎文章的丰神意韵。曹聚仁称道章氏“论学论事,如说家常,时常插入风趣的谈话,浅易处常有至理”(《章太炎先生》,收入《文思》,北新书局1937年)。如此驾轻就熟、收放自如的风采,在白话版《国学概论》中就很能彰显,到了文言版《章太炎国学讲演集》中就大为逊色了。比如前者记录了这样一段讲辞:“凡称之为诗,都要有韵,有韵方能传达情感。现在白话诗不用韵,即使也有美感,只应归入散文,不必算诗。日本和尚娶妻食肉,我曾说他们可称居士等等,何必称做和尚呢?诗何以要有韵呢?这是自然的趋势。诗歌本来脱口而出,自有天然的风韵,这种韵,可达那神妙的意思。你看,动物中不能言语,他们专以幽美的声调传达彼等的感情,可见诗是必要有韵的。‘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这几句话,是大家知道的。我们仔细讲起来,也证明诗是必要韵的。我们更看现今戏子所唱的二黄西皮,文理上很不通,但彼等也因有韵的原故。”(《国学概论》第一章《概论》)先用日本和尚能够娶妻食肉来嘲讽白话诗的名实不副,又以鸟兽啼鸣和优伶唱戏来佐证诗歌必须用韵。后者则将这段演讲记录如下:“《尚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云云,可见诗必有韵,方能传达情绪,若无韵亦能传达情绪,则亦不必称之为诗。譬如日本和尚吃肉娶妻,可称之为居士,不必称之为和尚。今之好为无韵新诗者,亦是吃肉娶妻之和尚类也。”(《章太炎国学讲演集·第三日讲学记》)且不论未能保留“你看”“我们更看”等容易营造出现场感的口语词,因而失去了口吻毕肖的效果,单以内容而言,也只剩下日本和尚一例,而将其他两例略去不提。章太炎早年流亡日本,“就想披起袈裟做个和尚,不与那学界政界的人再通问讯”(《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收入《章太炎全集·演讲集》),对日本和尚的情况自然不会陌生,演讲时信手拈来,必定能使气氛显得更为轻松活泼。而用来强调诗歌必须有韵的另两例,论证的逻辑并不严密,甚至显得有些枝蔓芜杂。即便是曹聚仁本人,后来在《章太炎先生》一文中转录当年的记录稿,也只节引至日本和尚即止。不过如此毫不经心、自由散漫的闲谈,却颇具传神写照的功效,别有任意挥洒的意趣可供读者仔细玩味。

章太炎在演讲中时常会兴之所至地大跑野马,在概述汉代以来今文、古文两大经学派别的发展演变后,就兴致勃勃地插叙了一段往事:“自孙诒让以后,经典大衰。像他这样大有成就的古文学家,因为没有卓异的今文学家和他对抗,竟因此经典一落千丈,这是可叹的。我们更可知学术的进步,是靠着争辩,双方反对愈激烈,收效方愈增大。我在日本主《民报》笔政,梁启超主《新民丛报》笔政,双方为国体问题辩论得很激烈,很有色彩,后来《新民丛报》停版,我们也就搁笔,这是事同一例的。”(《国学概论》第二章《国学的派别(一)——经学的派别》)《章太炎国学讲演集》也没有记录这段内容,或许认为此类有关私人恩怨的轶事琐谈无关宏旨吧。不过中规中矩地围绕设定的主题来确定记录的内容,所呈现的章太炎的形象终究显得过于拘谨严肃,失去了嬉笑怒骂、庄谐并出的本来面目。当然,现场的听众对此大概也并不感兴趣,恰如曹聚仁所感叹的那样,“这五六十个听众中,并没有皮锡瑞、康有为其人,老实说大家并不关心今古文家的争辩,甚至连什么叫做今古文家都不明白”(《关于章太炎先生的回忆》,收入《文思》)。可幸亏有他这些细心的记录,后人才能藉此遥想章氏究竟是怎样“如唐·吉诃德一样向羊群舞矛”(同上),体会到他当时落寞孤寂的心境。

张冥飞、严柏梁的评注虽然旨在为读者扫除阅读障碍,可有时却与章太炎持论相左。例如他们记录章氏解释“经书”时说:“‘经’字原意,乃是‘一经一纬’之‘经’,即线是也。所谓‘经书’,无非是一种线装书之谓。……古代记事书于简,不及百名者书于方。事多一简不能尽,遂连数简而记之,连各简之线,即‘经’是矣。盖‘经’之为书,特当代记述较详而时常备阅者。不但不含有宗教意味,即汉时训‘经’为‘常道’,亦非本意。”在评注中先概述历代载籍形制的递嬗迁变,最后强调说:“用线装订成书,始于宋季锓版印书之后,古书编之可考者如此。今谓‘经’为线装书之意,似仍不如训‘经’为‘常道’之说为长。”(《章太炎国学讲演集·第一日讲学记》)平情而论,评注的意见更近于事实。可章太炎如此诠释并非信口乱道,而是他一以贯之的主张。晚年在章氏国学讲习会授课时,他仍然坚持:“经之训常,乃后起之意。……今人书册用纸,贯之以线,古代无纸,以青丝绳贯竹简为之。用绳贯穿,故谓之经。经者,今所谓线装书矣。”(王乘六、诸祖耿记录《经学略说(上)》,载《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之所以有这样的界说,其实也别有用意。章太炎虽然大力提倡读经,甚至认为“于今读经,有千利无一弊也”,可并不像康有为等今文学家那样奉经书为圣典,甚至大肆鼓吹尊孔复古,而是要将读经落实在“修己治人”之上(王謇、吴契宁、王乘六、诸祖耿记录《论读经有利而无弊》,载《章太炎全集·演讲集》),因此自然要以平实切近之语来开示引导后学。评注者未能仔细体察章氏用心所在,当然不能令他满意。
兴许是出于个人的喜好,评注者有时还会有意歪曲讲辞的原意,势必会引发章太炎更多的不悦。例如章氏主张撰作文章者必须通晓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在评注本中有这样一段记录:“清桐城派略通小学,所引古书,知者则用,不知者仍不敢用,故尚无贻笑处。”随后有评注云:“清古文家,有桐城派之目,始自方望溪(苞),盛于姚惜抱(鼐),至曾涤生(国藩)极推崇之而名愈震。其作文也,格律谨严,非经史中雅驯之字不敢用,故为斥弛之士所不喜,然理法井井,终不可没。”(《章太炎国学讲演集·第二日讲学记》)乍读之下,似乎会以为章氏对桐城派颇为许可,实则大谬不然。章太炎对桐城派并无好感,甚至直斥道:“桐城诸家,本未得程朱要领,徒援引肤末,大言自壮。”(《訄书重订本·清儒第十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反观曹聚仁当时的记录——“桐城派也懂得小学,但比较的少用工夫,所以他们对于古书中不能明白的字,便不引用,这是消极的免除笑柄的办法,事实上总行不去的”(《国学概论》第一章《概论》)——显然更能代表章氏的真实想法。

当然,评注本虽因种种原因而导致“不可卒读”,但也并非一无是处。就体例而言,正式付梓的《国学概论》已经依照章节体重新整合,将演讲内容分为五章。尽管结构上更为整饬明晰,可演讲的具体进程却无从追索。而《章太炎国学讲演集》则依照“第一日讲学记”至“第十日讲学记”的顺序逐日编排,虽然不免有割裂之弊,比如在讲到“治国学之法”时,所列“辨书籍真伪”“通小学”和“明地理”“知古今人情变迁”“辨文学应用”等五项内容居然分属第二、第三两次演讲,不过倒是可以由此了解演讲时的进度安排,并进而考察章太炎的兴趣所在。就内容而言,《章太炎国学讲演集》虽多错谬疏漏,可普通读者其实还是需要借助注释才能读懂原文。曹聚仁就提到日译本《国学概论》附有注解,以致他“原想翻检《章氏丛书》,也作一回笺注工作;可是动起手来,非三五年不能完成”(《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第十一部分《述学》),最终只能放弃。《国学概论》虽然附录了邵力子、裘可桴、曹聚仁的数篇文章,针对演讲内容提出商讨,但涉及的问题毕竟有限。倘有学者参酌评注本再做一番删汰繁芜、补苴隙漏的工作,甚至将这些不同的记录稿相互比勘以见其异同取舍,必定能裨益后学,甚至嘉惠学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