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阳︱你以为的进步,其实是失足:评《极简进步史》
1890年代,高更离开了巴黎、离开了家庭和股票交易员的职业,来到了南太平洋的小岛上。在这里,他与原始人同居,并创作出了一幅充满神秘韵味和人物的长卷——“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去往何方?”
罗纳德·莱特的《极简进步史》始于对高更这幅名画的凝视。这本书,是作者对高更问题的回答。在莱特眼中,我们的文明,是一艘满载着过去文明内涵,高速驶向未来的蒸汽船。但是,由于这艘船已经走得太快太远,“世界已经变得太小,以至于不能承受我们任何的大错误了”。

这些错误,在莱特看来,来自于我们关于“进步”的理念。按照历史学家西德尼·波拉德的说法,维多利亚时期形成的进步理念,是“一种认为在人类历史上存在一个变化规律的想法……这规律包括了单向的、不可逆转的变化,这单向则是指向进步”。
这种单向度的进步观念,认为“哺乳动物比爬行动物更敏捷;猿类比牛更加聪明细心;而人,则是所有生物中最聪明的物种。我们的文化是用技术的发展来衡量人类进步的:棍棒比拳头厉害,弓箭更胜于棍棒,子弹又胜过了弓箭”。
“进步”观念假定人类文化永远在变得更高级、更复杂、更大,更快,更新;只要科技和物质在发展,进步永无止境;反之,就是退步。
然而,莱特认为,这种观念在历史上是站不住脚的。他以火药为例:自从中国人发明了火药,从炮仗发展到火炮,再到自动武器,再到原子弹。虽然技术一直在进步,但是这种进步,并不总朝着人们希望的方向发展,相反,可能会带来人类的毁灭。 “当我们能够制造的爆炸可以摧毁我们的世界时,我们的进步就过了头儿。”参与制造原子弹的爱因斯坦承认:由于这种“进步”,“我们因此滑向了前所未见的灾难。” 正如美国总统肯尼迪感叹:“如果人类不终结战争,战争就会终结人类。”。对技术“进步”的追求,可能将人类带入死胡同。
——这就是莱特所说的“进步的陷阱”。
对技术和物质发展的无休止欲望,会让人类过度掠夺自然的资源,破坏赖以生存的环境,进而摧毁自身进步的能力,走向毁灭。
史前人类的教训
莱特指出:进步的陷阱,存在于人类发展的各个阶段。在史前时期,由于狩猎技术的进步,人们可以多打一两只猛犸象,这可以算是一种进步;但是,当贪婪让他们用同样的技术多打了两百只猛犸象,人类就要因此挨饿了。最近关于史前的考古表明,一次驱赶上千只动物让它们在悬崖下摔死,并不是史前人类偶尔为之的事情。
人类在漫长的史前时代,就开始滥用所掌握的工具等“高科技“,灭绝了无数物种,改变了数个大陆的自然环境。最近的研究发现,美洲和澳洲的草原是早期人类人为地焚烧森林所造成的后果。我们甚至灭绝了人类的近亲——尼安德特人和其他许多早期直立人种。在文明产生之前,人类“进步”的欲望早已开始破坏生态,毁灭物种。
而农业的产生,也是一个进步的陷阱。农业虽然提高了食物的产量,却改变了原先人类复杂均衡的饮食结构。人类被迫以一两种谷物为主食,从而牺牲了健康。后果虽然是人口的急速增长,却在数量之下,失去了质量。结果,人不仅变得极端依赖驯化的那几种谷物,而且必须忍受营养不良和贫困。
当财富被制造出来之后,并不会自动平均分配,而是会出现金字塔形的财富分配结构。复杂社会的发展规律,是财富的增加和分配的不均总在同时出现,造成社会向金字塔形结构发展。这往往要通过战争、饥荒、革命等社会剧烈变动,才能改变。
同时,技术的进步、人口的增加、要求社会取得更多的资源,特别是土地资源。从欧洲史前克罗马农人与尼安德特人对生存环境的竞争,到二战时期希特勒的“生存空间”理论,人类文化中的阴暗面并没有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改变。技术的进步,丝毫并没有促进道德的改善。对待同类和环境,人类依然像过去那样贪婪、残忍、不负责任。
对土地资源的贪婪,是莱特所说的“进步的陷阱”的典型特征。对自己领地的自私和占有欲,催生了后来被称作“爱国主义”的情感。在书中,莱特精辟地写到:“爱国主义是一个无赖最后的避难所,也是独裁者的第一个收容所。”爱国主义让独裁者轻易地操纵了那些担心外来者的人。排外的爱国主义,也许并不像想象中那样光荣灿烂,反而可能充满人性中最阴暗的自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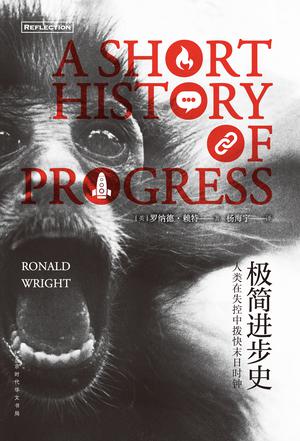
四个衰落的古代文明
书中最有趣的部分,是四个失败文明的例子。这些文明,都是由于陷入了“进步的陷阱”而导致衰败或毁灭的。
第一个例子,是南太平洋充满巨大石像的复活节岛。在莱特看来,这是一种文化因为“进步的陷阱“而失败的实验。针对岛上火山湖的花粉研究显示,复活节岛曾经有很丰富的水资源,植被也很葱郁,富饶的火山灰支持了茂密的智利酒椰子树林的生长,岛上也没有任何自然灾害:没有旱灾,疾病、和火山爆发。
复活节岛的灾难完全是人为的。
在大约公元五世纪,一些波利尼西亚的移民坐船来到复活节岛。他们带来了家畜和作物,在这片富饶的岛上定居。他们在此建立了村落,形成了氏族。日子过好之后,开始用来自火山湖的凝灰质石料建造巨大的石像,象征他们的祖先。随着时间的推移,石像崇拜变得越发具有竞争性,也越来越奢侈,每一代人制造的石像都要比上一代人的更大,需要消耗更多木材和绳索,需要更多的人力来把石像抬到神坛上。树木被砍的速度快过了成长的速度,这个问题又因居民带来的老鼠而变得糟糕。
公元1400 年,火山湖里的化石积层再也找不到花粉的踪迹,这意味着岛上的森林,已经被人类完全摧毁了。莱特写到:这时,人们应该已经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去制止砍伐,保护小树苗,重新种植树木。并遏制石像的建造,把宝贵的木材留作建造船只和房屋,而不是用来修造和运输石像。但是人们还是把最后一棵树给砍倒了。
终于,再也没有木头做可以远航的船只,建造屋顶,人们只能搬去山洞居住。为了争夺古代遗留下来的厚重木板,和腐烂的海上漂浮物,爆发了战争。这时,小岛几乎已经成为不毛之地。可是人们依然没有停止建造更大的石像,却再也无力将它们运到神坛上去。于是,岛上出现了高达六十五英尺,重达两百多吨的石像,造好后,只能躺在原地。
小岛的自然环境完全被破坏,人们却不愿放弃高资源消耗的生活方式,直到完全落入“病态的意识形态”的陷阱——小岛为燃烧的村庄、血腥的战争、还有人吃人的残酷而颤抖过。当欧洲人在十八世纪来到复活节岛的时候,岛上没有一棵树,没有一栋木屋。可怜的幸存者依偎在石像旁边,“矮小、瘦弱、胆小并且很悲惨。”
第二个例子,来自于今天伊拉克南部的古代苏美尔文明。九千年前,这里是一个水道发达的湿地三角洲,鱼类成群,芦苇密布,沙洲上长满海枣树。在藤丛里,生活着野猪和水禽。河流冲积下来的土沉积在波斯湾入海口。这样的冲积土,让粮食产量比别处高数十倍。早在古埃及人构思金字塔之前,苏美尔人已经建造了高大的吾珥古城,用楔形文字写下了《吉尔伽美什史诗》。
但是,人口和文明的急速扩张让苏美尔的城邦陷入了“进步的陷阱”。对古森林的过度砍伐和焚烧,造成了冲毁城市的洪水。过度的耕作和放牧,导致了对土壤的破坏。为了养活增长的人口,人们把当地含盐的水引入到干旱的土地,水分蒸发掉之后,留下了盐。灌溉也引起含盐的地表水开始向上渗出。过度的耕作,土地的盐碱化,土地轮休期的缺乏,让地力耗尽,直到再也没有新的土地可以开垦。这时,人口却达到了顶峰,统治的危机到来。
莱特写道:“正如复活节岛的居民一样,苏美尔人没能对自己的社会体系进行改革,以降低其对环境的影响。”相反,他们试图去加强农业生产,将剩余资源全部集中用于建造宏大的建筑工程。苏美尔最后一代阿卡德帝国,终于在公元前两千年时灭亡。
苏美尔文明的衰落,源自于对未来的掠夺,无节制地使用自然给予的资源、过度的财富和荣耀。虽然几代人享受了繁荣,毁灭性的灾难终于来临。此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再也没有恢复过来。剩下的人们搬去了北部。即使四千年后,这些古城周围依旧是半荒漠地带,“浸透着进步灰尘的白色”。
如果复活节岛和苏美尔文明的衰落是由于环境的破坏,那么古罗马和玛雅政权的灭亡,则是同时由于生态灾难和财富分配不均。
古罗马位于欧洲最富饶的土地,达到了古代文明的顶峰。但是人口的扩张,公有土地的私有化,征服战争的蔓延,传统的民主制度的消亡,都带来了贫富的急剧分化。同时,文明发展也遭遇生态瓶颈。“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考古研究发现,在帝国时代出现的严重土壤侵蚀与高度发达的农业活动之间有密切联系”,紧接着发生的是人口的剧减和逃离。
莱特引用约瑟夫·泰恩特(Joseph Tainter)的《复杂社会的崩溃》(The Collapse of Complex Societies)里提出的“帕金森定理”——“复杂的社会体系不可避免地会见证递减的收益。即使其他的条件保持不变,运转和防卫一个帝国的成本也会越来越高,最终使得帝国不堪重负”。虽然最有效的对策是抛弃整个帝国的上层建筑,回到过去那种本地组织的形式。但是改革总是难以启动。在惯性之下,军费和政府支出高昂,行政效率下降,劣质货币泛滥,外敌入侵,灾害丛生,让帝国不堪重负,最终崩溃。
第四个例子是位于西半球的玛雅文明。玛雅人在与欧亚大陆隔绝的情况下独立发展出了高度的文明。但是在公元八世纪初,对有限资源的争夺让权力斗争加剧,军事主义开始占据上风,旧的联盟分崩离析,政治变得不再稳定;统治阶层却依然通过铺张奢华的建筑项目来强化其统治。蒂卡尔城的建立经历了漫长的时期,但是最高的那些建筑,都是在文明的最后一百年里建造出来的。“算是毁灭前夜的繁华”——莱特写到。
尽管战争、旱灾、疾病、外族的入侵和叛乱,都是玛雅衰落的原因,但是莱特认为,这些因素可能都源于生态的恶化。同样,有关玛雅地区沉积物的研究显示出土壤普遍出现了侵蚀和退化——显然由于年复一年的过度耕作。
曾经参与玛雅主要遗址考古的大卫·韦伯斯特(David Webster)这样评价玛雅文明的衰亡:“对于蒂卡尔王国的垮掉,我们认为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是人口的过度增长和农业的歉收,以及伴随这些问题而来的政治影响。”
在玛雅文明的最后一个世纪,大城市看起来兴盛,其实已经浩尽了所有的自然资本。森林被砍伐,田地不堪重负,人口过多。蓬勃蔓延的房屋建设占用了更多土地,使用了更多树木。同时,资源却往统治阶级集中,贫富差距增大。发掘出来的人类骸骨显示出富人和穷人间的区别——有钱人长得越来越高大,而农民的体质、健康、和平均预期寿命则在下降。
随着危机的加剧,统治者不是去寻求变革,不是去削减政府和军费的开支,不是去开垦梯田改善土地品质,更不是去鼓励人口的调控(尽管玛雅人已经掌握了相关的技术)。“统治者们自掘坟墓,继续着过去的生活方式,并且还变本加厉了。……修建更高的金字塔,让国王握有更多的权力,让民众的劳动量更大,发起更多对外战争。”
终于,一次旱灾,虽然并不比过去的更严重,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稻草。
历史对“进步”的启示
复活节岛、苏美尔、古罗马和玛雅的衰落,都源自于文明的过度增长,远远超过生态资源的供给能力。对于存活至今的文明,比如埃及文明,莱特认为是因为当地土地特别肥沃,人类利用自然资源效用较高,而且人口增长缓慢。而对于延续至今的中国文明,莱特认为是因为厚厚的黄土高原提供了层层的可耕土,“古代中国肥沃慷慨的生态体系”让中国文明即使在无数次战乱和叛乱之后,仍然可以恢复过来。换言之,主要还是运气好,没有把自然资源耗尽。
在历史上兴衰的种种文明,在莱特眼中,都是“文明的实验”。实验的结果表明:人类是可以预测的生物,我们由类似的需求、欲望、希望和罪恶所驱动。当人类为了自己进步和发展的欲望,无节制的破坏环境时候,他们就像是最愚蠢的寄生虫,杀死自己的寄主,走向毁灭。
于是,莱特写到:“需要对科技决定论的观点保持警惕,因为科技决定论的观点通常会低估文化因素,把复杂的人类适应性的问题简化成一个简单的逻辑:我们是历史的胜者,为什么其他的人不和我们一样,做我们做过的事情呢?”换句话说,科技决定论者没有看到的是,无数历史证据表明,科技可以轻易导致生态的灾难和文明的毁灭。
从第一块打磨过的石器到第一把锻造的铁器,人类花了大概三百万年;而从第一把铁器到第一枚氢弹,人类仅仅用了三千年。莱特感叹:文明发展一直在不断加速,让任何的错误,都变得更仓促而难以纠正,带来更灾难性的后果。从二十世纪初以来,世界人口已经增长了差不多四倍,而全球经济这个衡量人类对自然负担的粗略数据,则增长了四十多倍。
在书的结尾,莱特再次提醒读者:依赖科技的文明扩张,绝不是自然规律的一部分。所谓单向度的“进步”与发展,只是人类的一种虚妄的想象。无限制的进步,可能只是一个深不可测的陷阱。
也许,是时候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了。
